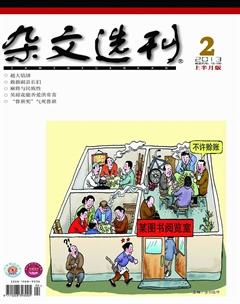我们在莫言的故事中
方大丰
北京时间12月11日凌晨,莫言身着燕尾服,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诺贝尔奖的金质奖章。
授奖词称赞“莫言是个诗人”。
1949年,福克纳的领奖致辞,是这样走向结尾的:“人之不朽不是因为在动物中惟独他永远能发言,而是因为他有灵魂,有同情心……”
莫言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是在故乡的谷仓里,仅用三十五天创作完成的。对这片土地的深厚认知以及对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的深切领悟,使得莫言的故事总有些“残酷叙事”的味道。
莫言在瑞典文学院做了一个演讲,像是开了一个故事会。这使得国内一些有别样期待的人感觉不够精彩和絮絮叨叨。但我真的更愿意听故事。我们,又何尝不是活在莫言的故事之中?
在斯德哥尔摩,莫言讲的最后三个故事,很多人进行了解读。
第一个故事充满了忏悔歉疚——儿时参观苦难展览时,当同学大多在老师的引导下放声大哭,一位同学不但没有哭泣且惊讶困惑,最后因同学举报而被警告处分。这使莫言悟到“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对此,有人解读为“这是对荒唐历史的反思,同时也是对个人自由的捍卫”。其实,这个发生在莫言小学时代的故事,也会发生在今天或明天。恰如莫言所说:“任何现实问题实际上都是历史问题的延续。无论多么遥远的一个历史故事里,也都包含着现代性。”
莫言的最后一个故事,留下了很多猜想空间——八个泥瓦匠于暴风骤雨中躲进破庙,有人猜测八人中必有一人干过坏事,于是用向庙外扔草帽的方式来决定唯一接受惩罚的人选,当选出的那个人被扔出庙门的瞬间,破庙轰然坍塌。
“一个和七个”的生死存亡被一些媒体解读为世间自有公道,为恶者逃不脱终极审判。而故事本身的寓意,其实应跟第一个故事相辅相成,至少说明:一切坏的结果,不一定都因为恶的动机,而非常不幸地,包括我自己在内,也难免会参与其中。“我在写小说的时候,写着写着我就会忘记我写的到底是历史,还是现实。后来我就知道我的小说里面既有历史,也有现实,是历史和现实的融合。”莫言说。
我们生活在莫言的故事里,同样可以像莫言那样讲故事,并从故事里获得各种启发。
今天,我就想试着讲这么一个故事。
若干年前,我费了好大功夫,给自己的车上了一套可以享受特权的牌照。某天晚饭后,我载着一个与我一样酒气熏天的朋友,疯狂地逆行在大街上,虽然带着醉意,我的这位朋友依然愤怒地勒令我停车,他吼道:“不要忘了自己是个老百姓!”
这个故事,我曾讲给很多人听,它启发我:做人的底线其实就是,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俗身。否则,你可能处于危险之中。
本来,我还想讲一个小生意人刚刚发生的故事,他银行卡里突然多了一笔两万多元的款子,二十天过去了仍然没找到汇款的人,他很焦急:“我不想失去平静的生活,不想毁了我的幸福。”
我想去采访他,期望获得一个人平安而幸福地生活的道理。
【原载2012年12月13日《工人日报·我在我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