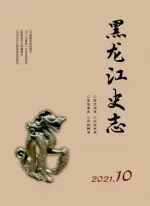读《方苞集》札记一则
秦 强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22)
方苞以家贫历来为学界所认同,但笔者在阅读《方苞集》相关资料后认为,似乎应当重新对方苞的家庭经济情况予以评估。尤其是随着方舟兄弟外出授经次数的频繁,方家的家境情况也在逐渐的好转起来。其最直接可以说明这一问题的材料当见于《方望溪遗集·与德济斋书》一文。在此信中,方苞准确明白的说道:
先兄早世,苞置圩田二百亩于高淳县,山田百五十余亩于江宁县,皆在康熙辛巳(1)以前。[1]p49
对于信中所述方苞购置高淳圩田、江宁山田的时间皆在康熙辛巳以前,那么这个时间是否真实可靠呢?因为毕竟方苞写这封信的时间是在晚年,对于自己年轻时期所做之事在晚年提起是否如实?同时,由于这则材料的真实性直接关系到笔者下文的分析是否正确,因此就十分有必要作一简要考证了。
一
笔者以为方苞在康熙四十年前分别从高淳、江宁两处购田的可能性是有的。原因如下:
第一,据方苞所作《兄百川墓志铭》称:“及庚辰(2)四月,余归自京师。七月,兄归自皖江而疾遂笃。”[2]p496康熙四十年(1701),方苞又在给韩慕庐所写的信中说:“又有不可已者,小妹适谢氏孤子,其家资累万,皆为姻家马姓所夺。妹及其家人数口,衣食于某兄弟者,盖数年矣。近以先兄久疾,未得客游授经,先世遗田百余亩荡弃已尽,不能复相顾。”[2]p674-675结合这两条材料可以看出,由于方家既要维持一家人的日常生活所需,又要资助小妹一家。再加上其兄久疾,所以到了康熙四十年时,其祖上遗留下的二百余亩田此时已几近于消耗殆尽。更不幸的是,方舟又于此年冬十月去世。弟弟方苞更是以古礼经为准则给哥哥服丧,直到康熙四十二年(1703)春才出门。假如方家在康熙四十年前没有购置田地或是没有充足的生活资料做保障的话,那么这期间一年多的时间,方家至少十几口人的生活开支将从何而来?
第二,关于方家在康熙四十三年(1704)秋重新入住故宅将园,似乎也可以说明问题。将园原是方苞祖上迁到上元时所住之地,后来方家定居土街时,将其卖掉。后来方苞念其父年老不能出游,于是将此宅重新买回并修葺,并于康熙四十三年秋七月又举家迁入这座故宅之中。另从《将园记》一文来看,旧宅早已六次易主。根据民间社会习俗,每易一次手,其宅子的价格就会上涨一次,那么赎回旧宅的成本也必定水涨船高。那么试想,在方舟死后不到三年中的时间里,如果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作支撑,方家又怎么会轻而易举购回旧宅、并将其修葺入住呢?
因此,结合上面两条分析来看,笔者认为方苞在康熙四十年以前购置高淳和江宁两处田地是有可能的,从而也可以说明康熙四十年,甚至是康熙三十九年前的数年,方苞家境实力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改善并有所发展。
二
我们在前文已基本上证实了方家购田的可能性。那么,这则短短的计有三十四个字的材料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认识呢?笔者以为,从此信中,我们可以看出如下几点:
1.方苞一家虽然早年比较贫寒,但由于兄弟二人多年来外出教习古文、授徒讲经,到了康熙四十年,其家境应该不会太差,反而比以前要好的多。
2.方舟去世于康熙四十年,而方苞在信中却说“先兄早世,苞置圩田、山田,皆在康熙辛巳以前。”[1]p49把置田的功劳归于自己名下,这似乎并不十分准确。雍正二年,方苞曾说过:“高淳二百亩,乃我二十年佣笔墨,执友张彝叹为购置者。”[2]p483二十年来靠佣笔墨所攒下来的钱有多少我们无从得知,也无法直接去考证。但以二十年所积攒佣笔墨的钱去购置二百亩圩田,恐怕不是一个小数目。在这里,笔者虽无法直接说明这笔钱的数目,但从《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一书中似乎可以找出一点蛛丝马迹来探究这个问题。经过笔者查阅,在该书附录部分有若干续表,其中有一部分表格中涉及到康熙年间安徽歙县的卖田契。[3]p582-583虽然江苏高淳县和安徽歙县的具体情况会有所不同,但似乎可从康熙年间歙县民间社会进行土地买卖的契约文书中为我们提供一点借鉴。为了行文方便起见,此处将表格省略。笔者从中抽取了康熙二十年(1681)至四十年(1701)间的数据并通过计算得出:康熙年间歙县的土地买卖价格每亩最高可达到近12两,最低可以卖到每亩6两。当然,由于两地情况不一样,加上所购之田有上、中、下三等之分,因此,我们不妨取中间值保守地去从整体上估量所购田所需的钱数。我们以每亩7两作为参考值,那么方苞在高淳所购之田需要花费1400两银子左右。
一般而言,山田的购置价格较之圩田也应较低一点。我们若以每亩所需4两(这个数值应该比较低了)算,一百五十亩也要600两银子。我们若将方苞购买高淳圩田的时间限定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至四十年之间,那么他积攒这笔钱的时间就要从康熙十九年(即1680年,即其十三岁)算起。众所周知,方苞在外主要生活来源是替人写文章、招徒授经。而招徒授经基本上在其十九岁以后才有。因此对于方苞来说自十三岁起就靠写文章来赚取一定的润笔费似乎比较艰难,况且与事实也有一定的出入。即便随着方苞年龄的增长,求其写文章的人会逐渐增多,以及其二十多岁以后开始收徒授经,这二百亩圩田所需的购置费方苞能够完全开出,那么再把一百五十余亩山田所需的购置费完全归在方苞名下,似乎未免有点牵强了。在这期间,家中虽有先世遗留的“二百亩田”,但据方苞所述“苞有先世遗田百余亩,在桐山之阳,岁无旱潦,可食家人之半”[2]p672那样,丰年都不够家里人食用,何况遇到旱涝之年呢?此外,父母子妹等人也需要一定的生活接济费用,而这部分钱也需要从方苞兄弟在外谋生所挣之财中支出。因此,笔者以为方苞自己所说在康熙辛巳前置办圩田、山田,其功劳理应有其兄的一份。况且在雍正二年时,方苞在给道希(3)兄弟的信中只提到了高淳二百亩田的来历,对于江宁一百五十余亩山田却只字不提,似乎也可以说明问题。
3.按上文中所分析以及方苞所说,家中的田地并不是在康熙四十年这年一次性置办的。这就说明了方家置办新田的前提必须是能够解决好自身的温饱问题的。假若连温饱问题都无法解决,又怎么会有余钱去置办新的田地呢?所以,能够解释清楚的就是方家在康熙三十九年前就已经摆脱贫困(因为此年后半年,方苞兄弟都在家。次年,方舟又病逝。),而且也似乎可以肯定其家已置办了新地(若没有置办,自康熙三十九年后半年起,至四十二年前这段时间,全家的生活来源在哪里?即便是三十九年置办了新田,但是从播种到收割也需要一段时间)。因此笔者认为,若把方苞追求科举的热情重点归于其家境的贫困上似乎有点站不住脚(康熙三十八年方苞参加科举,这时候恐怕不是为了生活所需)。的确,方苞在童年家境极其贫寒的情况下,其兄曾经向方苞说过“吾乡所学,无所施用。家贫,二大人冬无絮衣。当求为邑诸生,课蒙童,以瞻朝夕耳。”(2)[8]p496按照方舟当时之意,要想摆脱家中的窘困局面,只有走科举之途,考个秀才回来即可解决燃眉之急,似乎可以说明方氏兄弟二人的功名心。但是仔细推敲一下,却值得我们深思。在当时,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对于科举能够有多么深刻的理解?他所能够认识的无非是从现实情况出发,采用最简洁、快速的办法使家庭摆脱贫困,使双亲不在忍受饥饿与寒冷的折磨罢了。那么,方舟又怎么会想到去考取邑诸生呢?这是因为:按照科举规制,只要能够考中邑诸生,每个月就可以从官府领取一定数量的生活补贴。而且也有资格对幼儿进行启蒙指导。因而,方舟提出去参加科举的想法在当时的确带有相当大的主观功利性,这种功利性的侧重点主要倾向于“利”,希望借科举解决自身的生活来源问题。
如前所述,方氏兄弟最早参加科举确有其明显的功利性,但若此就把他们对于科举的认识与了解锁定在追逐名、利上,似乎显得有点不合时宜了。因为方苞早年就以古文为世人所熟悉。24岁便得到杜苍略先生的高度评价,李光地更以“韩欧复出,北宋后无此作也”[2]p869来夸赞他,可见其在青年时期就已名扬天下。同时,方苞在弱冠之年就开始讲学授经,因而“利”自然会有,而且收入还不菲。因此,“名”与“利”对于方苞来说早已有之,根本无需通过科举之途来取得。况且科举之途未必能够如愿,所花时间往往要历时好几年甚至穷其一生。另外,据《四君子传》知,方苞所结交的朋友刘古塘等人都是淡薄名利之人。如果方苞是热衷于名利之人,又怎么会结交这些淡薄名利之人呢?所以我们似乎不能简单的把方苞走科举之途的目的归在“名”和“利”上,以名利去看待方苞只会把方苞看的更加世俗化,离真实的方苞会越来越远。若真是以科举去衡量方苞的价值观,那么试问自有科举以来,那些奋力跻身于科举之门的读书人又有几人不热衷于功名利禄呢?
注释:
(1)此处的“康熙辛巳”为康熙四十年(1701).该年方苞34岁。
(2)此处的“庚辰”为康熙三十九年(1700)。
(3)道希,方舟长子,次子道永。
(4)(5)当时方舟十五岁,方苞十二岁。
[1]方苞.方望溪遗集[M].合肥:黄山书社,1990.
[2]方苞.方苞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3]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一)[G].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