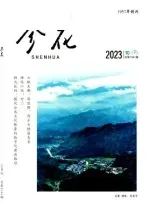“象喻法”在魏晋南北朝书法品藻中的运用分析
◎刘嘉
(河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0)
一、秦汉“比德”书法艺术品藻
先秦两汉对于艺术实用功利性的定位,导致其为数不多的书法艺术品藻一直受到人格品藻的影响。即注重对人物在德行、才能、风采等方面的鉴定与评价,尤其注重对德行的考量。孔子重视对艺术美的鉴赏,但是他的着眼点是人的道德。孔子品评人物的标准是德与才,他根据德、才的高下把人物概括为四个层次:圣人、仁人、贤人与小人,体现了一定的等级观念。[1]人物品评发展到汉代,正式被称为人物品藻,并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汉代实行“察举”制,中央或地方政府对士人的品行进行考察,然后向朝廷推荐,道德品行出众者即可入仕。自孔子的人物品评始,经班固的以九品论人,再至曹魏的以九品取士,人格道德对书法艺术品藻产生了直接主宰关系。直至东汉末年的蔡邕,写出了书法自觉萌芽下的第一篇脱离“比德”艺术品藻标准的书论:
为书之体,须人其形,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起,若愁若喜,若虫食木叶,若利剑长戈,若强弓硬矢,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矣。(蔡邕《笔论》)[2]
二、魏晋南北朝书法品藻的时代背景
东汉末年,社会极其动乱,外戚专权、宦官横行。伴随社会大一统的分崩离析,士人的正统观念日趋淡薄,束缚士人的经学思想黯然失色,思想界经历了一次重新洗礼。当汉末的士人挣脱了经学的枷锁之后,整个士人阶层的意识由群体意识走向了个体意识的觉醒。注重个性,张扬性情,成为魏晋南北朝名士的亮点。士人清谈品评重点亦由强调人的德行转变为注重人物的才情风貌,对超尘独步、神明睿智的人格理想的追求,成了这时期士人普遍风潮。书法理论和批评的品藻就在此时从人物品藻的附庸地位解脱出来,获得独立发展的道路。魏晋南北朝流行的哲学思想主要是以老庄为核心的玄学思想。玄学以“自然”哲学为核心,王弼云:“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老子·五章》注)。郭象云“:若不能保其自然之质而杂乎外饰,则虽犬羊之鞟,庸得谓之纯素哉! ”(《庄子·刻意》注)正是在这些“自然”观念的影响下,魏晋南北朝士人表现了自然天放的人格魅力。从追求人生的“自然”到发现大自然之美,这是魏晋南北朝审美意识的逐渐深化的过程。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指出,在魏晋南北朝,人格美与自然美被同时发现。
三、魏晋南北朝书法品藻中的“象喻法”运用分析
“象喻法”——即以具体的物象来比附事物,使人产生丰富的联想。[3]在具体的品评过程中,评论者常以简练含蓄的言语,贴切而生动地指出被品事物之美。在魏晋南北朝人的书法品藻中,常常借用一些有丰富文化意味的物象来比附精神的高超。魏晋南北朝书法批评中的“象喻”法主要有两种:
1.自然之景象喻书法形质
魏晋南北朝书论受当时“自然”思潮的影响,西晋时已出现了一批以自然界中千姿百态的物象、动态来描绘比喻各种书体形态美的理论著作,如成公绥的《隶书体》、卫恒的《四体书势》等,都有大量例证。上述书论莫不以自然物象喻书,下面以书论材料分析之:
成公绥《隶书体》描述成熟时期的隶书之美既险峻层叠,又飞动流畅,张扬了大自然的勃勃生机,其曰:
或若虬龙盘游,蜿蜒轩翥;鸾凤翱翔,矫翼欲去。或若鸷鸟将击,并体抑怒,良马腾骧,奔放向路。
仰而望之,郁若宵雾朝升,游烟连云;俯而察之,漂若清风厉水,漪澜成文。
索靖《草书状》表达了对尚未定型成熟的草书雄强气势和飘逸风姿的向往:芝草葡陶还相继,棠棣融融载其华;玄熊对踞于山岳,飞燕相追而差池。纷扰扰以猗,靡中持疑而犹豫。玄螭狡兽嬉其间,腾猿飞鼬相奔趣。凌鱼奋尾,骇龙反据,投空自窜,张设牙距。
卫恒《字势》试图用具象的自然之美描述抽象的文字之美:
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矫然突出,若龙腾于川;渺尔下颓,若雨坠于天。或引笔奋力,若鸿鹄高飞,邈邈翩翩;或纵肆婀娜,若流苏悬羽,靡靡绵绵。
卫铄《笔阵图》论到书法的各种点画,将其比作客观存在的自然之物,透露他们郁勃的生命态势:
横如千里之阵云、点似高山之墬石、撇如陆断犀象之角、竖如万岁枯藤、捺如崩浪奔雷、努如百钧弩发、钩如劲弩筋节。
王羲之《题笔阵图后》将书法比作兵法,可谓独一无二:
夫纸者阵也,笔者刀鞘也,墨者鍪甲也,水砚者城池也,心意者将军也,本领者副将也,结构者谋略也,飏笔者吉凶也,出入者号令也,屈折者杀戮也。
王羲之《书论》兼用自然之景物与人物来讨论书体之美与点画形态之美:
凡作一字,或类篆籀,或似鹄头;或如散隶,或近八分;或如虫食木叶,或如水中科斗;或如壮士佩剑,或似妇女纤丽。……每作一字,须用数种意:或横画似八分,而发如篆籀;或竖牵如深林之乔木,而屈折如钢钩;或上尖如枯杆,或下细如针芒;或转侧之势似飞鸟空坠,或棱侧之形如流水激来。
萧衍《草书状》认识到草书中的千变万化一如自然物象的丰富多彩,可观之,琢磨之:
及其成也,粗而有筋,似蒲葡之蔓延,女萝之繁萦,泽蛟之相绞,山熊之对争。若举翅而不飞,欲走而还停,状云山之有玄玉,河汉之有列星。若白水之游群鱼,藂林之挂腾猿;状众兽之逸原陆,飞鸟之戏晴天;象乌云之罩恒岳,紫雾之出衡山。
袁昂《古今书评》行文前段运用了“象喻法”盛赞书家:
臣谓锺繇书意气密丽,若飞鸿戏海,舞鹤游天,行间茂密,实亦难过。萧思话书走墨连绵,字势屈强,若龙跳天门,虎卧凤阙。薄绍之书字势蹉跎,如舞女低腰,仙人啸树,乃至挥豪振纸,有疾闪飞动之势。
庾肩吾《书品》亦受此法之影响:
波回堕镜之鸾,楷顾雕陵之鹊。
分行纸上,类出茧之蛾;结画篇中,似闻琴之鹤。峰崿间起,琼山惭其敛雾;漪澜递振,碧海愧其下风。
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评》运用此法集中评论了诸多书家,这里仅列举几人:
钟繇书如云鹄游天,群鸿戏海,行间茂密,实亦难过。
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
萧子云书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荆柯负剑,壮士弯弓,雄人猎虎,心胸猛烈,锋刃难当。
2.人物之神韵喻书法形质
这种书法品藻方法当是先秦两汉人物品藻在魏晋南北朝的延续。通过不同人物形象所蕴含的不同意义来直接描述不同书家书风的差别。
袁昂《古今书评》以“谢家子弟”、“洛阳少年”来隐喻“二王”书法的翩翩风度;而以“婢作夫人”论羊欣的书法虽然处于尊位,但神态不自然,终究不像真的。通过这种对比书家高下立现,如下:
王右军书如谢家弟子,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
王子敬书如河、洛少年,虽有充悦,而举体沓拖,殊不可耐。
羊欣书如大家婢为夫人,虽处其位,而举止羞涩,终不似真。
徐淮南书如南冈士大夫,徒好尚风范,终不免寒乞。王仪同书如晋安帝,非不处尊位,而都无神明。
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评》以帝王之姿涉书法之道,与袁昂有同工之妙:
羊欣书如婢作夫人,不堪位置,而举止羞涩,终不似真。
萧思话书如舞女低腰,仙人啸树。
王献之书绝众超群,无人可拟,如河朔少年皆悉充悦,举体沓拖而不可耐。
王僧虔书如王、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奕奕皆有一种风流气骨。
吴施书如新亭伧父,一往见似扬州人,共语语便态出。
徐淮南书如南冈士大夫,徒尚风轨,殊不卑寒。
3.魏晋南北朝诗文绘画对书法“象喻法”品藻的影响
魏晋玄学的影响了各种艺术形式的自觉意识和品藻方式。通过诗文绘画的艺术品藻形式,我们可以探寻书法“象喻法”品藻产生的文化土壤。
曹植《洛神赋》是诗文自觉的先驱:
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
短短一段话却暗示了审美观念的巨大变化。魏晋的文人不仅承认自然本身的美,而且认为自然美是人物美和艺术美的范本。
在《世说新语》中,这类例子俯拾皆是,魏晋时期的人物品藻已经从实用的、道德角度转到审美的角度。[3]不再那样重视经学造诣和道德品行,而是着重于人物的风姿、风采、风韵。
世目李元礼:“谡谡如劲松下风。”(《赏誉》)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赏誉》)
公孙度目邴原:“所谓云中白鹤,非燕雀之网所能罗也。”(《赏誉》)
从《世说新语》看到,魏晋士大夫文人对自然美的欣赏,已经突破了“比德”的狭窄的框框。[3]
再来看以王微和宗炳为代表的绘画理论家追求玄妙境界的审美心胸:
眉额颊辅,若晏笑兮;孤岩郁秀,若吐云兮。朴变纵化而动生焉,前矩后方而灵出焉。然后宫观舟车,器以类聚;犬马禽鱼,物以状分。此画之致也。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虽有金石之乐,王圭璋之琛,岂能仿佛之哉!(王微《叙画》)[4]
于是闲居理气,拂觞鸣琴,披图幽对,坐究四荒,不违天励之藂,独应无人之野。峰岫峣嶷,云林森眇。圣贤暎于绝代,万趣融其神思。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已。神之所畅,熟有先焉。(宗炳《画山水序》)
四、“象喻法”书法品藻的艺术自觉意义
中国的书法自觉当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变迁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上的表现,使占据统治地位的汉经学崩溃。取代烦琐,迂腐的谶纬和经术的是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5]由此开始极为关注人和自然的主题。
“象喻法”书法品藻以自然之景象和人物之神韵喻书法形质,是魏晋南北朝书法艺术自觉的表现之一。不论“以人喻书”,还是“以物喻书”,两者都有一个相同的特点,就是以“象”喻书。这种象喻方法完全产生于魏晋南北朝玄学影响下的艺术品藻的大文化背景之中。美是人的自由的本质的对象化,书法美的创造也不例外,书法美与人格美有异质同构的关系。它从审美观念自觉开始,经过内擫外拓技法的完善,楷行草书体定型,褪去实用功利色彩的写意精神确立,书法理论和书法批评的去“比德”化,从而完成书法自觉的整个过程。它颠覆先秦两汉书法作为政教宣传的附庸地位,使兼有具象、抽象文字的书写过程,逐渐变成表情达性的艺术手段。“象喻法”书法品藻正是这伟大书法自觉化的重要表征。
[1]阮忠勇,《论人物品藻对魏晋南北朝书法品评的影响》[J],浙江海洋学院学报,2009,(5)。
[2]蔡邕《笔论》、成公绥《隶书体》、索靖《草书状》、卫恒《字势》、卫铄《笔阵图》、王羲之《题笔阵图后》、王羲之的《论书》、萧衍的《草书状》、袁昂《古今书评》、庾肩吾《书品》、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评》篇目中的材料均引自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选编《历代书法论文选》[M],上海书画出版,1979。
[3]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人民出版社,2011。
[4]王微《叙画》、宗炳《画山水序》均引自潘运告,《汉魏六朝书画论》,湖南美术出版社,1997。
[5]李泽厚,《美的历程》[M],三联书店,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