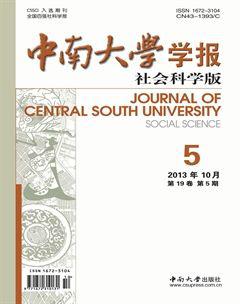药后驾驶纳入危险驾驶罪的证成与构设
储陈城

摘要:在醉酒驾驶和追逐竞速驾驶受到危险驾驶罪规制之后,药后驾驶行为也应当纳入到该罪的范畴内。这是风险刑法语境下的必然要求,也是相同行为相同处理的应有之义。在域外国家和地区立法将药后驾驶行为犯罪化的今天,我国仅仅将产生严重危害后果的药后驾驶按照交通肇事罪或者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来定罪,而将未产生严重危害后果的药后驾驶仅予以行政处罚,存在调控范围不全面、所需构成要件严格和调控手段失调的弊端,可能导致药后驾驶的失控。因此,我国刑法应当将服用毒品和部分合法药品后进行的驾驶作为危险驾驶罪处理,并采纳主客观相结合的证据标准来判断被告人是否构成药后驾驶型的危险驾驶罪。
关键词:药后驾驶;毒后驾驶;危险驾驶罪;风险刑法
中图分类号:D9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5?0117?08
一、“药后驾驶”抑或“毒后驾驶”?
《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酒驾驶和追逐竞速行为纳入到危险驾驶罪的范畴之后,就有人呼吁药后驾驶应该尽快入刑。[1, 2]这虽然有点像“头疼医头,脚痛医脚”,但是,在醉酒驾驶和追逐竞速驾驶受到有效限制之后,驾驶人员在服用足以导致人的精神意识或身体受损从而降低驾驶技能的药物之后的驾驶行为具有导致极为严重的交通事故的危险的行为如在刑法上无法进行合理有效的控制,是会使刑法的平衡性和权威性受到质疑的。“药后驾驶”的英文表述为“Drugged Driving”或者“Driving Under the Influence of Drug (DUID)”。在我国,药后驾驶的中文翻译和内涵尚没有统一的认识。就其中文翻译而言,很多学者认为应当翻译为“毒驾或者毒后驾驶”,[3?5]另外也有少数人将其翻译为“药驾或者药后驾驶”。[6, 7]而就其内涵而言,有学者认为毒驾就是吸毒之后的驾驶行为;[8]有学者则认为“是指驾驶人因吸食麻醉药品或精神药品后,在其药理作用时段内继续驾驶机动车,足以给社会带来危险性的行为。”[9]还有学者认为是指“非医疗目的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和麻醉药品后(查获时毒品检测呈阳性)驾驶机动车的行为。”[10]要确定是“毒后驾驶”还是“药后驾驶”,以及其基本内涵是什么,就必须了解哪些药物能够使人精神意识受损,从而降低人的驾驶能力。毒品,诸如海洛因﹑鸦片、大麻、冰毒等毫无疑问会使人产生倦意和幻觉甚至导致精神和意识错乱,自然会使驾驶人员无法正常驾驶机动车辆。而除了毒品之外的合法药物也会对驾驶行为产生影响。比如治疗咳嗽的可待因、右甲吗喃,用于止痛的芬太尼、美沙酮等药物会使人昏昏欲睡、视力模糊、注意力和判断力受损。[11]有研究显示,诸如黄连素、异丙肾上腺等药品中的苯二酚和三环抗抑郁药等处方药物摄入后驾驶,会导致发生交通事故的风险概率翻倍。[12]在摄入这些用于合法治疗的药物之后驾驶机动车辆也可能产生与吸食毒品和麻醉药物同样甚至更高的危险。可见“毒后驾驶”的概念过于狭隘,其字面含义无法涵盖麻醉药物和合法药物。因此,我们应当采用“药后驾驶”这一概念。那么“药后驾驶”可以定义为,驾驶者在服用毒品、麻醉药品或者其他足以“致醉或者导致麻醉”[13](187)的药物后,其精神状况或身体受到极大影响,无法正常驾驶机动车辆的行为。
二、药后驾驶纳入到危险驾驶罪之证成
(一) 风险刑法使得药后驾驶入罪成为必然要求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创设了“风险社会”的概念,其认为“现代性正从古典工业社会的轮廓中脱颖而出,正在形成一种崭新的形式——(工业的)‘风险社会。”[14](2)“在风险社会中,不明的和无法预料的后果成为历史和社会的主宰力量。”[14](27)“现代化风险……是非特定的、普遍的”[14](20)“这意味着,科学和法律制度建立起来的风险计算方法崩溃了。以惯常的方法来处理这些现代的生产和破坏的力量,是一种错误的但同时又使这些力量有效合法化的方 法。”[14](19)尽管有学者认为,贝克的风险社会观是全球性的风险而不是个人风险,其所谓的风险主要是核泄漏、生态危机等对整个人类产生威胁的风险,因而进一步认为刑法学界借用风险社会的观念创设风险刑法,实际上是扩大了风险社会的边界,所谓的风险刑法是和贝克的风险社会相距甚远。[15]但是正如贝克自己所言,风险的定义具有多样性,会存在越来越多的风险,“风险的理论内容和价值关涉意含着另外的成分:冲突着的文明风险定义的可以观察到的多样性……每一个利益团体都试图通过风险的界定来保护自己,并通过这种方式去规避可能影响到它们利益的风险……风险的存在随着不同的利益和价值而变化不定。在风险中产生的、实质的或潜在的破坏作用与工业生产体系间的因果关系,为无数的个体诠释打开了大门。”[14](31)简言之,刑法学界这一利益团体可以借用“风险社会”的理念来界定自己领域内的风险。“为了应对社会风险,刑法保护法益抽象化、普遍化以及早期化的倾向日益明显。”[16]也即,刑法开始扩大犯罪圈,对犯罪进行提前干预。正因如此,在风险刑法的语境下,很多制度技术被倚重,诸如“立法拟制”“推定”以及“犯罪标准的前移”等等。[17]
那么药后驾驶是否应当受到风险刑法的特别“关照”?这可以通过相关的数据来回答。在美国有20%的交通事故是由药后驾驶行为导致的,每年导致8 600人的死亡、58万人的受伤以及330亿财产的损失。[18]虽然我国目前尚没有官方数据来全面统计全国范围内药后驾驶的数量、导致的死伤人数和财产损失情况,但是从某些间接数据中或许可以管中窥豹,比如目前我国可查的吸毒人员总数已超过百万,他们当中有大量的人持有机动车驾驶证。[19]在2012年3~5月,公安部在全国各地发现客货运驾驶人吸毒并停运的人数达1 436人。[20]同时药后驾驶一旦发生危害后果,其和醉酒驾驶、追逐竞速相较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烟台王某吸毒驾驶案和扬州王某吸毒驾驶案都造成了极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21]有人会认为,当前药后驾驶在我国并没有醉酒驾驶和追逐竞速类驾驶行为那么普遍,仅仅属于个别现象,不具有普遍性,刑法不应当去干涉,[22](42?54)如果任何行为都随意入刑就会导致“运动式的立法”。[23]尚且不论暂时没有官方数据证明药后驾驶属于个别现象,就以目前的危险驾驶罪而论,已经入罪的追逐竞速型的危险驾驶罪在司法实务中被证明极为少见。①如果以“仅属个别现象”来论证药后驾驶不应入罪,不得不让人怀疑之所以药后驾驶不入罪是因为在《刑法修正案(八)》制定之前没有发生引起全国范围内关注的药后驾驶案件,这实有民粹主义刑事立法之嫌疑。②按照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药后驾驶和追逐竞速之所以要纳入到危险驾驶罪中,是因为在风险社会的背景下,虽然事故发生的概率非常小,但是,如果一个事故的发生会造成极大的危害性结果的话,“那都是太大了”,就应当予以提前的预防、缓解甚至是避免。[14](29)
(二) 药后驾驶入罪是平等原则的应有之义
根据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对药物和驾驶人行为之间关系的一项研究显示,毒品和某些处方药物对驾驶能力的影响类似甚至高于酒精,比如服用50 mg剂量的苯那君后的驾驶能力受影响程度和驾驶人员血液酒精浓度为0.1 g/100 mL所受影响类似。[24]而英国的一项研究表明,“吸毒后的驾驶比正常反应时间慢21%,酒后驾车则比正常反应时间慢12%。”[25]基于上述科学依据,在我国的行政法领域,饮酒驾驶和服用毒品、精神药物或者麻醉药品之后的驾驶的违法程度相当,均要受到相当的行政处罚。比如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规定:“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麻醉药品……不得驾驶机动车。”《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四条第三款规定,机动车驾驶人有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麻醉药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要依法给予处罚。《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规定:“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暂扣六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六十七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被查获有吸食、注射毒品后驾驶机动车行为,车辆管理所应当注销其机动车驾驶证。这体现了行政处罚中的平等原则,即“在行政处罚之事件中自同应适用,禁止对相同之行为做不同之处理,或对不同之事物做相同之处理。”[26](87)
平等原则在刑事法领域也应当有所体现,其“针对的对象是国家,即要求国家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27]平等作为一项法律原则,“其能够对立法、执法和司法产生全面的约束力,是对立法者、执法者、司法者的共同要求。”[27]平等原则规制的对象涵盖立法行为,其内涵不仅应当是对“人”的平等对待,还应当包含对相同③ “行为”的平等处理。用拳脚将人打死应当被刑法认定为故意杀人罪,用枪炮将人射杀必然也会在故意杀人罪中占据一席之地。平等是正义的核心,在康德之后的时期,特别是实证论,将正义缩减到仅是平等原则,即平等是相同事物应当同等对待。[28](175)“法律讲究平等与公正,如果失去了平等与公正,法律就失去了自身存在的条件和价值。”[27]正因如此,将药后驾驶和醉酒驾驶一样纳入到刑事规制的范畴是平等原则的应有之义,也是保证刑法正当性的要求。
(三) 现有刑法规范无法有效规制药后驾驶
“法律之规条,恒属固定,而世事之变化,每至无穷。”因此要“善为解释,是则欲尽法律之用者,于法理之探研,尤未可忽。”[29](自序1?2)刑法作为最严厉的法律,要给公民对刑法的可预见性,这要求刑法必须具有稳定性。但是由于社会事实的风云变幻,在刑法的稳定性和事实的变化性之间存在隔阂。消弭该隔阂的较为可行路径为进行刑法解释,使得变化万千的事实能够万变不离其宗,在既有的刑法典中寻找到其合适的“归宿”。 刑法典中既存的罪名中可以规制药后驾驶行为的有两个: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吸食毒品后驾驶机动车辆,并且造成1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构成交通肇事罪。这是药后驾驶在刑法中被评价的主要罪名,在司法实践中大量的药后驾驶案件都是通过本罪予以处理。通过交通肇事罪预防和惩治药后驾驶行为会有两个弊端:首先是调控范围过小,交通肇事罪只对吸食毒品后的驾驶行为,即纯正的毒驾,予以调整。正如前文所述,药后驾驶行为不仅含有吸食毒品的行为,还包括足以致醉的合法药物,交通肇事罪无法调整服用具有严重影响精神意识和身体控制能力的合法药物情况下的肇事驾驶行为。其次是调控所需构成要件严格,以交通肇事罪来规制本行为必须具备有发生重大交通事故的结果和相关的责任比例,没有危害结果或者处于同等以及次要责任则无法予以刑事处罚。由于药后驾驶与醉酒驾驶具有同样的危险性,设置为危险犯予以提前预防方符合风险刑法的调整方向,而将药后驾驶行为通过结果犯来调整则为时过晚。
规制药后驾驶的另一个主要罪名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以外的危险方法”没有进行任何的界定,这种模糊的立法表述使得本罪成为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兜底罪名。[30](609?610)因此司法机关可以将任何危害公共安全,但是不构成其他危害公共安全的具体罪名的行为,均解释为本罪的客观行为。在实务中,司法机关往往将药后驾驶行为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④比如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法院审理的杨博药后驾驶一案中,被告人在吸食毒品K粉的情况下,驾驶汽车造成1死4伤的后果,被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2年6个月。[31]另外,云南玉溪周永全药后驾驶案也是如此,被告人在吸食毒品甲基苯丙胺之后驾驶汽车,造成2死2伤的危害后果,被法院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32]
将药后驾驶行为解释为“以外的危险方法”从而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不妥之一在于,药后驾驶行为与“以外的危险方法”的危害程度不具有相当性。由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以及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兜底罪名,因此从规范解释学的角度来审视“以外的危险方法”所产生的危险程度应当相当于放火、决水、爆炸和投放危险物质等行为。这从该5个罪名的法定刑可以看得出来,该5个罪名的法定刑均有两个幅度,且每个幅度的法定最低刑和最高刑完全相同。那么作为违反安全管理规定型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药后驾驶显然不能和放火、决水、爆炸和投放危险物质等行为相提并论。在主观方面,其只对违反交通安全的法律法规存在故意,主观罪过较小;在客观方面,其所危害公共安全的范围和程度均小于上述4种行为。
尽管不是将所有的药后驾驶都作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进行判处,而只是将“造成了重大伤亡结果,且行为人对伤亡结果具有故意时”,[33]才能将药后驾驶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但正因如此,使得药后驾驶行为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来规制会导致对药后驾驶行为调控力度不协调。这种调控力度的不协调体现在对较轻药后驾驶行为过于放纵,对较重的药后驾驶行为过于严厉。一旦药后驾驶没有产生任何实害后果,驾驶人往往最多只受到行政处罚;而只有在产生严重伤亡后果的时候,药后驾驶才可能被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这种轻重过于失衡的调控使得驾驶人极易产生侥幸感,可能会导致药后驾驶行为愈演愈烈。
(四) 域外立法事实使得药后驾驶入罪具有可能性
在药后驾驶是否应入罪的争论中,反对药后驾驶入罪或者对药后驾驶入罪持保留态度的学者认为药后驾驶立法技术问题、执法难题和鉴定技术限制使得其入罪几乎在当前没有可能。比如如何设置和醉酒驾驶型的危险驾驶罪相类似的体内药物浓度标准,以使得驾驶人员体内的药物达到何种浓度才可以认定为犯罪;再比如设置何种识别和鉴定手段使警察能够准确地发现驾驶人员有药后驾驶的嫌疑,以及使得鉴定人员能够精确地鉴定出驾驶人员确实受到药物的影 响。[32, 34]不得不承认上述问题在目前很多国家都存在,即便是药后驾驶入罪较早且体系比较完整成熟的美国和澳大利亚也被上述难题所困扰。⑤尽管如此,这并不妨碍各个国家和地区在刑事立法将药后驾驶予以犯罪化上所达成的共识,而这种共识并不因自身是大陆法系抑或英美法系而有不同。
德国刑法典第三百一十五条A设置了危害铁路、水路和航空交通安全罪,该罪的构成要件就包括服用麻醉药品后驾驶相关交通工具的情况;第三百一十五条C则规定了危害公路交通安全罪,该罪就禁止在服用麻醉药品后的驾驶行为。[35](155)另外,第三百一十六条则对前述条文进行了补充性规定,防止遗漏惩 处。[35](156)在日本,该国刑法典在针对身体的犯罪一章第二百零八条之二第1款规定了危险驾驶致死伤罪,该罪的构成要件为受酒精或药物的影响,处于难以正常驾驶的状态,驾驶四轮以上的汽车,因而致人伤害的。[36](57?58)我国台湾地区刑法典第一百八十五条之三规定了不能安全驾驶罪,其构成要件为“服用毒品、麻醉药品、酒类或其他相类之物,不能安全驾驶动力交通工具而驾驶者”。[37](391)
在美国,已经有16州制定有药后驾驶(DUID)相关的立法。比如内华达州,该州的对于药后驾驶规定的标题是“在酒精或者管制或者受禁药物的影响之下进行驾驶”,其规定,在血液或者尿液中,受禁药物的含量达到一定浓度标准的为非法驾驶。⑥在英国,《1991年道路交通法》将因在饮酒或者毒品的影响下,而疏忽或者鲁莽驾驶致人死亡的行为,设置为犯罪行 为。[38](553)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2011年修订的《道路交通条例》加入第三十九条J,规定“任何人在任何道路上驾驶、企图驾驶或掌管汽车,而该人当时正受药物影响,程度达到没有能力妥当地控制该汽车,该人即属犯罪”。
相关的立法技术、执法难题和鉴定技术的限制在药后驾驶入罪的课题中应当予以慎重考虑和讨论,但是正如上文所言,这是在任何国家和地区几乎都要面临的难题,因此其不能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阻碍药后驾驶入罪的借口。
三、药后驾驶纳入到危险驾驶罪的构设:以药品为中心⑦
药后驾驶入罪并非将其机械地添加到危险驾驶罪中那么简单,仅仅从实体法的角度来说,就需要回答服用哪些药物后驾驶会构成药后驾驶型的危险驾驶罪,以及服用这些药物后达到何种程度才能认定为药后驾驶型的危险驾驶罪。
(一) 药后驾驶的药物种类
药物的范围很广,能够使驾驶人员的精神、身体受到严重影响从而降低驾驶技能,“进而使之发生难以正常驾驶的状态的药理性作用的药品,包括麻药、兴奋剂、辛纳、医药品和安眠药等等。”[36](60)那么是否服用任何药物之后驾驶都要被作为犯罪处理,这是药后驾驶行为入罪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1. 毒品
毒品本身的非法性和严重损伤性以及麻醉药品对于人精神意识或身体的影响均众所周知,因此一般来说毒品和麻醉药品应当属于药后驾驶中的药物。目前对于毒品和麻醉药品有两种立法例可作参考,一种是在其他与毒品相关的单行刑法中寻找毒品的归属,另外一种是在规定药后驾驶的刑事立法中直接列举属于药后驾驶的毒品的种类。
我国台湾地区即采前一种立法例,在规定药后驾驶的刑法典中并没有明确何种药物属于毒品或者其他具有相同效果的药物,而是通过其他单行刑法对毒品的规定来列举上述药物。其分别在《毒品危害防制条例》第二条和《麻醉药品管理条例》第二条中列举了毒品、麻醉药品的种类。[39](187)
而美国内华达州和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则属于后一种立法例。美国内华达州在其药后驾驶立法中设置了10种药物,禁止在摄入这些药物后进行驾驶。⑧在香港特别行政区,2011年通过的《道路交通条例》专门制定附表指明哪些药物属于服用后禁止驾驶的,共有6种药物被列入其中。⑨
根据我国刑法第三百五十七条之规定,“本法所称的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其他能够使人形成隐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已经由我国《麻醉药品及精神药品品种目录》明确规定。虽然该条文属于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类犯罪,但是“本法”是指“本条法律规范”还是“本刑法典”没有准确说明,由于毒品本身对一般人都会产生精神意识或身体的影响,因此将“本法”解释为“本刑法典”从而适用到药后驾驶中来未为不可。因此就药后驾驶行为单独设置毒品的种类并无必要,直接采纳第一种立法例较为适宜。
2. 合法药物
很多研究已经表明,由于服用合法药物所产生的影响和毒品相当,包括感知能力下降、减损反应时间、出现混乱、迷失方向、明显出现困倦、注意力迟钝、发音或者讲话含糊不清、动作迟缓、平衡和协调能力下降、不稳定以及站立和行走困难。[40]但是服用这些合法的药物而驾驶不能都作为药后驾驶型的危险驾驶罪处理。
如果将所有的可能对人的驾驶能力产生减损的合法药物均纳入到药后驾驶型的危险驾驶罪当中,则可能无法跨越期待可能性⑩的阻却。“期待可能性思想……充分考虑到了客观环境条件对人的相对自由意志的限制作用,因而充满了人性的光辉。”[41]虽然期待可能性是作为犯罪构成中违法性的超法规阻却事由,但是在讨论立法中何种合法药物属于药后驾驶中的“药物”,则需要借用该理论进行思考和论证。当前社会我们缺乏摄入某些合法药物能够减损驾驶能力的公众意识,也缺乏服用合法药物会导致因药后驾驶而被定罪的公共意识。再加上每天有大量的人因为疾病治疗的需要而在摄入各种药物,因此我们无法期待驾驶人员由于治疗轻微和普通的疾病所需,按照医师的医嘱服用含有致使驾驶人精神或身体受损成分的药物,就放弃日常的驾驶行为。即使这种情况下的驾驶也会对公路安全产生危险,也不能期待驾驶人选择安全驾驶而放弃疾病的治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寻求在保障公共安全和保证公民正常生活便利之间的平衡。因此,对于合法药物纳入到药后驾驶的范围应当采取严格限缩的态度,可以将合法药物局限为被民众所熟知的对人的精神意识或身体会产生极大的影响从而不宜驾驶的药物以及驾驶人处在医疗状态中,因为医生的嘱咐而明知会对人的精神意识或身体会产生极大的损害从而对驾驶技能产生极大影响的药物。
3. 药物的代谢物
需要在此指出的是药物的代谢物需要在药后驾驶类的危险驾驶罪中予以着重关注。人一旦摄入药物,体内就会对药物进行新陈代谢作用,使得药物分解。这个过程起始于由药物的主要化学成分所产生的活化作用。这会使得人的大脑和身体产生醉毒(药),并且产生快感。当所有的这些化学成分激活之后,就进入第二步程序,即减活化作用便开始了,大脑和身体开始解毒(药)。正是在这个阶段,绝大多数主要的药物代谢物产生出来。一些代谢物在药理上仍然是活性的,能够影响大脑或者身体不同器官的运行。其他惰性代谢物则根本不会对人的精神意识和身体产生影响。和酒精不一样,一些药物的代谢残留物,比如可卡因和大麻,在摄入后的几个星期甚至是几个月都能够被检测到。而这些经过长时间残留的代谢物已经成为惰性代谢物。[42]如果只要驾驶人体内发现药物的代谢物,就认定其构成药后驾驶型的危险驾驶罪,则无异于将药后驾驶型的危险驾驶罪等同于服用药物与驾驶行为的简单叠加,这就会造成该种类型的危险驾驶罪惩罚的对象只是服用药物,而不是具有危险性的驾驶行为,其保障的客体也不是公路交通安全,而只是国家对毒品药品的管理制度。因此在检测出驾驶人员体内存有药物的惰性代谢物之时,则应当排除驾驶人的入罪。
(二) 药后驾驶的入罪标准
在醉酒驾驶型危险驾驶罪中,其入罪标准——即判断醉酒驾驶是否达到刑事不法所要求的危险程度,是一致性的血液酒精浓度。那么药后驾驶如何实现入罪标准的统一就成为需要讨论的问题。目前实务界和学术界有两种入罪的标准。一种是诸如美国内华达州以及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所采纳的药物浓度的入罪标准。另一个是我国台湾地区以及学术界所讨论的以综合状态判断法来入罪的标准。
美国内华达州,服用不同的药物是否构成犯罪,都详细规定了药物在体内的最低浓度,只有在体内浓度超过最低标准的情况下的驾驶,才可以被认定为犯罪。具体如表1所示。
一种入罪标准是“零容忍”。 根据2011年修订的《道路交通条例》第三十九条K(在体内含有任何浓度的指明毒品时驾驶汽车罪)的规定:任何人在驾驶时,如他的血液或尿液含有任何浓度的“指明毒品”,即使没有呈现任何受毒品影响的症状,即属犯罪。任何人如触犯“零容忍罪行”,可处罚款二万五千元及监禁三年。另外,香港地区采取的另外一种标准则是综合状态判断法,在《道路交通条例》第三十九条J和第三十九条L分别规定了在指明毒品的影响下没有妥当控制而驾驶汽车罪和在指明毒品以外的药物的影响下没有妥当控制而驾驶汽车罪。对于“没有妥当控制”的证明需要有客观证据比如驾驶车辆飘忽不定、发生意外或者无法直线行走等等,方可成立。
我国台湾地区则完全采纳后一种方法。他们认为因为对于服用毒品、麻醉药品或者其他相类的物质而驾驶机动车辆,很难找出一致性的标准来判断驾驶人是否“不能安全驾驶”,所以只能依靠药后驾驶的各种现场表现和药后驾驶人的精神意识和身体状态来综合判断,比如“是否行车如同钟摆、是否不能金鸡独立、不能退步走”。[43](392)如张丽卿教授所言:“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条之三所谓是否达不能安全驾驶动力交通工具而驾驶,应依被告行为当时之主观精神意识状态及客观驾驶状态经法院严格调查后加以认定。”“若仅以一会议结论即得为科处刑罚之依据,显然草率。”[44] (381)
我国如果将药后驾驶行为纳入到危险驾驶罪之中,必须要解决采取何种标准使得药后驾驶入罪的问题。如果采取设置体内药物浓度标准,则我国香港地区采用的“零容忍”入罪对于内地来说暂不可行。虽然“零容忍”立法是最容易证明的标准,因为这种立法只要驾驶人员血液内或者体内含有禁止的药物的情况下驾驶车辆,即属犯罪行为,而不管这种药物对于驾驶能力是否产生影响。但是因为在相关的行政法规当中,药后驾驶同样也是行政处罚所要规制的对象。如果采纳“零容忍”的标准,那么区分行政违法和刑事违法的界限则只能“以法益之侵害作为判断标准,在同是服用药物的情形下,对于法益造成侵害或构成实害的应课以刑罚,若未对法益造成侵害或只是具有危险时,因仅仅是对法规纯粹的不服从,则只能为行政犯。” 由于危险驾驶罪本身即属危险犯,因此以是否侵害法益来界定两者之间的关系显然和本罪的性质完全不符。
如果单纯学习美国内华达州的经验,为药后驾驶型的危险驾驶罪中不同的药物设置不同的体内浓度,又在科学上具有难度,会有很多因素使得为人的体内的药品浓度设置一个类似于醉酒驾驶型案件中0.08%的血醇浓度具体的上限变得异常困难。首先,每种药物对于人的驾驶能力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其次,绝大部分的能够影响人精神意识或身体状态的药品的化学分子极为复杂,导致其被吸收、活动以及药效消失都很难被预测出来,而且在每个个体间这些化学反应发生的几率也存在极大的不同。[45]更让确定特定的药物对个体的影响难上加难的是很多人会同时服用多种毒品。还有可能是某人同时摄入了毒品、麻醉药品和合法药物,这样导致多种药物在体内发生药效。另外还包括任何一种毒品和酒精相互混合使用的情况。[46]
如果简单地采纳我国台湾地区的做法,则存在的问题更为明显。首先是行政违法和刑事犯罪之间的区分问题仍然无法界定。其次是对于驾驶人是否不能安全驾驶或者是否具有侵害公共安全的危险性完全依靠主观的观察和判断,而没有任何可量化的评价因素,在我国可能会导致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判决的准确性和权威性会受到质疑。
如果将美国内华达州、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入罪标准进行融合,取其精华,能够最大化地保证药后驾驶型危险驾驶罪在刑法上评价的适当。因此建议对服用后驾驶可能被认定为危险驾驶罪的药物设置最低的体内浓度标准,尽管要使得这种浓度标准的设置达到精确程度几乎不可能,但是可以采取法律拟制的方法使该浓度标准达到一个相对准确的程度。事实上在交通法规中这种对于模糊难以确定的事实经常会采取法律拟制的方法来解决。比如严格的限速规则,限速规则的目的是为了在相对恒定的交通车流量的公路上设置一个安全的速度。这个速度限定并不因为其他因素诸如气候条件、驾驶人员的技能或者车辆的安全性能的变化而变化。这就意味着如果一个人驾驶速度超过10 km/ph,即使其驾驶的车辆具有超强先进的安全性能,而且是在晴朗的天气下、干燥的公路上且没有其他车辆或者行人在附近的情况下,也会被予以行政处罚。相反,另外一个驾驶在湿滑的交通拥挤的公路上以不超过10 km/ph的速度行驶的驾驶人员,尽管其对公共交通的威胁更大,则也不会受到行政处罚。[47]设置了该标准之后,如果未达到此浓度,即应当视为违反相关的行政法规,予以行政处罚。如果通过化学检测,驾驶人体内的药物达到入罪的浓度,但是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驾驶行为受到影响,应当入罪,但是配置的法定刑应当在最低幅度内。在达到入罪浓度的标准下,如有相关的客观证据证明驾驶确属受到药物的影响,应当视为在药物的影响下不能安全驾驶,则应当配置相对前者较高的法定刑幅度。这样设置既解决了行政不法行为和刑事犯罪行为之间的关系,又能实现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
四、结语
在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为支撑点的风险刑法扩(刑法)圈论和以保障公民自由和权利为落脚点的刑法谦抑性限(刑法)圈论的争锋博弈的背景下,无论是以德日和我国台湾地区为代表的大陆法系还是以英美以及我国香港地区为典型的英美法系,其争论的焦点早已经从药后驾驶是否应当入罪的问题转移到如何设置更好更精确的药后驾驶刑事诉讼程序以能够最大化地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问题上。而我国大陆司法实务界和理论界却依然纠结于药后驾驶入罪应不应该和可不可以的问题上,迟疑不前,这也使得其他相关领域的学者更无动力去研究更为细致、科学的药后驾驶的执法、鉴定和司法上的程序和技术问题。最后可能导致我们既没有体系成熟的危险驾驶罪,也没有细致科学的应对该罪的刑事诉讼程序。
注释:
① 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调研报告称,危险驾驶入刑一年以来,太原市各基层法院共受理危险驾驶罪案件234件,均为醉驾型案件。参见《太原市审理危险驾驶犯罪案件调研报告》. http://www.sxfyw.gov.cn/funonews.asp?id=17868.2013-01- 25/2013-02-25. 广东省中山市2011年5月到2012年2月10日两级法院所受理的危险驾驶案件均为醉驾型危险驾驶,还没有出现追逐竞速类型的案件。参见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调研组. 醉驾入刑专题调研报告. 中国审判,2012,(7):99.
② 所谓民粹主义刑事立法是指立法的目的在于平息民众对近期社会影响较大的危害行为入罪,而该行为原来是由行政法或者民法所调整的。参见周详. 民生法治观下“危险驾驶”刑事立法的风险评估. 法学,2011,(2):25-27;陈珊珊. 量刑中的及量化与政策导向评析——以交通犯罪中最高院《量刑意见》的适用为例. 法学,2012,(2):142.
③ 当然,世界上没有是完全相同,只具有或多或少的相似,实质的平等仅是相似的关联。参见[德]考夫曼. 法律哲学第二版. 刘幸义,等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178.
④ 也有认定为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例子,参见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张国斌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二审一案。本案中,上诉人在一天内服用14颗用于止疼的精神类药品——盐酸曲马多的情况下驾驶,致5车受损,6人受伤,一审被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二审改判为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http://www.bsfy.gov.cn/News_View.asp?NewsID=929. 2013-02- 02/2013-02-22.
⑤ Laura Ann Wilson, Perceptions of Legitimacy and Strategies of Resistance: Melbourne Illicit Drug Users and Random Roadside Drug Testing, 23 Current Issues In Criminal Justice. 183 2011. Also see Jeffrey M. Morgan, The Admissibility of Drug Recognition Expert Testimony in the Prosecution of Individuals Driving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 Controlled Substance: State v. Klawitter, 518 N.W.2d 577 (Minn. 1994). 18 Hamline Law Review. 261 1994.
⑥ NEV. REV. STAT. ANN. § 484.379(1)(b) (West 2009).
⑦ 药后驾驶在违法性、有责性方面与醉驾型危险驾驶罪几乎没有区别,唯一的区别在于构成要件该当性,而该行为入罪,构成要件该当性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是摄入何种药物以及达到何种程度方可入罪。
⑧ See NEV. REV. STAT. ANN. § 484.379(1)(b) (West 2009).
⑨ 参见2011年香港《道路交通条例》附表1A。
⑩ 目前期待可能性理论在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学术界从整体上呈现严格限缩其使用的趋势,且如今其对实践的影响也已经淡化。参见[日]西田典之. 日本刑法总论. 刘明祥,王昭武,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40;林钰雄. 新刑法总论. 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6:223-272;林山田,许泽天. 刑总要论. 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6:157;刘艳红. 调节性刑罚恕免事由: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功能定位.中国法学,2009,(4):110.
来源于http://www.leg.state.nv.us/NRS/NRS-484C.html#NRS4- 84CSec110
Vgl. J. Bohnert in: Ordnungswidrigkeitengesetz, Karlsruher Kommentar(zit. KKOWiG-Bohnert), 2006, 3.Aufl., Einlleitung Rn.50ff.
参考文献:
[1] 肖荣, 施杰. 建议将“毒驾”纳入危险驾驶罪范畴[N]. 检察日报, 2012?03?5(5).
[2] 杨成. 范徐丽泰委员建议刑法(八)考虑滥用药物驾驶的问题[EB/OL]. http://legal.people.com.cn/GB/13989603.html.2013- 01-25/2013-02-27.
[3] 陈建忠, 曹凯, 张建兵.“毒驾”入刑的思考[N]. 江苏法制报, 2012?8?6(6)
[4] 刘长秋. “毒驾入刑”与“风险刑法”[N]. 文汇报, 2012?07? 02(5).
[5] 王逸吟, 殷泓. 毒驾入刑, 行不行?[N]. 光明日报, 2012?7?5 (15).
[6] 范和生. “药驾”:不容忽视的“马路杀手”[N]. 人民公安报·交通安全周刊, 2012?6?7(3).
[7] 陶功财. “药驾”要和“酒驾”同等对待[N]. 法制日报, 2012?11? 3(7).
[8] 陈少华. “毒驾”行为入罪的立法构想[N]. 江苏经济报, 2012?8?22(B3).
[9] 颜河清. “毒驾”入刑法律问题研究[J]. 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2(4): 71.
[10] 陈帅锋, 李文君, 陈桂勇. 我国吸毒后驾驶问题研究[J].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1): 58.
[11]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运输署. 毒驾及药驾[EB/OL]. http:// www.td.gov.hk/tc/road_safety/drug_driving/index.html. 2013? 01?25/2013-02-22.
[12] Aaron J. Marcus. Are the roads a safer place because drug offenders arent on them? An analysis of punishing drug offenders with license suspension [J]. The Kansas Journal of Law & Public Policy, 2004(13): 557?574.
[13] 林山田. 刑法各罪论下册[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14] [德]乌尔里希·贝克. 风险社会[M]. 何博闻,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4.
[15] 周详. 民生法治观下“危险驾驶”刑事立法的风险评估[J]. 法学, 2011(2): 27.
[16] 刘艳红. “风险刑法”理论不能动摇刑法谦抑主义[J]. 法商研究, 2011(4): 26.
[17] 劳东燕. 公共政策与风险社会的刑法[J]. 中国社会科学, 2007(3): 130?131.
[18] Tina Wescott Cafaro. Slipping through the cracks: Why cant we stop drugged driving? [J].Western New England Law Review, 2010(32): 33.
[19] 张文. “毒驾”伤人, 该当何罪[N]. 人民日报, 2012?3?28(11).
[20] 赵文. 施杰再呼吁: “毒驾”应尽快入刑[N]. 四川法制报, 2012?6?20(A1).
[21] 吴晓杰. “毒驾”, 不能承受之“轻”[N]. 检察日报, 2010?8? 17(4).
[22] [日]西原春夫. 刑法的根基与哲学[M]. 顾肖荣等, 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4.
[23] 焦轩. “毒驾”惊动“刑法”是否必要?[N]. 人民公安报·交通安全周刊, 2012?5?10(1).
[24] NHTSA. Drugs And Human Performance Fact Sheets (2004) [EB/OL]. http://www.nhtsa.gov/people/injury/research/job185- drugs/technical-page.htm. 2013?01?25/2013?02?22.
[25] 潘从武. 毒驾药驾危害等同酒驾却未被重视[N]. 法制日报, 2010?11?18(7).
[26] 洪家殷. 行政罚法论[M]. 台北: 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2008.
[27] 赖早兴. 论平等在刑法中的地位[J].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06(2): 83.
[28] [德]考夫曼. 法律哲学第二版[M]. 刘幸义, 等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1.
[29] 韩忠谟. 刑法原理[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30] 张明楷. 刑法学第四版[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1.
[31] 张文. “毒驾”伤人, 该当何罪[N]. 人民日报, 2012?3?28(11).
[32] 王逸吟、殷泓. 毒驾入刑, 行不行?[N]. 光明日报, 2012?7? 5(15).
[33] 张明楷. 危险驾驶罪及其与相关犯罪的关系[N]. 人民日报, 2011?5?11(6).
[34] 朱磊. 专家指出“毒驾入刑”尚面临司法认定难题[EB/OL]. http://news.ifeng.com/society/1/detail_2012_08/22/17012127_0.shtml. 2013?01?25/2013?02?23.
[35] 徐久生, 庄敬华, 译. 德国刑法典[M]. 北京: 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4.
[36] [日]山口厚. 刑法各论[M]. 王昭武,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37] 林东茂. 刑法综览[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38] [英]J.C.史密斯, B.霍根. 英国刑法[M]. 李贵方, 等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0.
[39] 林山田. 刑法各罪论下册[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40] Department for Transport, Road Safety Compliance Consultation (2008) [EB/OL]. http://collections.europarchive.org/tna/2008- 1223120624/http:/dft.gov.uk/consultations/open/compliance/.2013?01?25/2013?02?22.
[41] 刘艳红. 调节性刑罚恕免事由: 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功能定位[J]. 中国法学, 2009(4): 110.
[42] Matthew C. Rappold. Evidence of inactive drug metabolites in DUI cases: Using a proximate cause analysis to fill the evidentiary gap between prior drug use and driving under the influence[J]. UALR Law Review, 2010(32): 535?536.
[43] 林东茂. 刑法综览[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44] 张丽卿. 新刑法新探[M]. 台北: 元照出版公司, 2008.
[45] Tina Wescott Cafaro. Slipping through the cracks: Why cant we stop drugged driving? [J].Western New England Law Review, 2010(32): 33.
[46] Lawrence R. Sutton. The effects of alcohol, marihuana. and their combination on driving ability[J]. Journal of Study on Alcohol, 1983(44): 438, 442?443.
[47] Jeremy Prichard, et al. Detouring civil liberties? Drug-driving laws in Australia[J]. Griffith Law Review, 2010(19): 332.
[编辑: 苏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