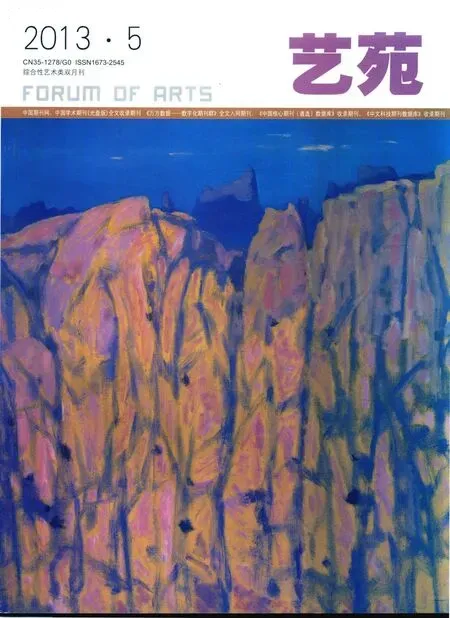李碧华电影剧作论
文‖王宇洁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新浪潮运动”在香港影坛曾风靡一时。在此期间,香港女作家李碧华参与编剧的电影处女作《父子情》(1981)获第一届香港金像奖最佳作品、最佳导演奖,为李碧华的电影创作之路开启了通往绚烂风景的大门。然而在之后的电影创作中,她“从朴素写实转到浪漫奇诡,于宗教的轮回与俗世的鬼神中找到了灵感,写下了一连串神秘气息很重,具有诡异风格的作品”,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李碧华模式”——通过对历史或传说的“新编”,在时空的轮回与错乱中叙述爱情悲剧,带着奇幻、诡谲、凄艳的美学风格,表达出对现实的隐喻,以及现代女性所面临的情感困惑。其创作的电影作品(编剧或原著)主要有《胭脂扣》(1988,获第八届香港金像奖最佳编剧奖)、《潘金莲之前世今生》(1989)、《秦俑》(1989,获法国巴黎奇情动作片大奖、第10届香港金像奖最佳作品提名)、《川岛芳子》(1990,获第三十五届亚太影展最佳美术指导奖)、《鬼干部》(1991)、《霸王别姬》(1993,获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奖)、《青蛇》(1993)、《诱僧》(1993,获第三十届台湾金马奖最佳原著剧本奖提名)、《三更2之饺子》(2004)。这些作品,二十多年来依然奇情摇曳,风姿不减,令人动容。
一、“男”与“女”:时空转换中的爱情悲剧
生活在香港都市的李碧华,笔下却极少出现都市生活的影像描摹,而专注于历史中那缠绵悱恻的爱情。这与其成长经历不无关系——李碧华成长在一个封建旧式大家庭里,生活在祖父传下的木结构旧式楼宇之中,老房子的那些人情世故、家长里短、是是非非都成了她残余的记忆,为其创作提供了素材和灵感。
“李碧华模式”首先体现在于时空轮回和世事剧变中透视爱情悲剧。在其10部电影剧作中,有9部(除《父子情》)涉及爱情题材且无一例外都是悲剧,其中3部(《胭脂扣》、《潘金莲之前世今生》、《秦俑》)跨越了不止一世情缘,其余也均跨越了人生的不同阶段或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时空跳转,爱恨纠缠,让爱情冲破了“恒久远”的神话,在世事沉浮中露出披着纯洁美丽的面纱而实为面目可憎的仪容。李碧华喜欢把爱情描摹得极尽绚烂动人转而来个冷酷决绝的煞尾,让观众在缠绵悱恻之誓言与凋敝破败之结局的落差中痛入骨髓。
比如《胭脂扣》描写了一段跨越半个世纪的虚妄爱情:30年代香港石塘咀的红牌妓女如花与人称十二少的富家子弟陈振邦相爱并谈婚论嫁,但由于身份家世悬殊,婚事遭陈家反对,振邦脱离家庭与如花同居,两人以胭脂扣定情。后因吸食鸦片,渐渐经济拮据,二人计划吞食鸦片殉情。结果如花死去,而振邦被救活。50年后,如花在阴间苦等不得心上人,便重返阳世找寻,历尽艰辛辗转却发现昔日的爱人躲在一电影剧组苟且偷生,老态龙钟。年轻时的爱情被渲染得崇高而坚贞——作为城中屈指可数的富家少爷,振邦对一名烟花女子动了真情已令人感动,之后更为了如花脱离名门望族、抛弃荣华富贵、甘愿共赴黄泉,更叫人喟叹不已。然而时光洗尽铅华,当年的不离不弃如今隔着阴阳之门,当年的容光焕发如今苟延残喘,当年的海誓山盟如今轻如鸿毛——振邦宁可选择如行尸走肉般活着,也不愿遵照誓言去寻找曾经心爱的人。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如花曾经的炽烈真情只化作一句决绝的“谢谢你,我不想再等了”,便交还胭脂盒而去,连背影都是一闪而过。爱情背后的苍凉、女性面对这种苍凉的绝望,以及绝望过后独立和自我意识的被动产生,都在电影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又如《青蛇》中,青蛇历尽千辛万苦找到已被封了五阴成了废人的许仙,然而为时已晚,当她发现素贞早已不见踪影,眼里闪过一丝凄凉,便决绝地将剑刺入许仙的胸膛,留下一句“你应该跟姐姐在一起的。”原本自在无忧的妖精,经过人间花花世界的一场游历,方知爱情的不可触碰与男性的不可信任。不论是如花还是青蛇,或许到故事的最后一刻,她们的女性意识才得以觉醒,而这一觉醒的代价便是死亡(自己的或他人的)和对爱情的绝望,这是值得人深思的——女性的生存以及爱情的勉强维持仿佛都必须牺牲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而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付出自己的女性又往往难以逃脱爱情中受难者的命运。

《胭脂扣》剧照
在李碧华的剧作中,女性始终是光彩照人的、丰厚饱满的,男性大多是反面的、单薄的、卑琐的(只有《秦俑》中的蒙天放是一个正面的男性角色),而女性却往往独自承担着爱情悲剧的凄凉,而悲剧的根源很大程度上来自强大的父权文化与男权文化。不论是迫使十二少离家的门户族规(《胭脂扣》),许仙收妖降魔的咒语(《青蛇》),还是红萼面对的政治动荡中的兄弟相残(《诱僧》),都是男权社会的符号表征。这体现了李碧华对男权社会中人的生存困境的思考——男性同样面临社会对爱情的桎梏,但是他们的爱情更显理性和自私,岁月静好时可以和女人相亲相爱,风雨来临时则懦弱逃避。恰如所指,“李碧华的这种设计其实是想从侧面来描述男权制文化对爱情的扼杀。这与塑造高大的女性形象正面回应相反,含蓄地指出男权制文化不仅对女性有束缚,也制约着男性,使他们在想爱的同时又受到强大的压力而不敢爱,只能选择保护自己或背叛爱情。”
李碧华在剧作中体现出的爱情观与其在生活中是一致的,她的一些经典语录,如“男人——负情是你的名字”,“只恨女子由来心眼浅,平白便点缀了众生,抬举了男人”,“再多高人指点,爱上一个人,仍是走投无路的”等等,都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爱情的虚妄和女性的弱势。“李碧华以如此清醒独立的女性意识深入地剖析了男性的劣根性,表现出她对男性无以复加的深深失望、鄙夷,和对整个男权社会的有力质疑。”她在剧作中从不美化爱情,为观众“造梦”以迎合其审美期待,而是真实抒发自己内心的感受,这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文艺创作的独立性与自主性。但是,始终对爱情持过于悲观的态度而没有更加深入的理性思考和正面引导,似乎对广大观众爱情观的建立带有一定的消极影响,就个人创作而言也落入了趋同化的窠臼,是值得商榷的。
二、“人”与“妖”:镜像凝视下的女性选择
其次,“李碧华模式”体现在善写“妖”,或者称之为非常态的人。剧作往往在“人”与“妖”的镜像观照中,展示女性性格深层的两面性,窥视女性的生存与情感立场选择。在一类镜像观照中,“人”往往以一个正面的传统的形象呈现,而“妖”则代表“人”在现实中并未暴露而在人性中又客观存在的另一面——或是相对于正义的邪恶一面(如《诱僧》中相对于红萼的青绶),或是未修炼成人的带着动物性的恣意快活的一面(如《青蛇》中相对于白素贞的小青),或是与传统道德或社会评价相抵触的女性满足自身欲求的一面(如《潘金莲之前世今生》中相对于单玉莲的潘金莲、《川岛芳子》中相对于童年显玗的成年金碧辉),在这类“人”与“妖”的镜像凝视中,“人”在社会价值体系中往往是正义的、无私的、贤良的女性,而“妖”是邪恶的、不完美的,或不合伦常的,但剧作的结局往往摆出“人”的生存困境:“人”全心付出而终遭毁灭,而“妖”却可以不念伦常逍遥快活。另一类镜像观照中的“妖”是相对于暗淡现实的光辉理想的一面(如《霸王别姬》中相对于程蝶衣的虞姬、《胭脂扣》中相对于凌楚娟的如花等),这类“妖”是作为现实女性的“人”的理想化身(在此姑且把程蝶衣作为女性来分析),但是这样的“妖”往往只能以虚幻的人物形象存在,而“人”则在现实的重压下形成自我的裂变,或在理想的追随中自我结束(如程蝶衣),或在现实的不尽人意中委曲求全(如凌楚娟)。无论哪一类镜像观照,仿佛女性走“人”的道路终遭毁灭,而“妖”才可以在女性主义的道路上自主选择生存的方式。这就对传统观念下女性的生存困境提出了思考——女性始终在男权主义的社会中处于弱势,女性对爱情的忠贞往往不能满足自我的期许,女性或许应该找到一条适合自我的、可能违背男权社会中伦理道德的生存方式。
就《潘金莲之前世今生》中的单玉莲与潘金莲而言,前者是一个在现世中老实本分做人,真诚面对情感与欲求,却屡遭人生挫折,最终选择与爱人共赴黄泉的正面女性形象,我们称之为“人”,而后者则是单玉莲背负着千古骂名的前世,我们称之为“妖”。在电影中我们可以发现,单玉莲其实只是试图以现代社会价值体系重塑自我的潘金莲,她的内心始终摆脱不了潘金莲式的“妖性”。如在与武大成婚之后,她不能自已地倾心于丈夫的堂弟武龙;又如在风流浪子西门祝的引诱下,与其偷欢被武龙撞见,她眼噙泪水无奈地说:“我好像忍不住……”“妖性”实际象征着女性自然产生的原始欲望,每个女人都是“人”和“妖”的结合体,但是男权文化迫使女性作“人”的选择,抑制了其“妖性”的一面,从而不可避免地造成女性的命运悲剧。李碧华的剧作中这种对女性命运的思考无处不在,如《青蛇》中的小青实际就是一个在自主选择命运的道路上踌躇的女性形象。白蛇修行千年,已幻化成人,成为了一个情愿放弃修行与爱人共享天伦、为之生儿育女的传统贤良女性,而青蛇修行尚浅,只有人形尚无人性,便在姐姐的影响之下体验了传统女性的人间生活,然而面对许仙的无能、法海的虚妄和姐姐的死亡,青蛇终究意识到“人”并不值得向往,最终还是选择了做回“妖”。白蛇和青蛇,其实是女性的两种生存状态的投射。“白蛇一厢情愿的或满腹委屈的痴情不过是现代女性在婚姻与爱情中的尴尬处境。对自身角色的选择、对男性的忠诚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也是最现实层面的选择。青蛇最后以剑杀许仙,这种‘弑父’式表达,隐含了女性作者在文本与现实中被贬抑的愤怒。”
由此可见,李碧华剧作以故事新编的形式,在世事轮回的缠绵悱恻中审视着爱情的苍白,在对人性的镜像凝视中书写着对女性生存困境的理性思考。这种独特而经典的“李碧华模式”赋予了剧作以坚实的思想和情感依托。但是,始终把女性命运与传统社会女性评价摆在对立的两面,暗示以一种消极的方式去解决二者矛盾,体现了“李碧华模式”的偏激与局促之处。
三、“虚”与“实”:虚构影像后的现实烛照
任何一种风格的电影,一旦脱离了社会历史的现实,在自造的梦境中沉醉,是注定没有持久的生命力的,尽管可能名噪一时,20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于台湾的琼瑶爱情文艺片便是明证。“李碧华模式”,选材的非现实化,外加奇幻诡谲神秘莫测的剧作叙事和影片风格,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琼瑶的“造梦”式剧作。然而深入分析李碧华的剧作,我们可以看出其每一部剧作都披着历史的外衣诉说着现实,处处体现着香港人的身份烛照,讲述着城市寓言,展露着后现代语境下都市人的迷惘惶惑,并给人以启迪和思索。而这恰是李碧华的功力所在,也是其剧作的生命力所在。
人们常以“新历史主义”来定性李碧华的小说创作。根植于后现代思潮下的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的存在并非一种绝对真实,相反,它充满着无限的隐喻、不确定和被遮蔽。新历史主义小说反拨伪浪漫主义和理想追求,拒斥主流意识形态的规定图景和预期,关注历史中的小人物,尤其注目于个体性的性格、人性的阴暗面在如何改写和左右着个体的命运,至于历史情境和历史事件对凡俗人生的决定性影响反而被淡化或忽略,甚至“历史”在文本中根本就是缺席的。据此,李碧华的电影剧作的确是将新历史主义的思潮贯穿始终。剧作中的故事始终安放在历史上的乱世——从荆轲刺秦(《秦俑》)、玄武门事变(《诱僧》)到民国(《胭脂扣》、抗战(《川岛芳子》)、“文革”(《鬼干部》、《潘金莲之前世今生》、《霸王别姬》),并巧妙地将繁杂而难以评述的历史史实加以为我所用的想象和描摹,来放大呈现人性的微茫。
首先,剧作通过一系列无法为自己身份定位的“边缘人”,来烛照了九七回归前后的香港,体现了明显的香港情结与香港回归前后,社会民众“自我认同感”的某种迷茫,反映了地域创作的特色。如作为“满洲国第一妖艳”的川岛芳子,她的一生始终陷于自身身份与性别的错位与迷惘中。她是满洲格格,又是日本浪人义女;她是上层男性猥亵的玩物,又作为将军处处以男装示人;对日本人而言她是侵华工具,对中国人而言她是日本走狗。从年幼时那个一脸泪痕哭喊着“我是中国人,不是日本人”小女孩到受控席上那个绝望冷酷地说出“我是日本人,不是中国人”的中年女人,我们不禁对这个找不到自身位置的一出生就成为政治工具的女子产生由衷的怜惜。《诱僧》中的石彦生亦是如此,他曾认定李世民为乱臣贼子,誓死不侍大唐,与手下隐居寺庙伺机蓄势兵变。然而当他发现世事不若期许,国泰民安,天下太平,便丧失了精神支柱,找不到了自己的位置而混迹于世间,内心在归顺和兵变间游离挣扎,屡屡破戒,最终看破红尘。这些边缘人物内心矛盾的刻画我们可以把它视作对香港这一特殊地域身份认同危机的折射。一边是血浓于水的祖国母亲,另一边是带着它从蛮荒走向现代化、制度和生活状态都已与之同化的宗主国,面对突如其来的“回归”,香港人如何找到自我的位置和安全感?恰如所指,“在香港这个高度发达的物质金钱社会中,个人动摇的人生、价值观,萌生发展中的重寻历史、追认身份的香港意识,充满华夏文化认同心理的、内心深植的中华意识,共同形成了李碧华的意识结构,也代表了很大一部分香港市民的思想意识。”在这样的文化隐喻中,李碧华的剧作便更具有了反映时代状态和诉求的深远意义。

《川岛芳子》剧照
其次,剧作中通过古今的对比和折射,来反映了后现代文化语境中人的精神危机和虚无、惶惑的生存状态。这很明显地体现在《胭脂扣》中老少两对情侣的爱情观的对比中。尽管相对于如花,十二少体现出明显的卑琐和负情,然而年轻时他也为如花真心付出,并且两人海誓山盟为爱殉情——然而如今,这样的爱情已不复存在。“你看看人家如花和十二少”,“今时今日谁还会像她这样痴情”,“我嫉妒如花,她敢做的,我这辈子也不敢做,连想也没想过”——楚娟声泪俱下的对白其实就是对现代人缺失真爱的一种追忆式想象。《秦俑》中蒙天放的三世情缘也呈现出愈发萎缩的态势——一世中韩冬儿对其一见钟情,冒死犯戒,猝火泥封;二世中朱莉莉开始意识不到真情,偏执追求富有帅气的大明星白云飞,直到最后才在蒙天放的保护下意识到真爱的存在,已体现出在爱情上明显的浮躁;三世中日本女郎山口靖子只露出莞尔一笑,给观众留下无穷的想象——在现代社会中,一个年轻貌美的日本贵宾与一个年老色衰的修补工之间会产生什么样的旷世奇恋呢?幸而电影对此作了留白,否则呈现给观众的可能只能是现代爱情的失落。爱情的失落如此,文化的失落亦如此——作为“秦俑”的蒙天放便是一个文化符号。他忠烈信义、侠肝义胆、对爱情忠贞不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然而当他步入现代社会,却只能被所有的人称之为“怪人”,露出对现代文明明显的迷惘和惶惑,最终蜗居秦俑堆中,从威武大将转为修补工。在剧作中表现出的对现代文明和都市文化的担忧,体现了李碧华对古典式爱情的向往、对现代爱情的失望和迷惘以及在此基础上带着一定文艺创作责任感的思考。
第三,对政治和社会不良现象的针砭与讽刺,也在李碧华的剧作中时不时闪现。如《鬼干部》则是以惊悚片为外壳的政治讽刺寓言,其中被血魔附体的干部不住地说大话空话,也对当代官场的某些不良作风作了隐晦的批判。当然,这些批判渗透在魔幻的剧情中,带着李碧华特有的神秘主义的风格,显得含混而具有理解上多义性,某种程度上这也成为李碧华剧作具有经久不衰魅力的原因——不同时代的不同人都可以在其剧作中完成文化批评语境下对时代和社会的自我言说。
对香港的寓言式烛照和对现代都市文化失落的担忧,渗透在李碧华的剧作中,赋予剧作以时代意义和理性哲思,使之载负了更高层面的社会文化承担。
四、“执”与“变”:模式套路外的绚烂风景
尽管李碧华几乎全部剧作均没有脱离“李碧华模式”的套路,但由于极其丰富的想象力、天马行空纵横驰骋的文笔以及瑰丽绚烂的文化承载,她的每一部剧作都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视觉享受,而不会使人陷入审美疲劳。
作为编剧,李碧华从不与固定的导演合作,体现了创作的独立性,但是每一部剧作都能找到与剧作的文化向度相适应的导演,两者相辅相成,使每一部电影都才华尽显,将其所展现的文化内涵张扬到极致。如与徐克合作《青蛇》,使徐克善于旧曲唱新的影片特色和大胆的极端化的美学风格尽显;与陈凯歌合作《霸王别姬》,将陈凯歌深厚的中国文化素养以其擅长的“京戏”作为载体淋漓尽致地展现;与陈果合作《三更2之饺子》,也发挥了陈果善于表达对欲望泛滥的现实社会之忧虑的写实风格。不论是应邀作剧还是一拍即合,李碧华的合作选择也处处体现了一代才女的慧眼独具。
李碧华剧作在美学上最大的特点是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在声画光影的运用中始终营造绚丽多姿、博大精深的文化奇观,体现出李碧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及扎实的美学功底。如《青蛇》中的对白以昆曲唱词形式念出,将苏杭的天堂式环境与杏花春雨般的柔情蜜意幽曲婉转地唱出,更好地体现出《白蛇传》这个中国式文化经典的意蕴;如《诱僧》,整部电影自始至终参透了“禅”的意味,尤其是影片中音乐的运用,在血雨腥风的杀戮时配上了清缓玄静的禅乐,将这个圣与俗、虚静与心动两种个人意识相克相生的故事演绎到极致完美;又如《霸王别姬》,更是以京戏的名义,将台上台下的人性守望呈现为一种东方式凄艳的美,20年来为中外评论家津津乐道,无可超越。不可否认,电影最终的成功与导演的功力密不可分,然而李碧华的剧作为完美的影像呈现描绘了最初的蓝图,其玄妙的艺术构思、丰富的想象力与扎实的文学功底是令人折服的。同时,对社会、人性、命运的执着思考使李碧华小说的主题思想达到了一定的广度、深度和力度,可以说李碧华的文本写作自内而外散发出文学的诗意,这种极高的文学价值和素养为其小说的电影改编奠定了扎实的根基。中国传统文化对李碧华剧作的滋养如同在精心烧制的瓷器上涂上绚烂的珐琅彩,瑰丽炫目,永不褪色。秉承着这样的创作理念,李碧华编剧的电影多年来仍然能在满目光影交错中脱颖而出,熠熠生辉。
结 语
从琼瑶到朱天文,从张爱玲到李碧华,台港文坛上的女性作家为广大观众贡献了许多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电影剧作。遗憾的是,李碧华的电影剧作近年来呈现式微的态势,所幸《生死桥》、《古今大战秦俑情》等又让观众在电视剧领域领略到了其作品再次绽放的异彩,话剧《青蛇》的创作改编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这些都为模式化的电影旧作提供了出路。在电视剧领域各类穿越剧的热播也体现了广大观众对于李碧华模式在娱乐性开发方面的肯定,而对于思想性和艺术性要求更高、更加要求反映时代核心价值观念的电影艺术而言,一味旧作翻新和美学风格的一成不变是无法满足广大观众的期待视野的。我们期待着李碧华的电影新作,也相信她能凭借自己的旷世奇才为广大电影观众再次奉上视觉的饕餮盛宴。
[1]钟晓毅.90年代的香港女作家[J].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评论和研究,1994(2).
[2]姚保兴.“古今言情第一人”笔下的情[J].南昌教育学院学报,2011(3).
[3]杜瑾.李碧华电影中绝望的爱情[J].艺海,2010(2).
[4]聂焱,齐督军.李碧华小说中的性别政治[J].文学教育,2010(3).
[5]肖朵朵.新历史主义视域下的人性书写与影像呈现[J].电影文学,2007(1).
[6]黄亚星.边缘的怀旧者——李碧华小说的意识结构[J].华文文学,2004(2).
[7]黄梅.渐老芳华、爱火未减、人面变异——论《胭脂扣》中的两性书写与香港意识[J].美与时代,2010(5).
[8]李鑫.李碧华小说的电影潜质分析[J].电影评介,2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