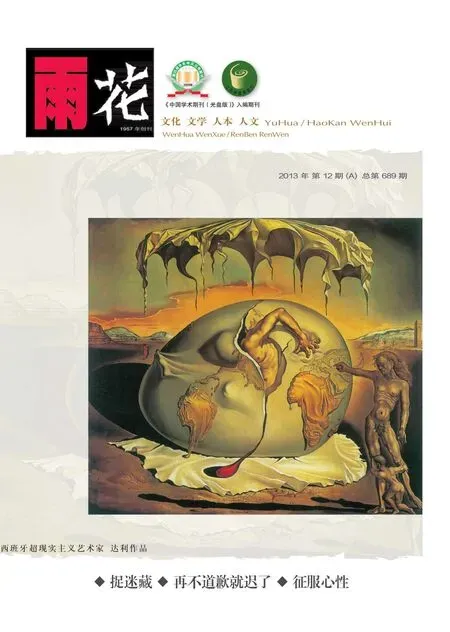旧影依稀
● 池 澄
新闻教程中有一句人们熟知的话语:“名人的烟斗也是新闻。”高晓声当然是名人,他的遗物就说那只竹篮子,不仅是他自己亲手编的,更是在2222年间相伴自己历经艰辛的可资纪念的物件。在下自诩是个“准收藏家”,对高晓声先生的竹篮子,却曾经失之交臂。
“故人”一词,有两种意思。老朋友可称故人,逝者也可称故人。“故人西辞黄鹤楼”中的故人,是指前者还是后者?未解。晴窗闲坐,想起几位前辈,他们都已是谢世的知名大家,忆往昔之交往,旧影依稀,思念之情油然而生,记以缅怀。
1996年,岁届甲子,宋文治先生在金陵饭店作画。那几日我读到一首好诗,是清初孔尚任的《六合石子》,雨花石因盛产于六合,明清时亦称六合石。诗中有两句咏石之色,尤为精妙。我备了两张彩色宣纸,想请文治先生按孔尚任句写一副对联。走进他的画室,他正在听录音,一见我就说,听,李世济唱的《锁麟囊》,正宗的程派。说着说着,未及其它先进入戏题,他谈京剧流派,又谈昆剧,边说边摆出《牡丹亭》中人物的身段,并手按节拍轻声吟哦起来。这次相见,让我深层次了解了他不仅是一位举世知名的画家,平常又是一位充满生活情趣的人。他在尽兴之余,问我有事么?我说明来意并递上写了孔尚任诗句的一张便笺,先生展纸低声念道:“碧水青苔衣,白云红树雨。”接着说:“此句好熟悉呀。”我听了心中一愣,难道孔尚任这一联曾经有人写过?为此请教先生,他略加思索连声说想起了、想起了:“清初,蓝瑛画过一幅《白云红树图》。”又说:“蓝瑛的画,画中有诗意;孔尚任的诗,诗中显画境。皆妙。”取回先生用俊秀的楷书写就的对联,我以《白云红树雨》为题即兴写了一首小诗——
秋山碧翠/日日积聚深沉/金风润染丹红/不逊春花之娇艳/飘来一阵雨/无序琼枝/垂落有声的珠帘白云依恋嫣红/游移不是飘逝/天涯过客/有多情之一瞬山雀欢歌/有音无影/夕阳佳木/一片多彩晶莹
上世纪70年代,我在南京附近的江浦农村当一个小官。那时的建制是人民公社,下属十几个大队,大队之下又有七八小队。官不上“品”,也就相当于刘邦当年的“泗上亭长”之类。工作之余,喜欢写写毛笔字,抄抄唐诗,不临帖。一日,老中医李大夫看见了,取去一张说是欣赏欣赏,也未经我同意,就贴在诊所的墙壁上。又一日见到我大声说,你的字大家看了都说写得好。隔几日就又有人问我要字,自己当时感觉,我写的几个字还行,不知不觉就有点“飘”起来了。
好友雷先生,也是书法爱好者。他比我认真,每天用一、两个小时习写颜字。某日,约我各带一张习作,到南京百子亭拜访林散之先生,林老是举世知名的书法家,曾任江浦县副县长,又可算是我的上级。他耳背,听不进话也很少说话,面色酡红,端坐书斋,很像一尊罗汉。有人戏说,降龙罗汉的龙飞走了,林老就像降龙罗汉。伏虎罗汉身边的老虎跑了,林老就像伏虎罗汉。见我们来访,林老举手示意,我俩递上各自的习作,他先打开雷的一张横批,看后,拿起手边的铅笔,在三指宽的小条子上写了五个字:“一纸黑墨团”。雷看着看着脸红了,觉得这个评语是“批”得很重的。林又打开我的习作,我写的是一张条幅,林看了似乎觉得我的字说不上好,也说不上“赖”,他没有拿笔写什么,也没有说话,让人纳闷。我俩告辞刚走出屋门,只听屋内说了一声:“聪明字啊。”声如洪钟。
雷先生拍打我的肩头说,林老说话了,可能是夸你的字呢。我说不对啊,不对啊。“聪明字”,写字耍小聪明,是指花里胡哨毫无功力,没有当面说是给我留点面子。而对你老兄的几个字,是评而不是“批”,“一纸黑墨团”,说你写得“黑”,只是学颜字“肥”过了头,改改就好,他同意了我的看法,又把那一张林老用铅笔写的三指宽的字条,取出来看了又看,宝贝似地藏起来。有人说,如果林老的墨书称“墨宝”,用铅笔写的就称“铅宝”。果然,若干年后这些铅笔写的纸条也成了藏家的珍稀,集有多张者甚至上了拍卖会。
知耻而后勇。走出林府后,我径往新华书店选购了一本《乙瑛碑》,一本《圣教序》。隔几日,又在旧书摊上淘到一本孙过庭的《书谱》,煞有介事地做了准备,打算认真临写碑帖,口边常挂着一句话,我要在书法上补一补“童子功”。一日,老爸对我说,“童子功”是穿开裆裤时练的,你年过四十,还能“补”?听他的话,我当时并未泄气,每日一课进行了两、三个月,尔后终因诸多工作琐事,就一曝十寒未能坚持下去。现在想起自己这漫漫浮生,红尘中浑浑噩噩,有多大的事比“孜孜求于一艺”更重要呢?时间就是沙漏,瞬间四十载一晃而过,若从那时起一日一课持之以恒,或有所成。当年,林老的一言之戒,我警知而未警醒,思之怅然。
1978年秋,某日我前往南京利济巷拜访魏紫熙先生,他正在画一张四尺整张的大画,只见画面群峰耸立,幽壑腾云,一幅佳作即将完成。南京画家在山水画中自成一派,清初,有高岑、吴宏等“金陵八家”,也称“金陵画派”。当今的傅抱石、钱松岩、亚明、宋文治、魏学熙,又被誉为“新金陵画派”,大都以画山水为主。若问钱、亚、宋、魏这四位山水画家,各自以画哪一类名山胜境见长并在世人中留下深刻印象?有评论家说,钱松岩的泰岳,亚明的三峡,宋文治的太湖,魏紫熙的黄山……这当然只是一家之言。
眼前魏老的这幅画就是画的黄山。只见他笔蘸朱砂,正在为群峰“点彩”,精心点染中似又带有几分随意,随意中又显收纵自如的功力。只见眼前的画面,一下子似乎就从万木葱笼的盛夏幻变为霜染枫林的金秋。一幅精品力作画就了,只见魏老张开左手,用三个指头在画幅上方空白处抹了又抹,要下笔落款了,口中轻轻地念了四个字:“黄山秋色。”提起笔又未落笔,蓦然转身问我,这张画以这一句为题怎样?我一时有点受宠若惊,一位大画家,下问于我这个小人物,我看看画面高耸的云峰,浓艳的丹红,愣愣地说,“黄山秋色”这四个字感觉“平”了一些,以《黄山高秋》为题如何?魏老迟疑片刻,就在画上提笔落墨写下了“黄山高秋”四字,接着又写:“一九七八年仲秋,画于金陵,紫熙”,然后铃印两方,又加押角印一方。事后回忆此事,以为魏老因爱女魏俐曾在我任职的公社插队,我也曾算是她的领导,题画时也许是为给我一点面子。经过若干年,证实并非如此。他在往后的近二十年中,画此类题材,大多题《黄山高秋》。这说明当年斟酌题款时,他是认可了我的建议的。每与朋友谈及此事,常感有自炫之嫌,但又觉得不可以一己之虑,而消隐魏老礼贤下士从善如流之德,故仍记之,知我者应能谅我。
上世纪80年代,我住南京肚带营,与高晓声先生是同一个单元里的邻居,二人又同供职于一个单位——江苏省作家协会。他是全国知名作家,我是协会驻会干部,在文学界他又可算是我等的前辈,我尊称他为老师。一日,晓声先生敲开我家门让我捎个信,他说:“复旦大学贾植芳教授邀请我去上海讲学,机关里有个小说作品讨论会,就不参加了。”我答话后,见他手中拎了一只竹篮,篮子里空空的。我说:“高老师你上街?”他说:“到菜场转悠、转悠,买点菜。”我再一次注意他手中的那只篮子,圆口、方底、竹片留青,编织成纽花的把手,好精致哟。高见状说:“池澄,你喜欢这竹篮子?”(似乎有一句潜台词,喜欢就送你。)接着他咯咯笑了起来,用带有几分自豪的语气说:“这篮子是我自己编的。”他走了,我心中嘀咕,高老师说的是真话还是玩笑话,这篮子真是他编的?
高晓声先生逝世七、八年后,章品镇前辈赠我一本他撰写的散文集《花木丛中人常在》,其中有一篇《二十年后,高晓声回来了!》,文中描绘了高被划右派后,落难二十二年,艰苦的生活是怎样度过的。章说高晓声是一能人,“他农村百事,常可一逞英雄,莳秧、耥稻……农活以外,还有手艺,编个篮子也是既规正又光滑。”读至此,证实晓声先生手中拎的那只篮子,确是他自己编的。他在常州农村“负罪改造”期间祸不单行,先是1965年自己生病,右边切除了一叶肺,后是1975年妻子钱素珍患病,家中六、七口人,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人民公社的工分值,一个“半残人”是不能养活这一家人的,篾匠的手艺,也许对高晓声曾经起到了一丝丝济困扶危的作用。在这样的大作家手中编成的竹篮,有什么象征意义呢?手中的一经一纬,胸中的百虑千思,在人生的逆境中凝聚成超凡的睿智……高晓声与章品镇二十年后重逢时,就带来艰难岁月中撰写的多篇小说。可以想见,划时代的巨著《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的初稿,那时都已在孕育之中了。
当今,中外举行的拍卖会上,名人遗物折射出鲜明的名人效应。弗朗斯基·培根用过的8支画笔,估价25000英镑。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情人莱温斯基用过的20余件物品,也都上了纽约拍卖会。新闻教程中有一句人们熟知的话语:“名人的烟斗也是新闻。”高晓声当然是名人,他的遗物就说那只竹篮子,不仅是他自己亲手编的,更是在22年间相伴自己历经艰辛的可资纪念的物件。在下自诩是个“准收藏家”,对高晓声先生的竹篮子,却曾经失之交臂。对这类藏品的拥有,并不是计较它现今已值多少银子,而是见物生情,见物思人,领受此中的历史积淀和人间世态,感悟高晓声老师这样的大作家半生困厄、饱含血泪的悲凉人生。一只悲欣交集的竹篮,岂是等闲之物。
“池澄,你喜欢这篮子,这是我自己编的。”耳畔又响起高老师的话语,和他爽朗的咯咯的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