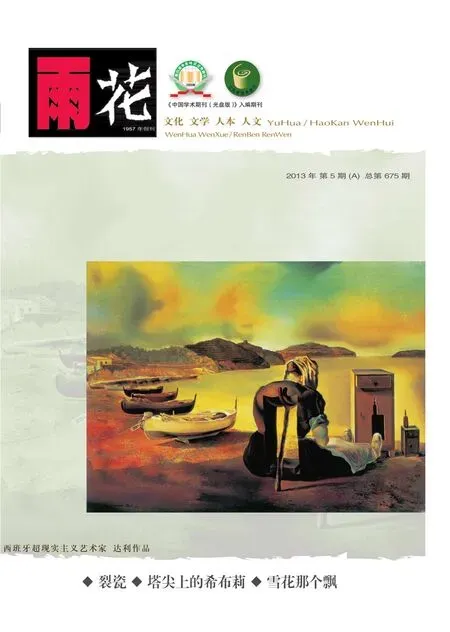鲁迅眼中的“改革难”
● 古 耜
在鲁迅看来,中国的改革之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就观念层面而言,许多人习惯于按部就班,墨守成规,不愿认同、更不愿参与改革;二是从社会现象来看,许多领域的改革常常多曲折,每驳杂,易反复,爱走回头路。
在鲁迅生活的时代,中国社会和国人精神亟待改革。然而,历史告诉人们的却是,在中国进行改革一向困难多多,阻力重重,殊为不易。正如鲁迅所说:“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娜拉走后怎样》)
在鲁迅看来,中国的改革之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就观念层面而言,许多人习惯于按部就班,墨守成规,不愿认同、更不愿参与改革。即所谓“旧染既深,辄以习惯之目光,观察一切,凡所然否,谬解为多,此所为呼维新既二十年,而新声迄不起于中国也”。(《摩罗诗力说》)二是从社会现象来看,许多领域的改革常常多曲折,每驳杂,易反复,爱走回头路。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的话说就是:“人类的历史是进化的,那么,中国当然不会在例外。但看中国进化的情形,却有两种特别的现象: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又恢复过来,即是反复;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而旧的并不废去,即是羼杂。然而就并不进化么?那也不然,只是比较的慢,使我们性急的人,有一日三秋之感罢了。”
中国的改革何以如此关隘重重,步履蹒跚?对此,鲁迅在一系列文章中进行过深入剖解与辟透揭示,其中除了严肃指出社会保守势力对改革的极力阻挠和多方破坏,即所谓:“反改革者对于改革者的毒害,向来就并未放松过,手段的厉害也已经无以复加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等。至少还有四个方面的内容独具只眼,很值得人们充分关注和仔细体味:
一是弱国子民的心态影响了“拿来”的自信和借鉴的勇气。中国的改革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当然离不开“拿来主义”,离不开“别求新声于异邦”,只是这“拿来”和“别求”的主体,却每因自身境况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对此,鲁迅的《看镜有感》有精彩描述:“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接下来,鲁迅做了进一步引申和概括:“无论从那里来的,只要是食物,壮健者大抵就无需思索,承认是吃的东西。惟有衰病的,却常想到害胃,伤身,特有许多禁条,许多避忌;还有一大套比较利害而终于不得要领的理由……但这一类人物总要日见其衰弱的,因为他终日战战兢兢,自己先已失了活气了。”不幸的是,当年中国的“拿来”和“别求”恰恰发生在自身“衰病陵夷之际”。值此背景之下,国人对于汲取和借鉴,瞻前顾后,疑虑重重,乃至寻找理由,固守残缺,自然符合心理和事物的一般规律。而中国的改革则因为怠于引进,畏于创新以致显得行程艰难,成效缓慢,亦乃势在必然。
二是儒家的中庸思想抑制了改革的观念与行为。儒家是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主流,中庸是儒家思想体系重要的观念范畴与思维方式。从全部的历史发展与社会实践来看,中庸思想与思维或许不无合理的、积极的意义,但具体到改革的情境和维度,它的消极因素显而易见。对此,鲁迅有着敏锐的省察和清醒的认识。他在《无声的中国》里指出:“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鲁迅的这一观点一直保持到晚年。1935年4月10日,他在致曹聚仁的信中又一次明言:“老先生们保存现状,连在黑屋子开一个窗也不肯,还有种种不可开的理由,但倘有人要来连屋顶也掀掉它,他这才魂飞魄散,设法调解,折中之后,许开一个窗,但总是在覗机想把它塞起来。”执此对照中国由来已久的国民性和国人相沿至今的心理结构,特别是用它来检视中国历朝历代变革的事实,我们不能不承认,鲁迅观点的精辟和正确,它确实道出了中国改革之所以艰难沉滞的深层原因——中庸让改革锐气尽失,大打折扣。这时,我们庶几真正读懂了鲁迅笔下那句意味深长的以问代答:“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这个与那个》)
三是缺乏坚定的、真正的改革者。近代中国的改革是在“西风东渐”而又列强临门的严重情势下,被动乃至被迫展开的。这意味着当年的改革,不仅思想和理论准备不足,即使参与其事的队伍也是五花八门,鱼龙混杂。用鲁迅的话说:他们的“终极目的是极为歧异的。或者为社会,或者为小集团,或者为一个爱人,或者为自己,或者简直为了自杀”。(《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有的人打出改革的旗号,仅仅是凭着一种热情、一种想象、一种感觉,甚至是为了寻求一种畅快、一种刺激。亦如鲁迅所写:有的革命者其实是“颓废者,因为自己没有一定的理想和无力,便流落而求刹那的享乐;一定的享乐,又使他发生厌倦,则时时寻求新刺戟,而这刺戟又须利害,这才感到畅快。革命便也是那颓废者的新刺戟之一,正如饕餮者餍足了肥甘,味厌了,胃弱了,便要吃胡椒和辣椒之类,使额上出一点小汗。才能送下半碗饭去一般”。这时,鲁迅举例说:“法国的波特莱尔,谁都知道是颓废的诗人,然而他欢迎革命,待到革命要妨害他的颓废生活的时候,他才憎恶革命了。”(同上)而这样的改革者在当时的中国亦比较普遍和常见。为此,鲁迅指出:“有些改革者,是极爱谈改革的,但真的改革到了身边,却使他恐惧。”(《论新文字》)因为“改造自己,总比禁止别人来得难”。(《论毛笔之类》)鲁迅甚至提醒友人:“大约满口激烈之谈者,其人便须留意。”(致姚克,1934年4月12日)改革者既然不具备起码的真诚和相应的素质,那么,改革事业的屡屡受挫或停滞不前,也就不足为奇。
四是掌权者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最终反对改革。近代中国一如既往地延续着封建集权与专制政体。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实施任何社会变革,都离不开掌权者的认可和参与。只是掌权者同时又大都是既得利益者,而从某种意义讲,改革则意味着利益的调整与变更。这便决定了某些掌权者常常从个人利益得失出发,以实用主义态度对待改革。在鲁迅看来,“权力者”未必一定反对改革乃至革命。因为他们“好像有一种错误的思想”,“以为中国只管共产,但他们自己的权力却可以更大,财产和姨太太也更多;至少,也总不会比不共产还要坏。假使共产主义国里可以毫不改动那些权力者的老样,或者还要阔,他们一定是赞成的。”(《中国文坛上的鬼魅》)然而,一旦发现改革需要自己做出让步乃至牺牲,即革命使得“遗产被革去了”,甚至“连性命都革去”(《通信》)时,他们便开始千方百计,不遗余力地加以阻挠和反对。于是,原先主张改革的权力者,“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改革偃旗息鼓,一切恢复原状——“曾经阔气的人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大抵如是。大抵!”(《小杂感》)这显然是改革的又一种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