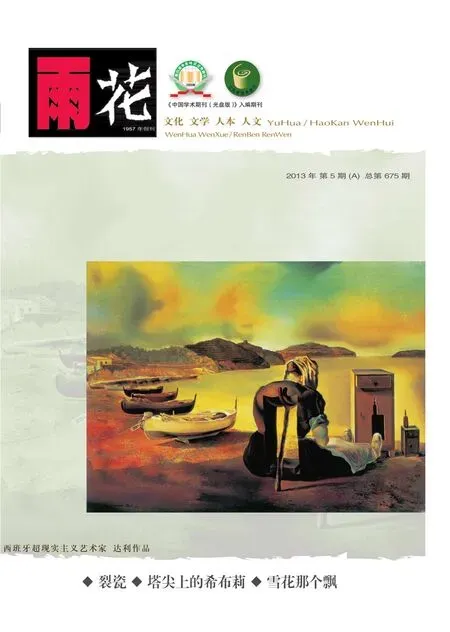王霈先生(外一篇)
● 陈永平
县委大院,名副其实是个大院子。
大院沿中轴线分两部分。东部为办公区,正襟危坐,板板六十四;西部是生活区,鸡飞狗吠,屎尿一笼统。
生活区都是民国时的建筑,是几个大户人家的宅邸。四周围墙围着,套着诸多小院,有两进的,也有四合院,院与院相通,院外的孩子来捉迷藏,经常转得头晕。后来干部渐多,大院空地上建起新房,红砖大瓦挨着青砖黛瓦,狗尾续貂,显得极不般配。
我家的院子是两进的,住着四户人家。西面是院门,东面一堵花墙。翻过花墙,是县委小花园,除了杂树杂草,另有几株枇杷树,一株香橼树,荒凉而生动,吸引人的程度不亚迅哥儿的百草园。我们这个院里住过一位县委书记,一位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一位银行行长和几位局长。这里的住户,包括我,再低调,也有一丝优越感。
到上世纪80年代,本院住户住不踏实了。隔壁行长一家急急找房子,“腾笼换鸟”,给一位老“右派”、“劳改犯”落实政策。其他住户先住着,俟条件成熟再搬。我们希望住新房,但这样搬,等于被挤走,心里觉得不舒服。后来听说,这是人家的祖屋,他在这里出生,对他而言,我们是外来户。
我终于见到了真神。王霈,一位谦和的老者。扁壳脸,见人不见人都笑眯眯的,稀疏的眉毛因此上扬;驼背,年轻时应当是高个儿,应当较魁梧。
初次见面,他送我一坛加饭酒,这让我们没了距离。只两三顿,一坛酒就光了,现已记不清这坛酒让我“加饭”没“加饭”。
我吃饭,王霈先生喜欢坐在一边,跟我聊天。他是学农的,解放前、解放后,都在新疆从事农业工作。上世纪50年代初,他作为新疆代表,出席全国性的农业工作会议,受到毛主席接见。他被打入炼狱,仍很崇拜毛主席,谈及那次接见,他很兴奋,很满足。
2.1分析上述患者护理前后MUIS评分情况,护理前,两组患者的数据均较高,但是护理后,数据明显降低,而研究组患者的数据明显比对照组低,p<0.05,见表1.
平反以后,工资补发,有9000元。那时刚有“万元户”,他腰缠9000元,什么概念!他想去农业部门工作,可他已面临退休,谁要?“关系”就一直挂在民政局。
他最后一份工作跟农业相距甚远。他告诉我上班第一天的经历,像讲故事。那天,民政局的人请他上车,带他上班。问去哪个单位,回答是民政系统。他满心欢喜。汽车一路颠簸前行,他昏昏欲睡;汽车下一个坡,他猛地睁开眼,什么没看见,就盯着三个字:殡仪馆。他吓一大跳,血压上升,脑子一时糊涂,以为自己死了。在确认还活着以后,他质问带他来的人,为何拖他到这里,回答是来上班,看大门。这么着,他看了两年殡仪馆大门,然后退休。
殡仪馆看门人,这已经是恐怖小说的题材了。
坐牢没有摧垮他的身体,但毕竟年纪大了,需人照顾。于是,院里住户见到了他的妻子。
王霈先生的妻子叫董苓湘。夫妇俩与汪曾祺先生是同学,俩人的名字我后来在汪先生小说《小姨娘》里见到了。小姨娘章叔芳和“包打听”的儿子宗毓琳“画地图”,就在王霈家的花园方厅里。王霈家的花园,就是我家花墙东面的花园!我相信《小姨娘》的故事是真实发生过的,作为小说,当然有敷衍成分,董苓湘的姓被改了,改姓童,童苓湘。董奶奶形象气质跟她的先生不同,她是按高知的模子刻的,随便在哪家高校里走,学生都会叫她教授。
因为命运弄人,他们的婚姻受到冲击。董奶奶远走武汉,在那里定居,抚养两个儿子。王霈先生出狱以后,辗转得知妻儿下落,然而很长时间里,他不敢贸然联系,他不知道他的出现,是否会搅乱妻儿平静的生活,他们是否接纳他。他度日如年,思念之情不降反升,越积越深厚。终于有一天,他修书一封,告知妻儿,他将溯江而上,于某年月日到达武汉,若相认,请届时出现在码头,若不相认,他脚不离船,原路返回故乡。
我听他叙说至此,不禁心旌摇荡,不能自持。我想起日本电影《幸福的黄手绢》,想象武汉码头的画面,船上,王霈先生已变身高仓健,他忐忑不安,不敢遥看人群,可又不能不看,但见树上、屋上,一方方幸福的黄手绢在风中摇曳……我简直感动得要流泪了。
结局是圆满的。尽管没有我想象中的浪漫,相见却如预料中的激动人心。他的妻子,儿子,孙儿孙女,全家人都来码头迎候。
老夫妇一年里大部分时间在武汉。夏天武汉热,他们相偕回老家歇夏。王霈先生光个膀子,穿个裤衩子,摇一把芭蕉扇,见到熟人就聊天(我怀疑他当“右派”,就坏在嘴上)。有时到点吃饭了,他聊兴未减,人家不能让他饿着,便邀他一道吃,他就不客气。夫妇俩非常节俭,这一行为一度让我认为老两口吝啬。后来他不止一次跟我唠,想把那笔9000元拿出来,建立基金,资助大学生。我没太当真。他舍得?
这事在我搬离县委大院前真办成了,之所以迟迟未办,是因他嫌钱少,要再攒点退休工资。当他攒到12000元时,举行了第一次资助活动,新华社为此发了新闻。他资助的学生,需第一志愿报考农学院。他领过一个孩子回来,请孩子吃饭,请我作陪。这位未来的农大学生青涩、腼腆,问一句,答一句。看得出,孩子有一点尴尬。最兴奋的是王霈,这个“话篓子”,嘴不停。
若干年后,因为基金利息大降,他请高邮中学一次性发给报考农业院校的几名学生。
在人们看来,王霈先生晚年是一个幸福的人,他曾经失去的,家庭、房子(部分)、钱,都有了,只一样,他钟爱的事业,失去了永不再回。“沉舟侧畔千帆过”,他不甘心没有留下一点痕迹。设立基金,为孩子,为农业,也为自己。只有这样,他才是真正幸福的。
人们啊,做让自己感到幸福的事情吧。
蔡包子
蔡仁源住在我们院子西南角,推开大门向右,第一扇门就是他家。
这里没人叫他名字,叫老蔡,叫蔡包子。他是县农业局水产技术员。机关干部;长得也不像包子,是个标准美男子,皮肤白皙,眼大嘴阔,口中牙齿排列整齐,笑起来亮闪闪的。叫他包子,只因为他姓蔡。一位帅哥,顶着个不雅的绰号,我猜与他率性宽厚的性格有关。这一绰号没有恶意,不敬是显而易见的,他却将它视为昵称。即使小孩这样叫,他也只是象征性瞪一眼,笑嗔:“小巨豆。”他老家苏州,“小巨豆”据说是苏州方言,意思跟“小鬼头”相近。
他是个快乐的人;直到今天,我没见过有谁比他更快乐。他表达快乐最常见、最直接的方式是唱歌,自娱自乐,自得其乐。在那个年代,在这座城市,敢于旁若无人高声歌唱的,似乎仅此一人。也只有他高声歌唱,人们才接受、容忍——不是欣赏,是接受,或容忍。
他在两处地方唱歌令人意想不到,印象深刻。从县委大院后门出来,沿鸡窝巷(熙和巷谐称,曾更名卫东街)向南150米,转向西100米,过了中市口就是菜场,他提个网兜一路唱去,唱进菜场,面对一个个菜摊子,时而唱歌,时而询价。正唱着,突然打住,夸张地惊呼:“这么贵,杀人哪!哈哈……”然后拾起没唱完的旋律继续唱下去。别的男人买菜都躲着人,他却生怕别人不知道。
他在浴室唱歌。浴室空旷的构造,使得声音能够产生奇妙的共鸣,不仅听着浑厚圆润,还有助打开嗓子唱出高音。他当然不会放弃唱高音的机会,一边搓澡,一边放声歌唱,歌声绕过肉林,撞向浴室的墙壁,发出奇妙的共鸣。我与他在浴池里不期而遇,忍不住恶作剧地想,他就是一条唱歌的鱼。
除了唱,他还吹口哨,这是他表达快乐的另一种方式。他会吹两种口哨,一种是传统技法,嘴部似嘬口,《桂河大桥》里英军士兵吹的那种;另一种没有明显嘴部动作,乐音从舌的后部发出,细长而富于变化。第一种我学会了,第二种怎么都不得要领,吹出的声音像给小孩儿把尿。
应该是童心未泯吧,他喜欢跟我们厮混。我们院子里,王霈先生之前住着银行行长,再往前是一位县领导。县领导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男的小承,女的小琳,跟我年龄相仿。老蔡用英语“先生”、“小姐”称呼兄妹俩:密斯特承、密斯琳;有时快活得不行,又改口叫密斯特老大、密斯老二。我那时刚进城,一身土气,两袖乡风,担心融不进去,没想到老蔡和兄妹俩都接纳我。老蔡给我起了个日本名:平四太郎。最见水准是后三个字,我排行老四,男孩儿。
有一天回家,没进门就听到院内喧闹的声音。他们看了印度电影《流浪者》,正在讨论外国人名儿,见到我,老蔡撇下小承、小琳,问:“拉兹爸爸的名字高邮话怎么说?”小琳向我摇手,我却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拉、贡、纳、特。”“纳”和“特”高邮方言是入声字,与外国人名强行嫁接,土气毕现,产生强烈的喜剧效果,几个人包括我忍不住大笑。作为回报,我要求老蔡用苏州话讲一遍,他忸怩半天,突然用家乡话怪叫:“拉—贡—纳—特!”话音未落,我不管是否滑稽可笑,张开大嘴哈哈大笑起来。
院里其他成年人常被他的快活劲儿弄得啼笑皆非,不明白他们口中的“蔡包子”喜从何来。我父亲说:“这么喜欢孩子,找个女人结婚,自己生嘛。”父亲这么说,我才意识到,老蔡老大的人,还是孤家寡人一个。问为什么,父亲撇撇嘴告诉我,他结过婚,妻子是他老乡;他完全没有长相英俊的人常见的自恋,很懒很邋遢,碗堆水池,袜子穿到置于地上不倒。他妻子来,从人到屋都要狠狠收拾一番,然后身心俱疲回苏州。后来人家不玩了,就离了。让人佩服的是,他的女人不要他,他竟笑得出来。不过那是人家的“前世”,“今生”除了比有家室的人更快乐外,没有不正常。
好像为了回应我父亲,他不久再婚,娶了三垛镇的一名女工,接下来就是按部就班生儿育女。跟县领导家一样,他得了一儿一女。他叫他们“心肝儿”、“宝贝儿”,叫声响亮,充盈万般父爱温情。那时人们把对子女的爱藏着掖着,从不公开表露;反过来认为老蔡“西化”,甜得发腻,太过溺爱孩子。
老蔡妻子在镇上上班,孩子跟着母亲好照顾,多数时候,他仍是一个人在屋檐下行走。他也邀请我们出门玩儿。有一次高邮师范放电影,他带小承和我去,一出院门就攥住我胳膊,让我跟在他后面;这样走路很别扭,我想挣脱,他不容商量紧握着。电影散场,我的胳膊再次被他攥住,一直到家。我猜他认为我是乡下孩子,街上有车(自行车),别不懂规矩被车撞上。反观小承,他则享受到充分的自由,大摇大摆,悠哉游哉。
小承的妈妈来自一座中等城市,下嫁高邮,她经常对人颐指气使。她在院门与老蔡家之间栽了一棵泡桐树,树生长迅速,没留神已在院墙上撑起一柄大伞,巨大的树根伸向老蔡家,将窗户下的墙面挤出一条裂缝。我到老蔡家玩,发现树根粗暴地拱翻了青砖,更放肆的是,树根上竟抽出一根枝条,放出宽大的叶子。屋内已没有一小块平整的地面,餐桌的桌腿只好拿东西垫上。一家人原本在兴高采烈地吃饭,看到我惊讶的神色,都一起沉默了。
我们所住是王霈先生家的老宅,民国建筑,很老了,阴沟壅塞,小承妈将污水倒在我家一侧,靠近我父亲卧室的门,时间久了,倒污水的地方凹进去,污物淤积在上面。父亲向小承妈表达不满,她装没听见;母亲进城探亲,见此情况,借来一把大扫帚,直接将污物扫到小承家餐厅前。小承妈傻眼了,梗着脖子吵几句,看着不是对手,只好闭嘴。
母亲探亲期间,小承妈一反常态,主动与我母亲搭话,还让小承、小琳送过一回西瓜。母亲走后的一天中午,小承妈猛地“炸”起来,声称家中被盗,请院内院外的人帮她破案。弄半天大伙儿才明白,她放在泡桐树下的脸盆不见了。这只脸盆我见过,应该已有砂眼,一般人家会用它栽点葱蒜,备炒菜时救急。小承妈坚称脸盆让人偷了,她跑到老蔡家,作势望了一眼,大声说:“蔡包子家我看过了,没有!我要看看是哪家偷的。”我问父亲:“她是要上咱们家搜吗?”父亲转身进屋,撂下一句:“想都别想。”重重地把门关上了。我很想知道戏怎样收场,拿眼睛的余光瞄着小承妈。很明显她乱了方寸,屋里屋外踏着碎步,手在胸前不停摆动,我不能确定是否发抖。这时,老蔡已吃过午饭,右手拿一把火钳,左手拎着煤炉到屋外,准备封炉门。小承妈急向他招手,把他让进屋,叽叽咕咕说着什么。老蔡突然高声嚷起来:“这不行,你开玩笑!”一边嚷一边往家走;小承妈跟在后面,陪着小心:“老蔡……你这样就不对了嘛。”“咣当”一声,老蔡把火钳扔地上。“我不对!你这样就对了?把我当什么人!”小承妈从没见过一个愤怒的蔡包子,敷衍几句,找个理由出门去了。
我直到今天也不知道,小承妈要求他什么,让他如此动怒,可以肯定,事情与我们家有关。这是我见过的他唯一一次发火,而且是针对一位炙手可热的人物。很快他们搬家了,以后在街上见着,仍然是一张热情洋溢的脸。两年前,他的一颗门牙掉了,他居然不补,任嘴上门洞大开。这样也好,喜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