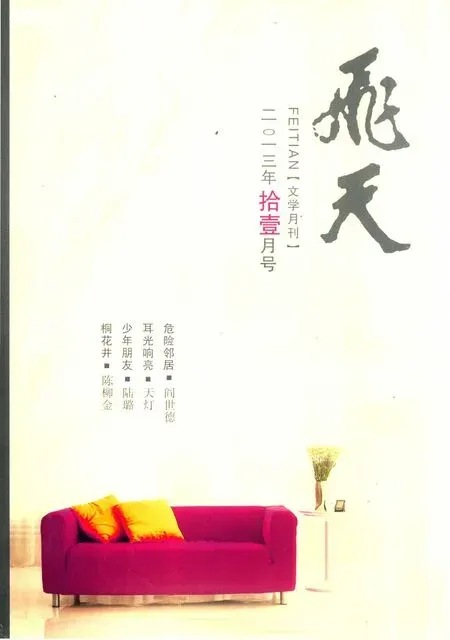桐花井
陈柳金
一
自从客家女张梓香嫁到颍川村后,村里就没平静过,每个女人和光棍都像一锅滚水,要把美得出类的张梓香烫熟。女人们是要下狠心地把她烫死,光棍们却是要把她烫成一张烙饼,晚上好睡在上面解馋。
光棍们只是在画饼充饥,能吃到饼的只有陈井生。鬼都没想到打了多年光棍的井生能娶到这么养眼的婆娘,真是火烧的喉咙里飘进了一滴甘露。张梓香帮井生止了渴,却无异于在那些光棍们的喉咙里加了一把火,他们每咽一口唾液都会剧痛。
光棍们咋都想不通,昨天井生还是他们队伍里的骨干,公鸡一打鸣就摇身变成了“脱光族”。想当初,井生跟着他们泪流满面地唱《光棍好苦》:我是个寂寞的光棍,痛苦的光棍,到了现在没有媳妇,昨天晚上加班过度,醒来以后想要呕吐……加班对于阴间挣钱阳间花的井生来说,是家常便饭。他爹没给他留下什么传家宝,倒传给了他挖井的苦力活。他爹是方圆百里都叫得响的挖井师傅,掘了一辈子井,也有了衣钵传人,本可以爬出井回到阳间吧嗒烟酒过几年舒坦日子。那一次却不知冒犯了土地神还是冲撞了太岁爷,快挖成的井发生塌方,把他埋在了井底,待众人七手八脚扒出来时,七窍都流了血,再还不成魂了。
井生一镐一镐地掘井时,倒恨起他爹来,为别人挖了一辈子井,造了一辈子福,以致自家的井拖了多年没挖成,一家喝水都得靠井生病恹恹的娘到凌江河里挑沙井水。这还不算,到头来把自己都埋进了井里去。其实井生爹当时谋划着等那口井挖成后,便回家挖自家的井,再给儿子讨个媳妇。而后便马放南山,让儿子去延续这造福百年的功德之业,自己过几天含饴弄孙的日子再说。
岂料一口井封住了他的一生,为自家挖井和给儿子讨媳妇的念想随着棺柩下沉到混沌的阴间。原来井生爹还在时说的亲事一夜之间告吹。姑娘眼亮着呐,嫁进这样一个连口井都没有的家庭,受苦的还不是自己?那句话咋说的,医生养的病婆娘,木匠住的烂塌房,阴阳家里鬼上墙。这句话像一张符贴在井生的后脑勺,他到哪家掘井,哪家的姑娘就躲着他。姑娘们认定他的命运也会重蹈他爹的覆辙,最终被埋进深不见底的井里。
井生就这样跟下了咒一样成了村里的光棍,光棍见光棍,相抱成牛粪。就是这些牛粪,却渴望鲜花能惊艳地插上来。他们在房间的墙上贴满了女明星照——林志玲、陈慧琳、张柏芝、阿娇、钟丽缇、李玟……他们的贴法也很特别,专拣墙的破洞贴,明星照一贴上去,破洞就不见了,还生出一张妖媚脸孔冲你放电。结果一数,井生房里贴的明星照最多,大概有三十张,而且贴的全是张柏芝。
光棍陈丙丁说,井生,每天晚上对着张柏芝打井,可别像你爹一样出不来啊!井生狠狠地啐了他一口。掰着指头一掐算,爹死了快五个年头,每年的清明他都没给爹上过坟,心里那个疙瘩还没解开啊。
病秧子娘每到清明便在他耳旁嘀咕,井生耳朵起了茧仍无动于衷。这一年清明娘把话说重了,没想到养了你这么个白眼狼,你爹生前累死累活还不是为了你?变成鬼了连香火都闻不到,哪天我死了干脆抛山上喂狼!井生是被他娘逼上山的,潦潦草草地祭拜了爹,没想到唤醒了爹的在天之灵。
据说,那一拜回来,屋旁的梧桐就开了花,雪白刺眼,像女人粉嫩的肌肤和晃亮的白乳房,激动得年近三十还睡冷被窝的井生直咽口水。也就过了两天吧,村前的凌江飘来一个媒人,泊船上了岸,在村口望了望,就朝开着梧桐花的井生家去了。
井生无缘无故有了媳妇,一晃眼毫无征兆地从光棍队伍里退役了,这让村里的光棍们一肚子的羡慕嫉妒恨。陈丙丁说,你这坨牛粪真的是插上鲜花了,这朵鲜花可真够倒霉的。你小子白天打井累死了,晚上那井我帮你打吧!井生又啐了他一口。
光棍们都说,井生媳妇长得还真有几分姿色,要脸蛋有脸蛋,要胸脯有胸脯,要腰围有腰围。啧啧,像谁来着?就像井生破墙上的张柏芝啊!在村里那些长舌妇的眼里,张梓香是井生爹的阴魂招来的,是带着妖气的一个狐仙。你看她那水蛇腰、锥子脸、柳叶眉,不是狐身是什么?
就连井生娘也感觉像做梦一样,昨天村里的姑娘还躲着她儿子,今天就走来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做她儿媳妇,地府里的老头子还真显了灵。
圆房时,井生感觉就像掘井,没想到跟女人掘井这么美妙,便拼了劲儿掘,以为已经挖了五米、八米、十米,滑入了软土层,钻裂了硬岩层,深探到蓄水层。张梓香脸若桃花,酥麻着说,再使劲,还没到底呢!井生嗷地一声,使出了千钧力气。张梓香娇喘着说,井生,再前进一点,快出水了!井生觉得跟女人打井真的是一门技术活,便把留着攀爬上井的最后一丝力气也用上了,两股水终于喷射而出,水浪裹卷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把井生吞没到了欲生欲死的井底……
是张梓香把他拉出井底的。睡了个囫囵觉,恍惚中看见爹脚不挨地走来,进了厨房,抓起长嘴的锡酒壶倒了一大碗娘酒,咕噜一下喝干了,醉醺醺地走出破院子,大声说,井生,你给我生出个带茶壶嘴的孙子来!
井生惦念着爹的话,这些天拼了命跟媳妇打井。
背上驮着一座山的井生娘感觉腰杆子直了很多,但哮喘还是没法平息,一阵急喘猛咳,正要拿那条两头挂着铁钩的扁担去凌江挑水,被张梓香抢了过去,说,娘,以后挑水这活归我管了,你老人家歇着去!井生娘说,这泥巴路不好走,脚要起泡的,你细皮嫩肉的受不了!张梓香说,娘,我进你家门不是来享福的!说着两个铁钩就勾了两只木桶,挑在肩上咿咿呀呀地去了。
喘着粗气的井生娘目送儿媳走上泥巴路,直到凌江边的沙井旁。沙井水抚平了她的皱纹,一夜间年轻了十岁。
但井生娘担心的是,村里好些光棍也到凌江边挑沙井水,会不会与儿媳生出意外来?沙滩上长出的那十几个大窟窿,像是凌江澈亮的眼睛,窥视一场有关颍川村的风月事。光棍们本来就有使不完的劲,张梓香一来,那劲儿更是发了酵,勺子一下一下地往桶里舀水,眼睛却盯着逶迤而来的张梓香,水溢出了还收不住手。等张梓香舀满水扁担上肩时,光棍们才躬着腰挑起水桶,看着张梓香小碎步走八字圈,圆屁股扭杨柳腰,摇曳出千万种风姿。陈丙丁一开始脚下生风,但发现走快了必定是要超过张梓香的,便蓄着劲,忽然把步子迈小了,肩上的桶便左右晃荡,成了随风摇摆的秋千架。陈丙丁多么渴望张梓香能坐在这秋千架上,与他一起荡出颍川村去。
张梓香纤纤细指拿捏着分寸,与不属于她的男人们保持着安全距离。等光棍们把水桶荡回家,只剩了两半桶水。而去凌江一里长的路上,洒着蜿蜿蜒蜒的水痕,活像一条条蠢蠢欲动的草花蛇。
待张梓香又一次把两桶水挑回家时,驼着背的井生娘看到水面上浮着几朵白桐花,说,阿香,这水是用来喝的,不是用来看的,不要把眼看花了!这话带着荆棘刺,张梓香神经生疼,说,娘,我把花撒在水上,就是要证明水的清白!
井生娘总是放不下心,等晚上井生回来时,在他耳边急喘着说,你爹没把井挖出来,这一次再不挖,恐怕留了人留不住心!井生站起身,走出门去,昏暗的灯光把身影拉得老长。眼睛在院子里四处打量,趁夜选择打井的吉位。就是那了,梧桐树下,大树底下好遮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二
第一个走出村去闯世界的是陈丙丁,听说到了遍地黄金的深圳,什么挣钱就干什么,就差没杀人放火抢银行了。这昔日在村里穷得丁当响的光棍,才两年便捞了一笔横财,身边缠着几个妖精一样妩媚的女人。
当陈丙丁清明节开着车回到颍川村时,村里的女人们看到车上走下一个比张梓香还漂亮的女人,惊呆得眼都直了,啧啧两声,大老板就是不一样,娶了个明星做老婆,张梓香给你老婆洗脚都还嫌孬!光棍们听到陈丙丁带回一个女明星,全赶到他家,羡慕得眼珠子都掉了出来,说,丙哥,你媳妇越看越像张柏芝,啥时结的婚,咋不请哥们喝酒?陈丙丁打着哈哈,哥哪里结婚了,是女朋友,有好几个呢!想不想出去跟丙哥干?你们明天去,明天就能交上女朋友!光棍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那女人走前去,跟一个个光棍拥抱,还啪嗒吻了一下他们的嘴角。光棍们像被电击了一样,赶紧回家收拾包袱去了。
陈丙丁带着女人进了井生的破院子。梧桐花开得正艳,像从天上飘来一朵白云,破院子就有了点白云人家的味道。都过了两年,井生家的井还没挖成,他正在几米深的井里掘土呢。陈丙丁半蹲在井口,朝井里扔下一根中华烟,说,兄弟,抽根烟,井咋还没打成?声音撞在井壁上,响起了回音。井生说,这两年村民们都抢着挖井,我一个人忙不过来!陈丙丁问,为啥?井生说,上游的李屋庄在挖磁铁矿,听说那洗矿水含强致癌物,全冲到凌江。大伙谁还敢去河里挑沙井水喝?都争着要我给他们挖,弄得我家的井到现在还没挖好……陈丙丁不知是赞扬还是讽刺,就你井生人好,好人呐,想不想跟我挖井?井生纳闷道,你家也要挖?陈丙丁笑了,跟我到深圳挖井!井生吧嗒着烟,烟雾从井底升腾而上,好一阵沉默。陈丙丁问,兄弟,你在村里挖一口井多少钱?井生说,一千!陈丙丁站了起来,提高嗓音说,兄弟,我给你双倍的价钱,还包吃包住!
光着膀子的井生从井里爬了出来,用力拍打泥土,忽然看见一个女人惊艳地站在梧桐树下,问,兄弟,她是……陈丙丁把嘴附在他耳边,女朋友,玩儿的!井生一本正经地说,可别糟蹋了人家闺女!陈丙丁大笑,兄弟,哪像你那么认真,现在的城里人都喜欢玩,怎么样,这个价钱成不?井生愣在那。其实他心里清楚,村里要挖的井差不多都挖完了,过些日子自己就将面临失业,再说陈丙丁给的工价很高了,一个顶俩,谁会跟钱过不去呢?可这一走……
这时,张梓香挑了满满一担沙井水进了院子。陈丙丁拉着女朋友走上前去,说,快叫嫂子!那女的搔首弄姿地站着,也不喊,就那样没心没肺地笑,笑得张梓香心里忿忿的,嘴里却说,怪好看的,我还以为是仙女下凡了呢!陈丙丁就说,哪有嫂子你漂亮呢,她是九尾狐,你是何仙姑!其实陈丙丁就是要用九尾狐的妖气来降服何仙姑的仙气,现在这世道,是妖精当道,仙人让路,谁也奈何不了!
陈丙丁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又说,嫂子,还挑沙井水喝啊?这句话蛰疼了井生和张梓香。张梓香说,我们是穷人家,哪像你大老板连水都是人家喂你喝!这句话含沙射影地刺到了陈丙丁的女朋友,她扭着腰肢走过来,阴阳怪气地说,喂水又咋的?我还喂他奶呢,成功男人是动口不动手的!张梓香眼也没抬,恨恨地把水挑进屋里去了。
井生对陈丙丁说,你别跟她一般见识。陈丙丁把话挑明了,你们商量好,去的话明天一早就坐我的车走,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说完挽着女朋友黏黏糊糊地出了院门。
烟快烧到手指了,井生猛吸了一口才扔掉。下到井底,举起铁镐狠劲掘土,恨不得今天就把井挖好。他用灰桶装满土,挽在吊钩上,张梓香在井口一拉绳子,桶就上去了。当桶随着绳子吊下来时,里面放着一碗红糖水,井生端在手里,喝了一口,怪甜哩,心里却五味杂陈。他终于开了口,阿香,我想跟陈丙丁出去闯!张梓香沉默了许久,说,外面有很多九尾狐,就怕你出去了像陈丙丁一样学坏!井生说,陈丙丁是啥人,他一人吃饱了全家不饿,我好歹还有你和娘哩!又沉默了一阵,张梓香说,留了你的人留不住你的心,但这井还没挖好,你一走我们还得喝沙井水,你就不怕我和娘犯癌症?井生心里不是滋味,把头压低了,说,陈丙丁说跟他打一口井,给我双倍的价钱,要走明天就坐他的车走!
猝然一只鸟怪叫着飞出树冠,桐花扑簌簌地飘落。井生仰起头,一朵花瓣落在脸上,香香的,有股子媳妇的体香味。
这一晚,井生与张梓香狠狠地打了一次井。结婚三年了,张梓香还没怀上他的骨肉。光棍们笑他老是给人家打井,把力气全填井里去了,跟媳妇打井便打歪了。他们瞎说呢,我井生白天打井是一条汉子,晚上打井是一头猛虎。但阿香的肚子就是不见隆起,他做梦都想着阿香的井里能飞出一条龙来,好慰藉爹的在天之灵,延续陈家几百年来的香火。
夫妻俩上半夜打了一次井,下半夜又打一次。跟媳妇打完这次井,也许要等一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打下一次了。井生把十八般武艺全用上,一会儿把阿香拉下井底,一会儿把她抛出井口冲上云端,颠得她魂不附体,飘飘欲仙。当张梓香又一次从云端落到地面的时候,公鸡打了四遍鸣。两人已经累得散了架,也不知井生是怎样从井底爬出来的。张梓香靠在他胸前,说,到了那花花世界,可别像陈丙丁一样迷了眼啊!井生呵她一口气,说,你老公又不是仙人,能呵一口气把别的女人变成九尾狐?我只爱我的何仙姑咧!
公鸡啼晓时下起了毛毛雨,全村房前屋后的梧桐都开了花,颍川村成了白云的故乡。
佝偻着腰的娘叫醒井生时,却不见了张梓香。井生急了,娘说,她到凌江挑沙井水去了,你快吃饭,陈丙丁一大早就来催了!井生胡乱扒了两碗蛋煮面,说,娘,我走后你要管好自己的身体,等你儿子在外面出息了,我接你和阿香去享福!娘说,你放心,阿香是你爹送来的何仙姑,她用桐花熬水治好了我的哮喘,娘现在吃嘛嘛香。到了那边,要多惦记你媳妇!
陈丙丁的车在门口亮起了一声响亮的牛叫,井生赶忙提了包袱冒雨走出院门,却还没见张梓香回来。陈丙丁从车窗伸出头,咋的,昨晚还没和阿香亲热够?井生挤进后座,已经有好几个光棍坐着了,他们腾出一个空位,说,光棍都跟着丙哥出去了,咋还担心你媳妇?怕她飞走就在她胸前拴上一根风筝线!井生没心情跟他们开玩笑,眼睛透过车玻璃东瞄西瞅,远远看到凌江的沙井边蹲着两只木桶,却不见张梓香。
陈丙丁瞄了一眼后视镜里的井生,带头唱起了那首《光棍好苦》:我是个寂寞的光棍,痛苦的光棍。到了现在没有媳妇,你怎么能这么的残忍!打我的手机,想让我以后没钱娶妻!你能不能打我的坐机,打我的坐机,或者直接来我家里……
车沿着凌江一路往下游开,光棍们唱得激情飞扬,井生心里却像堵着一把臭咸菜,完全不是以前的那种味儿。
景物一股脑在后视镜里倒去,村庄变得越来越小,只有千树万树的桐花白,成为井生眼里的一片云。而倏忽之间,这片云也将成为幻影。
忽然,坐在副驾驶座的九尾狐指着窗外,说,有人撑船!大伙扭头往路边的凌江看,一个白衣女子撑着木船顺流而下,箭一样逐浪飞驰。井生说,是阿香!陈丙丁加了油门,车开得飞快,他要赶在张梓香前面到达码头,把她截住,让井生当场审判一位出走的女人。
当车赶到凌江水库的码头时,张梓香却已等在那了。井生钻出车门,浑身湿透的张梓香噙着泪说,我来送你,这个平安符是天亮前缝的,你要戴在身上!井生接过平安符,眼泪再也忍不住,吧嗒吧嗒掉落。张梓香说,快上车吧,不要挂念我和娘!
车开上渡船,到了彼岸。从此,一条河隔成了天南水北……
三
没想到深圳这高楼林立的地方,半空中也飘着一朵朵桐花似的白云。只不过那白云不是长在树上,而是从高高的烟囱里飘出来。
陈丙丁的厂子就在这某一朵白云下。厂子不是很大,却挤着上百号人,在车间里开机器染色。井生没进去看过,听光棍们说我们身上衣服的颜色,都是染出来的。你想把布染成胭脂红,唰地就变成了胭脂红;你想染成观音绿,唰地就变成了观音绿;你想染成柠檬黄,唰地就变成了柠檬黄。还能印花呢,什么花都能印。井生心想,阿香最喜欢梧桐花了,等回家时,我一定要送她一件印着梧桐花的衣服。
井生便很想进车间去看看,但主管不让进。他就只能闷在宿舍里看窗外的白云。老家的白云都在天上,能看到蓝天和飞鸟。而深圳的白云却停在半空,严实地遮住了你的眼睛,像老人眼里的白内障,怎么看都是白兮兮的。看着看着,井生就睡着了,嘴角流出了哈喇子。
这一睡,就睡到了晚上。要不是光棍们吵醒他,也许他就错过了上班的时间。光棍们白天上班,晚上休息。而陈丙丁安排他白天休息,晚上上班。他的上班地点不在车间,而是在厂子后面的荒地里。
陈丙丁说,这井要掘大,比老家的井要大两倍,还要掘深,一直通到地下河!井生心里就长了痂,原来给我双倍的价钱,是要挖双倍大、双倍深的井,天上哪有掉馅饼的好事!井生吊着个苦瓜脸,但人已出来了,好马不吃回头草。陈丙丁说,井生,只要挖好了,不会让你吃亏的!
井生刚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陈丙丁还安排了光棍大柱给他打下手,当天晚上就开工了。大柱说,今后我们都是穿山甲,晚上打井,白天钻洞。你说丙哥为啥要打这口井?井生说,也许他喝不惯自来水,想喝老家一样甘甜的井水。大柱说,就这珠三角,能打出老家一样的井水?骗鬼吧?打这井肯定是另有所图!井生说,那你说他图啥?大柱搔破头皮也没想出答案,岔开了话题,这丙哥身边有好多女人呢,天天晚上打井,不把井打枯了才怪!井生不屑一顾地说,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刚才你说啥来着,穿山甲?对,他们每天吃穿山甲,打井特别厉害,再深的井也能打出来!大柱笑得嘎嘣脆。
一直挖到第二天凌晨,井生累得像一头病牛,眼皮早打架了,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眼睁睁地看着窗外一动不动的白云,思绪飘回了颍川村。他仿佛看到阿香正挑着桶到凌江边担水,两只木桶压弯了腰,像娘背上的那座山。井生心里一阵痉挛,给人打了上百口井,到头来自家却还要去挑沙井水喝,累坏的还不是媳妇?眼看快要挖成了,又被陈丙丁兜里的钱引到了这深圳,为他打这不明不白的井。他一万个埋怨自己,半倾着身狠狠扇了自己一记耳光,平安符从胸间蹦了出来,井生紧紧地攥在手里,像捧着阿香的心。
井在一米一米地掘进。大概一个月后,在井底掘土的井生接到张梓香的电话,井生,我身体不舒服,老是呕吐。井生一颗心跌到井底,以为媳妇整天喝沙井水,真像村民说的犯了癌症,便声音颤抖地说,那快去看医生啊!张梓香说,看了,医生说这病没法看!井生又是一惊,咋了,啥病?张梓香嘎嘎笑,真是毛驴子拉磨走不出圈,能有啥病?医生说我有了!井生一喜,真有了?今年我要当爹了!
当他兴奋地爬出井底时,太阳从东边的高楼群升了起来。这天,他舒舒服服地睡了个觉,还梦见了爹,爹满脸堆笑,什么也没说。井生就知道,爹高兴呢,明年清明,我要到爹的坟前烧高香放响炮!
睡到傍晚时,下了一场大雨,井生和大柱没法挖井,便跟村里的光棍们坐在宿舍里大眼瞪小眼。胜武就笑井生,出来一个月了,想不想跟你媳妇打井?见井生不搭理,又故意气他,你熬得住,张柏芝可守不住空房,你就不怕戴绿帽子?井生乜斜着眼剐他。胜武便转移了话题,丙哥的九尾狐可骚了,听说天天晚上跟丙哥打井。这话像一滴水掉进了热油锅里,气氛马上活跃了。胜武又说丙哥有好几个九尾狐呢,一晚三个,还不把地球打穿孔?光棍们笑得满地找牙。
胜武说,闲着也是闲着,我带大伙去个好地方!大伙打了伞跟在他后面,还在犹豫的井生被大柱一拉,也跟去了。穿过厂子旁边的一条窄巷,再拐个弯,就看到一间亮着暗红色灯光的小店,胜武说店里坐着的全是九尾狐。光棍们把滴着水的伞搁在门边,嘻嘻哈哈走了进去,坐在长椅子上的九尾狐像磁铁一样粘了上来。井生站在门口,一股浓重的脂粉味熏得他打了个喷嚏。正在进退两难的时候,路边的垃圾桶旁站着个头发蓬乱的疯老头,手在翻拣什么,嘴里却叽里哇啦,一会儿朝你咧嘴傻笑,一会儿又往地上乱吐唾沫花子。
井生杵在那,门里伸出一只玉藕似的手,一拉,就把他拉了进去。九尾狐百般娇媚地说,大哥,进来坐坐嘛,妹子替你解解闷!井生没进过这样的地方,说话颤巍巍的,我不闷,我有老婆的!九尾狐嘻嘻地笑,你有老婆?在哪呢?咋不把她带来?井生满脸涨红,在老家,我真有老婆的!九尾狐戳了一下他的脑门,傻不傻,远水救不了近渴,今晚妹子做你老婆!井生两腿吓软了。九尾狐脱下上衣,露出雪白的乳罩。井生转身就跑,却被九尾狐拉住了,想跑?给了钱再跑!忽一下两只铁钳似的手扼住了她的喉咙,憋得她脸上充血,井生仍死抓不放。九尾狐眼角流出了两滴泪,井生想起了张梓香送他时眼里的泪珠,手慢慢松了,一闪身跑了出去。
回到宿舍,雨停了,井生感觉坐在监狱里,压抑得喘不过气来。他下了楼,跑到厂子后面,一个人下了井。井里积了半米深的雨水,一镢头下去,浑浊的泥水溅了满身。他爬出井提来水桶,一桶一桶把水舀干了,重新举起镢头,火山爆发似地往出使劲。
一身泥水的井生从井底爬出来时,新一天的太阳又出来了。大柱惊讶道,昨晚咋不见你?大伙以为你被九尾狐吸了精血!胜武笑着说,井生是猛男,他在九尾狐身上打了井,又去厂子后面打井了,丙哥没看错人!
又过了一个月,井快要掘成了,井生高兴呐,一高兴就给张梓香打电话。三个多月了,小家伙在肚子里捣蛋呢,肯定是个小子!井生说,给他取啥名呢?张梓香想了想,说,就叫桐桐!
井生躺在床上,满脑子是活蹦乱跳的桐桐。这天吃了晚饭,陈丙丁来到井边,给井生和大柱甩了一根烟,说,活干得漂亮,你俩再挖一条沟,一直通到厂里的车间,我给你们每人再加五百元工钱!
终于把井打到了地下河,水哗哗作响。井生突发奇想,这河能通到凌江吧,我今晚泅水,明天早上就能回到村里!大柱就笑,想回家跟阿香打井了吧,说不定泅到半路遇上女水鬼,一张口把你吞了!井生啐了他一口。
两人又按陈丙丁的要求挖了一条沟,埋了大口径的水管接到车间。井生和大柱大致猜到了陈丙丁的企图。井生又扇了自己一记耳光,打了上百口井,都是造福,这次却帮着人家造孽!
果然,陈丙丁叫两人趁着半夜把污水偷排到井里。五颜六色的脏水发出恶臭,蟒蛇一样嘶叫着蹿出车间,溜过水管,跳到深井,四散着漫进了地下河。这些动作神不知鬼不觉,其实从一开始陈丙丁就策划得滴水不漏。他大老远把井生请来人工挖井,避开白天晚上作业,就是要掩人耳目。要是请工程队机械钻井,那动静可大了,弄不好捅出娄子,他本事再大也吃不了兜着走。偷排污水可是犯法的事儿,他顶风冒险,还不是狗日的排污费太贵了,挖个井排出去,一年能省十几万哩!
陈丙丁还叫井生用水泥浇筑了井盖,在上面铺泥植草,这个井就在荒草地上消失了。
接下来两人的活就轻松了,每天半夜偷排污水,但必须高度绝密。就保密这事陈丙丁专门找他俩谈了一个上午,两人意识到上了同一条贼船,提着脑袋挣工资。
一眨眼又过了半年多,春节就在眼皮底下。这天,井生又接到张梓香的电话。一接听,传来一声响亮的婴儿啼哭,井生激动得泪花儿打转,说,桐桐,快叫爹!张梓香躺在床上,微弱地说,昨天出生的,六斤三两。快过年了,你就不回来看看儿子?井生埋下头,狗日的陈丙丁不让回家过年,说厂里活紧,过年发两倍工资!张梓香泪水涌了出来,心里燃起一团火,但嘴里还是说,大过年买点好吃的……
年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过来了,依然是白天睡觉,半夜排水。又过了几个月,转眼到了清明时节,井生来深圳整整一年了。这天晚上,陈丙丁叫他俩打开井盖查看一下,好像近来排水有点慢。两人打着手电用力挪水泥盖,盖子移开了一个口,井生匍匐着趴在井口探头往里看,一股恶臭饿虎一样扑出来,井生手一软坠了下去。想不到,井生再也没爬出他亲手掘出的十几米深的井。他三十多岁的人生,就这样被染色厂的污水染成了黑色的噩梦。
张梓香接到电话时,陈丙丁和大柱已护送着井生的骨灰盒到了凌江水库的码头。张梓香哭嚎道,你们别再恶心井生了,我来码头接他回家!仅半个钟头,一条木船就驰到了码头,眼睛血红的张梓香抢过骨灰盒,说,井生,我们回家,娘和儿子在家等你呢!
撑船逆流而上,泪水打湿了骨灰盒。在颍川村白云朵朵的桐花香里,张梓香抱着井生回了家。她笑着对佝偻的娘说,娘,井生回来了,他说他好想睡在梧桐树下的那口井里,我们一打开门就能看见他!她又把骨灰盒抱到儿子面前,说,桐桐,爹回来了,让他好好看你一眼……
这口挖了几年没掘成的井,成了井生最后的栖息地。一个高高的坟包垒起时,张梓香长长地唤了一声——井生!树上的桐花扑簌簌地飘落,像千万只白蝴蝶,覆盖了一个挖井汉始终没有合上的双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