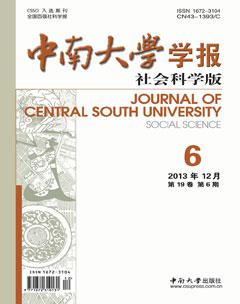论贾平凹90年代以来乡土小说中的家庭伦理叙事
摘要:家庭伦理叙事在贾平凹90年代以来的乡土小说中特别突出。他通过家意识的丢弃者、守护者、矛盾者的叙说,呈现出作家对乡土家园蕴意的多样性思考;通过离婚不离家的婚姻模式和传统女性美德的刻划,展现出在现代文明进程中重建乡村婚姻道德意识的努力;通过三代人父辈的生存正义、子辈的浮躁利益至上观、孙辈的我行我素主义,刻划了时代变迁进程中人的道德选择问题及代际间伦理观念的差异。
关键词:家意识;婚姻道德;代际伦理;女性美德
中图分类号:I24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6?0192?05
家庭伦理关系是乡土作家们书写的主线,作家往往通过其多样化的伦理叙事来折射出中国乡村社会发展背景中乡土意识形态下的伦理变迁。90年代以来,贾平凹以《土门》《高老庄》《秦腔》为代表的乡土小说对乡村家园意识、婚姻道德意识、代际伦理问题等家庭伦理问题的书写,展现出中国西部乡村社会近二十年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时代变迁进程中人们道德意识的转变,再一次证实贾平凹是一向坚持了认同自己认同的农民身份和坚持了平民立场写作立场的。
一、对家园意识现状的叙说
贾平凹在小说中充分展现出社会变迁中人对乡土中家意识的多样性阐释,即通过复调手法写不同人物的家意识。“复调的实质恰恰在于:不同声音在这里仍然保持各自的独立,作为独立的声音结合在一个统一体中……可以这么说,复调结构的艺术意志,在于把众多意志结合起来。”[1](50)家的意识复调表现为:一是从乡村走向城市者的冷漠;二是长期身居乡村者的热诚;三是生长在农村又不甘于乡村生活的年轻一代尴尬者的矛盾。从中展现出乡土社会变迁中人们家意识发生的变化,其中不乏表达出作家乡村家意识的困惑感。
(一) 家意识的丢弃者
贾平凹在其乡土小说中表现出城市知识分子家意识的迷茫和遗弃。贾平凹的乡土小说中突显的两类人物:一类是纯粹乡村农民,另一类是由乡村走向城市的知识分子,后者与乡村有着不紧密的关联性,他们完全脱离土地,在城市有立足之地,相对拥有名望,在思想观念中有倾城市情节,并稍带鄙视乡村。作家在其中勾勒出知识分子回乡后,对村人的冷漠与其所受村人的尊宠形成鲜明的呼应,他们以一种冷漠姿态、主动积极方式离家、离婚,最终遗弃乡村中家的意识。
从乡村走向城市的知识分子在进城以后,选择向上看的生活姿态建构自身;在回乡过程中,表现出以城市人姿态漠视乡村家园。《高老庄》中的子路与《秦腔》中的夏风对乡村社会中家意识持相似态度。一方面,他们有着相同的人生经历,从农村家庭凭借自己的文学才华走向城市,成为省城著名作家和教授,凭借着省城的名人身份博得世人的尊重和宠爱,受到村人的高接远迎。另一方面,夏风、子路以城市知识分子姿态俯视着乡村中的家,并没有因受村人的宠爱而回赠给热情,对乡村家族琐事持漠然态度,有意淡化乡村家的意识。子路在回乡后对家族琐事的得过且过,不愿意去派出所营救家族堂弟晨堂,看不惯晨堂的唯利是图;夏风对家族事表现的不积极态度,甚至抱怨白雪多管闲事。夏风、子路身处城市生活,已让他们变得冷漠,原有的家园意识已变得淡薄,厌恶乡村世俗,以一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清高,不愿融入乡村中的家,与村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感。
作品中又表现这类人倾慕城市、鄙视乡村的意识。
夏风很少回乡,新婚期间也以工作忙为由提前回城,甚至在妻子怀孕期间也难得回乡,面对白雪回城无望和丑陋又残疾的孩子,从而彻底告别乡村家园,弃妻儿不顾而长居城市。子路因为父亲办三周年的祭祀而回乡,但也因在村中呆不下去而提前回城,与菊娃离婚暗示他彻底摆脱了乡村中的家,进城后嫌弃菊娃的乡村生活陋习最终拜倒在现代女性的石榴裙下。子路离婚的原因一是忍受不了单位舆论;二是忍受不了菊娃的病态,从中发现他并没有因外遇而反省自己的行为,反而为自己找借口,没有极力地去挽回婚姻和挽救乡村中的家,他以知识分子姿态审视乡村人的各种陋俗,主动地抛弃乡村家园而永远地回归城市。
(二) 家意识的守护者
与此相对,贾平凹又在乡土小说中塑造了一些身居乡村的家园守望者形象,他(她)们对乡村、土地有着深厚的情感,传统习俗让他们对乡土家园充满着坚信和执着,面对现代化社会进程对农村的不断干扰,他们仍然保持着原有的生活姿态,平静地面对着浮躁的乡村现状,体现出作家的伦理叙事对乡村家园意识的多样化阐释。
《秦腔》中夏天智、白雪对秦腔的执着,其背后实质是对乡村家意识的挚爱。夏天义对土地的坚守,其实质是对乡村家意识的坚信。白雪为不离开乡村而失去婚姻。作家在作品中突出这场婚姻失败的必然性:白雪热爱秦腔,夏风讨厌秦腔;白雪作为秦腔演员,经常走乡串巷,家与事业已决定她无法隔舍与乡土的深情;夏风身居省城,清醒地认识到秦腔在现代社会中的衰亡趋势,所以他认为守护秦腔已是毫无意义。一个守护乡土家园,一个则放弃乡土家园,两者有着乡土意识的悖论。白雪的乡土家园意识让她坦然地面对婚姻的失败,在乡村平静而辛勤地生活着,充分说明她是一个守护乡村家园的成功者。夏天智作为乡村知识分子,始终认为无论时代怎样变迁,乡土意识中的家才是人的永恒根基和归宿,所以他筹买宅基地,希望儿子将来能落叶归根,牢守浓重的乡土文化精粹—秦腔,画马勺成为他的最爱,对白雪坚守秦腔的万分支持和尊敬,表明他是乡土家园的坚信者。夏天义容不得后辈荒废土地,整日劳作于田间,反对年轻干部浪费土地,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忠诚地守护着乡村人的最后生存之地。
《土门》中成义、梅梅、云林爷是乡村家园意识的挽救者。他们发挥最大能力守住仁厚村不被城市化所吞没,想法设法建药房、修村牌楼、拒绝建新式的公寓楼等来维护村庄的存在。云林爷无私地用医术支撑着仁厚村人的生存,成义这个充满侠情仁义的村长建构着乡村理想家园意象,“农村应该是农村的样子,比如:家家住平房,出门有院落,人不离地面,人能接地气……但不能有是非,不能偷盗,不能奸淫;孩子都上学,上学免费,家家孝敬老人”。为筹集钱款发展家园,他不惜牺牲生命。梅梅在母亲去世后成为了乡村无家者,但她很快与云林爷、成义叔成为新家人,不惜一切要守望最后的家园,反感眉子的爱慕城市行为,保持乡村人具有的质朴美,与村人共同坚守重建家园信念。
(三) 家意识的矛盾者
贾平凹1990年代以来的乡土小说中塑造了时代当下者面对乡村家意识的矛盾心态,从中也体现出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对乡村发展前景的思考。
《秦腔》中翠翠、光利不安于乡村生活,离乡走向他乡或城市。翠翠爱慕于清风街外来唱流行歌曲的陈星,暗示受当下生活新方式的主导,而不是家中的守旧推磨。光利也不满于父亲庆金提前退休让他顶班的乡村供销社工作,社会经济制度向市场化转变中已让这代人不再像父辈那样安于农耕守家的现状,光利远赴新疆打工,翠翠也跟随城里人而去。作家通过文本表现出这代人作为时代推动者所处的尴尬处境,对乡村家园意识充满着矛盾与困惑,想逃离乡村,但父辈还耕植于乡土,他们在城市中的身份与夏风、子路完全不同,没有固定职业和栖身之地,作为新生代的农民工,终将会回归乡村。作家对这代人的伦理关怀持模糊的书写姿态,暗示着贾平凹对当下乡村伦理发展走向的迷茫。
通过贾平凹前后期文学创作的比较,可以看到其价值观念的变化,1990年代之前的乡土家园意识观念相对于近年来转变较为显著。新时期的乡土小说《腊月·正月》《鸡窝洼的人家》《天狗》《小月前本》《浮躁》《商州》中对乡土意识中故乡有明确的坚信态度,通过乡村社会改革让家园变得美好。1990年代以后的乡土小说,贾平凹对乡村家园意识的态度已不那么确信,小说结尾对这种乡村家意识表现出一定的模糊性。《秦腔》中清风街连为夏天智抬棺材人的都找不到,暗示出年轻一代离家导致乡村未来建设者的缺失,乡村家园由谁来主载,令读者难以想像。《高老庄》中子路离开了高老庄,西夏留下来是否能为高老庄人守住乡土家园?作家并没有给读者一丝隐晦希望,把乡村的未来者石头刻画得神奇古怪,更隐含出建设乡村家园意识的无望。《土门》中仁厚村人已经失去了现实中的家园,成义的死亡,梅梅回归母亲的子宫神秘魔幻的结局,作家对乡村家园的未来拥有怎样的命运结局,在这三部乡土小说中都没有明确的阐述,进一步说明贾平凹在社会改革发展的当下时代中,是回归乡村伦理还是走向他处,作家无法解答。
二、对乡村婚姻道德意识变化的构写
(一) “离婚不离家的”婚姻模式叙写
贾平凹在乡土小说中建构异样的婚姻道德理念,重复建构乡村社会中“离婚不离家”的非婚姻生活模式,婚姻关系破裂后,都是女性留居乡间与公婆共同生活,男性多为不在场的状态,长期留居城市或重新组建家庭。女性多为公婆认可的好媳妇形象,男性多为婚姻的背叛者形象。
婚姻关系中爱情的缺席、亲情的弥补形成了离婚不离家模式。贾平凹在文本中有意打破以往两性关系书写手法,轻写夫妻间的亲密,重写婚姻关系中感情的不和谐,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男性在家庭生活中的不在场状态,突显出亲情的重要性。《秦腔》中写夏风婚前更多看重白雪的美貌,婚后抱怨妻子不顺从,由早期的争执发展为后期的吵闹,甚至于丢弃亲生残疾孩子的无情无义行为,充分说明这段婚姻没有建立在深厚的感情之上,缺乏爱情。作家在文中把疯子引生对白雪单恋式的感情写得如此深重,却把清风街人公认的男才女貌、门当户对的“完美婚姻”中的夫妻情感加以淡化,作家这种写作意图似乎在有意暗示这场婚姻失败的必然性。婚姻中爱情的缺失导致女性更多地把感情寄托于公婆关系上,因长期共同的家庭生活而建立起深厚的亲情,相互间无微不至地关怀,媳妇的明事理和孝顺赢得了公婆的尊敬和厚爱,最终公婆大义灭亲,离婚后不认儿子,却认媳妇为女儿,浓厚的亲情关系促成了离婚不离家的生活模式,从中不乏作家对女性传统美德的颂扬。
模糊的夫妻关系促成了离婚不离家模式。夫妻双方因生活观念和身份地位的差异而导致婚姻失和,但夫妻间的情感依然存在,女性因留恋旧情对复婚充满幻想致使离婚仍不离家。《高老庄》中子路与菊娃的婚姻关系与夏风和白雪的迥异,两人的感情深厚以至于离婚后仍挂念对方,本都对复婚抱有幻想,后又写子路再婚后对菊娃充满内疚感,从两人相见时的对白、行为中表现出两人的情未了。文本中写子路一次主动去菊娃店里,两人情不自禁地倾诉相互惦念之情,而且不由自主地发生了性关系,充分说明两人感情的厚重,菊娃也因此而迟迟未改嫁,双方的藕断丝连,甚至不顾及村人对妻妾身份的舆论,都表明菊娃与子路婚姻关系的模糊性,从中显示出作家对两性婚姻道德异化的建构。
贾平凹在文本中还展现出农村社会对男性背叛婚姻的不道德行为的默认。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思想观念的开放,不再对一些违背伦理道德的行为充满鄙视和否定,而是保持着默认甚至是羡慕的姿态。作家文本中展现婚姻中外遇的行为,打破人们对婚姻忠诚观的坚守,《高老庄》中子路在外遇中抛弃结发妻子,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受到村人鄙视,相反村人对他再娶高挑年轻娇小妻子十分羡慕,视菊娃与西夏为妻妾,夸耀子路的能耐大,充分表明时代发展进程中人们对婚姻从一而终意识的淡化,认为像子路这样有地位的省城教授不离婚,没有个大、小老婆是不正常现象,乡村社会无意中默认了背叛婚姻的不道德行为。《秦腔》中庆玉与黑娥在清风街明目张胆地偷情,逼迫发妻离婚并借家族势力强行霸占人妻本是极不道德的丑事,却在村中大摆婚宴邀请村人参加。父亲夏天义无法阻止儿子的丑恶行为,村人也并没有因此而大力指责和排斥庆玉,对此不道德行为采取默认姿态。贾平凹表现出现代农村社会人伦观念的退化,深刻指出现代婚姻观念中个人私欲的膨胀造成了夫妻伦理的遗失。
(二) 乡村真善美理念的建构
贾平凹在乡土小说中充分表现他对纯朴美的执迷与热衷,突出乡村女性的朴素美。《秦腔》中白雪是作家建构乡村女性的真善美化身,通过其外貌的静美、性格的温和、为人处事的融洽、对长辈的孝敬而突显出来。文本首句写引生喜欢白雪,因为白雪长得很美,所以引来很多清风街的爱慕者,夏风也是因为白雪在清风街长得美而娶她。白雪的朴素大方不同于夏家的其他媳妇,知书达理、勤劳善良、为人和蔼、不与人纷争,更不看重家中的钱财名利。结婚后在夏家起早扫院、洗衣挑水,对堂兄嫂的客气热情,主动为堂兄瞎瞎交税费和罚款,为伯父夏天义洗衣服,关心伯母的眼病从而在长辈和同辈中博得一致好评,正如堂嫂竹青对夏风所说:“世上的婚姻真是说不清,不是冤家不聚头,十全十美的就你和白雪。”男人羡慕夏风娶得白雪,女人欣赏她的温柔贤惠。作家以引生为代表的清风街男性视角去审美白雪,如同菩萨、天使一样纯美,其对白雪的痴迷体现了作家对乡村女性真善美理念的建构。
贾平凹用现代美来衬托传统美。以《高老庄》《土门》两部作品两组人物的对比来展现乡村女性的朴素美和现代城市女性的时尚。从人物内在的性格与外在的处事方式及村人的态度,表现出作家的比较手法,突显对乡村朴素的倾慕。作家书写乡村女性凸显质朴美:菊娃出场时总是衣着朴素,不爱打扮,与西夏初见,“女人中等个头,瓜子脸形,弯眉大眼”,从这一描述中更多突出菊娃的一种纯净美。梅梅也是一身乡村气息的着装,虽为年轻的待嫁姑娘,但从不化妆,不买名牌衣服,喜欢乡土风格,不为同龄人眉子追求现代流行服饰所打动,保持乡村人的朴实。她们待人处事的方式大方、宽容、善良。从子路抱怨菊娃舍不得花钱,突显其勤俭持家的风范;菊娃对前夫妻子西夏充满着宽容和关怀,突显性格温和,平易近人;在公公三周年的祭祀仪式中,热心的忠告让西夏减少不懂乡村风俗的尴尬,西夏受伤后又送来药膏和罕见的黄牛肉,让她品尝乡村野味,受到高老庄人的认可,对她是高看三分。梅梅在仁厚村眼里更是一个好姑娘,一心为村民谋利益支持乡村发展受到村人的好评。
与此相对的是现代女性受到村人的鄙视和唾弃,甚至是羞辱,她们虽然生长在农村,但以城市人姿态生活,无论是着装打扮还是行事方式都是现代风范,对乡村的感情比较淡薄,受现代金钱物质观的影响,以个人主义为中心,《土门》中的眉子自我迷恋式走向城市,主动式背弃乡村,满足于物质享受和傍大款,“喜欢豪华的套间住房,喜欢城里人的气质和做派”,其行为总是与仁厚村人背道而行,村人仇恨房地产开发商,而她却做起开发公司办公室的秘书,为成就早日变为城里人的梦想而告秘于开发商,极早地促使仁厚村走向消亡,成为村人公认的叛徒,引来村人的侮骂和排斥。《高老庄》中的苏红由乡村走入城市而发家,在乡村经济体制转变中,又回到乡村谋取财富,参与金钱和权力的勾结,掠夺高老庄人的资源和利益。所以村人当众羞辱她做小姐挣钱的不良行为,甚至借机欺侮她的得势求利,文本中突显出现代社会生活氛围中,人的道德意识的颓败。高老庄人对现代女性苏红的羞辱、眉子的鄙视,对本分的乡村女性梅梅、菊娃充分肯定,作家在表现女性质朴美超越现代女性时尚美的对比中,突出作家对传统女性道德的重建意识。
三、对乡村代际伦理冲突的刻划
现代乡村社会进入价值多元时代,不同代人之间因社会生活背景不同而导致价值判断、道德观念的差异,代际间因此产生代沟,这种代际冲突是现代社会发展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贾平凹在小说中,常展现出祖孙三代人异样的道德标准和不同的道德选择。年长的父辈是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继承者,遵从“父慈子孝、兄良弟敬、夫义妇听、长惠幼顺”的家庭伦理观,注重兄弟间的和睦友好和相互关怀。《秦腔》中老一代兄弟间的齐心协力,造就了夏家在清风街的气势,兄弟间是有求必应,从不拒绝,从中体现出兄良弟敬、兄友弟恭的和谐家庭道德观。但这种孝悌观念却在子辈中走向了终结,夏家最后一次团聚会的冷场,与以往的隆重形成鲜明对比,暗示着时代变迁中传统的家庭和谐观走向衰竭。
父辈的重亲型伦理观子辈身上发生了转变:一是兄弟间的失和,二是孝道的淡化。夏天义五个儿子(金玉满堂、瞎瞎)的兄弟间从未平静,为各自利益、金钱分配、赡养父母问题而生发的永无休止的争吵,妯娌之间闲言碎语、叔侄间打骂逞凶,这些充分说明时代转变中人们对悌孝意义的淡化。夏天义不愿吃轮流饭,儿子们拒绝交粮赡养父母,漠视父母疾病的治疗,父子争家产等等,暗示着子女孝道意识的淡薄。作家在此通过子辈孝道意识的淡化与金钱利益重化的对比,充分展现出乡村伦理的嬗变。
孙辈以自我为主导,按自我意愿行事。翠翠在又哭又闹中离家出走,冲破父母阻碍,与外来者陈星相恋,不被村人及父母认可的不正当的私情,在她看来却是自由恋爱。文本几次写她与陈星的情欲,表明翠翠这一代已转变柏拉图式的恋爱观,精神情感已满足不了对身体欲望的追求,代际伦理观念的差异致使翠翠在父辈与村人眼里是一个不正经的女子。光利也是勇于主宰自己命运的先锋者。他不满父母的安排冲出重重阻碍,远赴新疆寻找自己的人生之路,从中体现出当下者的务实观和利益观。体现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物化和金钱为主导的价值观逐步入侵乡村社会,并无形地改变着乡村人的交往方式、家庭伦理观念和道德准则。
贾平凹在乡土小说中,往往通过两种代际伦理的书写,展现出他对父辈的为人正直、行事为公等传统伦理美德的颂扬,对子辈的谋权力、顾私利、不务正业浮躁观的批判。
父辈的正义与子辈的浮躁形成鲜明对比。贾平凹在乡土小说中刻画中国乡村老一代农民形象,他们见证着社会制度变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由年轻的颠峰走向年老的没落,但做人的原则却从未动摇,为人守诚、正直、处事稳妥、为民求利等都是后人所不及的。《秦腔》中夏天义看不惯儿子庆玉对公家事的得过且过、瞎瞎的无所事事、侄儿君亭的张狂和随心所欲,他用七里沟修地行动来保护清风街人的利益,坚决反对村干部君亭不顾集体利益,责备儿子的假公济私行为,从夏天义的言行举止中都表现出父辈们做人的正直。作家还突出父辈们对乡邻的行善关怀,夏天义、夏天智一生坚持着“多做些好事”,是清风街公认的乐于助人者。夏天义得知秦安得了脑瘤病劝君亭主动消除与秦安的矛盾隔阂,并发动村民为其捐款;夏天智夫妇对秦安病重期间无微不至的关怀,经常给予物质方面的帮助和心灵上的安慰,体现出老一代人浓厚的人情美德。
相对于父辈的正义,子辈却表现得浮躁。君亭为谋得权力而不择手段,去派出所报案将打麻将的秦安当场抓获,顺利地夺取了村支书的权位,让内心细致的秦安因失位心情抑郁而患重病。与反对他的老支书夏天义作斗争,借捉奸事件让三踅放弃告状,从中见出君亭为人处事的圆滑与狡诈。庆玉的唯利是图、得过且过,如竹青所说,庆玉是家族众堂兄弟中最能惹是生非的“搅屎棍”,对待学校工作的三心二意,以自己利益为中心,抱怨夏天义对他的苛刻。瞎瞎整日不务正业,打麻将瞎混着日子,活的没有人样却偏爱惹是生非,经常与村人骂架打仗,赌博输钱无钱交纳税费等,都体现出现代人浮躁的生活观念。代际思想观念的差异显现出社会发展进程中人们不再以正直无私为荣,而是注重利益先行,甚至无情地嘲讽老一辈的正义行为。
四、结语
20世纪90年代以来,贾平凹在乡土小说中对乡土家园意识、婚姻道德、代际伦理差异等问题的探讨,展现出他的文学创作仍然以乡村生活为源头,并从乡村社会生活的积淀中发掘人的伦理道德美,关注家庭伦理嬗变中的现实问题。从中体现出贾平凹面对乡村伦理现状,有意筑建中国传统伦理美德理念,体现出知识分子责任感,并以文学创作承担着道德使命感。
Reconstruction of Moral Consciousness, Return to Local Homestead——On the Ethical Narration in Jia Pingwas Local Novels since the 1990s
LI Wei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Significant ethical narration had been showed in Jia Pingwas novels since the 1990s, by using the triple polyphonic artistic technique of home consciousness of the abandoned, the guardian and the contradiction. The writer presents his consideration of the diversity of local homestead implications. Through the fuzzy marriage pattern and the traditional womens virtue, he reveals the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marriage moral consciousness in the process of the reconstruction of modern civilization. By comparing three generations conception of justice, namely, parents survival justice, childrens the supremacy of impetuosity and benefits and grandchildrens persistence of their own ways, he shows peoples moral choice and differences of intergenerational ethics in the era changing process, which reflects Jia Pingwas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s an intellectual and his moral sense of mission in literary creation.
Key Words: homeland consciousness; marriage ethics; inter-generation ethics; female virtues
[编辑: 胡兴华]
收稿日期:2013?05?21;修回日期:2013?07?1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二十年乡村伦理变迁与乡土小说发展之研究”(11BZW116);山东大学博士研究生自主创新项目“论新世纪以来西部乡土小说中的伦理观”(yzc12045 )
作者简介:李伟(1983?),女,江苏连云港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