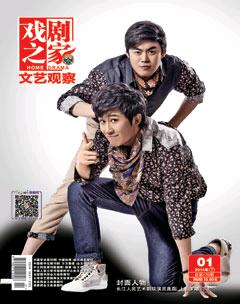皮影——浅论张艺谋电影《活着》平民化倾向中的民俗元素
孙潇雨
(河北传媒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71)
作为中国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张艺谋在电影界一直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的很多影片都改编自小说。因为有明显的情节,所以,像《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等根据文学名著改编的影片因为极强的故事性在国内外频频获奖。“他几乎每推出一部影片都能引起强烈的关注。其引发的话题从传统文化到当代现实,从民族精神到后现代语境,无不触动转型时期中国人敏感的神经。”1994年,张艺谋将《活着》搬上银幕,同年获戛纳电影节银熊奖,扮演男主角福贵的葛优也凭借本片成为第一位华人影帝。影片虽被禁映,但依然引起广泛的反响。
电影《活着》的最大特色在于它的平民化倾向。张艺谋是第五代导演的代表,在这部片子中他抛弃了第五代导演站在哲学的层面俯视生活的惯用手法,而是站在地上,以普通人的目光平视生活。因此,原著中那种轻盈与沉重并举,人生真实可触却又如大梦一场的感觉也一扫而空。“造势,不用造型,意念的方法去营造氛围,不搞民俗,不猎奇,实实在在地说一个中国家庭的辛酸往事,让观众喜欢地道的中国故事,喜欢中国普通人,喜欢中国人的情感表达方式,而不仅仅是喜欢电影中的那些神秘的的画面,那些离奇的民俗,那些色彩……让观众以惯常的眼光看中国电影,这种电影其实最难拍,最要功力。”在这部影片中,福贵一家在电影中的悲惨遭遇只是故事的表面,而影片的主旨却是演绎人与命运抗争却无能为力的境况,从而去再现张艺谋想表现的宿命论人生观。张艺谋并没有表现出对中国民俗本身的热衷,反而是用中国民俗去表达了他对人生在世上的命运关注。《活着》这样深刻的涵意没有张艺谋其他的任何一部电影可以比拟。
皮影,在张艺谋的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到类似的东西。例如《红高粱》中的颠轿子,《菊豆》中的栏棺,《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点灯、灭灯、封灯等。这些民俗使画面更具可视性,形成了张艺谋绚烂的创作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与它自身的客观情况是分不开的。张艺谋的影片大多在国际上放映,这类民俗无疑是一种文化符号,从某一方面说,它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使中国观众体会到一种前所未有的亲切感和历史责任感,同时也能让外国观众更多地了解中国,引起他们观看影片的兴趣。
皮影戏是戏,它是不真实的,有脚本,可以预测情节。皮影戏带给电影《活着》的涵意是多方面的。用戏来衬托福贵的一生是最好的。“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所以我们就不必把它当真,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这部电影,虽然充满了死亡,但我们感受到的气氛却不是那么的沉重。
皮影戏是偶戏,象征了人如玩偶这一比喻。皮影被操纵和电影中福贵的命运被操纵在相呼应,把命运在电影中完美。在影片中,张艺谋不断地呈现出“人和皮影一样”这一意象。为了生活,福贵抛妻弃子,成了皮影戏团的班主。他为生存风餐露宿劳碌奔波奔波的镜头和皮影戏交叉出现在荧幕上,我们甚至无法区分皮影戏和电影,还是张艺谋为了强化主题的。当解放了,社会制度发生了变化,但是福贵悲惨的命运仍然继续着。在超英赶美大炼钢铁的运动中,福贵的儿子有庆被车给撞死了。如果不是福贵非要把疲倦不堪的有庆送到学校,有庆本可躲过一劫。而肇事者不是别人,正是和福贵在战场上的一起同甘共苦的伙伴春生,在无法抗拒的命运面前,福贵本人俨然成为了被他玩于股掌的皮影。戏剧性的巧合又继续发生着。文革中,一直伴随福贵的那箱皮影未能逃过劫难,虽然被烧毁,但福贵的厄运却没有随着那些皮影灰飞烟灭。福贵的女儿凤霞产后大出血得不到及时的救治而命丧黄泉。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本来可以救福贵女儿凤霞命的王教授因为太饿吃了福贵为他买的七个馒头而噎得不能动弹,命运再次向我们展示了狰狞的力量。
在影片结尾时,福贵的外孙馒头(小说中的苦根)问福贵把父亲给他买的小鸡要放在哪里的时候,福贵把那个原来装皮影的木箱拿出来,和馒头一起把小鸡放进去,在这里的我们可以看出小鸡代表着希望,象征着未来。而曾经装皮影的木箱则表示囚禁和羁绊,象征命运。通过这一象征,告诉了我们,人类将继续受命运的控制,无法摆脱命运的摆布。
张艺谋所有的电影中,民俗元素是随处可见的,但每一处的作用都是非常特殊和个性的,不可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