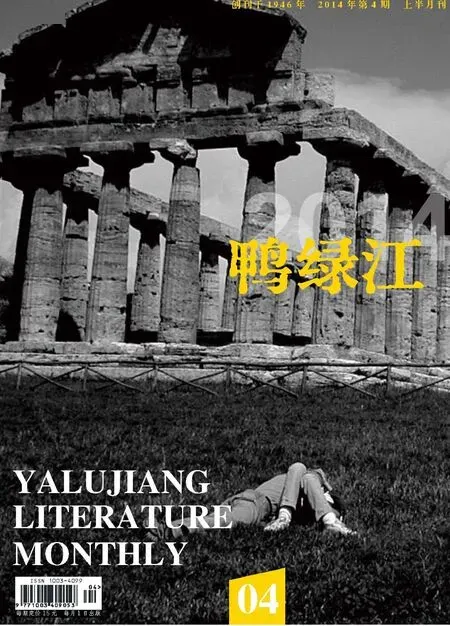悲悯中展现温暖,精致中蕴含深刻
——浅析安勇的小说
张 英
【理论·本省聚焦】
悲悯中展现温暖,精致中蕴含深刻——浅析安勇的小说
张 英
安勇是辽宁锦州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他近十年代表作品说主要包括《蚂蚁戏》《玩一个游戏》《老刘的厕所》《请大黄不要乱叫》《钥匙》《软肋》《诺洁斑马线》《青苔》《钟点房》《一九八五:性也》等。作为近年来逐渐崛起的新锐作家,安勇的作品虽然多是短篇,却具有浓厚的悲剧意味,但又让读者体悟到了一些温暖与幽默,留给读者心灵的震撼与共鸣是持续的、挥之不去的。
一
悲剧意识是人类的一种特有的精神现象,海德格尔曾用“深渊时代”和“世界之夜”来描述悲剧,他认为悲剧是人的精神沦落和毁灭的一种精神状况,是一种“世界的黑暗化”“精神的阉割、瓦解、荒废、奴役误解”。 [1]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它的媒介是经过‘装饰’的语言,以不同的形式分别被用于剧的不同部分,它的模仿方式是借助人们的行动,而不是叙述,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2]“悲剧”一词对读者来说,不仅在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而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并不陌生。在小说、电影、电视剧等艺术形式的表现中,悲剧比喜剧往往更能造成受众心灵的震撼,留给受众回味和共鸣的空间更多一些。正因为悲剧通常以人物悲惨的结局来结尾,所以揭示生活或命运的罪恶的力度更强,在受众心中激起的悲愤更久。安勇的小说就充满悲剧的意味。《蚂蚁戏》中的小赵老师从一出场就带给我和几个小伙伴心灵的震撼,小赵老师是那样美,那样优雅,像阳光温暖着孩子们的心灵和梦想。孩子们是那么喜欢她,以至于发现小赵老师和小常来往频繁时,孩子们顿生嫉妒之情。可是当小赵老师回城的梦想一点点破灭后,“小常走后,小赵老师的脸上再也看不到那两个圆圆的酒窝了,她的脸色非常苍白,和她死时的脸色一样。我固执地认为,从那时起,小赵老师实际上已经死了。”(《蚂蚁戏》)小赵老师的美在小常、二叔的玩弄践踏之后走向毁灭。小赵老师的后背被二婶用柳条抽打成一道道红印子,在二婶的打骂声中,小赵老师满脸泪水,一句话也没有说,没有任何反抗,她就像蚂蚁戏里被关起来的蚂蚁一样,深陷绝境,无处可逃,任凭怎么挣扎也无济于事。读安勇的《蚂蚁戏》不禁让人想起严歌苓的《天浴》,《蚂蚁戏》中的小赵老师和《天浴》中的女孩文秀都是那样美丽、善良,那样富有青春气息,她们都是知青,她们都梦想有一天能回城。然而对她们来说,回城终究是一场梦,而为了实现这一梦想,她们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她们一点点走入歧途,走向毁灭。

张 英,辽宁锦州人。渤海大学国际交流学院讲师,辽宁师范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从〈小团圆〉看张爱玲接受热潮》(《小说评论》2010.6)、《论明星选秀节目》(《新闻爱好者》2008.1)、《张爱玲小说“影视热”原因探寻》、(《电影文学》2007.12)、《中国当代军旅小说的受众接受研究》(《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2009.3)、《网络娱乐新闻图片编辑的问题与策略分析》(《编辑之友》2010.10)等多篇论文。
“悲剧用形而上的慰藉来解脱我们,不管情况如何变化,生命仍然都是坚不可摧的、充满欢乐的。”[3]在世界上,爱是永恒的主题,爱也是最具悲剧性格的。《软肋》中高傲而聪明的褚艳天一点一点被覃远志所俘获,成为覃远志的奴隶和玩物。她在知道覃远志已婚的事实后,一怒之下动了杀机,开始失去理智后的疯狂报复。“有三五秒钟的时间,褚艳天好像突然变成了一尊石像,保持着僵立的姿势一动不动。然后,她的喉咙里传出一阵野兽般刺耳的尖叫,在叫声里,她飞快地跳下炕,把挂在北墙上的一把砍刀握在手里,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对准覃远志的一只手砍了下去。”而疯狂之后,褚艳天仿佛看见自己成为自由自在畅游的鱼,她真的能解脱吗?
《一九八五:性也》中的我、智行东、薛德松、薛德松的老婆每个人都逃不出时代和个人的悲剧命运。《一九八五:性也》中的智行东,绰号“自行车”,同学和老师都这样叫他,他坦然地接受这样的称呼,反而觉得我叫他的真名奇怪。而当智行东经受一系列打击后,他不再允许任何人再叫他“自行车”,“自行车咔嚓一声就从班级里消失了,就像它出现时一样突然。后来我想,其实智行东是变得越来越接近我们了,但反而让我们越来越感觉陌生。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说不清道不明的。”智行东的话带有苍凉的意蕴,也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你看这些叶子,最初可能长在一棵树上,但风一吹,就各奔东西,指不定飞到哪儿去了。是不是就像我们,如今在一起,中考后就要天各一方?”《青苔》中的小顾,虽然智力不够健全,但是不能掩盖他自身的美和他对爱的渴望。这样一个善良的小顾在莫丽雅的谋害下淹死了,小顾不会再成为莫丽雅与老秦婚姻道路上的绊脚石,而当莫丽雅的心愿实现了,带给她的不是喜悦,而是不尽的悲哀。《钥匙》当中依然流露中很强的悲剧意识,“坐在床头的椅子上,看着面前躺着的那个人,她蓦然感到,人的生命原来是如此的奇怪,那些经过的漫长的岁月,不过是画出了一个圆弧,从终点回到起点时,人,又回复到了他呱呱坠地时的形态。”
《钟点房》里的主人公覃晓雅想为自己活一次,想出轨一次,可是出轨的对象綦连安和丈夫的反应都和自己想象的相距甚远。她感到无比失望。覃晓雅想把青春的时光再抓回来,可是青春早已在生活的打磨中远去。“她终于意识到,男欢女爱的故事已经离她很遥远,远得就像前胸和后背,左耳和右耳,纸牌的正面和反面,虽然近在咫尺,但却天涯相隔。她已经翻过来了,现在和兰姨一样都是反面,有的只是刻板的图案。她已经不再留意时间,那些时间散落成一颗颗沙粒,而她是一条被扔在沙上的鱼,挣扎是死,不挣扎同样是死。”通过人物形象的心理刻画,安勇将人物的悲剧命运展露得淋漓尽致。
二
文学创作是一种特殊的精神创造活动。不管时代如何变换,不管文学作品的评价标准如何改变,有一种标准恐怕不会因读者和时代的不同而不同。那就是文学作品总会在某一层面上带给读者精神的共鸣和慰藉,带给读者心灵的震撼和温暖。不管是哪种文学体裁——小说、诗歌、散文,也不管文学作品的篇幅长短,优秀的文学作品总能体现出这样一种特质。安勇的小说就是这样。虽然安勇的作品中人物都为悲剧命运所笼罩,但是读安勇的小说会带给读者一种莫名的感动和温暖。这种温暖来自于安勇对人生和世界的认识,来自于作品中人物形象。作为审美活动,文学创作的核心是尚“善”。 真、善、美即文学创造的价值追求。作为一种精神活动,文学创造的价值取向在不同的题材领域、不同时代的作品中各有自己独特的表现内容,然而人文关怀则是古往今来一切优秀文学作品的永恒主题,它是“善”的集中体现。安勇的《青苔》《诺洁斑马线》《钥匙》等小说中,人物的身上充满一种善良与温暖,体现着人性的美好。《青苔》中的傻子小顾用自己的方式去诠释他对爱的理解,《请大黄不要乱叫》中的父子之间隐晦的感情让人动容。《诺洁斑马线》中的人物佳惠和成发虽然是残疾,但他们都有一颗善良的心,当佳惠的女儿车祸去世后,“四马路小学放晚学的时间到了,佳惠拿起那面小旗穿过马路站在路边,抬头向马路的对面一看,成发正和她相对站着,手里拿的是自己干活时穿的红围裙。两个人隔着马路比一个手势,就无声地笑了。从这以后,每当中午和晚上放学时,佳惠和成发就会准时出现在路边,每人手里一面小旗护着学生们过马路。”他们的行动让每一个人肃然起敬。虽然生活当中有很多不幸,有很多悲剧,但是安勇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另一面,让读者看到了温暖和希望。“按常情,循常理。当我以这样一个定位重新打量身边的人和事时,我发现,原来可以写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诺洁斑马线》这篇小说,就是在这个思路下写出的一篇习作。”(安勇创作谈《平平常常的生活》)
《钥匙》中的女主人公对公公的猥琐龌龊的行为非常愤怒,但是却没有跟丈夫发泄的勇气,在如何解决的问题上不断挣扎。此时,公公的车祸让事件发生了转机,也让女主人公的心理态度发生了改变,当她面对躺在病床上双腿截肢的公公,她再也恨不起来了,“这些事做完后,她用力搬起那个人的身体,把那只弄脏的垫子撤了下来。在水房里洗净了垫子,她打来一盆热水,又给他擦了第二次。倒掉脏水,打了一盆干净的热水,她给那个人擦洗脸和手。她做得很慢,很细致,躲开扎在手上的针头,把每一寸皮肤都仔细擦净。她做这些事情时,那个人始终紧闭着眼睛,好像是睡着了,也好像是又一次陷入了昏迷之中。给那个人擦脸时,她发现他的眼角里涌出了两道泪水。她淡淡地笑了笑,轻轻把眼泪擦掉。但一转身,眼泪又涌了出来,她再次擦掉,还轻轻在那个人的脸上拍了拍。”这就是人性,此时的女主人公无比坦然放松,安勇刺痛了人性深处最脆弱的那根神经,也拨动了人心灵深处最温暖的那缕情怀。
《一九八五:性也》中人物的生活条件极其艰苦,正当少年的孩子们住校以后每顿饭都吃不饱,即使吃了,一会儿也就饿了。“我”向父母求救,当父母知道我的窘境后,火速送来吃的,这就是人间最温暖的亲情。作者用无比形象心酸的语言呈现给读者这样一个场景:“爹后来告诉我,妈边翻饼边哭,眼泪掉进锅里,不时发出滋的一声响。爹也急坏了,向二伯借了自行车,把饼给我送到了学校。爹到时,饼还热乎着呢!”

当代作家当中,余华的小说也不乏带有这种温暖幽默的东西。在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中,在物质匮乏、生活艰苦的日子里,在接连吃了几十天的稀粥之后,许三观用口述的方式给儿子们做红烧肉:“看在我过生日的份上,今天我就辛苦一下,我用嘴给你们每人炒一道菜,你们就用耳朵听着吃了,你们别用嘴,用嘴连个屁都吃不到,都把耳朵竖起来,我马上就要炒菜了。想吃什么,你们自己点。一个一个来,先从三乐开始。”“我就给三乐做一个红烧肉。肉,有肥有瘦,红烧肉的话,最好肥瘦各一半,而且还要带上肉皮,我先把肉切成一片一片的,有手指那么粗,半个手掌那么大,我给三乐切三片……”[4]面对着饥饿,《一九八五:性也》中我用顺口溜儿向亲人诉苦:“今有一事相求,不知如何开口。食堂吃得太差,饿得实在难受;肚子咕噜乱叫,浑身上下发抖。要想儿子活着,快送吃的来救。”半夜里,“黎大白唬突然惨叫一声,蝎子蜇了似的从炕上跳起来。同学们都被吵醒了,胡立伟拉亮电灯。原来,是黎大白唬另一侧的同学,在梦里啃猪蹄,把他的手拉过去咬了一口。大家笑一气,再躺下时,都加了小心,把手藏进被子里。”就这样,安勇笔下的人物用幽默化解困苦,他试图让读者看到悲剧背后的一抹亮色。
三
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仅有深刻的思想意蕴,还有完美的艺术表现,是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结合。安勇的小说篇幅相对短小而完整,精致而含蓄,却不失韵味。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比起来,长篇小说由于篇幅较长,章节较多,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故事情节的推动等方面,作者在创作的过程中是容易出现瑕疵的。作者不可能每一章都写得很精彩,是可以有张有弛的。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会忽略一些不出彩的细节。而中短篇小说则缺少这方面的“优势”。在有限的篇幅内设置完整的故事情节,刻画鲜明的人物形象,特别是性格丰满的圆型人物形象是很难的。这对从事中短篇小说创作的作家来说,无疑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和要求。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之父的鲁迅就是这样一位作家。我们知道,鲁迅一生没有进行长篇小说的创作,他的小说集《呐喊》《彷徨》中的作品,无论是表现农民题材的《阿Q正传》《故乡》,还是表现知识分子题材的《孔乙己》《伤逝》《在酒楼上》等,都是短篇小说,都是难以超越的文学精品。安勇也以创作微型小说和短篇小说见长。《蚂蚁戏》《玩一个游戏》等都是短篇小说。安勇作品的取材相对狭小,题材具有一贯的连续性,但是在温婉的书写中彰显犀利的笔锋。安勇笔下的人物,不是帝王将相,不是英雄人物,而是一些平凡的人物,特别是一些底层的人物。在题材人物的选取上,颇有鲁迅的遗风,蕴含“小中见大”的精神特质。《玩一个游戏》《老刘的厕所》《诺洁斑马线》等小说中的人物都是生活底层的人物。作者试图展示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当代作家余华曾指出:“我知道自己的作品正在变得平易近人,正在逐渐地被更多的读者所接受。不知道是时代在变化,还是人在变化,我现在更喜欢活生生的事实和活生生的情感,我认为文学的伟大之处就是在于它的同情和怜悯之心,并且将这样的情感彻底地表达出来。文学不是实验,应该是理解和探索,它在形式上探索不是为了形式自身的创新或者其他的标榜之词,而是为了真正地深入人心,将人的内心表达出来,而不是为了表达内分泌。”[5]在人物和题材的选择上,安勇在提到创作《诺洁斑马线》这篇小说时说:“我也终于明白,诺洁大染房这个店名起得恰如其分,因为在这繁华热闹的街边,他们用独特的方式守护着一个只属于他们的世界,拒绝了外界的纷扰和喧嚣,固守着他们内心的那份纯洁和宁静。而这份纯洁和宁静,不正是每个人都在渴求和期盼的情感吗?”(安勇创作谈《平平常常的生活》)
安勇笔下的这些人物之间的情感有的甚至很卑琐,难掩一种畸形的情感和心理的纠结。《玩一个游戏》中小慧和丈夫在平淡的生活中失去性爱的激情,在一个游戏中,他们将彼此想象成另外的人,在想象的刺激中两个人都扮演着他人,这种表演不断地痴迷入境,惟妙惟肖。直到有一天,当丈夫扮演的大王因为受贿被捕,妻子扮演的余小娥也抓起来了,他们才停止了游戏。《老刘的厕所》中老刘为了在只有二十平米的家里给日渐长大的女儿腾出一张床的地方,想尽各种办法。最后把厕所挪到了悬空的阳台上。老刘满意自己的杰作。而晚上,老刘拉着妻子玉兰在厕所里完成“天时地利人和”的事儿。《钥匙》当中的公公竟然钟情于自己的儿媳妇,《青苔》中的精明美丽的莫丽雅不由自主和傻子小顾发生了关系,《请大黄不要乱叫》里的父亲犯的错误是偷看别的女人上厕所。《钟点房》里覃晓雅的梦想是能有一次出轨的机会。这就是安勇独特的叙述视角和情感切入点,作者没有直接歌颂或揭露生活和人性,也没有主观去评价,而是在这种冷静的叙述和错位的爱恋中,滴滴带血地一一呈现。
四
安勇的小说语言通俗,带有浓厚的东北地域文化色彩。东北方言是东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北方言简洁、生动、形象,富有节奏感,特别能体现东北人豪放、直率、幽默的性格特点。“东北语言是最具有亲和力的语言,它从来都是直白和直通人心的,犹如一望无际的大草原,质朴而纯真,不矫揉造作,不留余地。它充满了张力和情趣,能神奇地把人和人之间的距离缩短,让你永远都感到不用设防的亲切和真诚。”[6]安勇原来在地质勘探队工作,这样的工作经历使得作家的足迹遍布边塞江南。多年的野外生活,使安勇获得了丰富的人生阅历。安勇小小说的叙述语言生动形象,世俗化的叙事,与生活贴近,亲切而自然。通过方言表现人物形象的作品,给人以全新的感觉。东北读者读起来会感到格外亲切,即使南方的读者基本也能看得懂,而且阅读新鲜感十足。《老刘的厕所》中这种东北方言运用得非常鲜明。如“在北方干五六年了,能想出把厕所挂在窗户外的还一直没遇着过,不用问,老刘是第一位。瓦工说,这可真应了那句话了,高空中拉屎——有一腚(定)水平啊!”这种歇后语的使用使得小说充满幽默色彩。再如,“女儿的小床和他们的大床就隔着一道布帘子,放个屁都得一点儿一点儿地往出抻,更别说和王玉兰有点儿啥举动了”、“老刘就不敢再叹气了,他平时挺听王玉兰的话,王玉兰虽然说话冲点儿,可对他特别好,一点毛病也挑不出来。”、“后来纸盒厂黄了,王玉兰虽说没工作,人家一直也没闲着”、“第二天早晨,老刘烧完开水,就借了老赵头儿家的倒骑驴,自己骑着上了建材市场。建材市场上随处都有拉脚的”“接了水管子顶天每月给老孟家一些水费也就行了。”在这里,“啥”“冲点儿”“黄了”、“拉脚”、“顶天”等词语都是北方常用的生活俗语和方言。《软肋》中这样的例子也有很多,大头对蝈蝈挤眼睛,说:“我看跟咱一斤倒挺合适的,要不我们哥儿几个帮你拉古拉古?”(“拉古拉古”是联系、撮合的意思)大头看雪下得很大,就急了,冲着老龙瞪眼睛,直着脖子吼:“干啥玩意,下这么大雪还能出去干活吗?”老龙照大头屁股来一脚,“小兔崽子,你冲老子嚷啥子,自己出门往山上看看。”《一九八五:性也》中:“饭不饱,就闹个水饱吧,总比饿着强。课上到一半就坏菜了,不知不觉尿来了。”(“坏菜”是糟了的意思)“拉古拉古”“坏菜”等词语的运用十分符合作品中人物的时代背景和身份角色,无形中增添了作品的真实感和形象性。

“读者对作品的接受绝非无条件的、被动的接收,像一架收录机那样,而是在阅读之前由其全部的生活经验和审美经验构成了对作品的一定的鉴赏趋向和心理定势,即期待视野。这种期待视野潜在地支配着他对作品的接受方式和程度。”[7]安勇的小说不仅语言通俗,运用大量的方言土语,而且他的小说带有浓厚的东北地域文化味道。用安勇的话说,这是一种“故乡的味道”。读者在阅读的过程当中会有极强的亲切感。安勇的《蚂蚁戏》写的都是童年的记忆,故事都发生在一个小村子里,作家给这个村子起名叫八间房。“这个名字起得有些随意,不太负责任,不太正规,光看这个地名,也不太像能生长出小说的地方。如果浏览比例尺足够大的地图,很快就会发现,在东北三省的版图上,叫八间房的地方一抓一大把,再一抓,又会有一大把。它们顶着同一个名字,星罗棋布在广袤的东北大地上,看似毫无个性,甚至难分彼此,但实际上,每个“八间房”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每个“八间房”也都会放飞属于自己的游子,而每一个游子的心中也都有一条永远无法斩断的根。”安勇的作品力求清新简练,他笔下的人物纯真质朴,感情随心而动,那种作品当中的很多细节勾起一代读者不尽的回忆,“那年冬天,知青们浩浩荡荡开进村子里时,我正胯下骑着一根木棍,驰骋在村中的土路上。我左边跑着的是于大华,右边跑着的是丁二光。我们用手响亮地拍着自己的屁股,嘴里喊着‘驾,驾’‘嗑达,嗑达’”、“骑驴的游戏很简单。一个人弯腰成九十度,撅着,另一个人从远处跑过来,双手按一下他的后背,从他的身体上掠过去。有点像现在体操比赛中的跳马。”(《蚂蚁戏》)字里行间,娓娓道来,让读者不由得跟随着他们一起回忆童年的生活、儿时的玩伴、家乡的土路、院子里的鸡鸭鹅狗、青春的梦想……
2004年,安勇开始进行文学创作,转眼已近十年。十年,安勇从放弃工作到正式写作。十年,从开始的激情写作到现在的沉下心来,感受生活。安勇的小说让我们看到了写作的重量与魅力。十年,安勇的创作从青涩走向成熟,奉献给读者一部又一部精彩的作品。十年,安勇具备了在文学的殿堂崛起并通向巅峰的实力。十年,辽宁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对安勇的创作给予充分的肯定。但这又将作为一个新的起点,我们期待安勇的下一个十年,也相信安勇的下一个十年更精彩。
注释:
[1]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
[2] 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63页。
[3] 尼采:《悲剧的诞生》,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版,93页。
[4] 余华:《余华作品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5页。
[5] 余华:《我的写作经历》,南海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149页。
[6] 才政、张淑丽:《试析东北语言的亲和力》,《新闻传播》2004年第5期,69页。
[7] 王卫平:《接受美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年3月第一版,第46页。
责任编辑 陈昌平
安勇作品年表
微型小说:
《仇恨》2005年1期《天池小小说》,入选2005年中国小说学会小小说·微型小说排行榜。
《光头》2006年21期《微型小说选刊》,入选2006年中国小说学会小小说·微型小说排行榜。
《分析题》2007年15期《微型小说选刊》,入选2007年中国小说学会小小说·微型小说排行榜。
微型小说集《一次失败的劫持》2008年4月由东方出版社出版。
短篇小说:
《蚂蚁戏》2004年9月下《小说选刊》“新浪链接”栏目,入选漓江出版社《2004中国年度短篇小说》《跳蚤女孩——好看短篇小说精选》。
《烟囱里的兄弟》2004年11月下《小说选刊》“新浪链接”栏目。
《老孟和大孟》2004年6期《短篇小说》杂志。
《王小水是最纯净的水》2004年12期《短篇小说》杂志。
《玩一个游戏》2005年1期《青春》,《小说精选》2005年3期转载。
《美丽的马粪》2005年12期《青春》。
《老白在世上的最后三天》2005年9期《都市小说》。
《红墨水》2005年6月下《青年文学》。
《大柳筐》2006年1期《佛山文艺》。
《老刘的厕所》2006年2期《福建文学》。
《较劲》2006年2期《芒种》。
《纸月亮》2006年8期《佛山文艺》。
《证据》2006年5期《雨花》。
《拯救韩雪》2006年6期《星火》。
论古诗地名使用的同一性和差异性——以唐诗中的“清湘”与“清淮”为中心……………………………………李德辉(128)
《马勇敢的午后》2006年7期《短篇小说》。
《雪白的馒头》2007年5期《雨花》。
《蟑螂》2007年8期《当代小说》。
《抢劫犯胡海山》2007年4期《佛山文艺》。
《衣柜里的男人》2007年6期《佛山文艺》。
《咱们的烟囱》《有凤来仪》2007年2期《芳草》。
《诅咒》2008年2期《文学界》。
《油锤灌顶》2008年5期《青春》。
《地震》2008年6期《佛山文艺》。
《袁有福之死》2008年7期《黄河文学》。
《殊途同归》2008年11期《啄木鸟》。
《大白菜多少钱一斤?》2008年9月下《山花》。
《请飞儿带走那条小路》2009年1期《佛山文艺》。
《这孩子》2009年9期《青春》。
《钥匙》2010年2期《文学界》。
《单房差》2010年2期《佛山文艺》。
《枕头》2010年4期《青春》。
《胜男的土地》2010年6期《黄河文学》。
《诺洁斑马线》2011年3期《天涯》。
《软肋》2011年6期《山花》。
《重返亚特兰蒂斯》2012年4期《青春》。
《走眼》2012年5期《雨花》。
《青苔》2012年5期《山花》,《小说选刊》2012年6期转载,入选漓江出版社《2012中国年度短篇小说》获得辽宁文学奖短篇小说奖。
《做伴儿》2012年5期《黄河文学》,《小说月报》2012年8期转载,获得首届《黄河文学》双年奖二等奖。
《野猫》2012年8期《文学界》。
《草狸獭》2012年12期《海燕》。
《钟点房》2013年10期《山花》。《文学教育》2013年11期转载,配发评论。
《仙人掌》2013年10月《青春》。
《雅格达》2014年1期《福建文学》。
《603寝室失窃事件》2014年2期《文学港》。
中篇小说:
《孽障》2008年8期《芳草小说月刊》。
《永远的幸福》2009年7期《厦门文学》。
《杀死杨伟大》2010年5期《芳草小说月刊》。
《一九八五:性也》2013年4期《山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