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場變賭場
王五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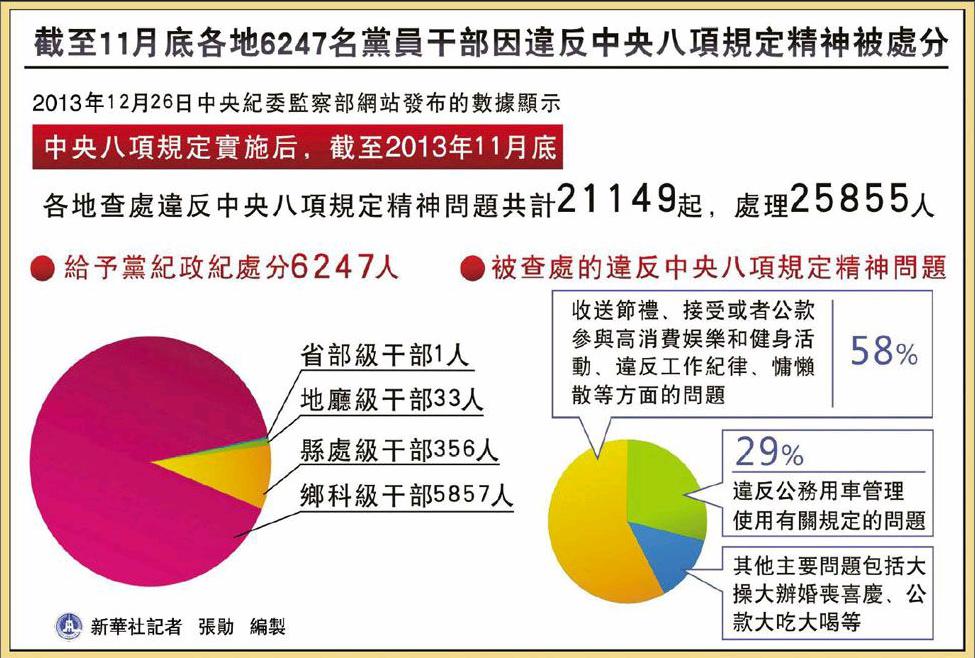

(接上期)
古之決鬥者,雙方面面相對,一槍打不准敵人便要小心被敵人打死。而籠外這些閑極無聊的網路遊民和南方某報一類心術不正的新聞流氓,對著籠子射擊,完全不必有這個擔心,如同趴在戰壕裡的狙擊手,面對眼前開闊地上的一群活靶子,打了這個打那個,一槍打不中打第二槍。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喜歡上了這種零風險的戰鬥,加入了這種比野戰遊戲有趣得多的娛樂。
如此一來,籠子裡邊,閃展騰挪,武功盡廢,人人自危。當官成了賭博,官場成了賭場。“微笑門”,“名表門”,“貴煙門”“豔照門”“背趟門”“婚宴門”……“門”出不窮,“門”你沒商量,誰也不知道自己哪天會被“門”著。籠外甫“門”,籠內即查,內外響應,立竿見影,一抓一準。
按當今中國官場上的倫理慣例,一個人一旦被立了案、調了查,就算是進了司法火葬場、死人一個了。大膽揭發的、落井下石的、敬請倒楣者把屎盆子全頂過去的,一齊來。更可怕者,罪案即立,查者與被查者,自然成敵——查出的問題越多,查者的臉上就越有光、說明立案的決策越正確。於是,祖宗三代,七姑八姨,挖地三尺,查者的動機已不是為國除奸,更不是還人清白,而是為自己找回臉面。如此機理,雖焦裕祿再世難逃法網。為政治收屍而設計的“一萬起”的量刑標準,其司法破壞力,被這“賭博式反腐法”進一步增強了。
反腐之道,因官府的階級背景不同、政治哲學不同、歷史時代不同、主政者的性格特徵不同等等,而花樣多彩。有西漢郅都“血流十餘里”之酷,亦有蔣家王朝官官相護之腐;有五十年前的人人過關,亦有三十年來的政治火葬。而當今“擊鼓傳花”式的“隨機反腐”、誰碰上誰倒楣的“賭博反腐”,空前未有,應屬制度創新。回想三十多年前,同一個領袖集團,先是宣佈“從今再也不搞群眾運動”,再是公開號召政府機關經商乃至軍隊經商,然後又由一些半官半商半匪半諜的“學者”出面鼓吹腐敗是“改革開放的潤滑劑”。上下輿論,齊心打倒了反腐敗的極左傳統。在朝的革命幹部一併放了心,在野的江湖人士紛紛紅了眼,齊齊往官場鑽,當官成了最科學的投資門徑。如此官場,勢成染缸,好人進去,淈泥揚波,同流合污,貪也得貪,不貪也得貪,否則便不得入群,無地自存。而彼之官祿水平,明顯地是建立在“貪污假定”的基礎上,貪污假定反過來又給了官員們強烈的鼓勵貪污的暗示。如此三十多年下來,一個無官不貪的官僚機器打造得鑿鑿實實,一個空前絕後的壞人統治好人的社會形態,構建得完完美美。
如今,三十多年過去,那位“打造者”“構建者”,仍然以“總設計師”的神號供在神壇上,而他締造的這個官僚機器卻要開始反腐了,而且是用這種奇特的“賭博式反腐法”,這就應了孟子的那句話,“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官雖非民,然而千萬之眾,再加上其背後的老婆孩子,足可以同理譏之了。
貪官也是人,要打要殺,也應講個公平合理,講個“不患疏而患不平,不患密而患不公”。公平與效率兩個概念,就反腐而言,非相對待乃相統屬之關係也;有公平反腐,才有有效反腐。似此賭博式反腐,同罪不同命、同罪不同罰、同罪不同辱;撞上槍口倒楣,撞不上慶倖;撞上者,雖至廉難逃一辱,撞不上者,雖巨貪逍遙法外;做官的學問只在於躲避槍口,而不是廉潔自重——如此反腐,拿著一些倒楣鬼送人情、平民憤、邀民心,是有點效的,而絕無實效於廉政建設也!
世人老說“無官不貪”,細究來,世上其實原沒有“無官不貪”這回事兒的。沒有這回事兒,為什麼有這個詞兒呢?是因為有人用了錯誤的邏輯方法來定義貪污,從而人工製造了一個“無官不貪”的概念。貪污,當然有衡量標準。為貪污定標準,有兩個方法,一是理論的方法,一是實踐的方法。理論的方法,也可以稱為形而上學的方法:人為地訂一個紙標準,下一個紙定義,規定如何算貪污。實踐的方法,也可稱為辯證的方法:貪污與廉潔,依生活實踐中的具體情勢,比較而定。老子說, “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較,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接著老子的句型說下去,還可以續出好多,如:窮富相對,貪廉相較,等等。這種四六句所表述的,就是共產主義哲學體系中響噹噹的“辯證法”,響噹噹的“實踐主義”。在一個矛盾統一體中,不能離開了其中的一個去孤立地認識另一個,也不能在客觀事物之外設一個抽象標準來為一個矛盾統一體的其中一個下定義。實踐不但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也是檢驗貪廉的標準。一個人是貪官還是廉官,不由理論來檢驗,不由主觀標準來檢驗,不由書本來檢驗,不由紙來檢驗,而由實踐來檢驗。
實踐如何檢驗?貪廉相較。
貪,是實踐意義上的貪,是比較意義上的貪,是相對意義上的貪,是辯證意義上的貪,而不是“一萬一年”的那個書本意義上的貪、形而上學的貪;廉,也是實踐意義上的廉,比較意義上的廉,相對意義上的廉,辯證意義上的廉,而不是“一塵不染”意義上的廉,焦裕錄意義上的廉。明白了這個辯證邏輯,就可以說,世界上並沒有一個官僚機器是無官不貪的,也沒有一個官僚機器是無官不廉的,貪與廉永遠是“實踐相較”或“辯證相較”的。一個貪污25萬的官員,在一個官僚體系中可能應該吃槍子兒,在另一個官僚體系中則可能應該戴紅花兒。“無官不貪”是一個反實踐主義的概念,是一個反辯證法的概念,是一個形而上學的概念,是一個錯誤的概念。
辯證法,不但在理論上指導著如何給貪廉下定義,而且也應是反貪實踐的指導哲學。在一個由紙的標準製造出的“無官不貪”的概念下,主張老虎蒼蠅一起打,就等於是在辯證邏輯概念下的貪官廉官一起打;而“只拍蒼蠅不打老虎”,根本就不是在反貪,而是在反廉。因為,按照“貪”“廉”的辯證定義,“蒼蠅”不是貪官,而是廉官。離開了實踐,離開了辯證邏輯,拿著一本書來反貪,拿著人造條文來反貪,一定是百戰百敗。
司法火葬場發明之前,中共在反腐上曾有過另外一個發明,其內容可一言以蔽之,“九五之術”(團結百分之九十五)。此方法在操作上有一個難點:操作者要有本事玩“人人過關”。道理很簡單,只有 “人人過關”的篩子才能辨出,誰屬百分之九十五,誰屬百分之五。只有把27億與25萬放在同一個篩子上篩,才能分辨出二者誰該吃槍子兒,誰該戴紅花兒;才不會出現“該吃槍子兒的榮華富貴,該戴紅花兒的鋃鐺下獄”這樣的陰陽倒錯。
這“人人過關”四個字,可謂字字珠璣,偉大無比。把這四個字掰成兩半來看:前一半,“人人”,講的是公平;後一半,“過關”,講的是慈悲。與此一公平慈悲相配套的,還有“竹筒倒豆子”“洗澡下樓”“卸包袱” “交待從嚴,處理從寬”等一系列回味無窮、閃耀著人性光輝的歷史字眼兒。只有“人人”,才有公平排隊;只有“人人”,才有貪廉相較;只有“人人”,才能把“百分之九十五”離析出來,幫他們“洗澡下樓”;只有“人人”,才能把老虎篩出來、梳出來、排出來、孤立出來,才能穩准狠地打擊這百分之五。
人人過關,文眼在“過關”。一次運動,問題交待清楚,“洗澡下樓”,組織結論既定,再無新犯者,即往不咎,輕裝上陣。公平而慈悲!而反觀當今,被“老虎”綁架著的“蒼蠅”們,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哪裡有澡盆?哪裡有樓梯?哪裡有關口?沒有,哪裡也沒有!你的命運、你老婆孩子的命運,只與籠子外面那些悠閒的射手有關係。哪一天哪一彈射到你、“門”到你,你就等著吧,受著吧,熬著吧。也許你走運到底,至死也沒有被射著,被門著,那是你的造化。你想金盆洗手?你想痛改前非?你想退休轉行?可以,但“業報”一直背在你身上,沒人給你解脫的機會。刑法上的追溯期是二十年,如果你在堅持了十九年的時候被流彈射中、“門”中,這十九年的戒行就白費了。
“老虎”們身上都披著厚厚的政治鎧甲,而且是躲在籠子的核心,有“蒼蠅”們為其擋著槍子兒,除非他們自己內哄,籠子外的槍彈是打不著他們的。本來,最怕“人人過關”的是老虎,而蒼蠅們卻不知好歹地跟著老虎起哄,把“人人過關”的極左路線批得臭不可聞——蒼蠅們原以為,打倒了“人人過關”,就變成了只是老虎過關,與自己小蒼蠅無涉了,從此就可以免受七、八年一次的“洗澡”“下樓”之苦了。他們哪裡想到,打倒了陽光下的“人人過關”,迎來的是“賭場”中的“人人自危”。破除現代迷信,不搞群眾運動,實行法制反腐——這是老虎的革命,蒼蠅的惡夢。如今,落得個求“洗澡”而不得其水,欲“下樓”而不得其梯,想“過關”而不得其門。豈“鬱悶”兩字了得!
1905年,中國的新潮知識份子忽悠著西太后取消了科舉考試,當時就有人指出,朝庭這是把授官權交出去了。沒有了授官權的紫禁城,七年關門。百年後的今天,紫禁城旁邊的中南海,通過這“賭博式反腐法”,把罷官權交出去了——籠內的反腐司法系統,成了為籠外的賭博盤口補辦手續的橡皮圖章。如此,中南海……?不好說。(完)
(作者系澳門理工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