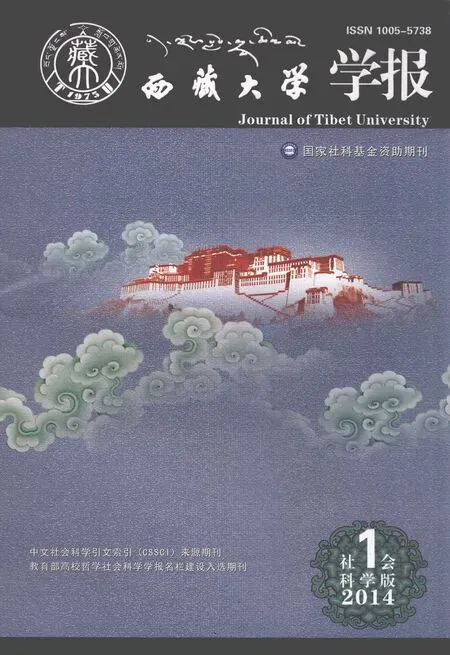道光《拉萨厅志·杂记》的有关问题及作伪证据
赵心愚
(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 四川成都 610064)
道光《拉萨厅志·杂记》的有关问题及作伪证据
赵心愚
(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 四川成都 610064)
李梦皋所撰道光《拉萨厅志》是清代西藏唯一的一部厅志,《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等已著录。文章对民族文化宫抄本、中央民大抄本及几种版本进行比较,分析了道光《拉萨厅志·杂记》内容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指出通过对《杂记》内容及资源来源的分析,可发现其作伪证据,证明其应为后人伪作。
道光《拉萨厅志》;西藏地方志;方志研究;作伪证据
道光《拉萨厅志》(以下称《拉萨厅志》),李梦皋撰,其自序署年为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中国地方志综录》与《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皆著录。[1]作为清代西藏地方志中的唯一一部厅志,此志不仅受到方志史研究者的重视,也引起了中国藏学史研究者的关注。[2]笔者以前翻阅方志目录,对《拉萨厅志》这部非通志性的西藏地方志有着过眼难忘的印象,因为清代西藏方志中府县厅志极少,此为唯一的一部厅志;同时,又产生了疑惑,因为有关史志中并没有清道光年间拉萨设厅的记载,既未设厅,何来厅志?此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后读吴丰培先生所写跋:“西藏府县之志,昔未之闻,有则自《拉萨厅志》始。李梦皋官藏地久,……庶当时拉萨概略,粗见于斯,并足证清代对于西藏地区,久以内地之府县视之,在建置未曾完备之时,概用厅州之制,以待渐行改革,惟未设行省耳”。[3]此跋读后,感到吴先生所言应是,于是不再疑惑,在教学中谈清代西藏方志时都要提及此志,以其为清代西藏亦有府县厅志的铁证。近日细读《拉萨厅志·杂记》,并抽时间到民族文化宫图书馆和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古籍部查阅此志原抄本中的相关内容,发现《拉萨厅志·杂记》存在一些值得注意并应指出的问题,而且从所采资料中,发现了其作伪的证据。笔者撰此文,意在抛砖引玉,希望有关研究者对《拉萨厅志》给予更多关注。
一、《拉萨厅志·杂记》的有关问题
所谓有关问题,是指抄本和不同版本的《拉萨厅志·杂记》内容中存在的一些值得注意并应指出的问题。《拉萨厅志》本无稿本,初仅有抄本流传,1959年中国书店、民族文化宫出现据吴丰培先生所藏抄本的油印本,近二十年来,才陆续被收入多种方志集成、汇编,得以正式出版。[4]比较现可看到的抄本及各种版本,可以看到署名李梦皋所撰的《拉萨厅志》均分上下两卷,全志体例为平目体,除疆域图外,共十二目或十一目,《杂记》为其卷下第三目,也即全志的最后一目。[5]但是,具体比较《拉萨厅志》的原抄本及各种版本,可发现《杂记》一目内容中存在一些值得注意并应指出的问题,在对其内容及资料来源作进一步分析之前,需要先对这些问题作必要讨论。
首先是内容的完整性问题。民族文化宫图书馆及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古籍部所藏《拉萨厅志》原抄本(以下简称“民族文化宫抄本”、“中央民大抄本”)《杂记》从“《汉书》记载图伯特人”开始,到“连其屯界之贼,尽皆剿灭矣”结束。《西藏地方志资料集成》(第一集)所收《拉萨厅志》(以下简称“藏学本”)中的《杂记》目,也从“《汉书》记载图伯特人”开始,到“连其屯界之贼,尽皆剿灭矣”结束。[6]《中国地方志集成——西藏府县志辑》所收《拉萨厅志》(以下简称“巴蜀本”)和《中国西藏及其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所收《拉萨厅志》(以下简称“学苑本”)之《杂记》虽然也是从“《汉书》记载图伯特人”开始,但到“二十二年,高宗大准噶尔征讨”就结束了。此处的“二十二年”,为乾隆二十二年,“高宗”即乾隆皇帝。比较之后可以发现,“巴蜀本”与“学苑本”的《杂记》内容不全,缺了最后的数条记载,根据“民族文化宫抄本”及“中央民大抄本”原文,应补:“四十五年,高宗七旬,万寿节,当第六世班禅喇嘛罗卜藏巴丹伊什来朝祝贺。五十五年,廓尔喀部巴勒部,称其三部。五十六年,达赖、班禅两喇嘛飞章急告卫巴忠,高宗,奉命嘉勇公福安康命将军超勇公海兰察参赞,屯练士兵,调进讨之。五十七年,索伦兵三千名,金川各司兵五千,皆集西藏。大清兵三千,裸麦七万石,牛羊二万余,众采买一年粮食,供足,内地运输。连其屯界之贼,尽皆剿灭矣。”以上这一大段文字“巴蜀本”与“学苑本”为何缺载,原因不明,但《拉萨厅志》之《杂记》目完整内容本应有这一大段文字,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其次,内容中两条资料的先后顺序问题。“民族文化宫抄本”与“中央民大抄本”中,“《后汉书·西羌传》:爰剑后子孙支分凡百五十种,其九种支分河首以西,蜀汉徼北,五十二种衰少自立能,其八十九种为钟最强盛”这一条资料,位置在“盖西羌属百余稠族”语之后及“《晋书·西戎传》据土谷浑鲜卑种族……”条之前。“藏学本”中,“《晋书·西戎传》据土谷浑鲜卑种族……”这条资料不是在《后汉书·西羌传》这条资料之后,而是在之前了,换言之,也就是这两条资料位置前后发生了变化。“巴蜀本”及“学苑本”中,这两条资料的前后位置与“藏学本”相同。为何“藏学本”、“巴蜀本”及“学苑本”中这两条资料的位置与“民族文化宫抄本”、“中央民大抄本”不同,原因不明。从内容叙述顺序以及言及吐谷浑来看,《后汉书·西羌传》这条资料应列《杂记》第三条,在《晋书·西戎传》条之前,而《晋书·西戎传》资料本应是在《后汉书·西羌传》资料之后。“民族文化宫抄本”、“中央民大抄本”应是。
再次,内容中的用字及脱字、改字、删字、衍字问题。这种情况较多,仅举几例。“民族文化宫抄本”、“中央民大抄本”《杂记》首条资料有“舜三苗三危窜,喀木即等地”语。“藏学本”此语为:“舜三苗三危窜,喀木印等地方。”“巴蜀本”、“学苑本”与“藏学本”此语同。此语中的不同用字在“即”与“印”。从其意来看,“即”可解,而“印”则不可解。因此,“民族文化宫抄本”、“中央民大抄本”应是,改作“印”误。又,《杂记》中有《晋书·西戎传》一条资料,其中一语“民族文化宫抄本”、“中央民大抄本”均为“据土谷浑鲜卑种族西零以西”。“藏学本”为“据土谷浑鲜卑种族西塞以西。”“巴蜀本”、“学苑本”与“藏学本”相同。此语中不同用字在“零”与“塞”。这条资料的确抄录自《晋书·西戎传》,此传中本为“西零”,可能为“先零”之误,也可能为一地名。因此,“民族文化宫抄本”及“中央民大抄本”是正确的。同条资料,在“西零以西”后为“甘松界,有白兰,极数千里亘,土谷浑以氏……”语。“民族文化宫抄本”、“中央民大抄本”中作“数千里亘,土谷浑以氏……”;“藏学本”作“数千里亘土,土谷浑以氏……”。“巴蜀本”与“民族文化宫抄本”,“中央民大抄本”同;“学苑本”中,“亘”作“互”,“亘”字此处当意“远”,“藏学本”中前一“土”字明显为衍字,“学苑本”改作“互”则误。在叙述到元代时,《杂记》中有“元帝金银财宝赐与限是于西番释教国”语。“民族文化宫抄本”与“中央民大抄本”作“赐与限是于西番释教国”,“藏学本”作“赐无限是西释教国”,“巴蜀本”、“学苑本”作“赐与限是西释教国”。此语中,“赐与”可解,“赐无”或“赐无限”皆不可解,应以“民族文化宫抄本”、“中央民大抄本”为是。此语文字明显有错乱,本意当为限于在西番地区赐金银财宝,“藏学本”与“巴蜀本”、“学苑本”均脱重要的“番”字。此处“西番”,即指“西藏”,若无“番”字,读之则不知所指。《杂记》中还有一字需要特别指出。叙述到清时,其第一条资料“民族文化宫抄本”、“中央民大抄本”为:“清朝崇德二年,喀尔喀总称三汗。五世活佛。”“藏学本”为:“清崇德二年,喀尔喀总称三汗。五世活佛。”“巴蜀本”、“学苑本”亦作:“清崇德二年,喀尔喀总称三汗。五世活佛。”比较几者所记,“民族文化宫抄本”、“中央民大抄本”多一“朝”字,称“清朝崇德二年”,后几种版本则均少一“朝”字,称“清崇德二年”。在李梦皋撰此志时,也就是在清道光年间,按当时的写法与习惯,不可能称“清朝”,初疑“朝”字为衍字。但是,如果此志真正撰成时间并不在道光年间,甚至不在清代,“朝”字就应为撰者无意识留下的可反映撰稿时间的痕迹。所以,原抄本中的“朝”字还不能简单视为衍字。后几种版本均无“朝”字,也很可能为编者所删,因为编者亦可能认为此字为衍字,所以删去。鉴于这种情况,对于此字不能简单处理,需要结合《杂记》内容的分析再作判定。《杂记》内容存在的以上三类问题之中,最后一类较多。很明显,内容中的这些问题有必要先比较抄本及各版本的情况,并分析讨论,这样更有利于其内容及资料来源的进一步分析。
二、《拉萨厅志》内容及资料来源分析中发现的作伪证据
细读几遍后可发现,《拉萨厅志·杂记》若干条只是资料的堆砌,全篇内容缺乏逻辑联系,资料采择随意性显得较大。更需要指出的是,其内容文字存在不少错乱,句子也多不完整,不连贯,也不通顺,又由于文字删改太多或减去一些内容,不少资料显得非常零碎,所记多只是一鳞半爪,远未说清问题,对人与事都缺乏完整记载,读之费力也费解。以下根据“民族文化宫抄本”及“中央民大抄本”,择其重点对其内容及资料来源作一分析。
“《汉书》记载,图伯特人古代三苗种族,舜三苗三危窜,喀木即等地方。又汉士,古代曰西徹,称西戎或西羌。周平王东迁前七百年后西羌种族。”这段文字为《杂记》内容之首。读《杂记》此段文字,读者会感到问题很多,除句子不完整又有错字等外,重要的是《汉书》中不可能有“图伯特人”和“图伯特人古代三苗种族”的记载。不过,分析这段问题颇多的文字,可知其内容是在谈西藏、藏族的源流及族源。清代西藏地方志中,最早较为系统地探讨西藏源流的是马揭、盛绳祖所著的《卫藏图识》,其《识略》上卷开篇即为《西藏源流考》。[7]将其《西藏源流考》内容与《杂记》此段文字比较,可发现后者实际上抄自前者,但不是照抄,而是做了一些删改与添加,前已谈及的“《汉书》记载”即为抄者所加。其《西藏源流考》原文为:“西藏唐古忒即图伯特国,部落繁多。明统称乌斯藏,然溯其源,盖古三苗种也。舜徙三苗于三危,三危者,为喀木,为危,为藏。”在此之后,《卫藏图识》撰者还作有一注:“敬见康熙六十年上谕”。注之后又为:“平王东迁后,羌逼诸夏,杂居陇山伊洛之间。”《西藏源流考》这段内容,首先明确西藏即“图伯特”,又明确称“盖古三苗种也”。《杂记》显然抄于此,但在前加上“《汉书》记载”,反出现了问题。三危即喀木、危(可又译作卫)、藏的说法,是康熙在《地理水源文》中,也就是注中所言康熙上谕中提出的。《杂记》此段文字中的“喀木即等地方”,本意当为“喀木等即三危地方”,但文字改成此状,读之颇难解。在《杂记》首段内容中,尽管其作者还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了一些话,但总体上仍可看出基本上是抄自《卫藏图识》之《西藏源流考》。值得一提的是,《西藏源流考》原文中本作“舜徙三苗于三危”,《杂记》改作“舜三苗三危窜”,意为“舜窜三苗于三危”。《西藏源流考》此语显然依据的是《后汉书·西羌传》:“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和《史记·五帝本纪》中“迁三苗于三危”的记载。《杂记》将“徙”改作“窜”,很可能摘抄时还参考了《尚书·舜典》“窜三苗于三危”的说法。这说明,《杂记》的作者在作《杂记》时,除《卫藏图识》外,还参考了《尚书》及《史记》、《后汉书》等。
“秦始皇筑长城,前二百十四年,曰西羌。汉武帝西羌塞上居,种族番衍。晋怀帝时至亦亭羌姚弋仲子姚长,苻秦灭其迹,再传刘裕宋为灭。盖西羌属百余稠族。”此段文字在首段之后,句子也多不完整,问题也多。这段文字仍是继续谈西藏的源流。比较《卫藏图识》之《西藏源流考》,可以看出《杂记》这段文字仍基本抄自其内容,只是又作了一些加工。其《西藏源流考》原文为:“秦始皇筑长城,汉武帝令居塞上,拒之,曰西羌。晋怀帝时,有赤亭羌姚弋仲者,子苌,灭苻秦称帝,袭号于长安,再传为刘裕所灭。盖西羌属凡百余种。”比较之后还可发现,《杂记》摘抄《西藏源流考》资料时,将“赤”抄作“亦”,将“苌”抄作“长”,“种”也写成“稠”。这段内容中提到的“赤亭羌”姚弋仲,为烧当后裔,晋怀帝时率部落东迁。姚苌为姚弋仲第二十四子,多权略,公元384年(一说386年)建立政权,称帝,即后秦,但苻坚虽被其缢杀,至姚苌死时前秦仍未亡。需要指出的是,后秦灭于公元417年,即后秦永和二年,晋安帝义熙十三年,此时刘裕还未称帝建南朝宋。这段历史《卫藏图识》作者在《西藏源流考》的叙述中虽也有不准确之处,但基本是正确的,《杂记》摘抄时则多加以删改及颠倒,反出现不少问题,特别是前秦与姚苌后秦,谁灭谁?改后反不清楚了。在刘裕之后加一“宋”字,也与史实不合,至少读之易产生歧义。
“《后汉书·西羌传》:爰剑后,子孙支分凡百五十种,其九种支分河首以西,蜀汉徼北;五十二种衰少,自立能;其八十九种中,为钟最强盛。”这段文字为《杂记》的第三段内容,前已谈及。这条资料首先明确其出处为《后汉书·西羌传》,这种情况在《杂记》中较少。《后汉书·西羌传》原文为:“自爰剑后,子孙支分,凡百五十种,其九种在赐支河首以西,及在蜀汉徼北;……其五十二种衰少,不能自立,……其八十九种,唯钟最强,胜兵十余万……”。二者比较,《杂记》此条资料基本上为照录,改动较少,读起来文字也显通畅,仅有“不能自立”改作“自立能”,令人难解。
“《晋书·西戎传》:据土谷浑,鲜卑种族,西零以西,甘松界,有白兰,极数千里亘。土谷浑以氏,其牙营在青海西十五里。”此为《杂记》第四段内容,前也曾谈及。与前条资料相同,这条资料也明确记其出处。《晋书·西戎传》在明确记吐谷浑为鲜卑人后又记:“吐谷浑……其后子孙据有西零以西,甘松之界,极乎白兰数千里,然有城郭而不居,随逐水草……”。比较之后可发现,《杂记》此条资料虽部分引《晋书·西戎传》原文,但改动较大,又加了一些另外的资料和作者自己的理解。如果说,前面引《后汉书·西羌传》那条资料与三苗——西羌——西藏、图伯特的源流溯源有关的话,《杂记》作者采择《晋书·西戎传》中吐谷浑这条资料时并没有提及吐谷浑与图伯特也就是与西藏有何关系。分析其原因,是因为《卫藏图识》作者在《西藏源流考》中,在写诸羌之后又写吐蕃建国之前已灭吐谷浑(土浑),“尽有其地”。《杂记》删去《西藏源流考》中这一段话及有关吐蕃的全部内容,但又摘录了《晋书·西戎传》关于吐谷浑这条资料,于是出现了吐谷浑与图伯特也就是西藏有何关系未加说明的问题。由此还可以认为,《杂记》作者在作《杂记》时查阅《后汉书》、《尚书》、《史记》等典籍,并引其资料或采其说法,实际上也是看了《卫藏图识》之《西藏源流考》后才采取的行动。
在第四段之后,《杂记》引数条资料记元明时期西藏大事及人物,涉及八思巴、元世祖、明太祖、哈力麻及宗喀巴等。经比对,这数条资料仍多抄自《卫藏图识》之《西藏源流考》,当然也有不少加工改动,需要强调的是,有的内容甚至还参考了成书时间更晚的书。如:《杂记》中“明太祖洪武六年,乱惩之制御思,惟其俗佛教”一语,《卫藏图识》之《西藏源流考》原文为:“洪武初,太祖惩唐世吐蕃之乱,思制御之,惟因其俗,尚用僧徒,化导为善。”比较后可看出,《杂记》作者除了明确时间为“洪武六年”外,将文字改得面目全非,无法阅读。简单对比之后,一般可能认为《杂记》此条记载应采自《卫藏图识》之《西藏源流考》,但再作比较,就可发现《杂记》作者显然还参考了光绪年间成书并刊行的《西藏图考》[8]。《西藏图考》卷二亦为《西藏源流考》,其著者黄沛翘在此文前,还专门谈及《卫藏图识》的《西藏源流考》,可以认为,黄沛翘写此篇受了马揭、盛绳祖原作的一定影响。《西藏图考》之《西藏源流考》中,抄录了不少《卫藏图识》之《西藏源流考》的材料,前已言及的《卫藏图识》之《西藏源流考》那条资料亦全采用,应注意的是其后还有“故洪武六年以摄帝师纳木嘉勒藏博(即喃加巴藏卜)为炽盛佛宝国师……”一语。《卫藏图识》中那条资料只称“洪武初”,《杂记》作者明确时间为“洪武六年”,显然是参考了《西藏图考》有关内容。当然,仅此肯定还不能断定《杂记》作者参考了《西藏图考》,但之后的多条资料,可进一步证明。
《杂记》最后从乾隆三年起有数条资料,分析其内容及资料来源,很能说明以上问题。“乾隆三年,准噶尔地噶尔丹策楞復。”“十五年,是先颇罗鼐死,其子朱尔墨特封袭郡王。”“二十二年,高宗大准噶尔征讨。”“四十五年,高宗七旬,万寿节,当第六世班禅喇嘛罗卜藏巴丹伊什来朝祝贺。”“五十五年,廓尔喀部巴勒部,称其三部。”以上这五条材料,均明显参考了《西藏图考》之《西藏源流考》,当然文字作了一些改动,也有添加、删除,其时间顺序也基本按《西藏图考》,只是中间加了“四十五年”一条,但此条也明显参考了《西藏图考》卷六《藏事续考》中所引《布达拉经簿》关于班禅的记载。
最能说明这一问题的是《杂记》的最后两条资料:“五十六年,达赖、班禅两喇嘛飞章急告卫巴忠,高宗,奉命嘉勇公福安康命将军,超勇公海兰察参赞,屯练士兵,调进讨之。”“五十七年、索伦兵三千名,金川各司兵五千,皆集西藏。大清兵三千,裸麦七万石,牛羊二万余,众采买一年粮食,供足,内地运输,连其屯界之贼,尽皆剿灭矣。”这两条资料,前面谈及有的版本内容不完整时曾提到。这两条资料均记乾隆末年清军进藏击退廓尔喀入侵事,比较之后可知,均抄自《西藏图考》之《西藏源流考》。所谓“飞章急告卫巴忠”,即飞章急告当时在藏的侍卫郎巴忠,这本是乾隆五十五年廓尔喀侵藏时之事,《西藏图考》中“侍卫郎”一词的“郎”字脱,写作“侍卫”,《杂记》抄时又脱“侍”字,“侍卫郎巴忠”就成了不知所云的“卫巴忠”。乾隆五十六年,廓尔喀再侵藏,大扰扎什伦布寺,全藏大震,四川总督鄂辉、四川将军成德率兵四千赴藏进剿。乾隆知二人不足恃,再派福康安、海兰察领兵入藏。其原文为:“上知二人不足恃,乃命嘉勇公福康安为将军,超勇公海兰察参赞(《西藏图考》之《西藏源流考》在“参赞”前脱一“为”字),调索伦、满兵及金川屯练土兵进讨。明年,……闰四月,索伦兵二千,土屯兵五千并藏内官兵三千皆集。五月,连败其屯界之贼,尽复藏地。”比较二者,完全可以认定《杂记》最后两条资料是抄自《西藏图考》之《西藏源流考》。《杂记》作者抄时当然作了改动,也出现错字,如“土兵”抄成“士兵”,当时只有“屯练土兵”,并没有“屯练士兵”之说,如果“金川”二字不删去,更能说明原本为“土兵”。《杂记》作者将五十五年与五十六年之事合写,又将“上”改为“高宗”,“侍卫巴忠”也抄成“卫巴忠”,加上“高宗”之后“命”之前又衍一“奉”字,所以不仅读无法读,连标点也难以进行。至于最后一条的“大清兵三千”直到结尾这一段文字,实际上也是依据以上“藏内官兵三千”语,再参考《西藏图考》卷七《西藏艺文考》中所收松筠《西招图略》之《善始》篇所记,加上作者自己的理解写成,但将“稞麦”写成“裸麦”,将“克”写成“石”,又将结尾“连败其屯界之贼,尽复藏地”语改写为“连其屯界之贼,尽皆剿灭矣”。
在清代西藏地方志发展过程中,后人修志较多地抄录旧志,利用旧志资料是常见的事,引用史籍及档册材料也不鲜见,因此,《拉萨厅志·杂记》中抄录、引用《后汉书》、《尚书》、《晋书》以及乾隆末年刊行的《卫藏图识》的资料实际上在修志中是正常的事,但是,其中有的资料出自后出的《西藏图考》就很不正常了。这是因为,《西藏图考》刊行于光绪年间,李梦皋在道光年间不可能看到此书[9]。这只能说明,《拉萨厅志·杂记》是后人伪作,其与《西藏图考》有关的资料,就是作伪的证据。本文前已讨论的“清朝崇德二年”条中的“朝”字,很可能就是作者作伪时不小心留下的一个证据。房建昌先生在其文中,认为《拉萨厅志》为伪作,这的确是一重要的新发现[10]。笔者在《清代西藏方志史研究的重要资料——读几部清代西藏地方志的序、跋》一文中谈到此问题时,认为对全志是否为伪作还需要更多的材料证明。[11]实事求是地讲,笔者当时还未细读《拉萨厅志·杂记》。尽管目前有证据证明《拉萨厅志·杂记》亦为伪作,但全志是否都为伪作笔者仍认为需要进一步的深入分析,还需要进一步的材料。
笔者还认为,尽管《拉萨厅志·杂记》为伪作,但抄本与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仍应注意,这是清代西藏方志史研究中应注意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去分析、比对。
[1]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304;北京天文台.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852.
[2]编辑委员会.中国方志大辞典[S].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345;王尧,王启龙,邓小咏.中国藏学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81.
[3]吴丰培.拉萨厅志·跋[G]//吴丰培边事题跋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136.此跋实际上早已写成,收入此题跋集前略有改动。
[4]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在《拉萨厅志》的著录中只列了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吴丰培所藏两种抄本。吴丰培先生在《拉萨厅志·跋》中也明确说:“是书既无刻本,又不见著录。昔曾得旧抄本,录副以存,若因此得传,亦幸事也。”结合以上二者所记,《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中称民族文化宫藏有此志稿本应误。民族文化宫图书馆所藏应同样为抄本,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古籍部现所藏抄本应为吴丰培先生原藏之抄本。
[5]《中国地方志集成——西藏府县志辑》所收《拉萨厅志》为十一目,但比较其内容,是将《节气》目合在《风俗》目中了。见其辑,巴蜀书社1995年。张羽新主编《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第二辑《西藏厅县志》所收《拉萨厅志》与前者相同也为十一目,(其目录中《疆域》一目重复),也无《节气》。见其辑,学苑出版社2003年。
[6]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西藏地方志资料集成(第一集)[G].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9.
[7]本文所引《卫藏图识》材料,皆引自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西藏学文献丛书别辑[G].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5.
[8]本文所引《西藏图考》材料,皆引自西藏研究丛刊[G].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
[9]《西藏图考·例言》署年为光绪十二年,其光绪刻本封面上注明刻印时间为“光绪丙戌年秋”。丙戌年即光绪十二年。
[10]房建昌.伪造的吴丰培先生所藏《道光拉萨厅志》手抄本[J].西藏研究,2010(6).
[11]赵心愚.清代西藏方志史研究的重要资料——读几部清代西藏地方志的序、跋[J].待发表.
Discussion on Problems and False Evidence in Lhasa Local Chorography and Miscellanea from DaoGuang Period
Zhao Xin-yu
(Minority Studies Institute of Sount West Minority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041)
Lhasa Local Chorography written by Li Menggao in Daoguang period is the only chorography on Tibet during Qing Dynasty.It has been included in Combined Catalogue of Chinese Local Gazetteers.This paper compares several different versions including the copy in the Cultural Palace of the Nationalities and the copy of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of Lhasa Local Chorography and analyses major problems within the contents.By analysis of the contents and references of Miscellanea,it is obvious that false evident presented in the book and can be proved that these false evidences are done by people of later periods.
Lhasa Local Chorography from Daoguang Period;local chronicles of Tibet;research on local chronicle;false evidence
K29
A
1005-5738(2014)01-094-06
[责任编辑:周晓艳]
2013-12-15
赵心愚,男,汉族,重庆人,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西南民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