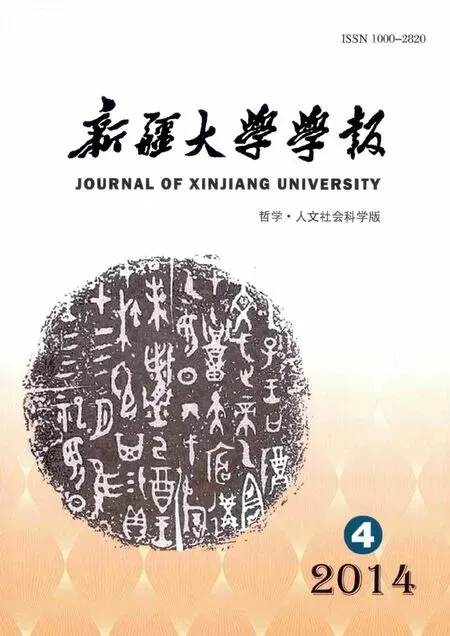论“水浒”人物的文化依存与命运走向∗
罗浩波,张海燕
(喀什师范学院 人文系,新疆 喀什 844008)
在传统的视野中,中国人的文化背景与生存哲思,主要是由儒墨道法等诸子之说的相互吸纳及整合,加之对外来佛教之思的积极包容并内塑而构筑的。其中除佛、道两家讲求解脱或摆脱社会苦海而归依生命轮回或个体逍遥外,儒、墨、法则以密切关注人的社会性生存的姿态,于先秦时期各自构建了一套表达不同族群的不同生存理念的独特思考,这些思考在后世的传递中,随法家在秦朝政治实践的破产和墨家至汉初组织形式的瓦解,就只剩儒家独享了汉、宋两朝的官方长期标榜并推广,而逐渐成为了后人选择并充当社会角色时,所必须借助与依靠的正统话语与核心理念。由此带动了儒家与儒学渗透或装潢下的墨、法两途的悄然变通,构成传统中国人依存社会的三种基本文化形态,本文姑且称之为仕宦型文化依存与草莽(草根)型文化依存、统领型文化依存。这三种依存社会的文化形态,在《水浒传》中的演示与体现,让人掩卷长思、喟叹不已。清人怀林和尚曾指出:“《水浒传》,虽小说家也,实泛滥百家,贯串三教。”[1]
一、仕宦型文化依存——儒者吏治化的生存反思
儒家强调学优而治世,《四书·大学》提出按“三纲领八条目”[2]来入仕途、求仁治,成了世代儒生的难以改变的人生航向,形成儒者回环闭合而又进退自足的生存系统,个体修行被限定在“正心诚意”地“致知格物”内,社会参与被规范在“平天下”而“止至善”上,这无疑圈定了儒者的最高作为是辅天下而不有天下、治天下而不主天下,从而导致儒家文化强调观念的善意性而不重视实现的有效性、强调行动的程序性而不重视操作的融通性的鲜明特点,塑造的是依附者而不是领导者,是仕宦忠臣而不是枭雄霸主,是知书顺民而不是草寇莽汉。以此透视梁山泊第一任头领王伦的人生悲剧,恰在于他违背了儒者人生定位的依存性原则。
王伦是纯儒为王的代表,自称“口不停诵、手不停批”,对此怀林和尚批点说:“(作者)独其有心贬抑儒家,只以一王伦当之,局量匾浅,智识卑陋,强盗也做不成,可发一笑。”这恰恰点出了致力儒家思维之人,确乎都存在不够灵活、有些迂腐而不堪独当一面的特性,这不是泛泛责备王伦气量狭窄、不能容人。王伦的文化意义正如明袁无涯刻本眉批所对比的那样:“王伦亲见了好汉,千推万阻,不肯容留;后来宋江但听得好汉,便千计万较,勾引上山入伙。英雄作略与头巾见识,相去千里”[3]226,指出王伦与宋江,不独显示着两人在生存谋划上的不同,更见出纯儒(所谓“头巾见识”)与法儒来自文化构成上的差异。李卓吾在林冲火并之后批道:“天下秀才都会嫉贤妒能,安得林教头一一杀之也?”[3]359可见王伦是“天下秀才”—— 儒生做派的一个代表而已。鲁迅先生对此有更宏观也更形象的归纳,即:“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4],所以王伦的“嫉贤妒能”只不过是乱世中自守寨主之位的儒生“奴化”思维的突出展示而已。
王伦被强调为“不第秀才”,宋江和吴用也算读书人,却没写“不第”的“小辫子”,至于他们是不能科考还是不屑于科考不得而知。但从宋、吴所结交者多为市井强梁看,王伦的文化程度应高于且纯于郓城押司宋江和乡村教师吴用的,他本要立志入世,走仕宦之途,却不意落第又落草而竟成梁山泊的头领。儒者往往考前自视甚高、满怀希望,到落榜又易自艾自怨进而自暴自弃的自闭型文化心态,使王伦清楚意识到一旦落草,永无新生,所以仕宦哲学使他被迫并无奈地安于水泊,只求自守的苟且而不奢进取的野心。江湖人介绍王伦显然语带不屑,如柴进对林冲介绍:“为头的唤做白衣秀士王伦”,阮小二向吴用指明:“那伙强人:为头的是个落第举子,唤做白衣秀士王伦”,无疑都在提示读者注意:“白衣秀士”与“梁山头领”之间巨大的身份反差。
王伦身为梁山头领,却始终保持儒者惯常的敏感、谦逊、谨慎与警惕的特性。他见林冲虚谦到:“我这里是个小去处,如何安着得你”,见杨志自谦说“小可数年前到东京应举时,便闻制使大名”,见晁盖七人又卑谦曰:“小可王伦,久闻晁天王大名,如雷贯耳”等等。“小去处”、“小可”的拘谨道白,与晁盖那“晁某是个不读书史的人,甚是粗卤”的答语相比,言语间流露着一派斯文的书卷气,却独无山大王的霸气。林冲上山惹动了王伦的蓦然寻思、黯然自伤:“我却是个不及第的秀才……他是京师禁军教头”,“自守之贼”的本位意识驱使他要赶林冲下山。明人余象斗于此落评:“伦一见林冲,蓦想自己本事低微,起心不容,可见一儒夫安能为一寨主矣!”[3]226可见“落第儒生”是王伦背负的最大名誉负担与心理包袱,以致林冲火并时还纠住这根“软肋”而大骂:“量你是个落第穷儒,胸中又没文学,怎做得山寨之主?”对此王伦是无地自容、无言以对,其气短自馁之状可知矣。
王伦并非没有才智,他玩执寨制衡之术颇有手段。林冲一来,王伦便寻思:“我又没什么本事,杜迁、宋万武艺也只平常。如今不争添了这个人,他是京师禁军教头,必然好武艺。倘若被他识破我们手段,他须占强,我们如何迎敌?”现实的忧虑使他不顾及柴进的推荐,不理会朱贵、杜迁、宋万等轮番劝阻,执意要赶林冲下山,无非是求得自存自保而已。对林冲刁而对杨志殷,无非算以能制能的帐,但这招因杨志执意下山的不配合而落空。王伦急切需杨志而自搅林冲的“投名状”,万般无奈下“方才肯教林冲坐了第四位”,书中淡淡一笔,却深蕴着王伦的又一政治招数,即用位次来防范林冲潜在的僭越可能。位次的重要性在王伦的这番潜心构建中,成为日后梁山不断壮大过程中的最棘手也最抢眼的一个课题。王伦苦心不但教育了林冲,使其在火并王伦后,不仅推晁盖坐第一把交椅,还推吴用、公孙胜坐二、三把交椅,以免除犯上的猜忌之患,而且教育了吴用,书生秀才即便号称“智多星”、所谓“谋略敢欺诸葛亮”,那也只适合做参谋型人才,是谋划者而非主宰者。所以在王伦影响下、林冲推让中,梁山泊悄然走上了所谓“以济世为志”、“与寻常绿林不同”(袁无涯眉批)的发展之路。吴用辅佐晁盖的梁山也不过是“自此十一位好汉坐定”,并无任何增扩之举,到宋江上山才连拉带拽、不断纳新而终有“一百单八将”之多。所以王伦因林冲而调动起儒者的全部智慧,赋予了一个普通的绿林山寨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内在忧患感,由此也决定了其人生定位的方向性迷失、门户自守的文化性束缚,必将断送其“白衣秀士”出生的梁山泊主的身家性命。
随着王伦的被火并,儒生秀才在梁山泊的作用也由寨主、头领归位成了军师,确立了吴用“摇鹅毛扇”者的身份和地位。吴用在排解刘唐与雷横的械斗纠纷中出场,但其三劝四挡却不如晁盖的一声“大喝”能制止斗殴,可见乡村教师在前台处理问题的能力远不如其在幕后出谋划策强,所以从孔孟的“说人而为”,有效规范了后世儒生的生存行为,使“拾遗补缺”的吏治理念比“敢作敢为”的权霸意识更符合秀才们的惯常逻辑。《水浒》由林冲来透识王伦、拿捏吴用,把一个江湖忧患型山寨悄然改造为“头领加军师”的初具廊庙政体型山寨。而吴用与王伦一旦承袭了儒生的身份,便也随定位的不同而水到渠成地推演出了命运的不同。
二、草莽(草根)型文化依存——墨学融通下的平等运作
如果说儒学培养的多为谋臣式人物,那么墨学熏陶的常是侠义型豪强。墨子在“兼爱非攻”等观念指导下力行大禹“以为民先”的做法,观点虽遭到大儒孟子的驳斥:“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5]但战国末与儒学并称“显学”,据李泽厚推断,“秦汉以来,墨家作为思想和学派逐渐消失无闻,并且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过相类似的独立学说、思潮或派别”[6],吕思勉先生分析说,“墨之徒党为侠,多以武犯禁,为时主所忌,又勤生薄死,兼爱天下……墨学中绝,即由于此”[7]。然墨学又因“持论不高,便于俗受”[8]108,故核心观念并没有消亡,而是大都转化成民间潜规则,浸染于下层民众的心底,烛照他们梦幻“平等”的企盼,而晁盖便是身逢乱末之世,敢于“以武犯禁”、负案而逃,并成为梁山泊第二任头领的“墨侠”类人物。
晁盖出生乡村富户,“最爱刺枪使棒”,任着本土县乡最低的村吏——保正(即保长)之职,除衣食无忧、悠闲度日外,据刘唐说“山东、河北做私商的多曾来投奔”,因而有“仗义疏财,专爱结识天下好汉”的能力,曾为维护本村利益而“抢塔镇鬼”,在江湖上被称“托塔天王”,名震一时,雄霸一方。可见其不是安分人。他强悍耿直、率真仗义,私下平交着各色人等并赢得极大信任,甚至生死托付,如武夫雷横、雅将朱仝、书生吴用、小吏宋江都跟他来往相系;莽汉刘唐和道士公孙胜性格不同,学养迥异,却都投奔晁盖主事、“犯科”;郓城知县听得他劫生辰纲时,竟慨叹:“晁保正,闻名是个好汉,他如何肯做这等勾当”;渔民“阮氏三雄”一见晁盖,也有“人物轩昂,语言洒落”的惺惺之惜感。所以晁盖应是感召性与亲和力很强的好汉,在“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的峥嵘之时,被推拥为王伦之后的梁山泊主也就不足为奇了。
鲁迅先生说:“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儒者,柔也’,当然不会危险的;惟侠老实,所以墨者的末流,至于以‘死’为终极的目的。”[9]在强本济困、尚武扶弱的墨者的入世思考,潜隐为民间“结义”底色的影响下,出生草根阶层的草莽英雄晁盖也有如“墨子救宋”(事见《墨子·公输》)一般的“急公好义”之心。“劫生辰纲”是“犯王法”的事,晁盖只是听一面之交的刘唐说“不义之财,取之何碍”、“天理知之,也不为罪”,就不假思索地表态:“壮哉!且再计较”。后聚集吴用、三阮与刘唐六人结拜而计划谋取,这时素昧平生的公孙胜突然闯来,嚷着送“十万贯金珠宝贝作进见礼”,晁盖一听便大笑道:“先生所言,莫非北地生辰纲么”。一派豪爽坦诚之气,毫无猜忌防范之心,不像吴用还要劈胸揪住公孙胜喝道“明有王法,暗有神灵,你如何商量这等的勾当”,吓得公孙“面色如土”。所以晁盖侠之“老实”、义之“志诚”真天地可鉴,司马迁所谓“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10]的“游侠”精神在晁盖身上得到了生动展示。
宋江也“仗义疏财,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听了晁盖“劫取生辰纲”的消息,还是“吃了一惊”,“肚里寻思”晁盖“犯了迷天大罪”,虽仍“担着血海似的干系”通知晁盖逃亡, 但后来从“公文”中得知晁盖是逃上了梁山,又“心内寻思”其干了“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可见宋江的“仗义”重掂量,晁盖的“仗义”践然诺;宋江的“疏财”常济人扬孝义赢得声名远播,晁盖的“疏财”多铁肩担道义蓄满内心炽热;宋江的“结好汉”要徘徊在仁义和法理之间而知行矛盾,晁盖的“结好汉”却执著于信义与天良之端本而知行合一。所以小说中晁盖与鲁达的英雄气略近,而宋江则与武松的市井味相投。由此反观,吴用的儒生情结,使之在与宋江的交流中逐渐脱离晁盖去紧随宋江;武松的世俗情怀,使之在与鲁达的合作中而逐渐淡远宋江却亲近鲁达,文化的依存度与人物塑造的精准性,在小说中得到如此深细而绝妙地呈示,确实令人叹为观止。直至宋江改晁盖“聚义厅”为“忠义堂”,一块牌匾就把“墨侠”的平等理念与“法儒”的等级意识的本质冲突,既水到渠成又戏剧性地昭示了出来。
金圣叹曾言:“一部书共计七十回,前后凡叙一百八人,而晁盖则其提纲挈领之人也”[3]258。此论未必得到学界的认同或看好,但晁盖劫“不义之财”之痛快酣畅、烧自家庄院之退逃于后、杀追捕官兵之打拼在前、谢宋江之恩念念不忘、定山寨规矩之杀伐不允,被林冲称为“作事宽宏”的为人风格,在后世武侠小说之侠客义士的塑造中确实得到不同程度的赓续与弘扬。从晁盖取代王伦、钩带宋江,形成梁山泊三任头领的情节扣合与性格比照看,晁盖的“提纲挈领”说也并不夸张。“火并王伦”后晁盖把持的梁山不再是王伦那文绉绉的山头了,所谓“竭力同心,共聚大义,打造军器,演练水兵”,一派新气象。同时人性化关怀也非王伦时可比,林冲提出接家眷,晁盖立即派人打探;初次劫客商,晁盖便告诫:“我等自今以后,不可伤害于人”。局面稍定,晁盖就想到“救过命”的宋江、朱仝,对吴用等叨念:“知恩不报,非为人也。”宋江刺配江州途中被劫上梁山,晁盖亲谢道:“自从郓城救了性命,兄弟们到此,无日不想大恩。”宋江江州题反诗入狱,晁盖听闻“大惊”,带了人马就“下山去打江州”,江州劫法场,亲临一线救宋江。晁盖这发自本心的宽厚仗义、恩怨分明,确非王伦甚至宋江可望项背。
韩非子言“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但“儒之分”历经了孟子、荀子及汉儒、宋儒等的不断整合与变通,成为悲情治世的法典,而“墨之离”却导致“巨子制”的分崩,墨者思维只能下融成民间帮伙奢谈平权的梦呓。所以吴用同晁盖交往只是义气的感召,受宋江青睐就变成知己的效命,众好汉也是盯着晁盖身先士卒却听从宋江调遣献身,晁盖与宋江在领导技术层面的差异是不言而喻的。死刑犯宋江被晁盖刚救上梁山,在位次的推让中,就一次性地仅屈晁盖之下而高于吴用、公孙,坐上了第二把交椅,并不动声色地行使了发号施令的特权:“休分功劳高下,梁山泊一行旧头领去左边主位上坐,新到头领去右边客位上坐”,众人齐道:“此言极当”。可见做过村吏的“草根”天王、“草莽”英雄晁盖,对位次的理解远不及落第“酸儒”、没做过朝官的王伦,因此晁盖的侠义盟主之地位被权谋雄主宋江所取代便是迟早之事。由此可知墨塑侠客只能为武侠传奇的底色,不能做历史演义的核心。
三、统领型文化依存——法家内敛后的权谋走向
郭沫若先生在《十批判书》中梳理法家的发展脉络时指出,“从远源上来说,应该是道家与儒家,而在行程的推进上则参加有墨法”,认为韩非子“在思想上的成就,最重要的似乎就在把老子的形而上观,接上了墨子的政治独裁的这一点”[8]343。可见法家的形成含有对儒、道、墨三家观念的整合,所以“秦尚法”的失败,恰为“汉尊儒”的回归开拓了新路。而法家理念随墨派组织在强秦被遏制、黄老之治到汉武遭铩羽,就只能内修成反求儒家资源包装的,为“有图王之志者”所用的一种文化依存。这种法、儒一体或叫外儒内法的文化实践,成为皇权施政乐为标榜的“仁和劳民、善为驱使”的合理合法且合情的明君招牌。以此反观梁山泊第三任头领宋江,便不难发现他是摇摆在儒、法与墨之观念平衡的痛苦徘徊者。
宋江在充满矛盾中出场,县村人氏,却“有养济万人之度量,怀扫除四海之心机”;押司小吏,居然“刀笔敢欺萧相国,声名不让孟尝君”;“于家大孝”又“仗义疏财”。可见生存的矛盾性是其显著特点:“大孝”似儒、“仗义”近墨、“刀笔”为法、“养济万人”藏纵横之色。其文化构成远较王伦、晁盖为复杂,这也使他能周旋在文吏武将、山贼水寇、侠客莽汉等各色人中赢得信任与夸扬。上山之前,他主要通过“结义”与“拜服”等手段来博得众好汉的追捧,但浪迹多年却徘徊下层,想待机而动又方向不明,更不堪因瓜葛梁山泊、怒杀阎婆惜,竟由押司小吏更沦为了刺配囚犯。所以在江州浔阳楼上,宋江痛彻于“学吏出身,结识了多少江湖好汉;虽留得一个虚名,目今三旬之上,名又不成,利又不就,倒被文了双颊,配来在这里”,而“潸然泪下,临风触目,感恨伤怀”,题下“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邱,潜伏爪牙忍受”、“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等诗句。韩非子言“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术”就是权谋,并指出“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11]。这理论层面的法术之谈,当时就被责为“危身之道”,而宋江却把“权谋”二字直抒于诗中、把造反黄巢当成自效对象,确实胆大心痴,无怪黄文炳要逐句读评为“自负不浅、不依本分、要生事、赛黄巢”而扬言宋江“有反心”了。宋江为推脱罪责,竟能装出“风魔失心”、“倒在尿屎坑里滚”,经史教育的斯文不要了,好汉敢当的名头也不顾了,最后“吃打不过”招认判入死牢。在这里儒生的“士可杀不可辱”、墨者的“赴火蹈刃,死不旋踵”,都让位于“大丈夫伸屈自如”的以功利于己为务的原则了。
经晁盖等劫法场、报私仇而活剐黄文炳开始,宋江的儒文化的束缚、禁忌从行为上来说都被破除了,被迫要与梁山造反者合流的现实,驱动其墨文化的影响外显、法文化的根基内扬,墨之“义”由此成了包装法之“术”的幌子。宋江屈志容身上了梁山,不期然竟拥有了大展所学、一试抱负的新天地。他在坚推晁盖继续坐第一把交椅的同时,又把吴用、公孙从“梁山旧头领”中单列出坐了三、四位,致使“左边一带”的“梁山泊一行旧头领”仅剩九人,而“右边一带”跟随宋江而来的“新到头领”却有二十七位之多。宋江运用由“术”而“势”的法家策略,悄无声息地巩固自己地位的手段可谓高明而高超,远不像王伦、吴用类纯儒弄权夺位时做得那么决绝与显眼。
宋江与晁盖的分歧,是从杨雄、石秀上山而首次公开彰显的。晁盖听得用好汉之名干偷鸡勾当,认为是“坏好汉名头”的小人所为,要立斩杨雄、石秀。宋江却不同意,除劝阻晁盖外,又虚拟出“我也每每听得有人说,祝家庄那要和俺山寨对敌了”的四条必打祝家庄的理由。一席话首先得到吴用“公明哥哥之言最好”的赞同,其次又有戴宗“不可绝贤路”的附和,最后是“众头领力劝”,生生把晁盖推向孤家寡人并被迫食言的境地。晁盖的“宽宏”而讲“正义”,在宋江看来则略显灵活不足,如王英、董平是好色之徒,宋江亦能容忍其行为,还有秦明、朱仝,为断其朝廷命官的归路,用些不仁道甚至是不地道的手段也可以。可见宋江行事并不全遵江湖规矩和民间道义,而有很强的“无毒不丈夫”的枭雄权霸色彩。
正是从“三打祝家庄”开始,梁山走出了被动劫财不伤人的晁盖时期,步入到主动火并地方武装、甚而挑战朝廷大军的宋江时代。宋江不安心于“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论秤分金银”的平等自得生活,不断下山征战,不择手段拉人入伙,在把梁山做大做强的同时,使晁盖成了“尸位”式的摆设,所以“架空晁盖”说并不是空穴来风。观念的分歧,导致晁盖中箭身亡前并没有逻辑地举荐宋江接班,而留下“贤弟莫怪我说:若那个捉得射死我的,便教他做梁山泊主”的遗言。金圣叹批点:“晁盖虽未死于史文恭之箭,而已死于厅上厅下众人之心非一日也”,可见宋江自称“长成亦有权谋”非虚言也。
宋江执行晁盖遗嘱也颇见权谋,先是哭得夸张,所谓“比似丧考妣一般,哭得发昏”,竟使晁盖之同伙吴用、公孙胜来反劝其节哀。其收买人心的火候掌握得极佳,不是新头领劝而是“林冲与公孙胜、吴用并众头领商议,立宋公明为梁山泊主”,描述的高明亦不动声色。果然宋江还在虚让,李逵就迫不及待叫道:“哥哥休说做梁山泊主,便做了大宋皇帝却不好!”至此宋江已无可争议完成了继任梁山首领的舆论造势,但还要声称“权居此位”,“待日后报仇雪恨已了,拿住史文恭的,不拘何人,须当此位”,把自己俨然打扮成晁天王遗愿的最忠实的践行者。同时临时寨主又不失时机地行使发号施令之权—— “聚义厅今改为忠义堂”,悄然从理念上展开了“去晁化”运作,并构建忠义堂为主寨,下分五大寨四小寨等等区划,造成“忠”于主寨的梯次序列,可见宋江的驾驭能力、管理手段确实非晁盖能匹。报仇非宋江所能,由此卢俊义便被连拉带赚,不惜劫法场、劫监狱、大战大名府而硬拖上了梁山。最终卢俊义替宋江完成活捉史文恭的任务,但宋江却通过以退为进的手段,履践了对晁盖的承诺而博得众好汉道义的支持,又使吴用、公孙甘心退居卢氏之下避免了人事纠纷,再让卢俊义孤悬高位而不生“得陇望蜀”之心,一石三鸟可谓机关算尽。
宋江掌控了梁山的话语权后,儒、墨观念在自己的行为处事中又开始了回潮,面对草根类草莽群体,需要用义气维系,不忘“扫除四海”之志,耿耿于“修齐治平”心怀,所以谋求梁山好汉的出路就成了宋江顺理成章的借口。由宋至明的理学、心学之争催衍了王阳明“致良知破心贼”之思,促动小说作者替宋江虚拟了“忠义招安”的理念上或可贯通、历史上从未实践的文本情节。这一在剿灭败亡与改朝换代之间选择的出路,随着宋江被朝廷毒死的结局,也揭示了任法谋权的统领型角色与固有皇权不相并存的铁血事实。
四、易依存为适存的心智启示——佛道对社会生存的个体救赎
当我们考察完王伦、晁盖与宋江三位梁山泊主,以不同的文化认同与入世述求,演义了乱末之世难于回避的人生悲剧后,进一步发现王伦死而归位的吴用,把儒生谋臣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化,却因宋江遇害丧失知己,而与书卷化武将华荣一同吊死宋江墓前,晁盖死而催生的卢俊义,把墨侠英雄的作为挥舞到最强烈,又不免朝廷以武犯禁的猜疑,而与草根型莽汉李逵都遭毒害之命运,可知《水浒》是一本人物系统性极强、生存关联度极高、社会认识价值极大的古典长篇小说。
乱世进取对人之生存的极度扭曲,必然激发文化深度调整的有机回馈,而佛、道之思恰是中国文化遭遇困境时,反向求助的普遍而便利的精神资源。鲁达、武松与公孙胜三人也是小说较早出现,且在情节推进发生重大转变的关键时刻不时闪现的核心人物。鲁达偶入佛门但慈悲天成,识性通透,对招安前途以“衣遭皂染洗不干净”为喻,通俗精辟;捉方腊而不求授官爵言:“只得个囫囵尸首,便是强了”,真是洒脱透彻,得到听潮圆寂的善果。武松变身酒肉假行者,杀伐云游僧,虽第一个对宋江提出“异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时却来寻访哥哥未迟”,但上了二龙山却受鲁达感染,成为“招安”的冷静而理智的反对者,归朝途中滞留杭州做了“清闲道人”,得以“八十善终”。道教代表公孙胜最早脱离梁山队伍、还家逍遥奉教,引出归朝的樊瑞、朱武也弃官成了“全真先生、云游江湖,去投公孙胜出家,以终天年”。戴宗也“纳还官诰、泰岳出家”并“无恙大笑而终”,又有柴进效戴宗、李应效柴进,都纳官回乡、无疾而终。佛道之徒全得善终,反向说明末乱之时权奸成器、归朝难容,所以佛之普惠、道之无待,恰成保全心性、高傲气格、完善存在的变“依存”为“适存”的无奈救赎。
对“招安”后果的透辟认识,除了佛道人物从文化的深层排斥而捐弃之外,还有燕青,由现实联系到历史,以韩信、彭越、英布之例,劝卢俊义不能功高执着,可惜卢不听而只好自个勇退激流;有李俊及童威、童猛,诈病远遁,明哲保身,到海外暹罗(泰国古称)为王,怡然回到了梁山时代;有阮小七,被告穿方腊的龙袍而诬为“怀心不良”,被贬庶民而乐得还乡,打鱼为生,“寿至六十而亡”。这些人通过个体自救而反照出宋江招安之路的不可行。
明大涤余人在《刻忠义水浒传缘起》中评言:“正史不能摄下流,而稗说可以醒通国”[12],《水浒传》是把人物放置于民族文化的历史糅合同世俗接受中来系统刻画的,多维的文化选择、细微的依存差异,导演出的竟是命运的瞬息之变、天壤之别。小说细腻剖析人对文化的依附度之不同,而造成命运终极情状之迥异的生动描述,把传统中国人的生命感怀与生存智慧推向了精妙而完美的描摹境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