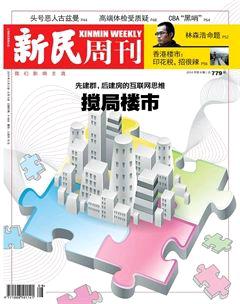林森浩命题
沈亮


当“复旦投毒案”的一审法槌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敲响的时候,对犯罪人林森浩的死刑判决的分析、思考、评论的热潮在网络和现实世界中涌动。
从文字上来说,“死刑”与“死缓”似乎只存在一字之差。但是稍有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其在法律上的深层含义大不一样。
此刻,静下心来对一字之差的法律含义、司法运用等加以考量,尤其显得必要。在这种考量中,我们民族的法律理念可以得到深化,社会主义的法治之路更能显示出民族性和大众性。
被公认的“恶意”
死刑在法律上的含义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刑罚方法。在我国刑法中,死刑是最重,因此也是最终的刑罚方法。1997年,刑法进行修改,死刑的适用对象确定为“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
刑法分则规定的四百多个罪名,将死刑作为选择刑的,除了危害国家安全罪、军人违反职责罪外,普通刑事犯罪主要是针对那些对国家、社会和人民利益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犯罪行为。
需要强调的是,即使是犯罪行为人触犯的是上述罪行,也不是都要一概判处死刑,刑法要求不仅罪行应当“极其严重”,而且死刑不得适用于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时怀孕的妇女。 2011年2月25日,《刑法修正案(八)》更增设了“审判的时候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的内容,足见我国刑法对死刑适用的严格。
那么,究竟如何来考量犯罪人的“罪行极其严重”?以法律的角度看,所谓“罪行”应当考察的是犯罪人犯罪行为构成的基本方面。
联系到“复旦投毒案”,我很同意有的学者的总结,涉案被告人林森浩将杀人视为“玩笑”或者“游戏”,主观上“随意杀人”、“漠视生命”的态度恶意极高,客观上采用投毒的方式实施杀人,其恶劣性当可确认。而且在完全有可能避免最严重后果发生的时候,作为一名懂得医术的人,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由此,一审法院认为其罪行极其严重而适用死刑是有理由的。
宽恕的条件
但问题是,罪该处死不见得都要立即执行。我国刑法创造性地规定了死缓制度(全称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制度”),亦就是说,对于那些应当判处死刑,但又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在判处死刑的同时宣告缓刑2年执行,实行劳动改造,以观后效。
考察死缓制度,基本要件应当有两项:一,罪该处死。二,不是必须立即执行死刑。我们不否认,第二项中的“不是必须立即执行死刑”的含义,在法律规定上确实不甚明确,不过,这个判断真的无法全面评价吗?
影响到刑罚轻与重的事实,我们习惯上称为“量刑情节”,起码应当考虑两个层面:
首先,在法律层面上,对于法律有规定的情节(法定情节),量刑时我们需要加以运用。比如说,从“从重”的情节看,犯罪人属于累犯;从“从轻”或“减轻”的情节看,犯罪人具有自首、坦白或立功表现的等等。
其次,如果犯罪人不具有法定情节,也并不是说量刑就不考虑任何事实了,按照刑事政策和刑事审判的经验,法官根据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对于犯罪手段是否恶劣、是否残忍;犯罪的时间、地点;犯罪侵害对象的具体情况;犯罪造成的损害大小;犯罪动机是否卑劣;主观恶性程度如何;犯罪人犯罪后的态度;犯罪人的一贯表现;犯罪人有无前科等等“酌定情节”,也会对量刑有影响。
只有把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合理地运用,一个案件的量刑才会是相对最为合理的,不仅能够被犯罪人所接受,也为社会公众所认可。
联系到“复旦投毒案”的犯罪人林森浩,“罪该处死”似无大的分歧,可否适用死缓呢?一审法槌落下后,此点上的议论甚多。
我们来谈谈一些可以思索的问题:
第一,法律所说的“不需要立即执行”所考量的因素中,是否有法定因素(情节)?有人认为,法定情节在裁量犯罪人“罪该处死”时已经运用,因此,除非法律有明文规定,否则,将已经在判处死刑时运用过的量刑情节再运用于“不需要立即执行”的判断上,就犯了“一事实二次运用”的错误。
对此,我不能认同。一来,死缓虽然是死刑的执行制度,但是,我国刑法目前尚没有对其规定明确的适用条件,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死刑本身的最终性,法定量刑情节的运用尤可着重考虑。加之法定量刑情节,尤其是从轻、减轻情节在适用上往往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刑罚方法的运用和执行制度上的运用不会产生冲突;二来,不论是刑法或是有效的司法解释,并没有明确列举死缓的适用条件,因此,作为司法者来说,将量刑情节中的法定情节在适用死缓制度时加以运用,和法律并无矛盾。
第二,根据这几年的司法实践,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起的故意杀人案件,是否应该适用死缓,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指导性案例等形式认为,较为通常的考虑标准主要有:被害人在案件起因上是否存在重大过错;被告人案发后是否进行积极赔偿,是否真诚悔罪;被告人是否取得被害人家属谅解。
但是,不应该认为只有在这三种情况下才能适用死缓。如果一味地认为民间矛盾激化引起的故意杀人案件“只能”按照这三种形式“才能”适用死缓,法律应有的实践发展性可能就无从谈起,法官在法律面前应有的独立判断就会丧失。
争论与进步
回到“复旦投毒案”,被害人在整个过程中确实不存在重大过错;案发后,林森浩及其家属尽管也有一定程度的补偿表示,但具体举动似不十分明朗;林森浩和家人在申辩时也多次提出这是一次“游戏”,悔罪态度似“不真诚”,被害人家属也不言谅解……但是,为什么网上和社会上会有一些议论认为应该对被告人宣告死缓呢?
我以为,一来,这是近些年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效果。当我们知道生命权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十分宝贵的,决定生命终结的死刑的适用就应当十分慎重。
二来,法为大众充分地关注。法律、法规、解释、指导案例、具体裁判中的证据和说理…… 这些过去似乎是“小众”关心的信息,现在都被大众加以关注。
三来,法律,具体到刑法的发展,也许真有一些新的课题可以让我们注目。
就在本案可否适用死缓的激烈讨论中,有人评论林森浩被判死刑“于情不忍”,一位刑法教授就此提出一个命题:于情不忍本身不就是不判死刑的充足理由吗?
法律来源社会,我们对所谓“民愤”影响司法提出了质疑,那么,将“情”引入量刑、且是从对犯罪人或被告人有利的角度来考量时,我们可以接受的吗?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