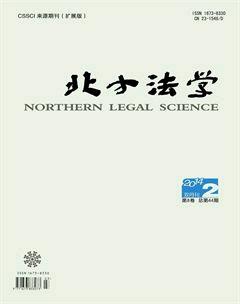技术网络化背景下的专利侵权判定
刘强
摘 要:以云计算为代表的技术网络化趋势对专利侵权判定规则及其适用带来了新的挑战。网络化技术实施过程中的分离式侵权行为和跨境侵权行为均难以根据现有规则被认定为专利保护范围,并由被告承担侵权责任。方法专利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也难以在网络化技术专利侵权诉讼中为权利人带来有效的救济。专利权人获得司法救济的法律障碍在制度设计时未能有效预见和应对,导致维权难度较传统技术领域显著增大。因此,必须克服专利侵权判定中的形式主义,以实质性侵权作为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价值取向,以期克服由于网络化技术发展而带来的利益平衡格局遭到破坏的状况,实现专利制度的价值和目标。
关键词:技术网络化专利 侵权判定 分离式侵权 跨境侵权 举证责任倒置
中图分类号:DF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330(2014)02-0059-11
以云计算为代表的新兴技术领域呈现典型的网络化特征,在充分利用网络通信技术的基础上,为提高计算服务、拓展服务内容和范围解决了技术难题。从技术发展趋势来说,云计算是基于信息网络而提供新型的网络计算、数据存储和应用程序服务,是一整套通过网络通信连接起来的计算机资源。就技术特点而言,云计算具有网络化、分散性和跨国性的特点,改变了传统的软件服务。①目前,云计算已经成为专利诉讼争夺的焦点领域。②但是由于其具有的技术网络化特点,对于专利制度设计时所针对的传统技术形态形成冲击,特别是专利侵权行为分离化趋势明显、专利侵权跨境化情形增多以及举证责任倒置法律适用产生困难,给专利侵权判定带来的新问题,必须通过制度设计加以解决。
一、分离式专利侵权判定问题
(一)分离式专利侵权的构成和产生原因
分离式侵权,是指在方法专利权利要求中并非由单个主体全部实施所有的工艺和步骤,而是由多个相对独立的主体分别实施其中若干步骤的侵权行为。例如,某方法专利包含步骤甲、步骤乙和步骤丙,其中步骤甲和步骤丙由网络服务提供商实施,而步骤乙由该服务商的客户实施。从专利侵权判定的角度看,网络服务提供商和客户均未实施全部三个步骤,因此均不能判定其构成对方法专利权的侵犯。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专利申请人为满足专利法对于申请文件的要求,特别是要求专利权利必须包含为实施发明创造技术方案不可或缺的必要技术特征(即所有必要的工艺步骤),否则不能授权。然而,为了满足专利法的该要求,加上专利申请人对于侵权判定标准中关于完成主体单一性要求的不了解,可能导致专利授权以后进行侵权诉讼时如果面对分离式行为,难以使其被认定为属于专利权保护范围,造成权利人处境尴尬。分离式侵权从形式要件来看可能并不构成侵权,但是从实质上侵害了专利权人的独占性市场利益,因此应当受到专利法的规制。
产生分离式侵权行为的原因包括技术原因和法律原因。首先,在技术原因方面,网络计算服务技术是根据客户需求提供的动态服务,因此强调技术实施的交互性,而服务提供商提供服务的过程与客户进行计算消费服务的过程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从技术实施过程来看,必然有客户参与到网络计算服务的具体步骤中来,而且要根据客户所提供的计算指令来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而在网络软件服务和网络数据存储服务中,也必然要求客户实质性地参与到最终产品的制造过程中。而在客户参与的环节,网络服务提供商会提供明确而细致的指导,因此,客户是在服务提供商的指导之下完成其所需要参与的步骤的。既然有客户参与,就为网络化技术的分离式专利侵权行为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性,并且这种可能性随着网络通信和网络服务技术的发展有逐步扩大的趋势。
其次,在专利法律方面,既有专利权人申请专利要求撰写技巧问题,也有专利保护范围的法律认定出现僵化和缺乏灵活性的制度漏洞问题。其一,从专利申请人的角度来看,为了避免分裂侵权抗辩而采取的专利权利要求撰写策略可能会与专利法对清楚限定专利权要求保护范围的要求产生冲突,因此,在撰写云计算等网络化技术专利权时要注意采用合理的撰写策略以平衡两方面的风险。其二,从专利侵权判定所针对的假设性技术模型来看,技术网络化发展超出了传统专利法所设计的“一项专利对应一种产品”的技术发展模式,有可能让两个以上相互独立的主体共同参与到技术实施中来。网络通信技术让实施方法专利的指令发送更为便捷,普通的客户也能够通过点击鼠标而发出指令,能够方便地参与到技术实施过程中。而在专利侵权判定中,技术网络化使得全面覆盖原则难以对权利人构成有效保护,规避侵权可能变得更为容易,特别是云计算方法专利则更加难以得到执行和救济,因此,必须对分离式侵权行为进行特别规制。
(二)分离式专利侵权行为判定的困惑
对于分离式行为,要判定其构成直接侵权或者间接侵权均存在法律困境。就直接专利侵权判定而言,全面覆盖原则要求被控侵权人的技术实施行为包含系争专利的所有技术特征,对于方法专利而言,即必须完成所有技术步骤。全面覆盖原则适用的前提条件是落入专利保护范围的技术实施行为应当由单个主体完成,并且必须由其完成所有的专利权利要求所涵盖的步骤。如果将侵犯专利权的产品作为零部件由另一行为人制造另一产品的,可以认定为“共同侵权”,但条件是“被诉侵权人之间存在分工合作”,也就是其主观上必须有故意侵权的意思联络。
美国专利法对于直接侵权也采用类似的立场,该法第271条第(a)款对于直接侵权在行为主体数量方面的要求为单独主体。③对于方法专利而言,全面覆盖原则也是针对被控侵权人主体的单一性而言的。在2000年的Canton Bios Medical案中,④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认为:“多步骤方法专利的直接侵权判定要求行为人实施了专利方法的全部步骤”。因此,如果不能认定被控侵权人单独或者与具有共同侵权故意的其他主体共同实施了全部方法专利步骤,则不能构成直接侵权。
由于分离式侵权行为由多个主体完成,特别是要通过接受网络计算服务的客户完成部分专利权利要求当中所包含的步骤,然后再由网络服务提供商完成其余的步骤,因此,对于客户和服务提供商而言,都难以认定其构成直接侵权。专利权人能否直接援引作为一般民法的《侵权责任法》第8条和第12条要求其承担共同侵权责任呢?行为人的主观要件可能成为法律障碍。美国法院在专利共同侵权问题上的意见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2006年On Demand案⑤曾采取比较宽松的“参与和复合标准(participation and combined action)”,即“如果侵权行为是由多个主体参与或者复合情况下完成的,则所有参与者均是共同侵权人并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方法专利中的部分步骤由其他人实施不能免除侵权责任”,并且同样要求“各个参与者承担共同侵权责任”。尽管单个专利侵权行为在归责原则上采取无过错责任,但是并不意味着在共同侵权或者帮助性侵权时也可以要求行为人承担无过错责任。“参与和复合标准”作为侵权判定标准在随后的BMC Resource等案件中被弃用。⑥共同侵权通常要求行为人具有侵权的故意,⑦而作为网络技术实施者,特别是服务提供商和客户之间是缺乏侵犯专利权的意思联络的,再加上作为专利侵权必须要具有《专利法》第11条规定的“生产经营的目的”,而作为接受网络服务的客户来说,其营利性目的是难以得到证明的。因此,对于网络技术实施者来说,不能认为具有认定其行为构成直接侵权的前景。
如果难以认定为直接侵权,还可以考虑通过间接侵权对于分离式侵权进行规制,但是仍存在法律上的障碍。其中重要的是,对于间接侵权而言,必须有直接侵权行为才能够认定。然而对于网络化技术而言,认定直接侵权行为本身就是比较困难的。在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2004年判决的Dynacore案中,⑧法院认为原告不能证明被告或者被告的客户构成了对系争专利的直接侵权,尽管被控间接侵权人的产品可能被用于直接侵权行为,但是也存在实质的非侵权商业化用途,因此,不能要求被告为“虚构的直接侵权行为”承担间接侵权责任。此外,被控间接侵权人要明确了解侵权行为的存在,在此情况下仍为其提供专利技术实质部件等帮助,才能够认定间接侵权存在。另外,间接侵权人所提供的产品必须除侵权用途以外,没有其他合理的商业用途。
(三)实质性直接侵权判定——联合侵权行为
由于根据传统专利侵权判定标准,云计算等网络化技术在认定直接或者间接专利侵权上存在困难,因此,必须克服专利法对于构成直接侵权行为在形式上的单个主体要求,转而对形式上属于多个主体但实质上属于单个主体的行为要求承担直接侵权责任。基于上述目的,为了寻找解决方案,美国法院通过近年来的一系列案例发展出“控制和管理标准(Control and Direct Test)”来对联合侵权行为进行法律规制,要求行为人在非传统侵权领域承担直接侵权责任。联合侵权行为类似于共同侵权,但是在证明主观故意比较困难的情况下,通过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来认定其行为具有联合侵权的属性,并且为寻求专利保护确立法律依据。在确立该规则之前,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Shields案中就认为,⑨如果专利方法不得不由除被告以外的第三人实施其中某个步骤,并且第三人是作为被告的代理人实施技术的,或者由被告向第三人提供技术指导,则可能认定有被告单独承担或者被告和第三人共同承担侵权责任。正式确立“控制和指导”原则是在联邦巡回法院2007年BMC Resources案,⑩并且在Muniaution案B11和2010年Akamai案B12中得到发展和澄清,使得该标准的适用范围和使用方式得到优化。
“控制与管理规则”的目标是要求被控侵权人为受其控制或者管理的其他当事人实施部分方法专利步骤的行为承担替代责任(vicarious liability),从而要求其承担直接侵权责任。适用该规则的前提是被控侵权人和其他当事人的单独行为均不构成直接侵权,否则无需适用该规则即可认定侵权行为成立。在此基础上,如果被控侵权人控制和指挥了整个方法专利的实施过程,特别是对于实施其中部分步骤的其他当事人的意志和行为具有控制能力,则需要对其整个实施行为负责。法院在BMC Resources案中认为,B13“如果被告对于整个方法专利实施过程进行‘控制或者指导,以至于所有方法专利的工艺步骤的实施可以归因于被告”,则可以认为被告必须要“为其所控制的具体行为主体的行为承担替代责任”。
在适用标准方面,被控侵权人和其他技术实施者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是满足“控制和管理”标准的关键要素。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Akamai案中B14将认定的核心因素从具体的技术实施指导行为转变为考察被告和第三人之间法律关系,特别是是否具有委托代理关系。联邦最高法院在1984年Dixson案中,认定具有委托代理关系的标准是基于代理人代表委托人的利益并且受到委托人的控制而产生的信托关系(fiduciary relationship),B15并且对于双方当事人而言均同意存在委托代理关系才能够认定该关系成立,而只有委托方的意思表示是不够的。联合侵权行为当事人之间必须具有代理关系或者负有合同义务。值得注意的是,独立承包人(independent contractor)身份不足以排除委托代理身份的存在。同样在Akamai案中,法院根据普通法的一般原则认为,委托代理关系不仅包含信托关系,独立承包人也可能包括在内,只要根据其他环境因素认为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即可。2007年Hudson案中,B16法院就根据法律习惯和传统作出这种认定。法院作出上述意见的依据是,形式上的独立承包人可能在实质上是负有信托义务的。
此外,合同义务也可能构成符合“控制和管理”标准的因素。如果双方当事人不具有委托代理法律关系,那么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负有的实施方法专利步骤的合同义务可能构成认定符合“控制和管理标准”的依据。在BMC Resource案中,法院曾经表示“当事人不能通过合同方式让第三人实施步骤的方式规避专利侵权责任”。当然,这种合同义务应当作狭义的理解,如果对于当事人来说有是否履行合同约定的方法专利步骤的选择权,则不能将其所享有的合同权利理解为合同义务。在Akamai案中,专利权人就认为被告Limelight公司提供了标准服务合同,因此对于Limelight的客户(即网络内容提供商)而言就有义务提供相应的内容并实施方法专利的部分步骤。但是,对于客户而言,只有在其决定使用Limelight公司所提供的网络数据传输服务后,才会实施标记等技术步骤,并且这种实施行为从性质来说是技术上的必要而非法律上的义务。对于其他网络技术服务的普通客户来说,由于其享有接受服务的权利,而不负有实施方法专利步骤的义务,因此也不能认为其具有合同义务,也不得认为客户的行为受到网络服务提供商的控制和指挥。法院在Muniaution案中就指出,当事人之间仅具有“长臂”商业交易关系(arms-length business transaction)不会引起任何一方承担直接侵权责任的问题。B17因此,要通过合同义务来认定当事人之间存在“控制和管理”关系必须是稳定的长期合同关系,而非基于偶然或随机因素而订立的合同关系。
二、跨境专利侵权行为判定问题
(一)技术跨境化引发专利侵权判定困境
技术网络化带来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对于跨境专利实施行为如何进行专利侵权判定。网络技术发展使得技术实施行为有可能跨越国界,超出特定国家的地理边界,从而造成专利保护难以实现。从技术角度来说,云计算的特点是打破了地域信息和物理信息的界限,整合物理上相对分散的网络资源提供计算服务,其使用的网络资源完全可能分布在世界各地。云计算提供商可以利用分布在全国范围(甚至世界范围内)的庞大数据中心资源,并且将数据通过网络连接起来,因此在云计算中数据可以传播于不同国家境内。云计算中心数据服务器位于境外,可能因此引发专利权是否具有域外效力的问题,其实施行为能否受到内国专利法管辖将成为专利侵权诉讼的焦点问题。
专利保护具有严格的地域限制,任何国家的专利法效力并不及于国家主权管辖以外的行为。如果对于在国境以外的专利侵权行为进行管辖,则可能构成对其他国家司法主权的侵犯,也不符合专利保护的宗旨——对于特定国家内技术产品独占性市场利益的保护。美国专利法第271条第(a)款明确要求被控侵权行为发生在美国境内才能构成直接侵权。B18美国1856年Brown案中,B19法院就明确指出,“‘专利权的效力本质上仅及于国内而且必须局限于美国国境之内,美国国会在专利立法时‘并没有而且无意产生超出美国国境的效果”。在2006年的Zoltek案中B20法院重申了由于被告部分方法专利步骤发生在美国以外,因此不构成直接侵权的立场。因此,作为专利权人来说,必须面对云计算等网络计算服务领域的行为能够得到其受保护国专利法管辖问题的挑战。
美国专利法第271条第(f)款对于跨境侵权问题进行了有限制的立法突破。美国最高法院1972年Deepsouth案认为,被控侵权人在美国境内所实施的制造零部件行为本身不构成侵权时,不能以在境外发生的对设备的组装和使用行为作为判定其侵犯美国专利权的事实依据。美国国会在1984年专利法修正案中,专门针对Deepsouth案的涉案事实和行为模式增加了第271条第(f)款,B21以期在特定条件下有限制地突破严格的专利权地域要求,从而对明显属于规避侵权责任但损害到权利人在美国国内市场利益的行为认定为侵权。根据该条规定,如果要对部分发生在美国境外的侵权行为认定为专利侵权,必须要符合五个方面的要件:(1)未经专利权人许可;(2)所提供的产品是发明的所有部分或者实质部分,或者所提供的零部件在商业上只能用于侵权而没有其他非侵权用途;(3)行为人主动提供或者促成向境外提供发明组成部分或者零部件;(4)如果组装该零部件的行为在美国境内发生则构成侵权;(5)行为人具有促成其在美国境外组装的主观故意。通过该条款,美国专利法对于形式上并未在其境内实施完整侵权行为但是在实质上构成对专利法所保护的独占性市场开拓权侵害的行为也进行类推适用,可以称为法律上拟制的侵权行为。2001年的Waymark 案B22就认为行为人对外输出并未在境外实际组装的产品零部件,但只要有组装的意图,也具有侵权性质。
(二)方法专利跨境侵权行为
跨境实施专利方法行为存在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方法专利的所有步骤均在境外实施,但是其实施的商业效果和技术效果发生在境内,并且构成对专利权人在境内排他性权利和独占性商业利益的损害。对于方法专利而言,专利法所提供的保护固然延及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问题在于,如果该“产品”仅指有形产品,那么在境外通过实施专利方法向境内提供网络计算服务就不受专利法限制。美国法院在这一点上持比较谨慎的态度。2003年的Bayer AG案中,B23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就认为美国专利法中对于方法专利直接获得的产品仅指有形产品,而不包括数据。该意见在2005年的NTP案中得到重申。B24另外,在国内实施对境外使用方法专利的指导,包括在境内对侵权产品的具体式样进行设计并向国外提供设计图样(design),尚不构成向境外提供专利方法实施的实质部分或者零部件。B25
第二种情况是部分方法专利步骤在境外实施,行为人是否构成对专利权的侵害。美国法院对此问题的意见存在相左之处,争议焦点在于方法专利步骤以及为实施方法专利步骤而提供的产品能否成为美国专利法第271条第(f)款所规定的产品组件或者零部件。首先,就方法专利步骤的法律性质而言,法院更倾向于不支持认定其属于认定跨境专利侵权构成要件中的“可提供性”。尽管有法院在Eolas案中认为,B26第271条第(f)款所说的受专利保护的发明并未限定在产品专利领域并排除方法专利,但是持否定意见的法院占多数。包括1998年的Enpat案B27和2005年的NTP案,B28法院从方法专利的本质属性出发认为组成专利的步骤不可能属于产品的实质部分或者零部件,也无法由境内主体向境外“提供”,因此不能构成跨境专利侵权。其次,对于为实施方法专利步骤而提供的设备或者工具而言,通常认为其不属于方法专利的实质部分或者零部件,因此即使存在向境外提供使用的情况也不构成对美国专利法第271条第(f)款的违反。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1991年的Standard Havens案B29中认为,实施一项方法专利但自身并未受专利保护的设备销售给美国境外消费者的行为不构成侵权。由于方法专利所包含的技术特征是具有时间顺序的步骤,而不是具有空间结构的产品,不能因为第271条第(f)款不限制技术领域的理由,就认为该条款可以适用于并非方法专利组成要素的零部件。
(三)计算机软件专利跨境侵权行为
对于不具有物理形态而以代码形式出现的计算机软件或者数据能否成为跨境侵权行为中向境外提供的发明实质部分或者产品零部件,美国法院通常持开放的态度。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如果其利用自然规律解决了相应的技术问题,应当属于专利权保护的客体。而计算机软件作为驱动设备的关键性要素,可以构成认定跨境侵权行为中向境外提供的发明创造实质部分或者零部件。在Eolas案中,法院就排除了美国专利法第271条第(f)款对于技术领域的限制,涉及计算机软件的发明从性质上说应当被包含在跨境侵权行为所认定的范围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软件方式向境外提供产品设计与实际提供产品部件的界限有时候是比较模糊的。一方面,如果认为专利产品仅限于有形产品,通常会因为软件是对产品进行设计而完成的蓝图(blueprint),因而被定性为对境外专利实施行为的指导,例如2004年的Pellegrini案B30法院就采用该意见。另一方面,如果专利产品本身就是包含软件的机器设备,那么向境外提供的软件将会被认为是专利产品的实质组成部分。在Eolas案中,法院就将Microsoft公司向境外提供的软件母盘作为专利产品的组成部分而认定为构成第271条第(f)款下对专利权的侵犯。当然,在向境外供应软件的行为模式上不能仅将体现软件的代码传送到国外,还必须要实际提供拷贝,否则仍然属于指导技术实施的蓝图性质,不会在实际上构成跨境专利侵权。因此,在涉及软件的跨境侵权行为中是否需要像实体产品零部件那样要求所有加载了软件的实物拷贝均从境内向外供应,是否可以用对软件代码的拟制输出代替实际的拷贝输出?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此前持肯定的立场,但是在美国最高法院对AT&T案B31作出判决后情况有所变化。在Eolas案中,被告微软公司将记载有软件的母盘(golden master disk)或者将软件通过网络输出给美国境外的经营者,再由后者将软件安装在实际出售的电脑产品当中,法院认定其行为是对作为零部件的软件的跨境“输出”,因此构成跨境侵权行为。在AT&T案中,微软公司对外“输出”Windows软件产品的行为模式类似,而其Windows操作系统在境外被安装在电脑中后,将会侵犯到原告在美国获得保护的语音处理设备专利。微软公司的抗辩理由是安装在实际销售的电脑中的Windows操作系统软件是在美国境外制造而并非从美国境内供应。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遵循此前判决的Eolas案,在肯定软件可以作为产品部件得到供应的基础上,对于向境外“供应”的行为模式也根据软件业的行业特点进行了扩张解释,将对软件“复制”作为“供应”的组成部分看待,因此,可以替代“供应”在跨境专利侵权行为中的作用,并认定微软的跨境软件传输行为构成侵权。然而,随着网络化技术发展,第271条第(f)款所规定的跨境侵权行为从专利范围到侵权行为类型的扩张有超出立法原意并打破当事人利益平衡的趋势。在专利立法确认之前,法院审理案件时对跨境专利侵权行为的认定标准进行从宽或者扩张解释应当更为谨慎。
(四)“影响因素”标准与实质性境内侵权行为的判定
为了解决技术网络化带来的跨境专利侵权行为判定问题,可以摆脱传统的完全境内实施原则,即要求境内实施专利技术行为全面覆盖专利权利要求的所有技术特征,避免由于法院拘泥于形式上的侵权判定要求而造成行为人有可能利用制度漏洞对于专利侵权责任的策略性规避。通过专利实施行为对于国内市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从而在实质上判定是否构成侵权将成为可行的制度选择,也符合专利法对于权利人所享有的独占性市场开发地位进行保护的目标。为此,作为法院如果认定在国内发生实质性侵权行为,可以将本国作为侵权行为地(locus of infringement),B32判别依据是侵权行为与本国具有最为紧密的联系,并判定其构成侵犯该国专利权。当然,基于对其他国家司法主权采取的礼让原则,要避免国内专利法产生域外效力。
综合美国法院对于跨境侵权行为进行审判的经验,我国在对于跨境侵权行为规制时,可以发展出一套“影响因素”标准对于实质性专利侵权行为进行判定。根据该标准,如果行为人跨境实施专利技术的行为对于权利人在国内的专利许可或者实施活动造成实质性的影响,则即使其部分实施专利行为发生在境外,也构成专利侵权。因此,即使行为人在境内实施专利行为并非完全覆盖系争专利的全部技术特征,也将构成专利侵权。对于专利权域外效力问题,专利法尚无需突破地域性要求,因为仅针对境内行为进行侵权判定已可规制实质性而非形式性的境内侵权行为。另外,即使判定跨境行为构成专利侵权,在赔偿数额上也应当仅以境内行为部分所造成的市场损害金额作为依据,而不应延及境外行为所产生的市场效益,原因在于境外市场效益是否合法以及如何分配应当根据所在国的专利法来进行判定。
对于判定专利侵权实质性的影响因素,可以结合技术因素和经济因素两方面来考察。在技术因素方面,如果在美国境内实施的部分是产品专利技术的设备、零部件或者方法专利技术的某些步骤,特别是体现专利创造性的技术特征,而这些技术特征将专利权利要求区别于现有技术,则构成判定其侵权的技术因素,可以认定其构成专利侵权,可以采用“技术效果标准(technology-based effect tests)” 。B33在具体判定侵权行为时要注重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在境内实施行为的技术重要性判断上,针对产品专利或者系统设备专利要采用“控制与收益性使用标准(control and beneficial use test)”,B34对于整体系统的控制性部件而非单纯的数据处理服务器是否在境内作为判定专利侵权的技术因素进行考察。在2005年NTP案中,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认为即使有部分产品部件位置在国外(该案中为加拿大),但是美国作为整体系统投入服务的场所,就可以认定为侵权行为地,因此构成对美国专利权的侵犯。而认定场所的标准是对系统的控制和使用获得收益的地点位于美国境内即可。其次,对于专利技术相对于现有技术具有创造性的“可专利技术特征标准(patentably distinctive test)” ,B35将最体现专利权利要求创造性的产品零部件所在地作为侵权行为地,也就是将区别技术特征(与现有技术相区别)覆盖的产品部件所在国作为侵权行为发生的国家。再次,在认定技术因素时,应当同等对待方法专利和产品专利,并且在产品专利中不能对实物产品和数据产品进行区别对待。B36对于产品专利和方法专利的区别对待不符合专利法的立法原意,在认定跨境专利侵权行为时不应当进行这样的区别对待。
此外,如果境外专利实施行为对于权利人对国内市场的经济利益造成显著影响,那么专利法将具有约束力。对于构成显著影响的情形,包括专利权销售专利产品数额的减少、损失潜在的颁发专利许可机会以及稀释了被许可人销售专利产品的市场份额等情况,B37不能仅根据部分实施行为发生在境外而认为其不构成侵权,如果构成显著影响,仍然需要承担侵权责任。
三、专利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倒置
(一)云计算专利侵权诉讼举证困难
专利侵权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对于云计算专利权能否得到有效保护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云计算技术专利通常属于方法专利,其技术特征由实施该技术的步骤组成,而实施该步骤的过程均在网络计算服务提供商的控制之下,即处于其作为经营信息和技术信息保密状态之下。作为专利权人,要通过正常手段获得作为对方秘密信息的技术实施情况,并与方法专利步骤进行详细比对以判断是否构成侵权是相当困难的。B38因此,专利权人更为倾向于利用专利制度中对于举证责任倒置的有利规定,从而提高赢得专利诉讼的机会。
作为举证责任倒置的法律依据,《专利法》第61条第1款规定,“专利侵权纠纷涉及新产品制造方法的发明专利的,制造同样产品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提供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的证明”。因此,只要方法专利所获得产品属于新产品,并且能够证明被告所生产的产品与方法专利所获得的产品属于同样的产品,那么被告应当承担证明其使用的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的责任,否则将要承担败诉的不利后果。该条款看似为云计算专利权利人减轻了证明责任,其实有利于其主张专利权。但是,由于云计算技术具有网络化和数字化的特点,因此,在适用举证倒置问题上存在诸多法律问题亟待解决。
首先,对于“产品”的定义,能否将以代码形式出现的信息产品认定为该条款中的产品存在疑义。普遍认为,在宏观上或者微观上具有空间结构的物质属于专利法上所规定的产品,包括机器设备或者化合物等。B39作为云计算专利实施所产生的结果,计算机软件代码和数据并不能成为专利法上的产品,也阻碍了将其认定为作为举证责任倒置法律要件的产品。值得注意的是,将信息产品纳入产品部件已经得到司法案例的支持,特别是上面提到的美国法院在2007年AT&T案中对信息产品能够构成专利产品零部件方面作出了认定,因此,如果拓宽产品范围或者允许产品零部件作为构成要件,则云计算专利可以作为举证责任倒置的对象在专利侵权诉讼中加以适用。
其次,对于“新”产品的认定。新产品的认定问题是涉及方法专利举证责任倒置司法适用中的核心问题,同样也是疑难问题。《专利法》和TRIPS协定第34条对于新产品的含义均没有作出解释。2002年Merck案中认为,B40通过专利方法让产品具有更优品质的改变或者改进可以满足“新产品”的要求。我国司法机关对于新产品含义的界定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起初“新产品”被界定为在国内市场没有出现或者在国内没有生产出来的产品,并且该产品在组份、结构或者质量、性能和功能方面与现有产品存在明显差异。B41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司法解释将判断专利新颖性的标准适用到新产品的认定上,认为“产品或者制造产品的技术方案在专利申请日以前为国内外公众所知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产品不属于专利法第61条第1款规定的新产品”,因此不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但是,将申请日作为判断新产品的固定时间标准,不能适应云计算等快速发展的网络化计算服务领域,因为该领域的替代技术发展较快,在进行专利侵权诉讼时很可能已经出现了不同于专利方法但能够实现同样功能的计算方法,因此,将动摇以新产品作为举证责任倒置条件的法理基础,将不适当地扩大举证责任倒置适用的范围。
再次,对于“相同”产品的认定。我们固然在认定相同产品时可以根据产品组份、结构或者质量、性能、功能等因素加以考虑,对于不存在实质差异的产品作为相同产品加以认定,然而,在云计算领域,如果要认定“相同”产品可能存在更多的困难。应当注意到,认定相同产品的前提是产品本身应当是稳定的,一旦专利方法启动以后,可以按照方法步骤所要求的内容得到能够预期的稳定产品。但是对于云计算专利而言,方法专利中的若干步骤是由接受网络计算服务的客户或消费者来完成的,因此,体现为结果数据的信息产品具体构成是不能够预期的。对于信息产品,“相同”产品的认定不能简单地将产品结构加以比对,而必须从信息产品质量或者功能方面进行对比才能得出结论。
复次,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范围过于狭窄,并且可操作性较差。原告要利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都需要证明被告制造的产品与方法专利获得的产品相同,并且通常都仅限于直接获得的产品。此处直接获得的产品范围与专利法方法延伸保护中所延及的产品范围应当是相同的。根据我国现有法律的解释,对于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范围限制过于严格,导致专利权人举证责任倒置难以实现。我国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司法解释第13条明确规定,“对于使用专利方法获得的原始产品,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专利法第11条规定的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也应当成为举证责任倒置认定中进行比对的产品对象。由于该司法解释条文还规定:“对于将上述原始产品进一步加工、处理而获得后续产品的行为,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属于专利法第十一条规定的使用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因此,除原始产品以外的其他后续产品均不属于使用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考虑到云计算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是计算结果等数据信息,通常还需要经过一定的后续处理才能够提供给客户实际使用。这种处理可能是比较简单的加工,比如进行存储或者压缩处理;也有可能是比较复杂的处理,比如图形化处理或者转变为可远程传输信号等。药品制造方法中由于存在中间物质等环节,已经出现方法专利延伸保护不足和举证责任倒置困难的问题。B42如果因此就切断了方法专利与最终产品之间的联系,不认为其是方法专利直接获得的产品,将使得竞争对手轻而易举地绕开方法专利延伸保护的领域,最终导致专利权难以得到司法保护。
最后,云计算专利权人要获取方法专利所得到的产品本身可能比较困难。由于云计算中的数据和软件储存地点对于用户而言都是保密的,并且云计算服务提供商不愿意公开其数据来源,除服务提供商以外的第三人也缺乏相应的地域和物理信息,因此对于专利权人来说要进行调查取证,证明被控侵权人作为产品所提供数据或者软件的事实情况是非常困难的。2000年Engg案中法院认为,B43如果要提起专利侵权诉讼,专利权人必须要证明其在申请专利以前就有合理的机会和能力证明存在侵权行为。在调查涉嫌侵权的云计算服务行为时,并没有从公开渠道可以访问和调查云服务提供平台的程序、软件和物理机构。因此,云计算的保密性和不可确定性为专利权人通过举证责任倒置进行诉讼维权带来了很多困难和挑战。
(二)实质性举证困难与举证责任倒置制度的选择
云计算方法专利在侵权诉讼过程中所产生举证责任倒置法律障碍等问题,是由于其技术网络化属性带来的。我们必须把握技术发展和竞争的特点,从实质上把握举证责任倒置制度产生的法律基础和技术原因,从打破现有制度安排产生的思维定式束缚,解决举证倒置制度适用方面的困难,从制度完善方面寻求突破。
首先,可以拓展“产品”范围或者增加产品部件作为认定依据。作为构成表面证据的要素,“产品”概念是对被告所生产的能够进行交易并具有经济价值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法律概括,但是其概括得未必准确。对于不能纳入传统产品范畴的某些材料,但是又构成经济价值的主要来源,比如可以装载到计算机并为人所利用的软件或者数据信息,应当对其作为“产品”或者产品部件进行类推适用。对于云计算技术等产生信息产品的方法专利能够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问题,必须对产品的含义进行拓展。另外一种可供选择的制度设计是将产品零部件或者产品组件作为认定依据,而计算机软件或者信息数据作为产品组件得到法律认可的障碍较少,原因在于其是实现产品技术功能的重要部件,而单独作为产品尚存一定困难。
其次,选择根据TRIPS协定第34条第1款第(a)项进行举证责任倒置立法。TRIPS协定第34条在方法专利的举证责任给予WTO各成员相应的义务,但是成员实际上可以在其允许的范围加以适当选择。我国目前是根据该条第1款第(a)项内容进行立法,但是考虑到“新产品”等举证责任倒置法律要件的设置而引发的证明困难和实质正义缺失,因此,可以考虑根据TRIPS协定第34条第1款第(b)项进行立法。TRIPS协定第34条规定,在涉及产品制造方法专利民事诉讼中,法院有权要求被告证明获取相同产品的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并负举证责任。在可供选择的两种情形中,我国选择了看似较为简便的第(a)项。但是,对于云计算方法专利(也包括药品专利等领域)而言,新产品要求并不容易得到证明。因此,该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无助于云计算方法专利的有效保护。我国在专利立法中可以考虑改为采用TRIPS协定第34条第1款第(b)项的规定,如果该相同产品有实质可能是以该工艺生产的,而专利权人又不能通过合理的努力确定实际使用的工艺,则被告要承担举证责任。采用第(b)项立法,可以避免由于难以对“新产品”概念进行界定而导致的困境。B44我国如果仍然坚持采用第(a)项作为立法依据,应灵活确定“新产品”认定时间界限,不能一概以申请日作为标准。如果起诉时间距离申请日已经5年以上,则应当以产品实际投入市场日开始计算。若投入市场时已经出现了替代制造方法或者产品替代制造商,则被告使用方法专利的概率大为下降,不应当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
再次,拓宽“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的范围。现有司法解释对于产品的解释过于狭窄,应当在借鉴美国专利法立法例的基础上,结合相关判例的经验合理加以确定。美国专利法第271条第(g)款规定,依照专利方法获得的“产品只要没有在实质上被后来的方法所改变”或者“产品成为另一项产品的不重要的和非实质的组成部分”即可。英国法院通常采用“本质消亡检验”标准(the loss of identity test)。B45根据该规则,除非后续步骤实质性地改变了依照方法专利获得产品的本性,依照专利方法获得的产品并不会因为后续处理就确定不再是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我国在确定方法专利延伸保护范围和举证责任倒置比对产品范围时,应当突破专利法条款上关于直接获得或者制造的文字规定,转而寻求让保护范围拓展到在实质上并未改变产品性质或者功能的后续处理措施之后的产品形态,使得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具有在云计算专利侵权诉讼中得到应用的可能性。
复次,合理确定举证责任与商业秘密权利界限。TRIPS协定第34条第3款规定“在举出相反证据时,应考虑被告保护其生产和商业秘密的合法权益”,因此,在实体上和程序上合理划分举证责任和商业秘密权益之间的边界非常重要。在举证程序上可以在两个方面进行制度优化:其一,其在披露证据的人员范围方面应当只提交给法院以及法院指定的技术专家,并且尽可能排除向原告及其员工披露。法院固然可以“责令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鉴定人、证人等诉讼参与人对被告的商业秘密承担保密义务”,也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要求“不得在公开开庭时出示”,但是只要原告及其员工接触了被告商业秘密,对于被告应当享有的商业竞争优势可能已经构成了损害。法院不仅要保护法律上规定权利,更要保护被告的合法利益(Legitimate interests),B46而商业利益应当在考虑范围之内。B47其二,考虑到对被告商业秘密的保护,其提出的证明制造产品方法的证据无需经过质证即可采行,防止商业秘密遭到泄漏。因此,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中被告提交证据“应当经过质证,方能采信”的规定不够合理,可能导致司法程序被滥用。国外对于举证责任倒置的司法理论认为,基于制造的产品对生产方法构成侵权的认定属于“可以用反证推翻的法律推定(juris tantum presumption)”。B48有鉴于此,英国2009年Generics (UK) Ltd. v. H Lundbeck A/S案中法院认为,B49通过被告可以在中间程序(interlocutory stage)提出反驳,无需向对方披露所提供的证据。法院甚至驳回了原告要求进行完整质证程序的请求,并认为可以直接作出不必举证责任倒置的裁决。
四、结 语
专利制度的正当性体现在促进技术发展,专利制度的改革动力也来自于技术发展。云计算等网络化技术近年来得到迅速发展,使得专利制度固有的侵权判定规则不能适应新的技术环境,形式上的侵权构成要件或者证明责任可能轻而易举地遭到被告规避,专利法规定的侵权责任也难以得到落实。专利法蕴含的权利法定主义原则固然使得立法机关进行的利益平衡得到较高程度的实现,然而随着技术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日益明显,专利立法者所设想的利益平衡格局将被打破,正如网络传播技术对著作权法所产生的挑战那样。严格按照专利法条文进行司法适用,特别是进行专利侵权判定,将陷入法律形式主义的误区,使得云计算等领域的专利权难以得到有效保护,也有违实质正义原则。专利制度的发展让我们避免面对技术变革所带来的冲击,并有效解决云计算专利保护的问题。从专利权人的角度来看,要避免维权困难,固然可以在专利权利要求撰写时采取比较谨慎的策略,使得单项权利要求所涉及的步骤能够为单个主体所完成,避免可能出现的证明侵权行为成立的困难程度的增加,但是,从立法者和司法者角度来说,制度漏洞仍然应当得到解决。我国必须在专利侵权判定制度上加以革新,以实现专利制度激励技术创新、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和增进社会福利的终极目标。
The Patent Infringement Judgment in Networking Technologie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tent on Cloud Computing Technology
LIU Qiang
Abstract:The trend of networking technologies represented by the cloud computing has brought new challenge to rules on patent infringement judgment and their applications. The divided infringement and extraterritorial infringement in the operation of networking technologies can barely be subject to patent protection scope in accordance with current rules, thus the defendant can escape the tortious liabilities. The reverse burden of proof doctrine in the process patent also fails to offer effective relief for patentees in networking technologies. The legal obstacle of remedies for patentees could not be foreseen and coped with during legislation, resulting in more difficulties for patentees than in traditional technology fields. Thus the formalism in patent infringement judgment should be overcome and the substantive judgment on patent infringement should be applied as the goal of value, so as to correct the imbalance of interest caused by networking technologies and to accomplish the aim and value of patent system.
Key words:networking technologies patent infringement judgment divided infringement extraterritorial infringement reverse burden of proo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