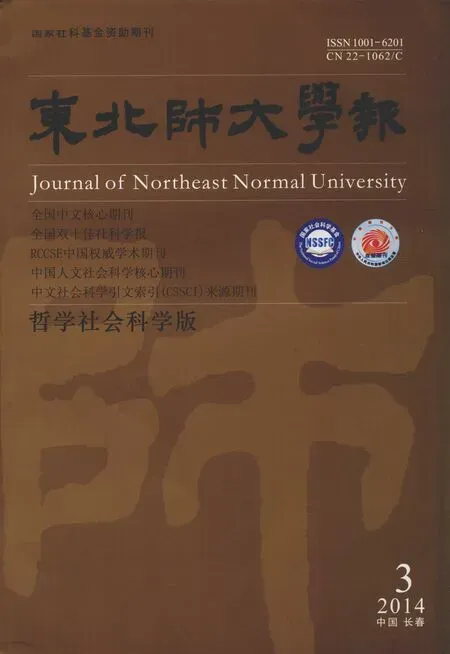北美汉学家韩南之研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以《金瓶梅》为例
张冰妍,王 确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24)
北美汉学家韩南之研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以《金瓶梅》为例
张冰妍,王 确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24)
韩南的《金瓶梅》研究,奠基于其自身的学术兴趣与他所处的学术环境。他的成果,展现出一种“学术本位”、“文学本位”的研究特色,从《金瓶梅》在中国古典小说史上的地位和意义的讨论出发,对《金瓶梅》的版本、素材来源等,进行了饶有成效的考察。他的研究,是以细密的文献考据和整体性的理论思维、历史思维相结合为特色的。
韩南;《金瓶梅》;小说史
《金瓶梅》诞生于明代万历中期,据明末史料笔记《寒花盦随笔》所载,它在问世之初,就曾被誉为“天下第一奇书”[1];到了明末天启年间,烟霞外史序通俗小说《韩湘子全传》时,将它与《三国志》(即《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相提并论,认为“《三国志》之森严”、“《水浒传》之奇变”、“《西游记》之谑虐”、“《金瓶梅》之亵淫”构成了四部“奇书”以及各自的艺术特色;而到了明清之际的李渔那里,《金瓶梅》与《三国》、《水浒》、《西游》并称“宇内四大奇书”的提法,正式确立下来[2]。正所谓名满天下,谤亦随之,作为一部“奇书”,《金瓶梅》因其不加节制的情色描写,向来备受非议;而它从整体上所呈现出的“曲终奏雅”、“始邪末正”的叙事倾向,又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人们为它辩护、正名的主要依据;况且,它对明代中期以后的社会生活生动、全面、深刻的呈现,对于当时以及后世的学者深入体认历史的动态,又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一切,都赋予了《金瓶梅》以丰厚的文化底蕴和艺术魅力,使它不仅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中华文化圈中影响深远,而且远渡重洋,在西方文化界引发广泛的关注和极大的兴趣。
据相关学者考察,《金瓶梅》在问世不到半个世纪后,就流传到了日本,目前在日本可见的最早的《金瓶梅》版本表明,至迟在1643年,它就被来华僧侣携带回国。18世纪上半叶以后,《金瓶梅》在朝鲜、越南也流传开来。鸦片战争以后,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传递空前频繁,《金瓶梅》大概是这一时期较早传入西方的中国小说,它在1853年就有了法文选译本,随后德文译本、英文译本、俄文译本、捷克文译本、斯拉夫文译本等相继问世。《金瓶梅》在西方引起巨大反响,它虽然价格昂贵,但销量极大,被视为“通向未知的中国哥伦布的航船”,是一部“世界名著”。从《金瓶梅》在西方的流传及其评价来看,它在西方人眼中的地位,甚至比在本土文化中还要高。人们把它作为认识中国的一个窗口,看成是中国传统小说的典范。它的负面因素,如其淋漓尽致的情色描写,甚至也被看作抵达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案例。本文以著名西方汉学家韩南的《金瓶梅》研究为例,展示西方文化视野中的《金瓶梅》及其研究概貌。
一、韩南的《金瓶梅》情结与渊源
韩南(Patrick Hanan)是西方汉学界成就极为突出的重要学者。他于1927出生在新西兰,1948年毕业于新西兰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49年获得英国文学硕士学位。此后到英国伦敦大学读书,又获得一个学士学位。后来,他考入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一边攻读博士学位,一边任教,其博士论文选题,就是《金瓶梅》。正是有关《金瓶梅》的系列研究,奠定了韩南在西方汉学界的学术地位。
根据韩南的自述,他在新西兰拿到英国文学硕士学位后,“为了进一步发展,我到了英国,准备在伦敦大学研究英国中古历史传奇小说,并以此作为博士论文。可是,就在修完博士课程,将要动笔写论文的时候,我读到了一些中国文学的翻译,这些充满奇异情调的作品,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以至于让我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重新上大学,从头学习中国古代文学。于是,从1950年到1953年,我在伦敦大学通过刻苦学习,又拿到一个学士学位”[3]110。也就是说,促使韩南下决心放弃原来的研究方向、“重新上大学”的因素,是一些充满“奇异情调”的中国文学译本。在这些中国文学翻译作品中,有没有《金瓶梅》?韩南没有详细提及,不过,从他后来的博士论文选题时的一些考量,我们可以略知一二。韩南说,“我本来选择的题目是《史记》,想从文学的角度对这部历史巨著进行研究。但是我的指导教授西蒙(Simon)认为研究《史记》的人太多了,建议我研究《金瓶梅》;当时学院的荣誉教授,著名翻译家亚瑟·威利(Arther Waley)也认为《金瓶梅》很值得研究。正好,我自己原也对这部小说很感兴趣,于是,就这样选定了博士论文的题目。”[3]110尽管韩南戏言自己不管是选择中国古代文学作为自己的专业,还是选择通俗小说作为主攻方向,都是很偶然的,但是,他所提及的“正好,我原也对这部小说很感兴趣”表明,至少在进入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写作博士论文以前,他就已经接触过《金瓶梅》,并且被它所洋溢着的“奇异情调”所吸引了。这是韩南从事《金瓶梅》研究的主要驱动力所在。
况且,在韩南的周围,有一大批优秀的汉学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他的选择。他的指导教授西蒙(中文名“西门华德”),是国际上知名的汉藏语学家,他是英籍德国人,早年曾发表过有关汉语语音和汉藏语比较研究的论文,引起过国际学术界的注意[4],与著名汉学家高本汉等学术交谊甚深——西蒙的建议,无疑是重要的,他对韩南以后的《金瓶梅》研究,在方法上也有重要的影响。韩南的《金瓶梅》以及中国白话小说史研究中所呈现出来的对于“语言”的敏感,一方面可能受到了西方叙事学理论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乃师的研究方向与方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而他所提到的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荣誉教授、著名翻译家亚瑟·威利,在西方汉学界更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翘楚,他一生翻译了大量的中国文学作品,对于中国古典诗歌、小说以及思想史等均有涉猎,在白居易、李白、袁枚研究方面,有突出的造诣。他虽然未曾翻译过《金瓶梅》,但对这部小说极为熟悉,曾有过专门的研究,1939年出版的英译本《金瓶梅》中,收入了他为该书撰写的导读文章《〈金瓶梅〉引言》。在这篇文章中,亚瑟·威利论及了关于金瓶梅的创作和流传情况、《金瓶梅》在明清时期被查禁的遭遇以及《金瓶梅》的创作时代环境等问题,显示出其对《金瓶梅》之创作、版本与流传等相关问题的熟悉。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他依据中国晚明时代通俗小说的兴起这一时代背景,讨论了以王世贞为代表的传统派文人集团与以袁宏道为首的公安派文人集团的区别,通过比较他们对于文学与时代、生活之关系的态度,以及他们对于通俗文学的理解之不同,指出了有关《金瓶梅》的作者为王世贞的说法的荒谬,并提出,这一名著的作者极有可能是“16世纪末‘写实’派领袖的作家徐渭”[5]。面对这样一位对《金瓶梅》有深厚研究积淀的重量级汉学家的建议,韩南确定将《金瓶梅》作为学位论文的选题,自然是在情理之中了。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说,韩南的《金瓶梅》情结并非偶然的,而是渊源有自。其一,他偶然间阅读到的一些具有“奇异情调”的中国文学译本所激起的惊奇感与学术兴趣,可以视作其后来的《金瓶梅》研究的触媒;而作为一部充斥着情色描写、作者身世和渊源又扑朔迷离的小说作品,《金瓶梅》恰好又满足了他对在西方“很少能够见到的”中国艳情小说的兴趣[3]112。其二,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学术环境,为其“定情”《金瓶梅》提供了外在的驱动力——其指导教授西蒙以及亚瑟·威利在学位论文选题方面的建议,对于一个攻读博士学位的年轻学者的影响自然是无须多言的,更重要的是,西蒙的研究方法,对其后来的研究产生了方法论上的持续影响;而亚瑟·威利在《金瓶梅》研究方面的造诣,则进一步确认了他的未来研究方向的价值。就这样,韩南开始了他的《金瓶梅》与中国之旅。
二、韩南《金瓶梅》研究的主要成果与观点
1957年,在开始攻读博士学位两年后,韩南来到中国,在北京进修了一年。在北京的一年里,他在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大图书馆接触到大量的文献材料,并且见到了心仪已久的郑振铎、傅惜华、吴晓铃等著名中国学者,他还在郑振铎的帮助之下,买到了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出版的明本《金瓶梅词话》——这套《金瓶梅》当时只印了1 000套,仅供专家学者研究参考使用,并不对外公开发售。在中国访学一年,加深了韩南对《金瓶梅》以及中国文化的认识,对他后来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韩南的《金瓶梅》研究,在西方汉学界起步较早。尽管前文提及,亚瑟·威利等学者已经就这部中国小说展开过一定的探索,但系统的研究并不多见。在韩南之前,西方汉学界更多从事《金瓶梅》的翻译,有关它的评论和介绍,也大都与翻译相关。如目前可见的最早的研究文献,是1940年Chang,Su-lee所撰写的《评伯纳尔·米阿尔译〈金瓶梅〉》,该文发表于《亚洲评论》杂志;在20世纪50年代,还有两篇关于《金瓶梅》的研究文献发表,一是约翰·毕晓普的《〈金瓶梅〉所含的一篇白话短篇小说》(《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954),二是梅仪慈的介绍《红楼梦》、《西游记》和《金瓶梅》的文章《中国小说》(《东方古典文学探索》,1959)。韩南于1960年撰写完成的博士论文《金瓶梅写作和金瓶梅探源研究》,应该是西方汉学界最早的系统研究《金瓶梅》的论著。后来,他将博士论文中的相关章节整理为《中国小说的里程碑》、《〈金瓶梅〉版本考》、《〈金瓶梅〉探源》三篇论文,相继发表出来——这些文章,是韩南《金瓶梅》研究的代表作。
在《中国小说的里程碑》一文中,韩南提出,《金瓶梅》是中国古典小说的杰作之一,它的价值和意义,应该放在文学史和小说史的层面加以考量。《金瓶梅》与早先的小说相比,其不同之处首先在于它是一种个人创作:“别的长篇小说都属于传统的章回体故事,有些小说至少是先前书面作品的改写本,而《金瓶梅》在很大程度上却是一个人想像出来的产品”;尽管《金瓶梅》有着庞杂的原始材料和素材来源,但“它并不怎么依赖于它的原始材料。作者决意将早先一部小说(即十四世纪的伟大侠义小说《水浒传》)的一个插曲加以扩展。作者所选用的场景意味着,他不必连篇累牍地引录传统性的材料……他只不过从早先和当时的文学作品中选用了那些适合他的需要的片段,而且随意加以改写”[6]。其次,《金瓶梅》体现出一种鲜明的“现实主义”创作倾向,它把叙事的重点,从传奇性的故事、事件,转向了能够反映出时代社会之横截面的人物形象塑造方面,这一方面使得整部小说充满了“协调感”,另一方面也深刻展现了明代中期以后的社会所流行的以“金钱”和“地位”为中心的时代思潮。从这种意义上说,韩南提出,《金瓶梅》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
为了论证《金瓶梅》所具有的“中国小说史的里程碑”的重要意义,韩南对《金瓶梅》的流传版本及其素材来源进行了极为细致、深入的研究。他在考察不同版本之异同的基础上,详细分析了《金瓶梅》的流传情况以及不同版本间的相互关系,并对其成书年代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而最能为其前述观点提供支撑的,是他关于《金瓶梅》素材来源的考察。在《〈金瓶梅〉探源》一文中,韩南通过大量的原始材料的爬梳,归纳出《金瓶梅》所抄录、化用过的素材的七个来源:长篇小说《水浒传》、白话短篇小说与公案小说、文言色情短篇小说、宋史、戏曲、俗曲、说唱文学。通读这篇文章,我们能够发现,《金瓶梅》对于前代文学作品素材的使用是异常丰富、驳杂的,这使得它看起来类似于一个“文学小古董的怪异集合”。然而,韩南的目的并不在于仅仅指出《金瓶梅》引用了那些陈旧的文学素材,而在于考察《金瓶梅》如何使用这些素材,创造性地写作出一部在小说史上据有划时代意义的典范性作品的过程。他说:“重要的不是引用本身,而是它的性质和目的……只有当我们探究它们怎样和为什么这样被运用时,它们才会有助于对《金瓶梅》成书的理解。”[7]也就是说,《金瓶梅》与传统的章回体长篇小说故事相比,其特异性并不在于广泛地使用了已有的文学素材,而在于处理素材的方法。韩南认为,虽然《金瓶梅》所引用的文学素材较之前代小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几乎遍及“明代文学的全部领域”,但是它通过有效的剪裁、严密的组织,使得整部小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内在的一致性”——所有的材料都是“为人物描写增加深度”,这是对其在《中国小说的里程碑》一文中所提出的观点的有力论证:《金瓶梅》是一部文人个体创造出来的新型小说,它在小说观念、创作方法以及形式探索方面,都对中国小说史做出了有力的突破。
从整体上纵览韩南的《金瓶梅》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他的探索,立足于扎实的文献和史料考据功夫,又具有整体性的理论思维和历史视野,能够从琐碎的文献考据中超拔出来,俯瞰《金瓶梅》的成书过程,因而能发前人之所未发,得出具有突破性和启示意义的观点和结论。这在他展开研究的20世纪50年代,是尤为难得一见的。这种研究特色,只有放在比较中,才能够显现得更加透彻。
三、从中国之旅看韩南的《金瓶梅》研究
韩南的中国之旅,虽然短暂,但收获巨大。从韩南后来发表的一系列关于《金瓶梅》的研究论文来看,他在中国访学的一年中,所获的成果,更多呈现为文献、资料上的收获,而不是学术观念、方法上的启迪。从韩南与同时代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的比较中,能够清晰地看到他的研究的特性。
前文提及,不论是在传统时代,还是近现代以后,中国学者最关注的,大多不在于《金瓶梅》作为一部“小说”所呈现出的文学史意义,而是它的主题和创作观念、意图。比如在明清时期,人们议论最多的,是《金瓶梅》究竟是一部淫书、诲淫诲盗的下流作品,还是一部通过展现欲望的放纵过程及其后果来讽世刺世、劝善惩恶的上乘“奇书”[8]。这种道德化的文学评判方式,一直延续到近现代时期。
在韩南来华的1957年,正值中国国内学术界《金瓶梅》研究的一个小高潮。1956年初和1957年,毛泽东相继发表了一些有关《金瓶梅》的言论和评价,诸如《金瓶梅》“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不可不看”、“《金瓶梅》可供参考”等。正因此,国内的《金瓶梅》研究稍有复苏,并且,韩南所提到的在郑振铎帮助下所破例买到的影印版明本《金瓶梅词话》,就是在1957年出版发行的。韩南在中国停留了一年,对于中国学术界关于《金瓶梅》的研究情形,应该是极为熟悉的。他所接触到的郑振铎、傅惜华、吴晓铃等学者,大都发表过有关《金瓶梅》的研究论著,尤其是吴晓铃先生,对其所进行的指导与帮助是最大的。韩南在一篇回忆纪念文章里写道,他在为马悦然博士举行的招待宴会上,偶遇吴晓铃。吴先生在获悉他以《金瓶梅》为研究方向时,表现出了超乎他的想像的关心和热情:“他开始问我一连串犀利的问题,表明了他在这个研究课题上的博学。他还叫我到他家去,这样对我的研究课题可以细谈……甚至给我安排了去他家的时间,并告诉我去他家的路线。”几天以后,韩南去拜访了吴晓铃,他说,“不用说,我深感荣幸。那是我和对《金瓶梅》极为熟悉(而且在学术上对此深有研究)的人的讨论,一次我最受教益最受鼓舞的讨论”。接下来的时间里,韩南多次与吴晓铃先生交谈、讨论,并从中深受启发,以至于多年以后,忆及这段经历,他依旧深情地感叹说:“吴先生天生是导师。”[9]在韩南后来的论著中,这些中国学者的论著,大都被引用、提及。但是,在1957年,真正引人瞩目的有关《金瓶梅》的研究,并不是这些先生的成果。相反,这几位先生在这一时段均为发表过相关研究成果,在国内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的,是文学批评家李长之和李希凡两位先生针锋相对的论争。李长之在发表于《文艺报》1957年第3期上的《现实主义与中国现实主义的形成》一文中提出,中国文学只有到了《金瓶梅》,“才开始有那么大的气魄去暴露封建社会的罪恶整体,才开始以一个家庭为中心的故事写出了一百多回的长篇,才开始触及了那么广阔的社会面,才开始以一个人的创作经营而不是凭借民间传统的积累而写出了一部统一风格的巨著,才开始有了鲜明的不同于浪漫主义作风的踏踏实实的力透纸背的现实主义作品”。他将《金瓶梅》标举为中国文学“严格的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而李希凡则在《文艺报》1957年第38期上发表了《〈水浒〉和〈金瓶梅〉在我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中的地位》一文,与李长之展开了言辞激烈的辩论。他认为,《金瓶梅》对于社会生活的表现,是“客观主义”而不是“现实主义”的,它与《水浒传》、《红楼梦》所取得的文学成就是无法比拟的。这一论争,在当时的国内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在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领域有关“现实主义”的讨论中,也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
韩南不可能没有了解到这些观点和讨论,一个直接的例证就是,在《中国小说的里程碑》一文中,他在肯定《金瓶梅》所体现出的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新型小说观时,格外指出,对于这种创作倾向,使用“现实主义”、“日常生活”、“社会的横截面”等术语来概括是可以的,“其中的每一个术语从文字上来说都符合这部小说的情况”,然而,“至于为‘现实主义’这个词花费时间去下定义是否值得,都是令人怀疑的”[6]。——这句概括,显然是有为而发,针对中国学术界围绕《金瓶梅》而展开的有关“现实主义”的讨论所作出的批评。这种批评的学术态度,表明韩南和同时代的中国学者不同的研究旨趣和研究方法——韩南更多从文学、小说本身来考察《金瓶梅》,他关于《金瓶梅》与其诞生的时代的社会生活的关系的考察,也是为了论证《金瓶梅》在小说史上的“里程碑”意义而进行的,即《金瓶梅》体现出的关注时代、关注社会生活的创作倾向,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一次观念的突破与创新。而中国学者,则往往根据道德的、政治的需要,将《金瓶梅》放在更为宏阔的社会文化的整体语境中加以讨论,李长之、李希凡等人,所讨论的虽然是《金瓶梅》的创作倾向、技巧问题,但其背后蕴含的是意识形态的冲突与矛盾。
韩南在他的研究成果中,对当时中国《金瓶梅》研究最前沿、最热门的话题的有意回避甚至是尖锐批评,显示出了中西学者在学术观念、旨趣和方法上的不同,由此也凸显出了韩南本人的学术旨趣。
四、余论:韩南《金瓶梅》研究的中国回响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韩南的《金瓶梅》研究及其有关中国古典小说、近代文学研究的成果,相继被译介到中文学界,在中国内地和港台学者中引发了巨大的反响。他对《金瓶梅》所进行的以考据为方法、以文学为本位的研究,对中国学者的影响尤其值得关注。
首先,在中国学者眼中,《金瓶梅》是一部“世情小说”,既有此定位,对《金瓶梅》所展开的研究,也就局限在透过小说看世情、世相,以《金瓶梅》为素材,考察明代中期社会生活。而韩南的研究,突出了文学本位,把《金瓶梅》作为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小说”进行探究,这种方法对中国学界关于《金瓶梅》的认识、定位以及研究观念,都有不可估量的影响。他对《金瓶梅》所做的“中国小说的里程碑”的定位,被广泛接受,人们对《金瓶梅》的研究,也开始转向以文学为本位的小说阐释和考察。其次,韩南所做的《金瓶梅》“探源”研究的方法,也在中国学术界引起过研究方法论上的反思。韩南在考察《金瓶梅》素材来源时所涉及的文献范围之广泛、数量之巨大,是前人所不能比肩的,有中国学者称,基于此种文献考据功夫的研究成果,即使放在当下,也是极具启发意义的。近年来,韩南的李渔研究、鲁迅研究等,又相继被中国学者所认识、肯定和接受。他的学术成就,在世界汉学研究领域是引人瞩目的。透过韩南,我们既能及时了解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识、理解和形象建构,又能在学术观念、方法上获得有益的启迪。
[1]吴晗.吴晗史学论著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35.
[2]苏兴.苏兴学术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95-197.
[3]张宏生.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韩南教授访问记[J].文学遗产,1998(3).
[4]冯蒸.国外西藏研究概况1949—1978[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137.
[5]阿瑟·戴维·维利.《金瓶梅》引言[A].朱一玄,王汝梅.金瓶梅古今研究集成[C].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1999:802-808.
[6]韩南.《金瓶梅》及其他[M].包振南,译.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
[7]韩南.《金瓶梅》探源[A].徐朔方,编选.金瓶梅西方论文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37.
[8]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C].北京:中华书局,1987:230.
[9]韩南.忆吴晓铃[A].张子清,译,张子清,等主编.文化相聚——美国作家、学者和艺术家在中国[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42-143.
On the Influenc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by North American Sinologist Hanan's Study——Illustrated by the case of The Golden Lotus
ZHANG Bin-yan,WANG Que
(College of Literature,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China)
The study of The Golden Lotus written by Han Nan is based on his own academic interests and the academia he situated in.His studies are with the features of“academic ontology”and“literary ontology”.Started from discussing The Golden Lotus's statue and significance in China's ancient novel history,he conducted a series of fruitful exploration from the angles of the editions and the source of the materials.His study is featured of finely textual research of the literatures and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etical thinking and historical concerns.
HanNan;Jin Ping Mei;Novel History
I207.419
A
1001-6201(2014)03-0149-05
[责任编辑:张树武]
2014-02-21
张冰妍(1982-),女,辽宁锦州人,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王确(1954-),男,吉林蛟河人,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