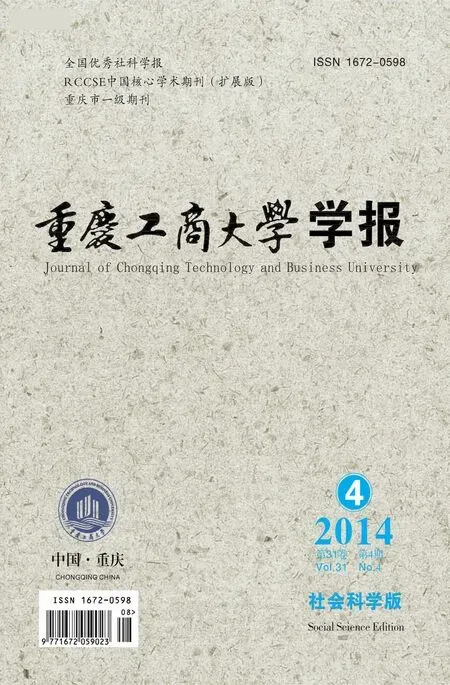生态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陈 武
(1.淮南联合大学,安徽淮南232001;2.南京理工大学,江苏南京210094)
生态文明作为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标志着人类在探索科学发展过程中取得了重大突破。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四中全会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五位一体”建设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提升到更高的战略层面。十八届三中全会再一次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中国共产党人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方法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然而在取得辉煌业绩的背后也滋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尤其是在生态环境污染方面,陷入了重蹈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覆辙的危险。伴随着生态运动的蓬勃发展,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思考世界生态危机的根源,探索消除生态危机根本途径,于是生态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
一、生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生态马克思主义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1979年,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教授本·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第一次提出“生态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80年代中国学者开始研究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1986年王瑾教授在《教学与研究》上发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社会主义”》一文,第一次将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引介到中国。2006年《新华文摘》第5期转载段忠桥教授在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中介绍“生态马克思主义”流派一文,从此以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译法便逐渐被中国学界所采纳。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的出现以及中国学术界对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理论的重视,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始被中国学术界广为接受和认可。综合这三十年间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当前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比较有影响的主要有三种主流思想。
二、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思想
(一)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捍卫与澄明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的领军式代表人物。他最大的理论贡献是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辩护和澄明。数十年来,马克思常常被指责为没有生态意识,甚至被认为是一位反生态的思想家。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詹姆斯·奥康纳也曾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把生态破坏置于资本积累和社会经济转型理论的中心位置……他们不仅没有准确预见资本在‘自然的稀缺性’面前重构自身的能力,也没有预见资本所具有的保护资源和防止或消除污染的能力。”[1]为此,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研读了马克思的原著,在2000年出版的专著《马克思的生态学》一书中指出“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种深刻的、真正系统的生态(指今天所使用的这个词中所有积极含义)世界观,而且这种生态观是来源于他的唯物主义”[2],首次提出了“马克思的生态学”概念,并在马克思与生态学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联系。福斯特将马克思与李比希、达尔文、马尔萨斯等生态学家相提并论,勾画了马克思的生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轮廓,挖掘出了马克思的物质变换裂缝概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不仅符合生态学的定义和原则,而且超越了生态学的狭义性,在更加广泛的人类与自然之中以及人类社会内部实践了生态学的基本原则。
(二)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的批判
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的批判是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共识,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是世界生态危机的总根源,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根除生态危机。福斯特认为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就不可能摆脱生态危机,因此“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不仅要求消除剥削劳动的特殊关系,而且要求‘以现代科学和工业手段合理地管理人与自然间的物质变换关系为媒介’超越人与土地之间的异化关系,即资本主义之所以存在的最终基础或最根本的前提”[3],因为“生态和资本主义是相互对立的两个领域,这种对立不是表现在每一实例之中,而是作为一个整体表现在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之中”[4]。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内的生态改革象其他的改革一样是有限的,因为一旦开始讨论这个制度自身的根本性质时,这些讨论马上就会被既得利益者打断。”[5]因此,摆脱生态危机的唯一出路就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为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福斯特仔细研读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三卷,发现马克思用大量篇幅论证了资本主义大规模工业和大规模农业的发展都是建立在对工人和土地的掠夺的基础之上。福斯特概括马克思的物质变换裂缝理论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变换由于未能满足自然的生命规律要求的土壤营养成分的系统还原,最终导致土壤构成要素的异化、物质变换产生裂缝”[6]。福斯特认为“物质变换断裂”在世界范围的扩展是造成全球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而断裂的形成则是生态帝国主义行为的必然结果。资本的本性是不断的积累,而积累则要打破自然规律,突破资源的限制,为了使发展不至停歇,需要源源不断地提供资源供给。
福斯特将资本主义这种片面追求利润的生产方式称为全球性的“踏轮磨房的生产方式”,企业投资人及经营者出于竞争的需要必然投入大量的财富用于扩大生产规模、进行技术革新。这种生产方式与地球基本生态循环不相协调,必然导致全球范围的生态危机。
(三)生态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
20世纪9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在环境问题上的伪善和传统社会主义的失败,是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生态社会主义者主张“人类中心主义”,反对“生态中心主义”,提倡用生态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生态社会主义者大多以人类为中心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的思想为解决环境问题提供了最好的思路,因而,主张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来理解生态问题。英国大卫·佩珀认为,实现生态马克思主义从绿到红的升华,既要克服现代环境主义乌托邦的缺陷,又要在构建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渗透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分析。美国詹姆斯·奥康纳认为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在于前者为实现生态均衡发展积聚了更充足的正能量。德国萨拉·萨卡、布鲁诺·科恩曾著文呼吁“所有那些关心人类与自然命运的人们能够接受上述思想,并与其他人一道,努力成为生态社会主义理想的积极实践者。”[7]然而在实际的制度建设中又难免陷入了乌托邦性。夏鑫博士指出“在现实生态运动中,佩珀认为首要任务是实现社会公正,而不是把生态运动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资本主义制度。佩珀实际上是以实现社会公正的经济目标取代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目标。”[8]这就注定了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只能是乌托邦的空想。
三、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新世纪、新阶段,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局限性逐渐显现出来,但无可否认,一些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了当代生态环境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生态学等现代理论有机结合,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注入了新的活力。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思想是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对我国在进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深刻启示。
(一)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大理论武器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提供行动指南,为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长期而系统的建设工程,建设过程中,一方面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理论,用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指导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生态学等现代理论相结合,系统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合理性,诠释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当代品质。另一方面,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理论学习,培育生态价值观念,不断提高生态执政理念,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社会。
(二)生态文明建设的道路: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道路问题,是关系到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体现着无产阶级自觉能动性的实践活动和实践过程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在一大就明确了中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方向和道路。在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邓小平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科学命题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发展的道路。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上增加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在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上增加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要求。[9]体现了在中国最大实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背景下党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新境界。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是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的践行者。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发展至今,已潜在具有向生态社会主义转型的趋势。奥康纳理解的生态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主义管理方式与生态保护的结合。在他看来,社会主义与生态学是密切联系的,大多数生态问题的原因和结果甚至它们的解决方法都是国家的和国际性的,社会主义的国家管理方式有利于生态问题的解决。保罗·斯威齐认为,我们应该“沿着社会主义方向改造社会关系,这种社会的支配力量不是追逐利润而是满足人民的真正需要和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要求。”[10]
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吸取教训,深刻总结党在探索、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遇到的挫折和付出的代价,另一方面要总结经验,正确看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中,我们锐意推进经济体制和各方面的改革,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人民生活明显改善的伟大成果。
(三)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保障: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党的十八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11]新世纪、新阶段,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就是要进一步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制度建设。
生态马克思主义主张建立基层民主,即把主要权力都交给基层组织,实行分散化和基层自治。这一主张虽然从理论到实践都有其不足之处,但实行基层民主并非一无是处。党的十六大报告把扩大基层民主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精辟地阐述扩大基层民主的内容、方法和领域等重要问题。新世纪新阶段,各种利益关系呈现多样化和复杂化,广大民众的政治诉求在不断提高,为保障基层群众充分行使当家做主的政治权利,必须进一步完善我国基层民主制度,使广大人民能够当家做主,在自治组织中充分行使自治权,对所在基层组织的社会事务实行民主自治。生态文明背景下的经济体制改革,要克服生态马克思主义“零增长”经济思想的乌托邦性[12]。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发展生态经济,构建绿色经济发展模式。妥善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将发展速度、资源的可开发度和社会的可承受度统一起来,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13]。社会主义的生态文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是我国生态文化建设的核心价值观。加强生态文化建设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化思想为指导,积极创造满足广大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新产品,理顺各种社会关系,在全社会营造一种尊重自然、爱护生态、保护环境、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文化氛围。
[1]Jame s O’Connor.Natural Causes[M].The Guildford Press,1998:124.
[2]J.B.Foster.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M].刘仁胜,肖峰,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viii.
[3] J.B.Foster.Marx’s Ecology[M].Monthly Review Press,2000:176-177.
[4]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耿建新,宋兴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
[5][6]J·B·Foster.Marx’s Ecology[M].Monthly Review Press,2002:40,156.
[7]萨拉·萨卡,布鲁诺·科恩.生态社会主义还是野蛮堕落?——一种对资本主义的新批判[J].陈慧,林震,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3):146.
[8]夏鑫.试论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J].社会主义研究,2008(4):144.
[9][11]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OL].Http://www.gov.cn/ldhd/2012-11/17/content_2268826.htm.
[10]Paul M.Sweezy.The Guilt of Capitalism[J].Monthly Review,1997,49(2):61.
[12]金鑫.论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当代发展[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4,28(3).
[13]胡锦涛.中国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文明发展道路[R/OL].http://news.sina.com.cn/c/2007-06-09/104011989438s.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