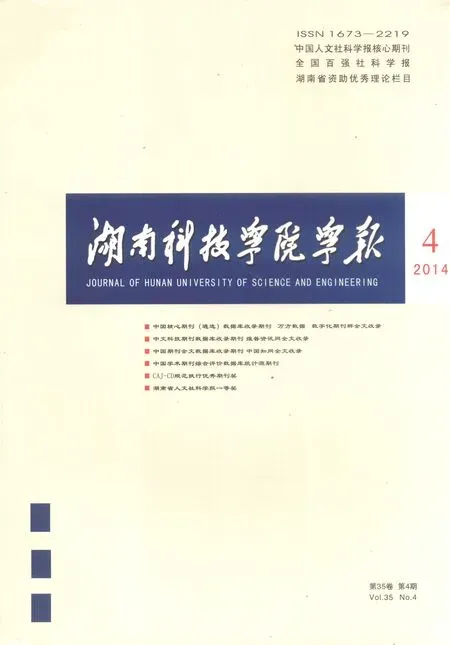川端文学的佛教思想与审美特质
施晓霞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外国语学院,广东 珠海 519090)
佛教虽然诞生于印度,但流传到中国之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也影响到了日本,影响到了川端文学。川端康成与佛教的亲密关系,既有由作家个人经验而形成的个体认知形态与审美取向的影响,也有本民族文化的积淀和传统文化的熏陶。[1]
首先,川端家族自祖上开始就与佛教有着深厚的渊源,祖祖辈辈对佛教的虔诚皈依决定了幼年和少年时期的川端的成长环境,浓郁的佛教氛围已经深深地浸透了他的心灵,成为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另外,川端自幼经历了太多一般孩子所不应承受的生死离别,他所体验和目睹的尽是人间的生老病死。青年以后的川端又接连遭遇了爱情的致命打击,亲眼目睹了关东大地震的惨烈,这一切又进一步加深了他人生无常的感觉。加之幼年时期的川端曾经拥有超自然的能力,上大学之后又接触了流行一时的心灵学说,使他相信灵魂的存在,并对佛教的来世之说充满了好奇和憧憬。这一系列经历都促成了川端与佛教的亲近。
另一方面,日本也是一个佛教氛围极其浓厚的国家,从国民的人生观、审美观到日常生活的婚丧嫁娶以及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到处都渗透着浓郁的佛教气息。特别是大正时期的日本文学界,出现了堪称“佛教文学热”的状况,在这样的民族文化语境下成长起来的川端,自然也会把自幼受到的佛教的浸染体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中。[2]当然,川端文学中的佛教因素,也并非原原本本地吸纳日本佛教,而是从他自身的审美取向和艺术理念出发,并根据文学创作的实际需要,进行了有选择的吸收和创造性的发挥。总而言之,佛教既丰富了川端文学的表现方式,也扩展了川端文学的艺术素材,增添了川端文学的审美韵味,最终形成了川端文学别具一格的审美特质。
一 佛教的“无常”观念与川端文学的“哀伤之美”
川端文学与佛教的第一个结合点即是死亡。如前所述,川端自幼经历了太多骨肉亲人的死亡,他从出生到离世,始终没有摆脱为亲友送终的命运,“参加葬礼的名人”冠其一生。这样的经历对川端的心理成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他总是背负着死亡的阴影。从川端踏上文学道路伊始,佛教就作为一种关于死亡的思想影响着他的人生和创作。从处女作开始,川端文学就一直贯穿着或明或暗的死亡主题和佛教思想的投影。实际上,死亡只是“无常”的一种极端形式。佛教认为人生有“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求不得、怨憎会、五盛阴。其中既包括个体人生的无常,也有世间万物的无常。在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期间的川端,曾经经历过一段刻骨铭心的初恋。然而这次恋爱在他心灵中留下的只是天际闪电般的无常感觉和经年不愈的伤痛。因为就在万事俱备,只等完婚之时,川端却突然遭到了简单、短促、不明缘由的悔婚。川端终其一生也没能了解造成悔婚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唯一的解释就只能是世事无常。
“诸行无常”的观念映射到川端的文学作品中,使得他的每一部作品,每一处字里行间都挥之不去人世间的种种哀伤与不幸。在川端文学中所出现的生命、爱情乃至存在本身都是无常的,似乎都在呼吸转瞬之间,其中的芸芸众生也同川端一样遭遇到家庭的丧失、孤儿的命运或者爱情的突变等等。然而,川端毕竟不是一个佛教徒,而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因此,在倾其毕生岁月的文学创作中,他不仅仅是以文学艺术的手段来感叹和低吟人生和世间的无常,更重要的是,他以文学艺术的手段来表现他在佛教中所获得的拯救和从佛教中得到的安慰和解脱,并在其中贯注其内心深处对超越死亡的渴望和永生不灭的憧憬。因此说,川端文学所体现的艺术美,给人印象最深和最动人的美当属“哀伤之美”。
二 佛教的“色空”观念与川端文学的“纯净之美”
《心经》(全称《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是佛教三藏十二部为数近万的经典中字数最少却内涵丰厚、流传最广的经典。《心经》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色”是外在的物质现象,“空”是内在的精神本质,“色”的极致就是“空”,“空”的表现就是“色”。[3]小说家希望通过文字传达出来的是表象背后的美,是抽象的本质,是“空”,然而要达于“空”,也离不开“色”。“空即是色”就是说空乃色之空,因而也不能离色而求空。
“色空”观念在川端的文学世界里,曲折地反映为自然即人,人即自然,二者平等合一,共同构成一个整体。也就是说,客观世界的具体的物象与主观世界的抽象的精神在本质上并无分别,大自然的草木雨雪与人类的心灵情感是一致的、相通的。[4]比如,《雪国》中川端所选取的自然风物——覆盖山野的积雪、曝晒绉纱的阳光、倾泻而下的银河等,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皆为“空净”之物。首先,它们都具有“性空”的本质。阳光银河自不必说,都是无法捕捉、没有实体的。实际上,雪也同样是自然界中最具有虚无特性的物质,它看似实体,却可以化为水、蒸为气,消失得无影无踪。经过这一系列性本空无的自然的熏陶,人的心灵也必然会顺应自然,归于虚空。另一方面,积雪有纯净无暇的洁白,阳光有消毒除秽的功能,银河有沁人心肺的宁静。对凡间世人来说,它们都具有净化心灵、抚平躁动的作用,使人烦扰顿消,物我双泯。川端正是通过体悟“色空相即”的佛理来实现向自然的回归和与自然的融合,同时洗去尘世的烦恼,达到心灵的澄澈,可以说佛教的“色空”观念为川端文学开创了一派“纯净之美”。
三 禅宗的“以心传心”观念与川端文学的“余情之美”
进入日本的禅宗,以其直觉性的思维迅速与日本民族诗性的审美思维结合起来,特别是其“以心传心、不立文字”的主张,与日本文学自古以来所崇尚的“余情美”息息相通,因此也深得立足传统文化的川端的心。禅宗对于语言文字的局限性有着充分的认识,常用诸如“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之类的话来形容一种无法言说的心灵体验;而“余情”是日本文学传统的审美趣味和艺术特色,是指蕴藏于行为或表象背后却给人以深刻感动的风韵和情趣,是一种言外之情。[5]“余情”的审美理论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深受禅理的影响,其讲求余韵、表现闲寂、展示直觉等特色,正是禅趣所赋予的。
这一观点也触发了川端的文学思考,他曾经明确地指出:“直观要比论理重要。真理不立文字而在言外。”[6]因此,川端在文学创作中总是力求以有限的文字表达无限的意蕴,总是有意无意地追求一种“文已尽而意有余”的境界。这使得川端文学在创作形式上产生了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他的小说似乎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戛然而止。《古都》中千重子和苗子的命运结局显然包含着继续发展的可能,《雪国》《名人》《湖》等都是中途搁笔之作,《水晶幻想》在杂志上分两次刊登,都没有写完。作品如何结尾、在哪结尾、何时结尾,好像连川端自己也不明确,似乎顺其自然地停在某处,只要日后没有再续写就算是终结了。这种言辞已止而意犹未尽的特点,正是深谙禅门的川端在文学创作中追求韵外之致,而造成的“余情之美”。
四 佛教的“轮回转生”观念与川端文学的“永恒之美”
如前所述,川端自幼以来的人生经历使他产生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认识,那就是:生是虚空,死是必然;生是无常,死是永恒。这一认识又在对佛法的领会中得到了印证和加强。佛教的“轮回转生”观念使川端相信灵魂的轮回转生,相信精神的永世长存,相信在肉身消亡之后美的发现将恒久不灭。不过,融合在川端文学中的轮回转生思想,并不完全等同于佛教中的“轮回转生”,这主要体现在川端对“因果报应”和“苦谛”的排斥。首先,川端对于佛教的轮回转生中“善恶祸福、因果报应”的道德说教成分十分厌恶,认为“因果报应”说是佛教轮回转生思想的“污点”。[7]另外,所谓的“苦谛”是佛教对社会人生以及自然环境所作的价值判断,认为世俗世界的一切本性都是“苦”。然而,读者从川端文学中所描绘的轮回转生中不但感受不到苦,相反却能够体会到安宁和希望,因此说,川端心中的轮回转生是一个童话般纯净美好的世界。
在微型小说《不死》中川端为读者讲诉了一个奇异的轮回转生故事。老人新太郎和少女美佐子以情人的姿态相互依偎着漫步,但他们的年龄至少相差60岁。这个开头很令人好奇。更奇妙的是,他们居然犹如一阵微风径直穿过了高尔夫球场的高架铁丝网。原来,他们是一对重逢的情侣,55年前少女被迫分手而投海殉情了。小说对于死亡有着不同于常识的全新理解。少女请求老人要好好活下去:“倘使新太郎死了,这个世界就不会再有人像新太郎那样回忆起美佐子了。美佐子不就真的完全死去了吗?”可见,这里对死亡的界定并不是肉身的消逝,而是只要还存在记忆和回想,被记忆的人就没有死。也就是说,精神的消亡才是真正的死亡。而且,少女因死亡而永葆了18岁的青春,老人却因活着而变得老朽。可见,死亡比生存更加美好。这两个人一个经历了死,一个面对着死,但他们都从未想过死亡有可能通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内心都不存在对死亡转生的担忧和恐惧。小说的最后,少女突然悟出老人也已成故人,她大为惊诧:“死了吗?是真的吗?……在阴府里咱们怎么没能相会呢?奇怪啊。来,是生是死,让我们再一次穿过树干试试看。要是新太郎是死了,咱们就可以一起钻进树里了。”这个情节不仅仅没有死亡的凄惨,反而充满了温暖和希望。老人死亡的信息带给少女的,非但不是悲痛,反而是意外的喜悦,因为死亡就是新生的开端,在一个新的轮回中,他们又可以在一起了。最后,两人双双消失在树干里,再也没有出来。这样,一对在此生被隔绝了55年的恋人终于通过转生而实现了永不分离的愿望,恰如小说的题目那样共同走向了永恒。川端笔下的转生是那么的美好,甚至令人向往,与佛教的轮回转生从同一个轨迹延伸向了不同的方向。
可以说,在佛法的启迪下,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川端,在否定“苦谛”和“因果报应”的同时,从佛教的轮回转生中发掘并汲取了唯美的和永恒的因素,把对生命不死的希求和对灵魂不灭的渴望转化为了对艺术永恒的追求,并最终形成了川端文学的另一种的艺术魅力——“永恒之美”。
川端康成一生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关于川端文学中的佛教思想也有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过不同程度的关注,然而大多都是从其文学叙事的层面加以关注,却很少从其思想源头深入探究。应该说,佛教因素进入川端文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在川端康成文学创作的不同时期和阶段,比如青年时期刚刚开始文学创作的川端的佛教思想和战后回归传统时期、晚年颓废虚无时期的川端的佛教思想显然是有所差异的。但是,川端康成自身的佛教思想反映在川端文学中所形成的川端文学独特的审美特质和艺术特征却是始终一贯的。因为深信佛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学”,所以川端文学中的佛教思想,也早已脱离了佛教思想的教条。在川端看来,佛教似乎跟伦理学、社会学等毫无关系,而只应该用文学的眼光来看待。[8]正是由于这一独特的美学见地,形成了川端文学独特的审美特质和艺术特征。
[1]张国安.执拗的爱美之心·川端康成传[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社,1994.
[2]谭晶华.川端康成传[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
[3]任继愈.宗教词典[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4]周阅.川端康成文学的文化学研究——以东方文化为中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5][日]铃木大拙.禅与日本文化[M].陶刚,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
[6][日]川端康成.川端康成文集·抒情歌[M].叶渭渠,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7]陈多友,谭冰.试论川端康成初期文学中的佛教思想[J].日语学习与研究,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