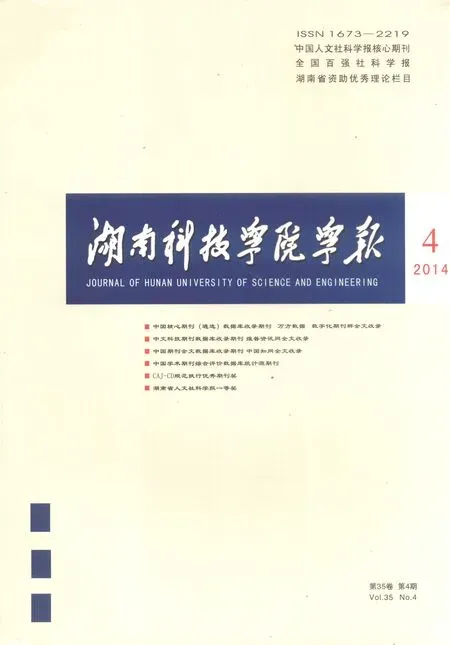审美人类学视野下的湘西婚嫁习俗
蒋海霞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6)
一 审美人类学的概述
审美人类学是运用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审美现象的一种新型交叉型学科。大约从 20世纪 70年代审美人类学在国外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在西方,关于美学与人类学交叉研究主要形成了以‘人类学美学’、‘美学人类学’、‘审美人类学’名称出现的研究群体,一些围绕以人类学研究方法开拓新的研究艺术的方向以及关注非西方族群的审美偏好等问题的相关著述相继问世,并引发了一系列关于人类学与美学交叉研究的前沿论题。”[1]审美人类学资源的开发主要有三个途径:“一方面来自古籍文献,是由书面化的语言构成的文化遗产;另一方面来自生活和现实,是物态化和观念化的精神,文化存在;再一方面来自出土文物和古代文化遗存,是物态化的古代文化的表征。”[2]审美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之一是以少数民族为主带有区域性、民族性、民间性的生活状况,包括该民族当地的宗教信仰、节日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以及婚嫁习俗。
审美与艺术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许许多多的日常生活场景其实就是某种审美和艺术的本真表达。如湘西少数民族婚恋习俗中的对歌和哭嫁作为一种习俗事象,凝聚着该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素质,充分地表现着该民族的传统文化特点,渗透着一种共同的民族审美心态和审美观念。
正如赵德利先生所言:“民俗是广大民众在生存活动中创造出来的具有物质与精神两栖性的生活文化。它的鲜丽的形式结构承载着人类的善真追求,表现出美的特性。”[3]P114从审美人类学的视角,去分析一个民族的传统习俗在其审美意蕴和社会文化功能中所蕴含的生命律动,无疑对该民族及其整体文化的认识、理解有着重要而深刻的意义。
二 湘西苗族恋爱习俗中的“对歌”及其审美文化阐释
湘西素有“歌海之称”。湘西少数民族如苗族、土家族,恋爱时以歌为媒的对歌习俗和结婚时哀婉动人的哭嫁风俗从远古一直流传至今。这些习俗凝聚着民族精神与民族审美、彰显着民族生命, 使得民族之美源远流长。
(一)湘西苗族青年恋爱时“以歌传情”的对歌习俗
湘西各少数民族的人们都能歌善舞,或轻柔婉转,或高亢激昂,未见其人先听见其歌声,以歌传情。恋爱的青年男女则以对歌表明心迹、通情达意。正如清代顾奎光所说:“凡耕作出入, 男女同行, 无拘亲疏, 道途相遇, 不分男女……以歌为媒。”[4]P170他们从结识到相会再到求婚都少不了歌声,可以说这一系列的过程都是在对歌中完成的。
首先是相识。男方要准备很多风趣的歌旁敲侧击,逗得姑娘们忍俊不禁,从而开始对歌。少数民族同姓不开亲,所以结交之初首先是问姓,当然不是直接问“你姓什么?”而是以歌开头,如《问姓歌》:
(女)刺枣不认识茅草,茅草不认识香椿。晓得是老表还是兄弟,只怕错认了自家的人。
(男)看着脚板编草鞋,大概不会同了边。就是相同也是好,多个姐妹结亲眷。
然后含蓄委婉地自报家门,相同便恭敬而别,不同便开始交往,以对歌表示相互间的倾慕。
其次是约会。双方结识之后,便相约在某时某地相会,第一次相会又有第一次相会的歌,比如用“才开编的草鞋”、“才上扎开织的布”,比喻才建立的关系。青年们对自己的爱情生活十分谨慎,他们用对歌的形式别出心裁地试探,考验对方的品性、智愚和是否忠贞。若是冬天则相对而坐,烧起篝火,对歌盘歌。总之,以歌抒情,以歌言志,话如流水,歌似鸟鸣,情声交融,别有一番雅味。
最后是求婚。经过若干次相会,青年们用歌声倾吐爱慕之情,以至求婚,歌愈对愈浓,心便愈谈愈拢,相互的了解也愈来愈深,逐渐成为亲密的恋人。
青年们出口成歌、以歌为媒互通心曲,一是缘于湘西没有自己的文字,青年男女只有借助歌声咏唱对意中人的倾慕。二是因为湘西位于重山之中,传统的山地农业经济,给青年男女提供了大量直接接触的契机。因此,在各种节日庆典或是上山劳动之时,青年男女便通过歌声来寻找婚恋对象。“歌声遥起乱山中,男女樵苏唱和同,只是鸾凤求匹偶,自由婚姻最开通。”[5]P435-436生动地描述了湘西少数民族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情形。
沈从文是湘西文坛大家,他的每一部作品都诠释着湘西的至纯至美,对歌的习俗更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渗透在他的作品中。
总之,对歌在湘西青年恋爱的过程中,扮演了至高无上的角色。这是一种健康的、独特的恋爱方式,以歌为媒、以歌交心、以歌传情,纯净脱俗,排斥了以金钱物质为基础的庸俗风气。这种独特的恋爱表达方式本身就是一种绝妙的民间艺术,它的思想性和技巧性极强,具有惊人的魅力。
(二)湘西苗族对歌习俗的审美文化阐释
歌德曾说:“古人的最高原则是意蕴,而成功的艺术处理的最高成就是美。”[6]P22审美意蕴是在审美活动中产生,是人与客观事物互相沟通、互相契合的产物,因而它必须受审美主体的审美意识和社会文化环境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即使是同一种客观事物,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圈、不同的生活氛围中成为审美对象,其意蕴也不尽相同。对歌的审美意蕴精髓,不仅在于歌词或赋或比或兴,新鲜隽永,意境深远更在于它是湘西男女展示爱情观、审美观、伦理观等的多姿多彩的音乐风情画卷,蕴含着丰富的审美趣味和审美情感。
对歌作为一种文化形态,集中体现了少数民族人民的心理素质,突出地表达了湘西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如《只爱与郎共枕头》:“打开房门真忧愁,白布帐子配红沟,家中什么都不爱,只爱与郎共枕头。”表达更为直白的要属《日日夜夜泪洗面》:“郎子别妹正一年,日日夜夜泪洗面,若把泪水积一起,足足能灌三亩田。”[7]P109少数民族的女子敢于表达自己的情感需求,这些品质已形成为一种崇高的民族精神,建立起一种具有丰富内涵的民族道德。它蕴涵着丰富的民族审美情趣,它不仅是民族审美的物化,更是生命力量和内在本质的具体体现。在当今它们依旧焕发着青春与活力,并且与时俱进。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对歌作为一种自觉的交流方式,作为审美交流的载体,是研究社会制度、文化现象的重要视点。对解决主体性问题、实现与他者交流有着重大的意义。这种对歌作为一种传统习俗,在内容上有着自己的体系,在形式上有着自己的特色,充分体现了该习俗的审美人类学价值。
三 湘西土家族婚姻习俗中的“哭嫁”及其审美文化阐释
(一)湘西土家族结婚时“哀婉动人”的哭嫁习俗
《哭嫁歌》是土家族的习俗民歌,是1957年土家族确认后第一部出版的民间文学作品。土家族哭嫁歌历史悠久,特色鲜明,风格别致,清代改土归流后,哭嫁作为土家族婚俗的主要内容而盛行。土家族姑娘的结婚喜庆之日是用哭声来迎接的,充分体现了土家族独特的文化意蕴。哭嫁,源于妇女婚姻的不自由,她们用哭嫁的形式,来控诉罪恶的婚姻制度。哭嫁歌词,通过不断地丰富和完善,有些已经成为固定格式在民间流传,它是土家女儿的集体创作。
哭嫁水平的高低是衡量姑娘们才智和贤德的一个重要标准。哭词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其主要内容分为:追忆母女情,诉说离别苦,感谢养育恩,拜托兄嫂事。哭词有固定的,也有即兴的,节奏自由,曲调朴素,语气词特定。如母女对哭的歌词有:
女:娘呀娘,我要走了呐,再帮娘呀梳把头,曾记鬓发野花艳,何时额头起了苦瓜皱,摇篮还在耳边响,娘为女儿摇白了头。
娘:铜锣花轿催女走,好多话儿没说够,女儿去哎娘难留,往后日子重开头,孝敬父母勤持家,夫妻恩爱度春秋。
如姐妹对哭唱的有:
姐:梭罗树上十二丫,我们同根又同丫;今朝姊妹要分离,离开绣楼好孤单!
妹:“梭罗树上十二丫,我们同父又同娘;今朝姐妹要离开,难舍难分情难断!
还有如“哭父”的歌词有:
天上星多月不明,爹爹为我苦费心, 爹的恩情说不尽,提起话头言难尽。
一怕我们受饥饿,二怕我们生疾病;三怕穿戴比人丑,披星戴月费苦心。
四怕我们无文化,送进学堂把书念; 把你女儿养成人,花钱费米恩情深。
一尺五寸把女盘,只差拿来口中衔; 艰苦岁月费时日,挨冻受饿费心肠!
女儿错为菜子命,枉自父母费苦心; 我今离别父母去,内心难过泪淋淋!
为女不得孝双亲,难把父母到终身; 水里点灯灯不明,空来世间枉为人!
新娘通过哭嫁歌,把自己自悲、自怜、自苦的心情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土家族新娘的哭嫁歌,既是无力保持女权的哀号,又是土家女儿聪明才智的表现。寨上相好的姊妹、表亲姊妹、未出阁的姑娘都会来陪着,倾吐相念难舍之情。如新娘哭到:“我的姐啊,我生的命丑我命薄啊,今儿的日子么,我梳头抹给敬祖公,我梳头抹给敬祖婆,我梳头抹给离祖公啊,我梳头抹给离祖婆啊,我的姐啊,我不走他要拖我的手啊,我不行他要赶我的脚啊。”从土家族姑娘那令人肝肠寸断的哭嫁声中,能深深地感受到她内心的痛苦和对娘家人的依恋。清代土家族诗人彭秋谭对此有明确的记载:“其嫁女上头之日,择女八九人,与女共十人为一席。是日父母、兄嫂,诸姑及九女执衣牵手,依次而歌,女亦依次酬之……十姊妹歌,恋亲恩,伤别离,歌为曼声,甚哀,泪随声下,是‘竹披’遗意也。”[8]P256具体描述了当时土家族“哭嫁”的场景。描写土家族哭嫁歌场景的诗词也屡见不鲜。如:
新梳高髻学簪花,姣泪盈盈洒碧纱。(田泰斗)
十姊妹歌歌太悲,别娘顿足泪沾衣。(彭秋潭)
侬今上轿哭声哀,父母深情丢不开。(彭勇功)
湘西土家族哭嫁歌结构严谨,篇幅巨大,内容丰富。随着时代的变迁,湘西土家族婚俗虽有变化,但婚俗中以歌代哭,以哭伴乐的习俗却仍然盛行,只是内容稍有不同,其婚嫁仪式中不仅充满了离别牵挂,还带有喜悦欢乐的群众文化娱乐氛围。因此,如今的哭嫁仅是一种仪式,且新娘所哭对象都会赠送红包,以期望夫妻恩爱。
(二)湘西土家族哭嫁习俗的审美文化阐释。
从审美人类学的角度看,改土归流之前土家族地区的社会生活形态早已存在着促使哭嫁歌萌芽的诸多因素,如历史上土家族存在过抢婚习俗,还盛行“还骨种”(姑妈之女必嫁舅舅之子)和“坐床”(兄娶弟妇或弟娶嫂子)的婚姻习俗,这些都是造成土家族女性婚姻悲剧的重要原因。“改土归流之后,土家族地区‘以歌为媒’的原始性自主婚姻彻底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包办买卖婚姻,从而把土家族女性推向了更悲惨的境地,土家族女性的婚姻悲剧也就体现出相当的普遍性,这就是哭嫁歌在此时期大量产生的根本原因。”[8]P257再加上土家族大部分人居住的地方都是群山连绵、地势偏僻,交通非常不便,姑娘出嫁的地方,近到二至三里,远则数百里,天隔一方,一别之后不知何时是归期,思前想后,不禁潸然落泪。
从新娘的这种哭嫁行为,我们能感觉到她们愤慨的心情和反抗的情绪。哭嫁,首先就是对父每包办婚姻的不满和消积的抗争,它是一种取得人们同情和抗争的手段,这种无力的抗争新娘从出嫁前一直到坐上花轿或到婆家。从她们的哭喊声中,我们能读到新娘的三种心情,一是婚嫁他人,全凭媒妁之言,不是自身情愿,埋怨父母把她嫁给他人;二是不愿离开自己的父母,姐妹及亲人,出嫁意味着失去在娘家受宠的地位;三是嫁到别人家里,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 不知男家经济情况和为人如何,有一种作媳妇的恐惧。土家族新娘为婚姻的不自由呐喊、哭泣, 也可以认为是为远古曾有过而现在却失去的女权而斗争。
以女子口头文学方式传承的土家族哭嫁歌,哭时声韵融为一体、优美流畅、动听感人,富有极强的文学艺术感染力。对于研究土家族的社会历史、文化、风土民情、民族宗教信仰、语言及音乐艺术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哭嫁歌情真意切、虽喜亦悲,凸显出土家族婚俗与众不同的独特文化现象,具有广泛的社会传承性。凝聚了土家族妇女千百年来的集体智慧,于情寓理,接受婚嫁歌洗礼,净化灵魂情操,传统优良的美德教育在婚嫁歌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具有强烈的思想性和价值取向,也蕴含着丰富的审美情感。
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是最能体现这个民族心理和民族审美的文化现象。“对歌”和“哭嫁”是湘西少数民族苗族、土家族婚嫁习俗中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民俗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有着深刻的文化内蕴和强大的生命力。这种习俗经过长时间的洗礼至今还保留在人们的记忆里,具有极强的艺术感召力。人们对历史的这种选择性记忆,充分表明在今天的现实环境下,“对歌”和“哭嫁”这种婚恋习俗仍然具有其审美人类学研究的价值。
[1]向丽.国外审美人类学的发展动态[J].国外社会科学,2010,(2):59-68.
[2]张利群.论中国古代审美人类学资源的利用[J].东方丛刊,2001,(4):68.
[3]赵德利.民俗审美论纲[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4).
[4]顾奎光.永顺府志[Z].湖南地方志少数民族史料(乾隆二十八年抄刻本).长沙:岳麓书社,1991.
[5]石启贵.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6][德]黑格尔.美学(第一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7]编委会.湘西歌谣大观[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0.
[8]陈素娥.诗性的湘西——湘西审美文化阐释[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