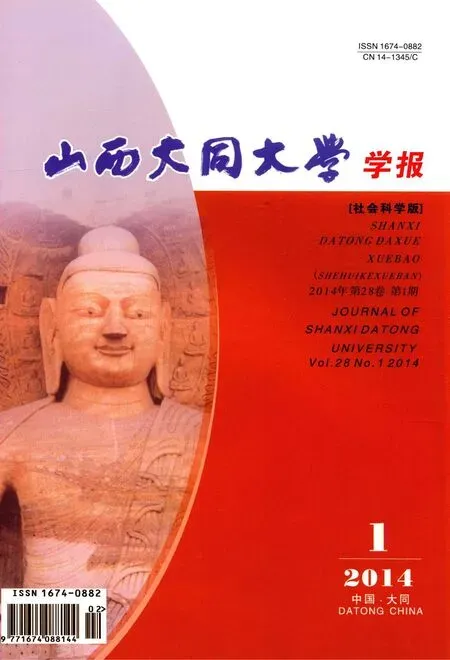中国当代艺术与文化形象研究
赫 云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南京 江苏 210096)
文化形象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代表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整体形象。中国当代艺术在相对包容的文化环境中逐步走向了前台,被世界文化所认识,成为全球当代艺术文化中不可缺少和无法代替的一部分。中国当代艺术表现或反映了本土的文化与社会等问题,也让西方世界看到一个民族当下的文化形象。这是中国当代艺术在世界艺术文化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但是,西方某些中心主义论却有另一种企图。他们希望除了自己的中心之外有一个被他们虚设的、边缘的客体,作为一种文化陪衬或补充。他们极力想打造一个异样的、不真实的、但符合他们意识形态需要的“他者”文化形象,如同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中所指出的“东方形象”一样,以此来保持西方自己的中心主义的地位。西方这个理论话语往往是隐藏在西方现代或后现代文化理论中的。因此,这是中国当代艺术家和理论家需要警觉的问题,中国当代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应努力构建一个真实的中国文化形象,尤其对意识形态、文化形象等问题要敏感一些,要有批判精神,并以一种平等的、对话的方式对待和了解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艺术与文化,从而塑造一个具有积极的价值意义的文化形象,使中国当代艺术承担起在当今世界文化语境中应有的文化责任。当然,在实际的中国当代艺术现象中情况比较复杂,参杂着各种不同的因素,需要认真梳理和研究。就中国当代艺术中塑造的“形象”来看,大致有三种,这三种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中国当代艺术的基本而复杂的走向。由此提出一个问题,即在国际文化视野和语境中,中国当代艺术隐含了“文化形象”的文化身份问题。这个问题又会引出一个“建构”的问题,即建构属于中国文化逻辑的中国当代艺术理论和创作模式,这才是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真正走向。
一、主题与隐形的文化形象
作为在世界文化语境里发展起来的中国当代艺术,不可避免地要面临很多当代性的问题,既是回应当下世界文化现象,也是提出本土文化问题。在当今世界意识形态极其复杂的格局下,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形象,俨然是一个绝对的、当代性的文化大问题。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形象,是通过文化、艺术、政治、经济等各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显现出来的。中国当代艺术以“整体”的方式在国际语境中的出场,它们所显现的鲜活艺术图式与艺术形态,都不同程度地、不同角度地体现了中国文化形象的方方面面。在中国当代艺术20多年的发展中,这已经成为一个事实。
从当下获得的世界地位和国际声誉来看,中国当代艺术经历了非常坎坷的发展道路。一些中国当代艺术家,在跨文化的视野中,努力在作品塑造的艺术形象和艺术主题中,展现一个正在发展中的本土文化形象。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有着正面价值的文化形象。当然,中国当代艺术通过艺术主题或艺术形象塑造的文化形象,不是作为一个主要的显学式的任务实现的,而是通过思考和提出一些当代文化、社会问题实现的,其作品中显现的文化立场、方式态度等方面,几乎是隐性的。也就是说是隐匿在图式形象背后的。一般而言,隐含文化形象正面价值的中国当代艺术,主要是50后、60后的一些中国当代艺术家所创作的作品。他们以相对严肃的、不亢不卑的创作态度,以中国传统的“士族”文化的批判精神,表达、提出和思考中国自己的文化、社会与历史问题。我们看到有很多当代艺术作品,在此方面给我们提供了良好的例证。李路明的《烟云》系列作品,叙述了一类人与特殊时代相重叠时的青春成长历程。我们都知道,50后的当代艺术家,他们出生于“文革”前的50年代,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时期”、“高考潮”、“8·5 艺术新潮”、“后 89 市场经济”等不同的历史阶段。这种不平凡的“经历”,让他们反思身处其中的“历史”。李路明作为50后的当代艺术家,有他自己的思考和认识方式,他认为最值得记忆的是“青春期”。正是由于相伴于那些特殊时期的“青春期”,才使它有值得记忆的特殊意义。作者深深地意识到,他的青春期与“文革”相伴,而“文革”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深刻地烙进了他们这一代人的“灵魂深处”。这成了他创作当代艺术的一个逻辑起点和前提。诚然这个时期的所有中国人,虽然各自的遭遇不同,但基本能够正常地认识与对待那一段历史。他们在描述那一段特殊的历史事件时,多数具有反思性和自省性,他们必然会用严肃和认真的方式去把握那一段历史“记忆”,并从中引起人们深刻的反思与回应。只是不同的艺术家,有不同的把握方式和表达方式,主题和形象也会因此而不同。油画作品《烟云》系列,正是画家李路明用自己青春记忆去重叠那一段历史的镜像,以此把某种自省意识隐含其中,将个人的这种感悟与体验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去表达出来。这样,艺术家的个人“经验”被描述成为一个集体的记忆,自然地隐含了一个文化形象的集体描述和记忆。所以,《烟云》系列采用了有“历史感”的图式,即画面采用了“黑白”图式,这种黑白图式也是被人们认同的“历史感”的图像呈现方式。当然,作者也借用了西方当代艺术家、德国画家格哈德·里希特 (Gerhard Richter,1932-)的绘画技巧,使用了故意模糊形象的方式,让历史呈现在“历史”中,再用“镜像”方式让历史反射在当下语境中,使其对当下社会产生意义。不过李路明在技法语言上,也采用了中国画传统的“空白”元素作为绘画语言,他试图努力寻找一种“国际语言”来与西方艺术做一个交流和沟通。因为在西方的绘画语言中,画家必须将画面涂满颜色才算完成,否则被认为是没有完成的作品,而中国绘画艺术中,“空白”恰恰是一种追求意境的语言图式,这样一种“空白”图式的语言西方人难以理解。故此画家用“云”的方式作为涂满了颜色的“空白”语言图式,既满足了“空白”的语言图式,又满足了“涂满”颜色的观念,从而获得中西方都能理解和接受的“国际语言”图式。
在主题和艺术形象具有某种相似性质的当代艺术中,还有张晓刚的“大家庭”、“大风景”系列等当代艺术作品。张晓刚被称为中国当代艺术的“F4”,足见他的影响力非常之大。他的《大家庭》系列以“文革”的片段为主题,《大风景》以“文革”前的片段为主题。“片段”就是一个侧面的记录或记忆。《大家庭》的反思性和批判性相对外显。图像以旧照片的形式提出了一个深刻而尖锐“血统”问题以及阶级划分人性的问题,画面人物形象中以“色斑”与“红线”连接,暗示了这类问题。《大风景》的反思性转向了隐匿,画面没有“文革”时期的政治性符号,而采用了“文革”前的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符号,如高音喇叭,蓝墨水,日记本,招待所的陈设等,这些成为艺术家的特殊文化符号。也许艺术家是想对中国当代艺术中“70后”的“反讽”态度作一个回应。这类作品所体现的严肃性和反思性,以自省的批判精神对待一个特殊时期的历史事件或某种记忆,实际上传递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士志于道”的精神,肩负了某种对社会的责任,对文化精神的某种传承的责任。
当然不是所有的中国当代艺术家都采用了某种特殊时期的文化符号或政治符号,来表达对一段历史的反思和回应。中国当代艺术的社会责任,也体现在对当代社会现象的某种表达。如忻东旺的“农民工”系列、徐唯新的“矿工”系列,虽然与上述画家采用的“形象”不同,母题元素不同,但在本质上也是提出了当下的一些社会问题和新的生活现状。他们的图像所采用的“形象”是当下新的弱势群体,这些作品严肃地提出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这个特殊群体在当下的境遇问题,尽管艺术家无法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提出问题是当代艺术家的一种责任。“农民工”虽然带一个“工”字,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工人”,依然是农民的身份。包括徐唯新的“矿工”形象母题,实际上这个“矿工”群体也是农民身份形成的群体。农民工在城市中的身份地位,也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现实问题。关注农民工的生活命运,还体现了对另一个生活在即将“背井离乡”群体的关照。刘晓东的“三峡大移民”系列作品,以最直接的写生方式做出了表达。对当代“农民工”主题和形象的描述,反映了中国当代市场经济时代急需改变的现实问题,揭示了改革过程中的阵痛,显示了当代艺术家的敏感和责任。
历史的当代叙述、现实的当下叙事和严肃的文化态度必然要求艺术家作出正面价值的文化形象建构。这个隐匿在中国当代艺术中的文化形象提供给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形象,而不是扭曲的、异怪的、不真实的他者文化形象。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类的形象表达,是中国当代艺术家以自身的观点和文化逻辑,提出了中国自己的文化问题和社会问题,并非以西方某些意识形态或意向来塑造一个“东方主义”的他者文化形象,而取悦于西方某种企图的需要。这种表现和关注自己“事情”的文化态度和文化立场,使中国当代艺术显现出一个良性的发展趋势。
二、互为关系的文化特征
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和艺术形态都具备跨越时空的特性,并以自身的文化形态在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不同时代构筑的世界文化语境里进行对话、交流与沟通。不过在当代世界文化语境中,中西方对话是不平等的。针对这种现象,中国学界正在通过跨文化的交流、沟通以及相互理解等各种方式,努力打造一个能够正常对话的空间和渠道。多数的中国当代艺术,正是以本土文化形象的身份参与到世界文化系统中进行对话、交流与沟通的。这种对话的前提是需要对话者,在交流与沟通中,把对话的双方视为“互为关系”。即互为主体而充分肯定。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的生产过程中就双重地肯定了自己和另一个人。”[1]真正有责任有担当的中国当代艺术,正是以“互为关系”的方式,通过对自己文化的表达,既不以西方艺术唯首是瞻,又表达自己的文化立场和艺术理想。尽管《烟云》作品系列使用了里希特的某些表现语言方式与手段,但李路明仅仅是把里希特的方式作为手段,表达的却是中国本土文化意识与理念。李路明也并不是完全把里希特的方式照搬过来,他还把中国画中的“空白”理念征用在作品中,实际上改变了里希特的理念与方式。而且,李路明很明确地说过,他只是要寻找一种能够沟通的“国际化”的语言而已,使“他者”能够阅读,方便理解与沟通,也并没有失去自己的主体性。从哲学层面上说,他的这种做法就是把“他者”作为一个主体考虑进来的。我们可以称这种方式是“互为关系”的方式。“互为关系”的方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即“阴阳相抱”。传统文化的这个智慧对应西方当代文化的一个观点,就是哈贝马斯提出的“互为主体”(inter-subjectivity)。“互为主体”就是为了使双方平等,双方把对方视为主体,就是说把“他者”作为“主体”来看待或理解,从而导向某种认同或共识,即“达到理解的目标是导向某种认同。认同归于相互理解、共享知识、彼此信任、两相符合的主体间相互依存。”[2]哈贝马斯的话语机制反映了一种平等的话语权力和平等的对话平台。与哈贝马斯持相同观点的是巴赫金。他认为他者“不是物,不是无声的客体,这是另一个主体,另一个平等的‘我’,他应能自由地展示自己。而从观察、理解、发现这另一个‘我’,亦即‘人身上的人’的角度看,需要有一种对待他的特殊的方法——对话的方法。”[3]显然,无论是中国文化中的“阴阳相抱”,还是西方的“互为主体”,在很大的意义上符合中国当代艺术与世界当代艺术所进行对话的方式和态度。
中国当代艺术中有很多作品,借用了“他者”艺术表现方式和语言,来表达对自身文化与艺术形态的诉求,获得了相互沟通、相互理解和相互阐释的对话能力和对话机制。艺术语言仅仅是一种表述方式,是形而下的技术问题,是为了表达自己并与他者沟通和交流。刘晓东借用弗洛伊德绘画技术中的某些手段,阐释和提出了中国当代社会问题。他的《三峡大移民》系列作品获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也获得了他者文化的认同,还获得了艺术市场价值。另一方面,艺术语言的追求也可以向内,向民间艺术语言中汲取。张晓刚的《大家庭》和《大风景》系列,在处理方式和技法上融汇了中国民间绘画的一些元素,也借用了清代海派人物画的处理方式,当然也借用了一些西方造型元素以达到沟通和交流的可能。中国当代艺术家的这种处理方法,使我们看到了“能指”始终置于能指的位置,并不企图使它转换为“所指”,“能指”只作为对话平台,并不作为所指”的对话话语,故此征用“他者”的话语方式仅仅是为了沟通和交流的需要。我们也可以把这种方式理解为“互为文本”(Inter-texuality)。如同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在《符号学:意义分析研究》中认为的那样:“任何作品的本文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本文都是其它本文的吸收和转化。”[4]因而,中国当代艺术只有采取不卑不亢的文化态度和方式来阐释自己的文化,提出社会问题,方能获得与西方主流文化在同等位置上进行交流和沟通。
真正的具有批评精神的中国当代艺术,所体现出来的尊重他者的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的立场,符合全球文化进程的要求。很多有见地的中国当代艺术家,摆脱了早期不自信的模仿状态,以自己的文化形象和意识形态争取到了与西方主流话语平等地对话的空间。中国当代艺术家及其作品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文化立场和文化态度,在某种程度上也消解了西方中心主义话语的霸权性和侵略性,使中国当代艺术文化与西方主流艺术文化,逐步走向互为主体的文化交流的格局。当然,不是说完全取得了平等,也不是说中国当代艺术就不存在自身的问题。
三、误读引发文化形象的另类表达
中国当代艺术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往往比“立场”还突出。这并不是说立场次要了或不重要,立场永远是核心,态度也是立场的反映,但是态度可以使立场发生变异。尽管中国当代艺术家都会基于本土文化或意识形态的立场,但是由于态度与立场的错位,立场也就变味了。我们从一些痴呆、傻笑的图式形象中可以发展,由于作者态度趋向不同,使其所创造的这些形象遭致一些学者的诟病。
如果说早期出现的某些“痴呆”、“傻笑”图式形象,是为了表达“文革”特定的历史时期的某种使人性因压抑而变形的扭曲状态,显现出批判的话语锋芒,那么以后的图式中反复出现同一意义的形象,而且是抽去了特定的历史环境或社会背景的形象,就有些问题了,至少是态度上出了问题。作为抽离了“文革”特定的社会历史中的意识形态,使人扭曲或变异的的图式形象,对于当代性来说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即使有的艺术家试图通过“延异”的方式来修正并使其获得当下的意义,但这对于当下的语境来说,明显是一种形象“滞后”。然而这个“滞后”却被西方主流文化刻意“意识形态”化,并用“经济市场”与“双年展”机制,再倒卖回来给生产国,使一些艺术家欣喜若狂地误认为被“国际”化了。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倒卖是西方预设的意识形态陷阱。在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结构中,使审美文化发生开放性转向,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审美结构的空间扩展,多层面的视角被关注和审视,减除了传统审视的死角。审美、泛审美、非审美和审丑,都同时进入了文化理论和文化实践的层面中,更得到当代艺术家的纷纷认同。艺术不一定非得审美,任何东西都有可能成为“艺术”。“审丑”可能是最受人追捧的焦点。但是,由于对“审丑”的误读或过度的阐释,使一些当代艺术家误以为“审丑”就是表现“丑”。这就是我们看到一些当代艺术中,纷纷表现“丑”的形象图式的重要原因。“丑化”又与“大众文化”联姻,通过各种手段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的大众文化的消费现象。在一些80后甚至90后的当代艺术作品中,丑的艺术形态频繁涌现。“丑”与所谓的“暴力美学”再一次联姻,又使丑怪与恐怖的形象出现在当今人们的视野里。严格说来,这些“当代艺术”不是我们认为的真正意义上的当代艺术。表面上看,他们表现丑与暴力,具有“雷人”的批判性。似乎表现了“丑”与“暴力”就当属当代艺术的范畴了,实际这是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误解,这也成了对中国当代艺术的一种误导,更是对“审丑”的最大误读。审丑,不是表现丑,而是审视丑、评判丑。如同审美,不是表现美,而是审视美、评判美。审美和审丑是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是让人们在审视和评判中做出自己的选择,因而“审美”或“审丑”不是表现的问题,某种程度上,把“审丑”作为表现“丑”,是误读和滥用了批判性作为当代艺术的核心话语的理论,更是把文化形象异化为一个不真实的、虚假的文化形象。
因此,图式中被异化的形象是必须批判的。中国当代艺术中形成的两种不同的态度和表达方式,需要我们认真梳理和判断,需要深入研究当代艺术的思想和观念变化的原因,做出文化判断和价值判断。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中国当代艺术和艺术家,在文化理论上更为成熟,在意识形态上更为敏锐,在文化态度上更具有批判精神,在艺术观念和思想上更具当代性、探索性和思辨能力;我们希望更多的成熟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严肃地对待西方后现代的话语和理论,尽量减少因误读带来的困惑,使当代艺术形态和话语在当下的审美文化空间中,有效地影响人们的行为和意识,承担起批判的责任。我们也相信,中国当代艺术在审美文化层面,追求批判精神、解释人文关怀,使其在跨越未来的新时空中不但具有“当代性”,更能保持崇高的精神价值与本土文化品味。
四、结语
中国当代艺术图像中的形象与主题,不仅仅是一个形象的问题,它已经涉及到一个形象学的问题。在世界文化语境中,任何孤立的艺术形象都是不存在的,它必然是作为某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形象在世界文化语境中出场。中国当代艺术是对本土当下的社会文化、政治等问题的思考、追问,也是对中国文化当下诉求的表述。但是这都是我们自身的事情或文化问题,需要依照自身的文化逻辑和文化演进的路径,从中提出自己的问题,并以此作为中国当代艺术家的文化责任,承担起在世界语境中显示民族文化形象,乃至国家形象的重任。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德)哈贝马斯著,张博树译.交往与社会进化[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3](俄)巴赫金著,白春仁译.文本对话与人文[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4](法)朱丽娅·克里斯蒂娃著,白春仁译.符号学:意义分析研究[A].朱立元.现代西方美学史[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
——评《全球视野下的当代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