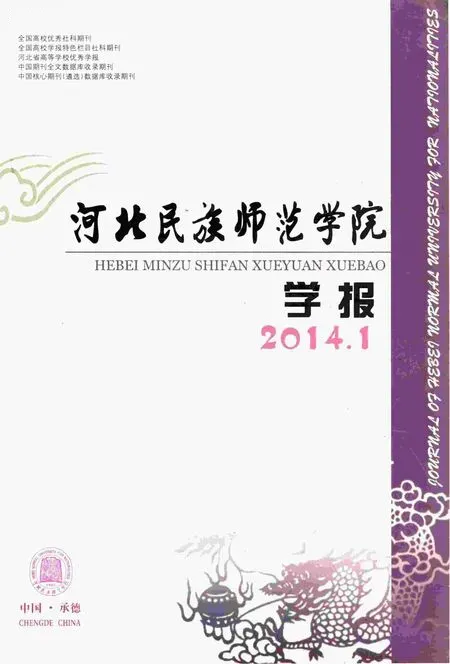古雁吐忧 文人孤鸣
——浅谈雁意象与唐代文人的怀乡心态
高 琳
(承德广播电视大学,河北 承德 067000)
中国古代文学史,可以说就是一部文人奔波的辛酸史。为了梦想和信念,为了前途和生活,为了家人和爱人,文人往往常年在外奔波,因而诗人们常常借鸿雁迁徙来比喻自己漂泊不定的悲哀,诗三百中百感交集,以象征性的形象描写来曲折地表现诗人的情感比比皆是。
《诗经·小雅·鸿雁》:“鸿雁于飞,哀鸣嗷嗷。”“哀鸣”即成为流民远走他乡四处漂泊的代表。《诗经·邶风》云:“匏有苦叶,济有深涉。深则厉,浅则揭。有瀰济盈,有鷕雉鸣。济盈不濡轨,雉鸣求其牡。雝雝鸣雁,旭日始旦。士如归妻,迨冰未泮。”因为雁儿南飞,冬临,而当济水结冰,以古代的规矩便得停办嫁娶之事了。“雝雝鸣雁”,空中已有雁行掠过,“雝雝”鸣叫让女子心中的焦躁愈深。于是“士如归妻,迨冰未泮”二句,显得热情意重!雁作为时令的同时,两相对比中体现了为伊消得人憔悴的不二意境。
孔颖达疏《书·禹贡》中“阳鸟攸居”“日之行也,更至渐南,冬至渐北,鸿雁是属,九月而南,正月而北”,古就有“随阳雁”之称,正由于大雁这种一年之中居无定所,南来北往,迁移不定的特征,逐渐被历代诗人纳入了创作的视野,成为诗歌的一种固定意象。
人好比是雁,是群体的动物,他们需要互相扶持与情感上的沟通交流,这种失群之苦是独来独往的人所难于体察的。杜甫的《孤雁》亦咏:“孤雁不饮啄,飞鸣声念群。谁怜一片影,相失万重云。……”渴望着亲人重逢,骨肉完聚。李益《春夜闻笛》:“洞庭一夜无穷雁,不待天明尽北飞”,也以雁的群飞归北的迫切,反衬自身欲归却不得如愿的羡慕与惆怅。杜荀鹤的《题新雁》:“暮天新雁起汀洲,红蓼花疏水国秋。想得故国今夜月,几人相忆在江楼?”杜荀鹤是晚唐诗人,他的诗以新雁惊飞,烟水苍茫,红蓼花疏的景致,描摹出一片凄紧的秋色。钱起《归雁》用拟人化的手法,雁因听到凄怨的丝竹声而感发乡情,毅然告别佳境回归北方:“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苔。二十五弦弹夜月,不胜清怨却飞来。”一个“不胜”见出内心的怀乡情结是多么强劲。鸿雁具有超越空间的能力,流民游子征夫戍卒却不能,雁遂成为古人寄托桑梓之怀的空中使者,诗人往往借大雁之南北往迁,喻客居他乡之愁思。
一、怀乡恋旧,离愁苦思
雁作为生活中的普通的鸟类,主要有两方面的特点:第一,雁随季节转换而南北迁移,通羁旅漂泊的流浪者;第二,雁象征信差,因此雁与乡愁又建立了另一种亲密的关系。离乡背井,对于有着浓厚安土重迁观念的古人来说,实乃人生遭际中的一大不幸,漂泊在外的游子的怀乡念旧之情最为强烈。雁的秋去春来,奔波不定,劳苦凄伤,成了古人羁旅情结的对应物。[1]22古人常常用雁自喻或寄雁寓情,抒写内心的伤感情绪和人生慨叹。
异乡人最渴望的是与亲人鸿雁传书,唐人写乡愁诗常借“雁”起兴,主要因为诗人因身处异乡,远离至爱亲朋等人生遭际变故,政治排挤仕途失意都会引起孤独情怀的流露,诗人经常借单飞的孤雁以自况,或借成双的雁来写人不如雁的人生痛苦。沈洵的《更著宴词》:“莫打南来雁,从他向北飞。打时双打取,莫遣两分离。”伉俪情深让人感动至诚;李益的《水宿闻雁》也表达了这样的主题:“早雁忽为双,惊愁风水窗。夜长人自起,星月满空江。”全诗寄予了离情与归思情感;韩愈《鸣雁》借雁南飞写自己由汴洲来徐州一事:雁饱受风霜,无依无靠;人寂寞悲苦,孤无慰藉。白居易《放旅雁》作为贬江州司马时,政治上的失意使诗人发出了“人鸟虽殊同是客”的人生感叹,诗人由冬日旅雁的饥寒交迫,继而被猎人捕杀,联系到自己的身世,不免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伤。[2]2194-195
“雁序”这一包含三纲五常的生活场景也饱含悲情,如唐苏鹗《杜阳杂编》即载王涯从弟王沐因贫困而入京寻兄,但前者“无雁序之情”。[3]149雁作为群体伦理意识的投射物,符号化之后又反过来整合强化这种观念意识。怀乡中的雁重在表现主体人的归依恋旧意向,有些孤雁意象却重在表现倾诉需要理解、慰藉,二者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但是仍然不能够相提并论。孤雁当然常被用来表现乡怀,但其茕茕无依感受的深切,情调的悲凉却每每非怀乡之情所能有。儒家伦理一贯推重群体纽带的维系作用,离乡失群者也愈益在孤雁意象下缺少心理承受力,孤雁乃至整个雁意象有了多重深意。
二、思乡怀友,羁旅愁思
把雁和人巧妙地融为一体,咏雁就是咏人,雁孤独就是人孤单,用失群孤雁及其困苦来比喻自己国破家亡后,南北奔走,羁旅漂泊,困苦、凄凉、孤单的悲惨生活。雁与特定处境、心境的人,形成了一种明显的同构异质的对应关系。谢灵运也借他人咏雁来伤叹自身,带有谢家大族的没落之悲。然而孤雁为有着特殊人生遭际的古人所深深爱重,常咏之不绝。这种遭际咏叹也是与怀乡情重紧密相关的。只有离开了故乡的人才能体会到故乡的可亲可恋,失去了祖国的人更体会出亡国的心酸。远在他乡难以自己的谢庄,就以《怀园引》咏叹:“鸿飞从飞里,飞飞河代起。辛勤越霜雾,联翩翩江河。去旧国,违旧乡,旧山旧海忧且长。回首瞻东路,延翮向秋方。登楚都,入楚关,楚地萧瑟楚山寒。岁去冰未已,春来雁不远……。”身为谢灵运从子的谢庄,曾任吏部尚书等高官,坚决反对与北魏议和,主张收复中原故土,因而他以雁来表达的不光是怀乡,亦有“汉女悲而哥飞鹄,楚客伤而走南弦”的思恋故国河山的深切情怀,以及借对“楚地”——江南山寒冰不适应的情感的抒发,强化重返“旧山旧海”的合理性。然而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后来的庾信了。其《秋夜望单飞雁》:“失群寒雁省可怜,夜半单飞在月边。无奈人心复有忆,今暝将渠俱不眠。”真是与同为由南入北的诗人王褒《燕歌行》两两相映:“试为来看上林雁,应有遥寄陇头书。”诗中的怀乡恋国之忱,都是以雁为核心载体的。真淳深挚的归依恋群怀旧心理往往存在于这些远离乡国的游子孤魂身上。
怀乡中的雁重在表现主体人的归依恋旧意向,有些孤雁意象却重在表现倾诉需要理解、慰藉,二者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但是仍然不能够相提并论。孤雁当然常被用来表现乡怀,但其茕茕无依感受的深切,情调的悲凉却每每非怀乡之情所能有。儒家伦理一贯推重群体纽带的维系作用,离乡失群者也愈益在孤雁意象下缺少心理承受力,孤雁乃至整个雁意象有了相当丰富的文化内容。
雁在特定物候中的经常性出没没纷扰,抑或雁作为特定物候背景氛围中具有代表性的飞禽,使得古人得以共时性地“能近取譬”。[4]82传统文化原型效应吸附下的文人主体情感的趋近于雁,也是闻雁生悲,悲则思雁的固定式的深在成因。雁的苦难,危险与不幸的遭际,还时时触发唐人的生命意识和人道主义同情心,引发其对自身或人民命运的关注。
频繁出现的雁意象即是文人抒发情感的外化,又强化了文人对家乡的怀念和旧恋。雁意象,雁文学的发展变迁,也正是古人自身存在与发展的必然需要所致。它表达了中国古人安土重迁,怀故恋旧,希望摆脱困窘孤寂的恒常心态与情感流程。
可以说,唐代除杜鹃外,雁所表达的怀乡意蕴是古典文学中任何其他的鸟意象所无可比肩的,但杜鹃之诱发怀乡,因为他在春季的鸣叫而引起的,雁在北国中,则为其秋季的离乡而引人动情,后者的乡愁表现因其凄清的氛围而更具感染力。漂泊在外者的故乡之怀往往与其自身孤凄身世有关,而背井离乡在安土重迁观念浓重的唐朝人眼中,本身就是人世遭逢中的一种不幸。雁的秋去春归,奔波不定,又时时蒙受自然界中鹰、狐狸以及人类捕猎的威胁,这一点绝类乱世中的飘零者——人,所以唐代以来背井离乡四处雇工的流佣被称为“雁户”。因为他们还要定期地、执着地重返故土,而后又离乡谋生,如同雁的南来北往,碌碌奔波。
在文学长河流淌的这几千年中,雁作为物种的习俗没有多大的变化,但其中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却如此地被寓意多端,给予中华民族的心灵史以不可忽视的微妙影响。
[1] 王立.中国古代思乡文学测议——文学评论[J].1988,(6):22.
[2] 汪荣祖.法官义疏九[M].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194-195.
[3] 邹志远.痛苦的家园记忆——百年中国文学家园情结的整合性论说[J].东疆学刊,2001,(03).
[4] 于晓梅,王晓春.对文学史重构的一个侧面考察——王立先生的文学主题学研究评述[J].黑龙江社会科学,2009,(04).
——崔涂《孤雁二首·其二》赏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