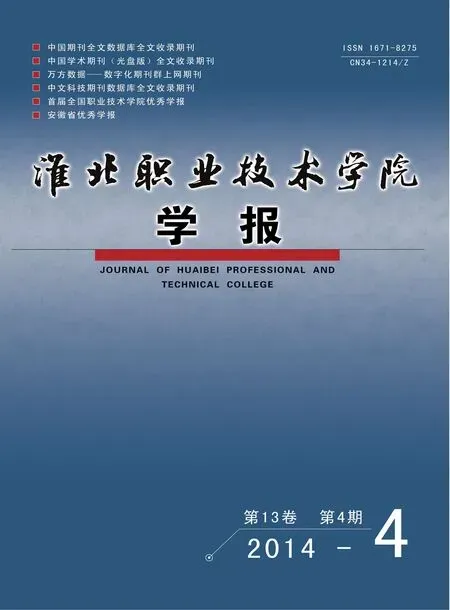超越的艰难——从阎连科小说看由乡入城青年的自我救赎
赖晓玥
(安徽大学 文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39)
自卑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心理现象之一。奥地利精神病学家阿德勒在《超越自卑》一书中给自卑下的定义是:“当个人面对一个他无法适当应付的问题时,他表示自己根本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此时出现的就是自卑情结。”[1]34在某些情况下,一个人能通过把生理的缺陷改变成优势功能从而获得“过度补偿”,实现自我超越。自卑者会通过他人的赞赏来减轻自卑感,将自卑化为驱动力,实现某种形式的超越,来达到一种“补偿性的自恋”,所以,自卑者往往是自恋者。阎连科的《和平战》《风雅颂》里的郁林其、杨科凭借自身努力逃离乡村来到城市,却在城市妻子的冷漠和蔑视下产生深深的自卑心理,为了摆脱“农民身份”带来的自卑感,他们回到乡村,以城里人自居,将在城市妻子面前的挫败感转化为在乡村恋人面前的优越感,然而这种欺骗式的自我安慰只能让他们获得暂时的精神满足,他们不仅没有实现对自卑的超越,反而在乡村恋人身上更强烈地体认到自身的“农民身份”。
一、乡村青年进城后的自卑
中国的城乡二元分割制度将农民禁锢于土地,对出身农村而又迫切想要改变自身社会地位的男性而言,婚姻成为他们进驻城市的桥梁和重要手段。与具有城市户口的女人结婚,他将有可能改迁户籍,获得合法的“城里人”身份。《和平战》中的郁林其和《风雅颂》里的杨科,都出身农村,是农民的儿子,但凭借着自身努力摆脱了原有的“乡下人”身份:郁林其通过参军入伍最终随师部来到古城,杨科则通过高考进入京城的清燕大学。进入城市后,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抛弃了乡下未婚妻,转而与城市女性结婚。他们在事业上以不同的方式完成了跨入城市的第一步,在婚姻上则以相同的手段达到了常驻城市的最终目的。讽刺的是,与城市女性的婚姻虽然提高了他们的身份和社会地位,使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自己,但在实际生活中,却成为乡村男性的不幸之源。“城市女人凭借着城市文明在价值序列上的优先性颠倒了和男性的传统性别权力关系,使得乡村男性女性化。”[2]193郁林其和杨科本是乡村社会里的“天之骄子”,有乡村最美丽的姑娘愿意为他们当牛做马、予取予求。然而城市改变了这一切,事业和婚姻的双重失败意味着他们在主流社会中身份建构的破裂,他们无法通过他人达到自我认同。在城里,他们被妻子冷落、蔑视、背叛。乡村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绝对权力在他们身上被完全颠覆,他们失却了作为一个男人和丈夫起码的尊严。
《和平战》中,郁林其从一开始就被妻子吴萍看不起,按她的话说就是:“过十个男人有九个比你强,过十个女人有九个不如我吴萍。”[3]38强烈的优越感使吴萍从内心里看不起农村出身的丈夫,不仅心理上反感他,生理上更是表现出十足的厌恶和恶心,“每一次做爱时,你爬到我身上,我都想到我身上爬了一个农民,我都觉得我吴萍窝囊。你在我身上,使我想到了你们家的黄土,想到你家村头上的牛粪猪粪,那时候,我连半点性欲也没了,恨不得把你从我身上推下床。”[3]52面对吴萍的蔑视和不屑,郁林其感到愤怒,感到屈辱,但却偏偏无法反驳。吴萍的话戳中了他内心的隐痛。《风雅颂》里的杨科,因一篇论文而有幸被赵教授看中,成了赵教授家的如意门婿。杨科和赵茹萍的婚姻刚开始是“门当户对”的,这种门当户对体现为传统婚姻中的“男强女弱”。赵茹萍虽然是京城人氏,且出身书香门第,但她自身学历却很低,只能在学校图书馆当管理员;杨科虽然出身农村,但他有学历有才华,年纪轻轻就已是名校的讲师。事业上的成功弥补了杨科出身的不足,赵杨二人婚后着实过了一段两情相悦、蜜里调油的日子。然而随着赵茹萍不断升迁,平衡被打破,当杨科第三次晋升教授失败时,婚姻已渐渐显露破败的征兆。杨科对自己的地位和处境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为了当上教授在妻子面前证明自己,他潜心闭关五年,完成厚厚的学术专著《风雅之颂》。当他兴冲冲地回家想要与妻子分享自己的喜悦时却发现赵茹萍正与清燕大学的副校长李广智通奸在床。
二、受挫后的自我补偿及其失败
人们往往需要通过他人的评价来辨别自身与他者,而这种评价就成了确认自我所必须的镜像。郁林其和杨科是乡土社会的“精英”,他们自信满满来到城市,自我之镜却在城市和城市女性的蔑视和羞辱中摇摇欲坠,他们急于找回那种被爱、被尊重和被崇拜的感觉。他们选择回到乡村、回到爱他的女性身边重塑原来的自我。然而,人类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所谓的自我,不过是“在形象中呈现出来的外观华丽的令本人称心的假面……主体自恋的空虚的欲望也许因此得到了满足,但假面在这种表演中却遮蔽了主体的视野,隐蔽了主体自身。”[5]51优秀、有能力、受女性喜爱,这是郁林其和杨科内心认定的自我,但他们不知道他们笃信的“我”的形象恰恰是那张外观华丽的假面。
生命快要走到尽头时,郁林其想起了李妮子,只因为“老婆从认识的那天起,从没有瞧得起过他,李妮子却从认识的那天起,都把他看得了不起。”[3]54六年后再见面,李妮子正在城里卖凉皮。郁林其远远地观察她,李妮子穿着深蓝色的直筒裤,这种直筒裤在古城已经过时,自己的老婆吴萍早已不穿,然而穿在李妮子身上,郁林其却觉得很合她的身份。这种心理上的审视隐隐含有一种城里人打量乡下人的优越感。当郁林其发现李妮子还深爱着自己,关注着自己的一举一动时,优越感瞬间达到高潮,他觉得在吴萍那儿丢失的,在李妮子身上都得到了弥补。回归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自我欺骗的心理过程,越是心理受挫严重,表面上越表现出极度的虚荣心与优越感,过度的自尊往往就是自卑。清燕大学副教授杨科,在京城遭受屈辱时一味的退让、自欺和逃避,回到家乡耙耧山村时,却俨然以高人一等的态度自居为“京城人”和“启蒙者。六年不见玲珍,杨科一见面便以高高在上的都市人眼光审视她,“比起乡下人,她一身都是城里人的味。比起大都市的人,她浑身又都是乡下人的味。”[6]90郁、杨二人从昔日恋人身上攫取优越感和自信,为了得到更多人的认同,他们甚至有意无意地做出一些舍己为人的“英雄行为”。郁林其甘愿为九班副担责、替指导员顶罪,为了不拖累妻子,他主动选择离婚,自己却在孤独寂寞中死去。在老家的生活中,杨科通过“瞒”和“骗”唬弄了所有的乡亲父老,“通过别人敬畏的眼神、给孩子摸顶的仪式,他似乎找回了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尊严。”[7]104对天堂街的妓女们,杨科更是化身为“拯救者”和“启蒙者”,他出入天堂街的每一家店,给妓女塞钱,让她们看工作证,告诉她们自己是京城来的教授,苦口婆心劝她们从良。在内心里杨科把自己幻想成英雄,从妓女们崇敬的目光中获得精神上的自我安慰。
然而,镜中之像在用迷人的外衣把虚假自我装扮起来的同时,也给予了人们认识本质的可能。当李妮子脱光衣服,赤裸裸地坐在床上向郁林其求爱时,郁林其不仅没有心动的感觉,反而想起了吴萍说过的那些话,他忽然苦涩地意识到,自己在面对妮子时,也有了同吴萍一样的感觉。他盯着李妮子粗粗大大、放在大腿上的手关节,一点儿性欲也提不起来。李妮子其实和郁林其一样,尽管她努力地在城市里生存,努力学城里人穿衣打扮,在郁林其眼里,她依然是个乡下妹子。郁林其就算再怎么像个城里人,他在吴萍的眼里,也永远是个农民。杨科一心想在老家和天堂街妓女面前树立起自己作为清燕大学著名教授博学、正直的高大形象,但在一次次的撒谎和欺骗中杨科自己首先认清了自己虚伪和猥琐的本质,他最后选择彻底放纵自己的欲望,不仅和天堂街的小姐们日夜淫乐,更在嫉妒发狂中杀死了玲珍女儿小敏的丈夫李木匠。郁林其最终凄惨地、默默无闻地在乡村老家死去,杨科虽极力想重返家园,但他的内心已经迷失,最后无处可逃,只能逃亡耙耧山脉深处,和一大群妓女、教授躲在大山深处,过着淫乱的群居生活。
结语
城市相对于乡村,显然代表着一种更为高级的文明,是现代化程度的象征。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已经不满足于只是成为城市的过客,他们向往城市文明,渴求城市人身份,把能到城里生活做一个城市人作为人生奋斗的目标。这些人怀着征服城市的梦想远离乡土,义无反顾地斩断自己与乡村的文化脐带,千方百计地融入城市生活。然而,尽管他们实现了文化身份的转变,却依然改变不了农村出身的事实,在城市人眼中,他们永远是“乡下人”。他们在城与乡之间陷入尴尬的状态,成为奔走于城乡间的“漂泊者”,身份的困惑产生认同的危机,这种认同危机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失去方向感、归属感的焦虑体验。阎连科以自己的切身体验敏锐地把握到时下一些农裔城籍青年的心理世界和生存困境,但由于作家本身具有浓厚的文化自卑意识,小说并没有为困境中的乡村青年找到真正的出路。郁林其、杨科不敢正视自己的“农民身份”,只能在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中获得自我满足,因而无法实现对自卑的超越。
[1]A·阿德勒.超越自卑[M].徐家宁,徐家康,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
[2]庞秀慧.男性的性别怨恨与城市女性想象——对“乡下人进城”男性叙事文本的一种考察[J].中州学刊,2012(1).
[3]阎连科.耙耧山脉[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1.
[5]福原泰平.拉康镜像阶段[M].王小峰,李濯凡,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6]阎连科.风雅颂[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0.
[7]洪治刚,欧阳光明.现代知识分子的沉沦与救赎——论阎连科的长篇小说《风雅颂》[J].南方文坛,20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