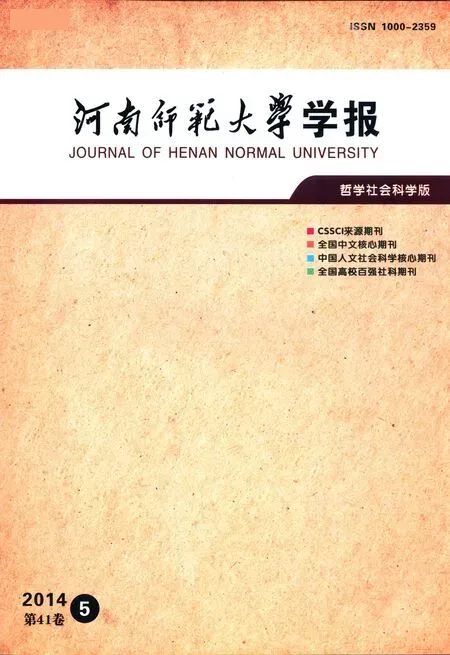怀疑论问题的当代论证及其启示
王晓红
(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北京100732)
当代有些哲学家如Dewey和Rorty都认为,自笛卡儿以来的怀疑论应该被抛弃了,因为近代怀疑论的问题,诸如我们知道什么、我们如何知道等,这些问题的前提就已经错了。这些问题的前提是,知识建立起我们和世界之间的联系,因此人们会对知识和世界是否一致、知识是否为真发问。但事实上,我们和世界之间的联系是通过命题、通过语言而非知识建立的。知识只是合理信念的社会建构体系,而不是和现实直接相联系的。怀疑主义的认识论导向的哲学传统已经过时了。但是不可否认,Rorty在攻击怀疑论的同时,也承认了怀疑论是近代哲学的核心问题,虽然是以否定的方式。
当代美国著名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卡维尔(Stanly Cavell,1926-)对怀疑论的研究则别开生面,他肯定了怀疑论在当代的意义。Rorty对此也写了一篇与其商榷的文章[1]。但正如Rorty宣布分析哲学死了一样,怀疑论也没有完全失去意义。相反,Cavell提出的观点甚至对我们更有启示。
Cavell在Claim of Reason一书中详细讨论了怀疑论问题,人能否知道外在事物?一个人能否知道另一个人的痛(心灵)?这些问题的讨论承续了20世纪哲学家、数理逻辑学家 Wittgenstein的研究。Wittgenstein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标准概念,认为只有满足了事物或疼痛的标准,我们才能说知道某物或一个人在痛。Cavell在讨论这一问题时质疑,如果根据标准,人的认识和外在事物之间能达成一致,那么进一步追问,这里所说的一致是哪一层面的,我们会得到怎样的答案?Wittgenstein的标准概念解决了什么问题?如何理解这一标准,从微观层面而言,同样影响着我们当前认识世界的首要方式——教和学。如果我们的教学活动要依据一个评价系统,那么它的标准是什么?这一标准是否可靠?
一、对标准的不同理解
Cavell认为,Wittgenstein的标准概念相当模糊和宽泛,也是日常生活的标准概念。他分析了日常语言中的标准概念,认为日常标准概念是由特定的人或人群建立的,目的是评价某物是否具有特定的地位或价值。一个概念要有意义,必然在原则上服从公共标准或正确性标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判断时,首先想到的不是合理,而是符合规范、标准,有时甚至把合规范等同于合理。对标准的采纳也意味着一致的判断。但由于这些标准产生的偶然性、任意性,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判断和标准的亲密关系,以及我们遵从标准的绝对性,这些标准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与外在事物的普遍性、人对自身及他人内在了解的困难性是相矛盾的。
但维氏的标准概念还与他的私人语言、生活形式、语法概念等相关。简单地说,比如“爱”这个字,不仅包括什么是爱,而且包含你在表达时所叫出的名字,你的指向、愿望、情感、表明的选择等等,这些都属于语法。不理解维氏的语法,就无法理解他的标准概念。维氏的标准也可以称为语法标准。
对于维氏的标准概念,有些哲学家却认为,它是与日常标准概念或官方标准概念相对立的,目的是为了确定事物存在的确定性。比如,Malcolm就认为,一方面,如果疼痛的标准得到满足,那么痛的存在无疑就得到确定。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偶然发现一个人表现出强烈的疼痛的行为,我们还能发现一些东西表明他其实不痛。事实上,Malcolm把“痛的行为”等同于“痛的标准”,而且他肯定这两种情况同时存在,即如果痛的标准满足,则痛肯定是事实和痛不必然是事实[2]。这种矛盾表明了 Malcolm在解决问题的立场上的犹疑。从根本上说,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而是依然存在。
McDowell提出的观点是,如果某个人声称痛,但结果证明那个人只是假装痛,那么痛的标准就只是表面上得到了满足[3]。然而,有人针对这一说法提出反驳,如果Wittgenstein的作为事物确定性的标准也表明了假装的可能性,那么这一标准也可以废除了。
Cavell则认为,即使某人只是假装痛,如果他假装的就是痛,那么他的行为就满足了痛的标准。Cavell得出这一结论的原因是,他认为标准并非事物存在意义上的标准,而是某物如其自身的同一性,不是事物这样的存在,而是事物这样的存在。亦即,痛就是以这样的形态存在的,比如面部扭曲、发出呻吟声等等,那么,只要人们能认定他的这种行为就是痛的行为,而不将其认作开心、恼怒等等状态下的行为,也就是说,只要他表现的确实是痛,那么,他就满足了痛的标准。至于,他是真痛还是假痛,并不在标准要考虑的范围内。实际上,Cavell认为,标准并没有达到存在。
这两种对标准的不同理解,以 Malcolm、Mc-Dowell为代表,他们强调事物是否真的存在,这实际上是笛卡儿意义上的维氏标准。而Cavell关注的并不是某物归于标准概念下的存在,而是标准概念自身的运用;不是关于现象的现实性,而是其可能性。这是在康德的意义上理解的标准。如果维氏活着,也许他不会承认双方中任何一方的观点是自己的。但更重要的是,哪一方能作为维氏学派的代表接着说下去。与此相关,Malcolm、McDowell认为,维氏是为了驳斥怀疑论的观点,以证明事物存在的确定性。Cavell则认为,维氏把怀疑论的问题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他不仅没有驳斥怀疑论,甚至也没有否定怀疑论的主题,即我们并不肯定地知道外部事物(或其他人的心灵)的存在。
如果说标准不涉及存在,那么提出这个观点不易,而更重要的是要从逻辑上论证这一观点的合理性。
二、标准与存在关系的论证
就标准与存在的关系的论证,Cavell提供了两个,即形而上学的同一性论证和日常语言的充分论证,他通过这两个论证证明标准并不触及事物的存在。
论证一:同一性论证
按照怀疑论的观点,如果只以感觉为基础,我们不知道外在事物。那么,我们如何知道外物?这一问题,具体说来也就是在问,我们如何辨认出这是一只小猫?以及我们如何知道某人在痛?转换成Cavell的问题就是,我们根据什么判断出这是一只小猫?小猫存在的标准是什么?痛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是某物存在的标准?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要搞清楚一个关键词know,知道或认识。“I know……”,我知道这是一只小猫。我知道他在痛。那么,什么是“知道(Know)”?说“知道”某物意味着什么?
这一论证接受了源自康德的基本理论,即知道的知识指向的是事物同一性的规定,而非它们的存在。首先,事物要成为普通逻辑学的对象,那么它肯定是一个无差别的对象,首先要满足A是A这个条件,也就是说具有自身同一性。否则,只是杂乱无章的感觉印象根本无法进入逻辑演算。只有满足这一条件的对象,才能成为知性运用自身规则的对象。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是如何得到自身同一物的呢?答案是,自身同一物即A是A是被我们构造出来的。“小猫在”比“小猫是小猫”的含义要丰富得多。我们通过对“小猫在”的一定“限制”、“规定”才得出“小猫是小猫”中的“小猫”,才得到自身同一的小猫。这一限制是通过纯粹的意识活动,通过知性本身具有的质、量、关系、模态等基本概念完成的。只有具有自身同一性的小猫,才能呈现为关联物而被我们经验到。“小猫在”作为自在之物是可不知的,我们能知道的只是我们“限制”后的小猫,经验到的小猫,现实的小猫。如此,我们才具有了关于小猫的知识。只有具有自身同一的事物才能成为科学对象,构成知识。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知道”的并非事物的存在,而是事物存在的样子,“这样”的存在。事物的标准指的也并非某物的存在,而是某物的自身同一性的标准。
论证二:充分论证
比如,有一只小动物,我们运用标准判断出,“这是只小猫”。这包含:第一,我们运用小猫的标准作出这一判断,同时这一判断也表明了,它不是别的东西,不会是除了小猫外的其他物。一旦运用标准对它作出判断,我们就再没有空间对它作出其他的选择。第二,标准已经是充分的,充分是指能让我们判断出,这是只小猫而不是其他。但充分并不意味着一切,充分只意味着可以充分判断出这是只小猫。第三,如果你认为描述不够充分,那么除非能够提出某个具体缺少的什么条件,比如说你怎么知道它不是小老虎,小老虎也有类似的毛色啊等等,否则,没有具体的反驳,而只是继续说这不充分就是愚蠢的。第四,充分意味着,我并不需要证明其他的不可能性。充分意味着充分表明这是小猫,但并不意味着充分表明它不是毛绒玩具小猫。充分意味着,我只要能够充分证明它是一只小猫就够了。我们并不需要提供材料,证明它是活的或是死的或是玩具小猫。即使后来证明这不是真的小猫,而是一只毛绒玩具小猫,这一事实也不会与我们的声称相矛盾[4]84。
事实上,Cavell提供的上述两个论证也是独自成立、相互佐证的。我们经验到的“小猫”实际上是通过知性本身具有的基本概念与感性直观相结合完成的,只是有“限制”的小猫,而非“小猫在”本身。而充分证明只要根据标准判断出它是小猫就足够了,并不需要提供充分的基础表明它是真的。无论是一幅画,还是一个玩具,我们都可以说,这是小猫。我认为,这两个论证也体现了Cavell试图沟通大陆学派和分析学派的努力,大陆学派倾向第一种论证方式,分析学派倾向后一种论证方式。但Cavell在此提供这两种论证,显然是认为这两种论证都成立,而且异曲同工,相互佐证,所达到的结果也相同。
标准并不涉及事物是否真实存在。标准是说,事物是否以这样的特征存在,只要提供的证据充分表明了它具备某物所应当具有的特征,能充分证明“A是A”就够了。即使最后证明它不是真的,这丝毫不影响我的声称的正确性。标准并没有达到事物本身的存在。
也许有人会说,想知道小猫是真是假很简单,轻轻触一下它,看它是否会动,抓住它,看它是否有温度就能判断它是否是真的。但问题在于,确认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认识论者想要知道的,显然不是一次次的确认,而是面对一般对象,寻求一般事物存在的真实性或标准。
三、标准和物
如果说,标准不能作为事物存在或现实性的标志,而是作为事物的同一性、辨识事物身份或认识事物的标志,那么它就和我们习惯上所称呼的物的知识相关吗?什么是我们所称呼的物呢?我们认识的物是什么?什么是物呢?
比如我们说,这是椅子。我们从哪里获取椅子这一称呼呢?有人会说,查字典,字典里有关于椅子的定义或标准。但我们知道,字典里的词也是根据约定俗成的用法记录下来的。Cavell的研究也表明,标准都是特定的人或人群建立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你知道这是椅子,是根据通常的、官方的或习惯的约定俗成的叫法。如果某人不知道这是椅子,一方面是因为他没有学习椅子这个称呼,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没有正确地学习这个称呼应用于事物的方法。
维氏的标准概念则给我们提供了不同的视角,我们需要在这里重温一下。维氏不是在具体对象的层面,而是在概念层面论述问题。他关心的是我们在和其他概念的关联中使用这一名称的概念的能力,亦即我们所拥有的概念和“椅子”这一概念是否相关或不相关,我们能否在各种不同的背景中运用这一概念。也就是说,维氏关心的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物,而是我们拥有的各种各样的概念和椅子这个对象的概念的相关,是这一物的概念在我们的概念系统中的位置。比如说,我两岁多的儿子知道这把椅子是黄色的、那个气球是蓝色的。可当我问他,这辆小汽车是什么“颜色”时,他仍然说“不认识”(他把不知道答案的一切东西皆称为“不认识”,这很有意思)。因为他还没有理解“颜色”这一抽象的概念,他还不知道黄色、蓝色、红色都归于颜色这一概念之下。维氏讨论的对象恰恰是这类抽象的对象或某种自然种类(如心灵、质料、感觉材料、意义、颜色等)。如果我们不知道某物的具体名字,也许我们就没有关于这一具体物的知识。但如果我们不知道维氏所说的语法标准,那么我们缺失的就不是一个知识点,而是关于某类知识,关于获取这类一般对象的任何信息的可能性。没有这一标准,我们不可能正确叫出这一类对象的名字。维氏语法标准的重要性正在在于此。也就是说,如果孩子不知道颜色这一语法标准,他就不仅不能针对“颜色”的问题回答出这辆小汽车的颜色,他也回答不出任何关于颜色的提问。因为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在“颜色”概念和这一概念下所具有的那类对象下的名字(黄色、蓝色、红色等)的概念间建立联系,那类对象叫做什么(颜色)的可能性还没有向他打开。即使他知道具体的黄色、蓝色、红色等颜色,但这些概念与它们所属于的“颜色”概念并没有在他的概念系统中建立联系。也就是说,颜色的语法标准还没有被他掌握,因此他也不能恰当地理解蓝色、黄色等概念。再比如,“北京”的语法标准中包含城市这一概念,如果一个小孩还没有城市的概念,那么北京在他的概念系统中就没有位置,他就还没有理解北京这一对象的概念。它(北京)是什么,这一问题就仍没有得到回答。
问题在于,当我们把称呼物的一个词思考为概念时,我们要根据这个词适合或将被发现适合应用的所有语法背景制定一套标准。在这个意义上,概念就是词的意义[4]78。但原则上,词在发展,我们不可能穷尽所有词将可能出现的意义,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穷尽词的所有语法背景。因此,我们说掌握一个关于“物”的概念实际上只能是掌握这个物的词已有的部分或全部意义,对于它将来的意义,我们不可能全部掌握。标准,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并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
但事实上,让我们的经验世界有意义是必要的。因此,正确的态度是,在面临自己不知道的情境时,诚实地说,我确实不知道。实际上,知道什么时候说“我不知道”和知道什么时候说“我知道”一样重要。说“我不知道”也同样要求具有这样说的能力和同样严肃的态度。能够严肃地作出“我不知道”这一论断并且严肃地接受这一论断,这对于我们的经验世界有意义是必要的,它也是我们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也许这是悖谬的,我们通过标准概念,试图寻找事物的肯定性,达到的结论之一却是我们要严肃地承认我不知道。但这一否定表达恰恰表达出肯定表达“我知道(I know)”的困难以及它所面临的实践上的难题。
四、“我知道什么”的难题
承认我不知道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我知道什么,虽然这一问题面临着诸多难题,尤其是关于他人心灵的问题。
比如,一个人正在牙医那里看牙,他坐在治疗椅上,面部抽搐,嘴巴张着发出尖叫声。我们会根据通常的情境推断,他正在治疗牙齿,又表现出痛的行为,因此,他肯定是因为痛才产生的反应。我们也许会因此作出判断,他痛得尖叫。但问题是,你如何知道他是痛得尖叫,而不是清嗓子、叫他的仓鼠或者在唱歌。如果后面发生的事实是,仓鼠听到他的叫声,从门缝里钻了进来。病人是在叫他的仓鼠。这说明,人的外在行为和内在经验之间存在着很大不同。假如我们又一次在乡间看到那个看牙病人,他并没有在看牙,但他确实是面部抽搐、尖叫着在呼唤他的仓鼠,而并不是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痛得尖叫。那么,这个例子不是说明,痛行为的概念作为标准是无效的吗?我们根据通常的情况作出推断,但事实上证明它是会错的。那么这个标准还有什么意义?事实上,Cavell通过这个例子想要表明的正是,标准概念的语法关系的必要性或者它们在什么意义上是必要的。又如在大多数国家,点头表示同意、赞成,摇头表示反对、否定。但在斯里兰卡、印度、尼泊尔等国家则相反,摇头表示同意,点头表示不同意。我们能说这是正常的,那是不正常的吗?Cavell认为,“正常性的问题实际上是实践问题,或者说是实践的限度问题”[4]90。即使大多数人仍没有某一实践,我们也并不能因此就否认它。因为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不可能掌握所有的标准,语法标准是开放性的,而我们的实践则是有限度的。我们不能因为自己在某一实践之外,就将其判断为不正常。同理,在对待具有不同环境、不同历史背景、不同宗教信仰的不同国家间的问题上,不同样如此吗?也许,谦虚谨慎、自信开放才是我们面对外物和他人时应有的态度。
五、教与学
如果我们承认,我们的实践是有限度的,并因此作出正确的判断,说“我知道什么”并不那么容易,那么同样,具体到我们的教学实践活动中,以及我们对教学成果的评价中,限度依然存在。
比如,在教小孩学习数字1到20这些符号时,我们经常会让孩子数串珠。当20以内能熟练计数了,我们会给予提示,让孩子们继续以类比的方式继续数21,22……等更大的数字。到最后不再提示,孩子也会以此方式继续,多数孩子都以这种方式成功地继续数下去。但如果有一个孩子对我们的提示没有反应,他不能按照我们的设想以类比的方式继续往下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给他一个评价,说他比较笨,不够聪明。这一评价标准已然为大多数人接受。甚至根据维氏的考察,在比较落后的部落里,人们也是以此方式筛选某个孩子是否聪明或愚钝[5]。
但是,我们是否反思过以此评价一个孩子聪明与否是否合适?Cavell的疑问是,这只能说明,我们在某些方面和这些人交流显然是失败的,可这些人真的不聪明吗?在我看来,实际上,这一现象在生活中总会发生。我们和我们的朋友、家人、同事都会在某些时候、某些事情上交流失败。甚至某些在某一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小时候也曾“不够聪明”,比如爱因斯坦。因此,在对教学这一实践活动的成果的评价中,至少有两点要引起注意:第一,我们要认识到,孩子并非完全不聪明。也许在若干个小时、若干天、若干月以后,他会以自己的方式达到我们所说的方法或结果。而且,即使他在这方面的理解比我们所要求的慢一点,也并不证明他在其他方面不会更好。第二,我们之所以焦虑并对他作出评价的原因是“我们不能使我们自己(对他)成为聪明的”[4]115。我们作出评价暗含的要求是,他“必须”能跟上我们的指点。如果他跟不上我们,反过来则显示了我们自己的无力,我们无力使他到达我们所希望的地方,因而使我们焦虑。
实际上,这种双方在交流上的成功与否,呈现为双方对对方意图的理解力。我们在作出暗示或手势时,对于他是否能理解我们的暗示的理解,我们以此方式是否能让他理解,或者是否以别的方式他能更好地理解,这种双方的、相互的理解到底能达到何种程度值得思考,但无疑它是有限度的。如果双方对彼此理解的判断达成一致,则理解就会发生,否则就可能失败。事实上,这一例子同时也体现了个人所掌握的知识的限度。如果一个人所掌握的知识恰好能根据对方的提示在自己的知识背景中勾连起一副图画,则他就会根据自己的理解作出反应;如果他的反应与对方所想表达的基本一致,那么他们就进行了一次成功的交流。另一方面,双方的理解力能否达成一致也受制于双方的经验限度,我们不可能总是有相同的经验,这个人的经验和那个人的经验并不会完全相同。无论如何,交流不可能总是成功。交流的目的是相互达成一致的理解。成功交流的基础则是,能宽容地接受对方,承认另外一种方式的表达的可能性。因为,毕竟,我们的实践和理解都是有限度的。
因此,首先,如果在判断一致的情况下达成一致的理解是有条件、有限度的,那么建立在判断一致的基础上的教也就更有限度,我们能教的太少,与学习的巨量东西相比,教显得相当无助。其次,如果教是如此,那么依据教这一实践活动的效果对被教的对象作出的评价是否公允就当然地成为问题。再次,归于知识的能教的东西,只是事物存在的样态,而不是其存在。对于世界整体和他人的心灵,教更是无能为力。根本上,人们只能在承认经验限度的基础上达成有限度的一致。
如果真正教的东西少之又少,那么我们还仍旧只限于用所教的那一点有限的东西来应对世界是不是显得茫然而无力?我们在教学中除了教知识外,是不是还应让学生学习更多的东西?我们在教中是否该更注重学,引导学生如何去学,让学生主动去学、去思、去问?也许这才是教学的最终和根本目的。更重要的不是教或被教,而是主动的学、思精神的培养。学什么?学“习”,中国古人也已经睿智地告诉我们。习,就是不断地重复练习,反复践行、实践。学不仅是学理论知识,还要联系实践活动。即使如此,我们得到的仍只是事物展现出来的样子,而不是事物本身的存在。而且这一成果也仍是在你自己的经验限度内的正确性。因此学习之外,还有学“问”。学习,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知行兼修。学问,对寻常之事发问,问事之根由。问而去思,思不可认识之世界之大全、存在,思现象之源。也许只有这样,才能认识事物纷繁复杂、变化多端的样态。因此,保持谦虚谨慎之心、自信而开放的态度,学习学问才能常思常新,世界才可能展现出新的、不同的样貌。
[1]Richard Rorty.From Epistemology to Romance:Cavell on Skepticism[J].The Review of Metaphysics,1981,34(4):759-774).
[2]Malcolm,N.The Verification Argument[C]//Philosophical Analysis,ed.M.Black,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50:83.
[3]John McDowell.Criteria,Defeasibility and Knowledge[M].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68),1982:455-479.
[4]Stanley Cavell.The Claim of Reason[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
[5]Ludwig Wittgenstein.The Blue and Brown Books[M].Blackwell Publishers Ltd,1998: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