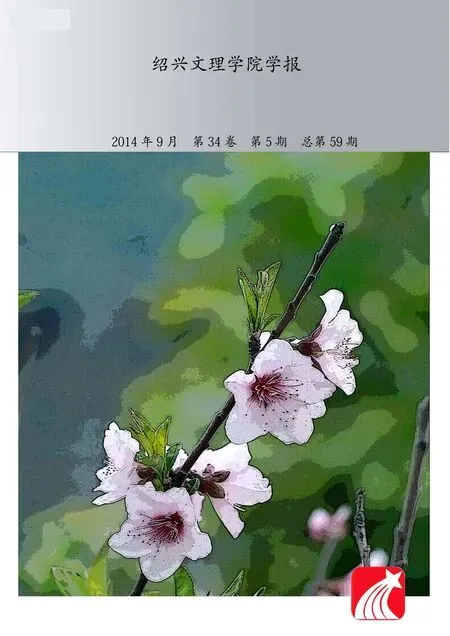夏承焘与新旧词学之转型
——以《词学季刊》为中心
熊舒琪 许和亚
(杭州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311121)
夏承焘与新旧词学之转型
——以《词学季刊》为中心
熊舒琪 许和亚
(杭州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311121)
20世纪30年代正处于新旧词学转型的关键时期,作为词学研究的专门刊物,《词学季刊》是联结词学家进行词学研究的重要阵地,成为新旧词学转型之枢纽。夏承焘先生引史学之法治词,开创词人谱牒之学,其系列词人年谱之作陆续刊发于《词学季刊》,以“知人论世”的态度说词,以科学严谨的方法治词,纠正了常州词派穿凿附会、主观臆断解词的风气,从具体词学研究实践和方法上推动词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成为新旧词学转型之关捩。
夏承焘;新旧词学;转型;《词学季刊》
“现代词学三大家”以龙榆生先生为主将,夏承焘、唐圭璋二先生羽翼之,他们以《词学季刊》为阵地,联结时贤耆宿,于词学研究互通声息,共同推进现代词学的建构。夏承焘先生尤以其具体实践和方法开辟词学研究新境界,逈出时贤,于新旧词学的转型厥功甚著。本文拟以《词学季刊》为切入点,从以下三个方面具体阐述夏承焘与新旧词学转型之关系。
一、《词学季刊》:新旧词学转型之枢纽
《词学季刊》是由龙榆生主编的在叶恭绰等人赞襄下创办的专门研究词学的同人刊物,自1934年4月创刊以来共发行11期,历时三年有余。处在词学研究新旧交替的关键时期,《词学季刊》是联结词学家进行词学研究的重要阵地,反映了词学研究在新旧文学传承过程中的生态,直接推动了现代词学研究体系的建构。
《词学季刊》是在“词之为学,久已不振,旧学既衰,新学未兴”[1]的时代背景下创办的,一经创办便已承载了词学研究“脱旧入新”的历史使命。《词学季刊》创刊号即已言明了办刊宗旨、社员要求及发文的主要范围,“本社以约集同好研究词学,发行定期刊物为宗旨”,“凡对词学素有研究兼有相当介绍者,并得为本社社员。入社之后,应负定期撰稿、搜集资料或经费方面之责”[2]。并进一步强调:“本刊专以研究词学为主,不涉及其他”[3],把这部杂志定位成以词学研究为基本内容、词学同好参与并发表著述、具有较强专业性的“内部”学术刊物。
在《词学季刊》之前,尚未出现如此专门研究词学的刊物,词学研究的文章大多零散发表于各大报刊上。由于专家少,只是凭兴趣偶尔涉及,加之学术刊物数量少,更没有专业的词学杂志,此前的词学研究尚未能形成气候。不少研究者混淆“学词”与“词学”的界限,“词学”作为一门学问尚未完全独立,仍依附于传统的诗学研究。《词学季刊》的创办,标志着现代词学研究的群体自觉。在新旧词学研究转型的关键时期,《词学季刊》如一面旗帜、一个风向标,指引词学研究的方向,促使词学作为一门学问的独立,推进词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统计数据显示,1933—1936年词学研究的成果量骤然猛增,年成果量平均达到150项,此前此后的年平均词学成果都很少,词学研究呈现较为缓慢的发展态势。“这固然与词学研究日益受到关注、词学研究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专业学科有关,更与一位词坛领袖、一个词学专刊有关,亦即得益于龙榆生和他主编的《词学季刊》的倡导和吸引。”[4]《词学季刊》的专业性、集中性,是前所未有的,其产生的词学研究的规模效应亦是空前的,具有当时其他刊物无法比拟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作为新旧词学转型期的专门词学研究刊物,《词学季刊》有其自身过渡性的特点,有对传统词学的继承,更有其自身的开拓性。从栏目设定上看主要有“论述”、“专著”、“遗著”、“辑佚”、“词话”、“词录”、“词林文苑”、“通讯”、“杂缀”、“补白”等,其中“遗著”、“词话”、“词林文苑”、“补白”等栏目中的相当内容属于传统词学范畴。词集序跋主要刊于“词林文苑”中,11期共47篇序跋,既有老一代学人如夏孙桐《朱彊村先生行状》、张尔田《彊村遗书序》、叶恭绰《欸红楼词跋》等的文章,又有新一代学人如龙沐勋的《新刊足本云谣集杂曲子跋》、夏承焘的《东坡乐府笺序》等。《词学季刊》的开拓性主要体现在“论述”、“专著”等栏目上,“论述”——“专载关于词学之新著论文”,“专著”——“专载关于词学之新著专书”。[3]在三年多的时间里,《词学季刊》共刊发了龙榆生的《词体之演进》、《选词标准论》、《词律质疑》、《研究词学之商榷》、《两宋词风转变论》、《今日学词应取之途径》、《东坡乐府综论》、《清真词叙论》、《漱玉词叙论》、《南唐二主词叙论》、《论平仄四声》、《论贺方回词质胡适之先生》,王易的《学词目论》,卢前的《词曲文辨》、《令词引论》,詹安泰的《论寄托》等理论性质的文章十余篇。龙榆生先生以主编兼主笔,在理论层面上推进新词学体系的建构。在“论述”、“专著”中出现的以考证见长的词人年谱、词人评传、词籍提要等,其规模与体系,亦是前无古人。主要有夏承焘的《张子野年谱》、《贺方回年谱》、《白石歌曲旁谱辨校法》、《姜石帚非姜白石辨》、《韦端己年谱》(附温飞卿)、《晏同叔年谱》、《冯正中年谱》、《南唐二主年谱》、《令词出于酒令考》,唐圭璋的《两宋词人时代先后考》、《宋词互见考》、《蒋鹿潭评传》,李文郁的《大晟府考略》,查猛济的《刘子庚先生的词学》,赵尊岳的《蕙风词史》及其系列词籍提要,缪钺的《遗山乐府编年小笺》等数十篇文章。尤以夏承焘先生的系列年谱考证影响最著。
《词学季刊》是20世纪30年代词学研究的重要阵地,所刊文章代表了当时词学研究的最高水准。张尔田、叶恭绰、赵尊岳、吴梅、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等人的词学论文全部或大多数发表于《词学季刊》,可以说《词学季刊》是培育这些词学研究者的温床,同时也造就了一批后来成为词学研究宗师级的大家。这些词学大家们在《词学季刊》上刊发的系列文章,促进了现代词学体系的建构,确立了现代词学研究的基本格局。
二、夏承焘与《词学季刊》
“现代词学三大家”与《词学季刊》皆有甚深之因缘,以龙榆生为主将,夏承焘、唐圭璋羽翼之,共同主持东南词学研究,推进词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据《天风阁学词日记》(下文简称《日记》)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九日:“雁晴转示暨南大学教员龙榆生(沐勋)二笺,愿与予缔交,问词有衬字考。又谓亦有意为词人年谱,欲与予分工合作。灯下作一书复之。”[5]124这是夏、龙二人交往的最早记录。自此二人便时常通过信笺切磋词学。《日记》一九三二年七月六日:“接榆生片。谓下学期决举办词学杂志,嘱介程善之。”[5]300七月廿八日:“接榆生片,谓词学杂志决于秋间着手,先出彊村专号,嘱予与圭璋各撰一文,并问蔡松筠君,盼予早写定词例。”[5]302十二月三十日:“接榆生片,嘱寄梦窗词后笺、子野年谱及论词函札,登词学季刊。”[5]309可知《词学季刊》从1929年10月便已开始酝酿,直至1933年4月才出创刊号,历时三年半时间,可谓千呼万唤始出来。在龙榆生先生的主持下,时贤耆宿的积极参与下,《词学季刊》成为联结各方词学研究的纽带。
从《词学季刊》创刊号伊始,夏承焘先生便在“论述”、“专著”、“词林文苑”、“通讯”等栏目上刊发文章,平均一期两篇左右,共计17篇,仅次于龙榆生(29篇)、张尔田(19篇)之后。这些词学论文多为词人年谱,如《张子野年谱》、《贺方回年谱》等共六种九家;也有考证性质的论述,如《姜石帚非姜白石辨》、《令词出于酒令考》等。亦有为友人所作的序跋,如《红鹤山房词序》、《东坡乐府笺序》、《杨铁夫梦窗词笺释序》等。夏承焘先生诸词人年谱将治史之法引入词学研究之中,考证甚精,词人行谊可谓信实。然而,作为新旧词学转型期的专门词学研究刊物,《词学季刊》因其自身的过渡性质,所刊部分文章不免为时所囿,《日记》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一日:“孟劬先生来信录下:‘……榆生所编词刊,较为纯正,然也不免金鍮互陈,尚未尽脱时下结习。……公所纂词人谱录,考证皆甚精,他日似当孤行,且须刊木,不宜与牛溲马勃滥厕也。’”[5]327此论虽有过激之处,然亦大致公允可信。夏承焘先生所纂之“词人谱录”即词人年谱诸作,以考证精当、征引赅博见称于时,其影响之大,于《词学季刊》的重要性亦可见一斑。
龙榆生先生在《词学季刊》第一卷第四号上刊发了《研究词学之商榷》一文,首次从理论层面上区分了“学词”与“词学”的不同,并将词学研究的范围分为“图谱之学”、“词韵之学”、“词史之学”、“校勘之学”、“声调之学”、“批评之学”、“目录之学”等七个方面,基本囊括了新、旧词学研究的内容。如果将龙氏此文作为现代词学研究成为专门之学正式确立的理论标志的话,那么夏承焘先生在《词学季刊》陆续发表的系列词人年谱,可以视为词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的具体实践和表现。正如龙氏所言:“历代词人,除少数位望较高,生平行谊,见于正史者外,大抵皆湮没无闻,有时里居仕履,及生于何年何代,亦不易探求。其或见诸野乘笔录,亦复艰于类聚。‘知人论世’,为治学者之所宜先。”[6]夏氏兀兀终年从唐宋人笔记、野史等处爬梳史料,旁搜远绍,匡谬决疑,作词人年谱数种为词人张本,详于考索行事,锱铢不遗,“于半塘、伯宛、彊村诸老搜讨校勘之外,勉为论世知人之事”[5]144。夏氏诸谱可谓有功词史,《日记》一九三五年二月四日:“接赵百辛复,许予词人年谱,谓‘十种并行,可代一部词史,此彊村未为之业,不但足吞任公而已。’”[5]361近代王国维撰《清真先生遗事》附《清真先生年表》,为考订词人行实导夫先路,然真正成其规模、影响之著者,非夏氏诸词人年谱莫属。自创刊号伊始,这一系列词人年谱皆刊发于每期《词学季刊》“专著”栏目之上。不独词人年谱,夏氏在《词学季刊》上刊发之文章亦有关“图谱之学”者,如《白石歌曲旁谱辨校法》、《与龙榆生论陈东塾译白石暗香谱书》、《与龙榆生论白石词谱非琴曲》、《再与榆生论白石词谱》。另两篇考证性质的论述文章:《姜石帚非姜白石辨》、《令词出于酒令考》,皆考证信实、旁征博引、论述精当、俨然规范的现代学术论文。
现代词学的开辟与建构,以龙榆生为主将,夏承焘、唐圭璋为羽翼,他们各擅所长,声气相通,龙氏长于推论,夏氏用力于考证,唐氏擅于辑佚,共同推进现代词学研究体系和格局的建构。夏氏系列词人年谱之作,从知人论世的角度说词,以科学严谨的方法治词,纠正常州词派以来说词穿凿附会之弊,可谓现代词学奠基之作。《词学季刊》作为新旧词学转型期联结词学家和进行词学研究的阵地,可谓嘉惠于夏氏;夏氏以其扛鼎之作为词人张本,亦可谓有功于词学。
三、夏承焘:新旧词学转型之关捩
夏承焘先生对现代词学的重大贡献在于开创词人谱牒之学。晚清词学,长于订律校勘而疏于考史,先生以深厚的传统学殖为根柢,继承彊村诸老之业,又不为其所囿,以词学与史学结缡,进而“为知人论世之事”[5]129。同时,先生秉持求真求实的治词精神,推进词学研究的科学化进程。这样便纠正了常州词派穿凿附会、主观随意解词的风气及其积弊,从方法论和具体词学研究实践上指引词学研究的科学路径,这是新旧词学转型的关键一环,亦是现代词学建构的必然要求。
夏承焘先生三十前后,始专攻词学,他旁搜远绍,精心考辨,匡谬决疑,著唐宋词人年谱数种,陆续刊于《词学季刊》。此时常州词派的流风余沫尚未完全涤清,“微言大义”、“比兴寄托”之说仍在词坛有不小的影响,夏氏秉持“知人论世”之态度,引史学之法治词,开创词人谱牒之学,在扭转常州词派“以经治词”的同时,将词学研究引入更加客观、严谨、科学的道路之上。
“比兴寄托”说为常州词派的核心理论,张惠言评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词:“此感士不遇也。篇法仿佛长门赋,而用节节逆叙。此章从梦晓后,领起‘懒起’二字,含后文情事,‘照花’四句,离骚初服之意。”[7]1609张氏论词主观随意,有穿凿附会之病,王国维批评他“固哉,皋文之为词也”[8]。《日记》一九四一年九月一日:“过吴眉翁谈词,谓北宋已有寄托,东坡‘我欲乘风归去’为不忘爱君。王安礼‘不管华堂朱户,春风自在杨花’为诮安石。予意诗人比兴之例,其来甚古,唐五代词,除为歌妓作者外,亦必有寄托。惟飞卿则断无有。后人以士不遇赋说起菩萨蛮,可谓梦话。常州派论寄托,能令词体高深,是其功,然不可据以论词史。”[9]332夏承焘先生并非否认唐五代词有“比兴寄托”的情况,在肯定张惠言提高词体努力的同时,严厉批评了张氏的穿凿附会之病开启了后来常州词人主观牵强说词的不良风气。同样,对于后人的穿凿附会,夏承焘先生也提出批评,《日记》一九二八年八月四日:“况(周颐)氏论词,时有腐论……即其论刘词忽涉及《词苑丛谈》载改之遇琴妖事,大发议论,谓:‘《龙洲词》变易体格,迎合稼轩,与琴精幻形求合何异’云云,亦妄诞可笑。”[5]32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作玲珑四犯考证,举张文虎一事。郑文焯好为野言,殊可厌。”[5]191同年六月二十四日:“阅刘子庚讲词笔记,附会牵强,几如痴人说梦。张惠言尝欲注飞卿词,若成书,则又一刘子庚矣。”[5]212对以上诸人以附会之说解词颇不以为然。常州词人往往疏于考史,韦端己《菩萨蛮》数阕,张惠言解为晚年留蜀思唐之作,殊不知韦词大都为五十岁及第之前流浪江湖之作。夏氏治词以考史见长,其“以清儒治群经子史之法治词,举凡校勘、目录、版本、笺注、考证之术,无不采用,以视半塘、大鹤、彊村所为,远为精确”[10],并非夸饰之虚语。
夏氏开创词人谱牒之学,通过对词人身世、时代环境的考证及作品系年,辩诬征实,在此基础上做出的批评才是确凿可信的。温庭筠士行尘杂,不修边幅,早已屡见史书、笔记,张惠言欲尊词体而推举“温庭筠最高,其言深美闳约”[11],又以其《菩萨蛮》词为“感士不遇之作”,且以上拟《离骚》,张氏疏忽史实而好以“微言大义”、寄托解词,可谓“虞翻易象满词篇”[12]579。值得注意的是,夏氏对于常州词派的词学理论并非一概否定,对其精辟独到、助益词学之处亦多有赞扬和继承。如周济的“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诗有史,词亦有史”的词史说,谭献的“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等多有褒扬之辞。再如“唐珏咏白莲”一事,夏氏评道:“清代常州词人,好以寄托说词,而往往不厌附会;惟周济词选,疑唐珏赋白莲,为杨琏真伽发越陵而作,则确凿无疑。”[13]373同时也指出常州词派好以“微言大义”故示玄虚的弊病,“常州词人尊奉温、韦,提倡比兴,由重形式而走向重内容,本是他们论词可肯定处。但张惠言、陈廷焯诸人都勇于立论而疏于考核,因之多附会失实的话,这也是常州词论家共同的缺点。”[14]413夏氏之论,以实事求是、知人论世为旨归,可谓切中肯綮。
《冯正中年谱》为夏承焘先生诸词人年谱中最得意之作,集中体现了其词人谱牒之学的主要特征。《年谱》将冯延巳置于南唐党争的背景中进行考察,考辨史料关于冯延巳行迹、品格等方面的记载,辩诬征实,为词人张本。马令《南唐书》、陆游《南唐书》及司马光《资治通鉴》记冯延巳遗事,多凭朋党攻讦之辞,夏承焘先生多有考证:“如陆书传谓其‘因(陈)觉附宋齐丘,同府高位者悉以计出之。于是无居己右者。元宗亦颇悟其非端士,而不能去’。马书传谓其‘与宋齐丘更相推唱,拜谏议大夫翰林学士。复与其弟延鲁交结魏岑、陈觉、查文徽,侵损时政。时人谓之五鬼’。又谓与弟延鲁如仇雠,并疏隔继母。今按‘与弟异居,舍弃其母’,乃保大五年江文蔚弹正中疏中语。”[15]19夏先生又考《钓矶立谈》为史虚白次子所作,史虚白与韩熙载友善,“顺义间与熙载同自后唐南奔,旋以放言见扼于宋齐丘,隐处以卒。故其子与宋党诸人斥贬至严。以恶齐丘、陈觉诸人,遂并及正中矣。”[15]20宋人野记之述南唐事者,除《钓矶立谈》外,其余各史书、笔记无有苛责冯延巳之论。《南唐书》及《通鉴》等书皆承《钓矶立谈》党与攻讦之辞论定冯延巳,疏于辩诬,可谓失察。
又如保大十年十一月,冯延巳以尽失湖湘之地,自劾罢相为左仆射一事。陆游《南唐书》本传以王师拓境致败归罪于冯延巳,谓“延巳初以文艺进,实无他长,纪纲颓弛,胥吏用事,军旅一切委边帅,无所可否。愈欲以大言盖众而惑主,至讥笑烈祖戢兵以为龌龊无大略。……”[16]《年谱》指出这段话源自《钓矶立谈》,此书多朋党攻讦之辞,不足为信。其次,据陆游《南唐书》本纪,李璟命何敬洙率师助马希萼攻潭州,弑其君希广,在保大八年。命边镐取潭州,刘仁瞻取岳州以灭楚,在保大九年。其时冯延巳方在抚州任上,尚未柄政。再次,从《通鉴》、陆游《南唐书》及《宋史》的相关记载来看,南唐之图进取乃李璟本意,与冯延巳无甚直接关系。然兴师致败,冯延巳正当相位,绌于才用,自劾以去。政敌于是纷纷攻击冯延巳,遂把王师败绩皆归罪于他。通过《年谱》的辩诬征实,我们可以确定冯延巳并非如史书所记载的那样,是个奸邪小人,而是有一定操守、性情平恕的文人士大夫。张惠言斥责冯延巳专蔽痼疾,又敢为大言,谓其《蝶恋花》数阕,“盖以排间异己者”[7]1612。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虽称其词“极沉郁之致,穷顿挫之妙,缠绵忠厚,与温、韦相伯仲”而亦鄙夷其为人[17]。《年谱》排比冯延巳之行实,并考南唐党争之曲折,偶亦订正《通鉴》、二《唐书》之失误,往事陈迹,词人行谊、品格,朗若列眉。
夏承焘先生以其“通赡之才,兼断制之识”[13]1积年累月成词人年谱数种,陆续刊于《词学季刊》,以“知人论世”、实事求是的精神治词,考证赅博,精审独绝,创立词人谱牒之学,可谓有功词学。词人年谱的创作正处于新旧词学转型的关键时期,夏氏以其具体词学实践和方法开辟词学研究新境界,推进现代词学的建构,具有继往开来的学术意义。
[1]夏承焘.影印《词学季刊》题词[M]//影印《词学季刊》.上海:上海书店,1985.
[2]龙榆生.《词学季刊》社简章[M]//龙榆生.词学季刊:创刊号.上海:民智书局,1933:225.
[3]龙榆生.《词学季刊》编辑凡例[M]//龙榆生.词学季刊:创刊号.上海:民智书局,1933:226.
[4]王兆鹏、刘学.20世纪词学研究成果量的阶段性变化及其原因[J].学术研究2010,(6):131.
[5]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一[M]//夏承焘.夏承焘集:第5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6]龙榆生.词学研究之商榷[M]//词学季刊:第一卷第四号.上海:民智书局,1934:15.
[7]张惠言.论词[M]//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
[8]王国维.人间词话·删稿[M]//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4261.
[9]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二[M]//夏承焘.夏承焘集:第6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10]程千帆.论瞿禅词学[M]//词学:第六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254.
[11]张惠言.词选序[M]//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1617.
[12]夏承焘.瞿禅论词绝句[M]//夏承焘.夏承焘集:第2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13]夏承焘.乐府补题考[M]//夏承焘.夏承焘集:第1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14]夏承焘.词论八评[M]//夏承焘.夏承焘集:第2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15]夏承焘.冯正中年谱[M]//词学季刊:第二卷第三号.上海:开明书局,1935.
[16]陆游.南唐书[M]//丛书集成初编:第385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240.
[17]陈廷焯.白雨斋词话[M]//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3780.
Xia Chengtao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Old-new Ci-poetics Centered onCi-poeticsQuarterly
Xiong Shuqi Xu Heya
(School of Humaniti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1121)
The 1930s lies in the critical juncture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old-new Ci-poetics. As a professional journal of Ci-poetics,Ci-poeticsQuarterly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linking up Ci-poetics researchers and Ci-poetics studies, hence a pivot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old-new Ci-poetics. Recommending historiography in Ci-poetics studies and initiating the genealogy of Ci-poets, Xia Chengtao had his series of Ci-poets’ chronicles published successively inCi-poeticsQuarterly. He expounded Ci poetry according to the fact, studied Ci poetry by rigorous scientific methods, and rectified subjective atmosphere in Changzhou Ci-school’s Ci-poetics studies. Xia Chengtao pushed forward the modernization of Ci-poetics studies in specific practices and methods, thus becoming the joint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old-new Ci-poetics.
Xia Chengtao; old-new Ci-poetics; transformation;Ci-poeticsQuarterly
2014-07-27
杭州师范大学研究生创新种子基金资助项目成果。
熊舒琪(1989-),女,江西九江人,杭州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许和亚(1990-),男,安徽阜阳人,杭州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I206.6
A
1008-293X(2014)05-0059-05
(责任编辑林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