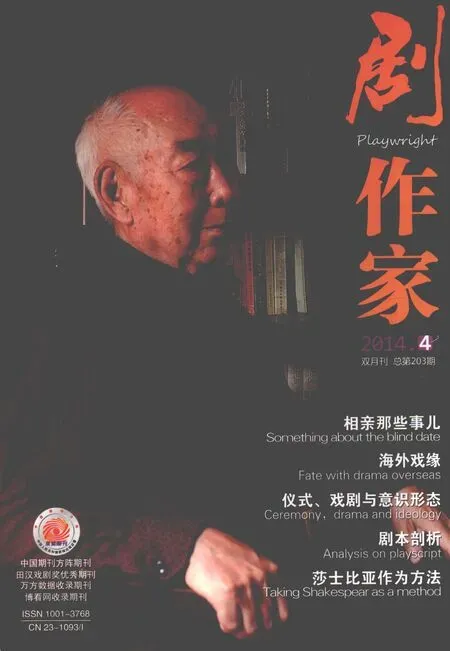仪式、戏剧与意识形态(续)
陈世雄
仪式、戏剧与意识形态(续)
陈世雄
四、中国戏曲史的重要一页:从民间目连戏到宫廷目连戏
上述禁忌只是官方意识形态与民间意识形态在戏剧领域展开斗争的一方面,而妥协与合作是斗争的另一方面。但妥协需要一个介于两者之间的协调者,一种起桥梁作用的力量,在中国,扮演这种角色的是士绅阶层。不管是在哪一方面,士绅文化与朝廷文化在控制与压制民间文化上都建立了一种意识形态合作关系。
士绅阶层是中国古代社会意识形态结构中最具活力的阶层。在元代,统治者将士绅阶层打入社会的底层,拒绝和他们合作,但是,士绅阶层作为中国文化大传统的代表,与民间小传统结合,推动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戏剧繁荣。到明代,汉族人重新掌握政权,恢复了传统中国官方意识形态与士绅意识形态在儒学礼教基础上的统一。清代政权虽然和元代一样是非汉族政权,但是,满族统治者自觉地认同儒家意识形态传统,并且将士绅阶层纳入统治集团。问题在于,满族人政权建立的法统与汉族文化传统的道统本身就是矛盾的,这就形成一种悖论,一种紧张的状态,清代的意识形态结构中始终存在着某种张力。清代统治者企图利用士绅阶层代表的正统儒学来证明其皇权的正统性,另一方面,士绅阶层又需要依附朝廷来发展自己。双方形成了一种微妙的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在文学艺术领域同样如此。
下面让我们看看戏曲艺术领域的两个典型例子,一是目连戏,二是《琵琶记》。
目连戏是从印度佛经中的目连故事发展而来的。目连是释迦牟尼的十大弟子之一,从梵文翻译为中文时,一般译成“摩珂目犍”,“目连”是它的缩音。目连救母的故事之所以传入中国,要归功于《佛说盂兰盆经》,它只有八百余字,却是后世所有描写目连故事的文艺作品的祖本蓝本。故事其实很简单,讲的是目连在祗园精舍悟到佛法,便想救度父母,以报养育之恩。他以道眼观世间,见其亡母生恶鬼道中,瘦骨嶙峋的没有饭吃,目连十分难过,便以钵盂盛饭前往。可是“母得钵饭,便以左手仗钵,右手搏食,食未入口,化成火炭,遂不得食”。目连受佛指点,于七月十五日十方僧众自恣时,为七世父母及现世父母厄难中者,作盂兰盆会,即以盆盛百味五果和甘美食品,供养十方僧众,以报父母长养慈爱之恩。因为目连的这一功德,他的母亲得以脱离恶鬼道。其他佛经中的目连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为人们所淡忘。但是,目连救母的故事由于符合中国儒家关于提倡“孝道”的思想,因而得到民众的认可,千百年来一直广为流传。
从佛经故事到目连戏的演变,是从宗教向世俗的演变,并且越来越具有民间性。主要有这么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是时间空间和人物的中国化和地方化。故事发生的地点从印度搬到河南的开封,甚至可以搬到湖南、四川或其他的什么地方;目连本人也由一个以母氏姓为名的佛门殉教徒,变为傅门的孝子贤孙。这种中国化和地方化的处理,为故事在中国各地的传播提供了便利,使老百姓更加容易接受,产生共鸣。
第二,是叙事体向代言体的转变。从唐代开始,目连故事以变文的形式开始在中国传播。变文是寺院中僧人向百姓宣传佛教的俗讲依据的底本。宣讲时,通常要与图画相配合,一边向听众展示图画,一边说唱故事。所用的图画称为“变相”(这种方式有点像当代的多媒体课件PPT)。目连变文有许多不同版本。仅敦煌变文中就有目连变文11种。[1]宣讲佛经的说唱也是一门艺术,但它是叙事体的。正如王国维所说,中国的“真戏剧”元剧之产生,必须兼备两个条件,一是乐曲上的进步,二是由叙事体而变为代言体。到了金院本中,便有了明显的进步。在现存仅有的金院本目录“拴搐艳段”中,有“打青提”一剧,据文献可以证明,这种艳段的演出形式是“有道念、有筋斗、又有科泛”的,也就是说,这种表演已经从讲唱配以图画发展成用演员的表演来图解讲唱的内容了,它“当是念舞并重,热闹而火爆的戏曲小段。《打青提》一剧属于这类院本,虽然没有剧情简介,但可以知道,该剧是以青提夫人为主角来演出的。联系到后来的目连戏演出,《打青提》很可能是青提夫人背誓开荤,被押入层层地狱时的表演”。[2]到了北宋,目连戏已经发展成可连演七天的大型剧目。比起说唱艺术,戏曲演出当然拥有更多的观众(《东京梦华录》说“勾肆乐人,自过七夕,便般扮《目连救母》杂剧,直至十五日止,观者增倍”[3]),其影响也更加广泛。目连戏的广场演出往往带有典型的广场文化的狂欢性质。
第三,民间艺人的辗转演唱与再创作。目连变文是融于民间说唱艺术中而被人们接受的。经过民间艺人的辗转传唱,已经刻画了具有鲜明性格的目连形象,增加了大量的人物和情节。原来的《佛说盂兰盆经》只有目连、目连母和佛,而在敦煌变文《目连缘起》中,目连有了俗家的名字罗卜,目连母亲号为青提夫人。还增加了目连之父傅相(古代官职“辅相”的谐音),以及阎罗大王、狱主、夜叉王、地藏菩萨、八部天龙等佛教诸神。除此之外,还插入了道教中的神祗,如泰山都尉和五道将军等。情节也大大地丰富了。明代是“目连救母故事假民间说唱和戏曲的形式,在百姓之中广为流传的高峰时期。以目连戏而言,这种民间的演出,是在某种特定的时期和条件下演出的,虽是百姓自娱自乐,但因其演出形式的原始,腔调的古朴,多为士大夫所不齿。他们在谈论目连戏时,多持贬语(如祁彪佳等)”。[4]这就证明早期的目连戏主要是百姓集体再创作的产物,而文人并没有介入,正因为这个缘故,目连戏成长为民间意识形态的载体和百科全书。
第四,与各种民间祭祀仪式和民俗活动的密切关系。目连故事最初衍为戏曲演出就是与北宋东京中元节的民俗节日相结合的。[5]后来,目连戏与民间节庆活动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刘祯在其《中国民间目连文化》一书中列举了南陵目连戏为民间祭祀活动和民俗活动频繁演出的例子:
(1)秋收以后,为还祈求风调雨顺之愿,接请班子演戏谢神,俗称“稻旺戏”。
(2)每年正月十五,芜湖县兴圩和修桥竣工都要唱目连戏。
(3)农历二月二日土地会,时人祈求丰年而唱戏。
(4)农历二月十九日为观音会,唱戏谢观音。
(5)农历三月三日唱戏纪念晏公菩萨。
(6)农历三月十九日是插花娘娘的娘娘会,许愿唱戏。
(7)弋江每年四月十五兴火神会,逢会唱目连戏祭神。
(8)农历六月二十九日,南陵农村有“打青苗”风俗,许愿唱目连戏祈求丰收。
(9)某地发灾或时疫流行,或牲畜瘟病,或有人患重病,也许愿接班子唱目连戏,以谢神驱邪。[6]
再看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在福建莆仙地区,目连戏的演出承担着宗教仪式的功能,“以戏中的目连人物为戏台下的信众(超度之家)做超度亡灵、荐亡超升的表演,呈现戏剧与宗教科仪的混同合一状态,这是全国各地所罕见的一种‘以戏演仪’现象。”[7]叶明生还将这种现象称为“宗教世俗化”与“戏剧仪式化”。[8]泉州的打城戏和莆仙的目连戏相似,也是一种为民众的超度亡灵仪式服务的剧种,仪式上必不可少的剧目就是目连戏。打城戏的一个特点是保存了大量绝活、特技的高难度表演。莆仙的目连戏虽然在这方面不如泉州打城戏,但是带有浓重的宗教氛围。有的演出在远离演戏的大棚十几里的地方(或乱坟堆边)设一小棚,让刘贾、刘四真在那里演“开荤”,而五方鬼卒从庙中领到“描朱”的“火牌”后,直奔此处,把这些正在吃大荤的人犯抓到,并押解回到距离十几里远的演戏大棚,这种实地演出的方式令人联想起20世纪美国导演谢克纳的“环境戏剧”,而且环境更为逼真,围观者数量庞大,气氛肃穆,有震撼人心的效果。
所有这些,都使目连戏具有其他剧目难以比拟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是持久的、深刻的和极其广泛的。经过宋元明清四个朝代,随着时间的推移,目连戏在中国各地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变体,内容越来越丰富,演出时间越来越长,甚至可以连演多日,对百姓的影响也越来越强烈,实际上“形成了与文人传奇并行的一条戏曲发展路线”[9]。这种盛况,引起了统治者的恐慌,到清代,终于导致了朝廷的警觉和禁演措施。
从王利器编辑的《元明清三代焚毁小说戏曲史料》可以看出,清代统治者“饬禁”目连戏的理由主要是:第一,目连戏“易至聚睹藏奸,为害地方。”第二,“耗费民财,败坏风俗。”“风尽淫词,伤风败俗。”第三,“装神扮鬼、舞弄刀枪”、“跳舞神鬼、穷形尽相”。
目连戏的某些消极影响固然不可否认,但是,封建统治者之所以禁演目连戏,“根本原因还在于目连戏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和理想愿望,它与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格格不入,不利于统治阶级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统治和愚昧,特别是演出时那种轰轰烈烈的场面让封建官府、统治者不寒而栗,容易联想到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暴动”。[10]
清代统治者对目连戏的禁令十分严厉。针对特定的一个剧目,前后数十年在许多地方一再颁布禁令,责罚越来越重,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
这里要着重讨论的是封建统治者的另一手,即对目连戏加以改造和利用,使它从民间意识形态的载体转变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载体。在这一巨大的工程中,统治阶级不能不依靠士绅阶层的帮助,这可以说是朝廷文化与士绅文化之间意识形态合作关系的一个典型事例。
早在明代,就已经有文人编撰的多种目连戏曲文出现,其中最著名的是万历年间郑之珍撰写的《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后人简称为《劝善记》。郑之珍是个怀才不遇的文人,因为屡困科场,便放弃功名,致力于编撰《劝善记》,目的是为了实现“立德立言以垂训天下后世”之初衷。经过这位才子加工的目连戏《劝善记》,比起明代目连戏的另一个系统,即《救母记》系统的曲文有明显的差别,其内容虽有迎合世俗的一面,但基本上还是相当正统的,曲文词语则有“俊雅之风”。相比之下,《救母记》因为没有经过文人加工,风格较粗犷,语言较俚俗,但是却在底层百姓中很有市场。
必须注意的一点是,郑之珍是自发地,而不是奉朝廷之命而编撰《劝善记》的。明代知识分子还没有与朝廷在改造利用目连戏方面进行合作。真正的合作是到了清代才开始的。康熙年间上演的宫廷目连戏《劝善金科》虽然至今无法查明其作者[11],但肯定是文人奉康熙皇帝之命进行再创作的产物。戴云在《<劝善金科>研究》中称之为“康熙旧本”。
戴云对比了郑之珍的《劝善记》和康熙旧本《劝善金科》。所得到的结论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劝善金科》增加了一条新的情节线索,“即朱泚、李希烈谋反叛乱,颜真卿、段秀实为国尽忠,李晟翦灭贼寇之事,并穿插了四个完整的故事,陈荣祖被张节逼得家破人亡,郑庚夫被后母所害,含冤自尽,李文道图财害命与莫可交忘恩负义等事”。[12]由于上述人物均为真实的历史人物,《劝善金科》就不再是单纯的宗教故事,也不是世俗生活的写照,而是带上了几分历史剧的色彩。
第二,为了将上述发生在唐代的历史人物及其故事增加到目连戏中,《劝善金科》将剧情的时代背景定在唐德宗时代。
第三,增加了刘贾、刘氏和傅罗卜的戏,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动。刘贾在康熙旧本中被刻画为一个里巷泼皮、市井无赖,犯下一连串恶行,最后终于遭到报应。刘氏在丈夫死后的悲痛心情,在开荤之前的矛盾心理,都得到更细腻的描写。另外增加了她死前死后遭到勾魂、捉魂的戏和其他场面。主要人物傅罗卜的戏也增加了许多,特别是在他救母途中设置了更多的障碍,突出地表现了他时时处处行善的精神和不畏险阻、一心救母的决心。
据戴云的研究,康熙旧本“非出自一人之手,其抑或为多名词臣合作完成的成果”,许多情节不是作者“原创”,而是根据多部旧戏“拼凑”而成。剧情拖沓,有些地方甚至很不连贯。[13]规模巨大,必须连演十天,是一部地地道道的宫廷大戏。但是它得到了康熙皇帝的高度重视。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即在平定三藩之后,为庆祝国家统一,清宫内架起高台,上演这出大戏,并且“用活虎活象活马”。行头砌末专门以黄金、白银制成。“演出过程中,康熙皇帝还亲自上台向台下抛钱,用以布施五城的穷苦百姓。而且是‘彩灯花爆,昼夜不绝’。可见演出规模之浩大。”[14]
如果说民间目连戏是民间意识形态的载体,那么,宫廷大戏《劝善金科》就成了国家意识形态的载体。其演出时间的选择就不同于民间目连戏。清以前的目连戏较多的是在七月十五中元鬼节作盂兰盆会前后演出,就是到了清代,民间演出也都固定在鬼节和其他农闲之时。《劝善金科》改在岁末演出,一种解释是满族人信奉萨满教,上演《劝善金科》是为了驱除鬼魅,祈求吉祥,这当然是编演此剧的目的之一,但是,毫无疑义,有着更为深层的意识形态上的考虑。
我们知道,康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帝王之一,文治武功皆卓越非凡。尤其可贵的是,他对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汉民族文化有深刻的了解。他知道,满族人入主中原,以及后来平定三藩,降服郑氏,靠的主要是武力。为了在国家统一后巩固自己的政权,他需要利用戏曲这一数百年来对汉族民众一直起着教化功能的工具,而目连戏则是他首选的剧目。他知道,将汉民族能够接受的忠孝节义观念植入目连戏中,更容易打动百姓,让他们绝对服从帝王的统治,若是有人敢于犯上作乱,那么死后就要被打入地狱,遭受无穷无尽的折磨。
从郑之珍的《劝善记》到明代各种版本的目连戏散本,最核心的内容是一个“孝”字,极少提到历史上的忠臣。只有在中卷的“过耐何桥”、“过升天门”两出中,提到忠臣光国卿“只因谏主,有忤权臣,死不敢辞。今在冥途,列位早上!”等极短的两句念白,加起来不足二十字。[15]而康熙年间重新编撰的《劝善金科》增加了大量郑本目连戏中没有的歌颂忠臣的情节,颜真卿、段秀实为国尽忠和李晟平叛之事成为全剧主要情节线之一,浓墨重彩地加以描绘和颂扬。剧本还将明代目连戏中的罪犯、草寇之类的人物“改造”为叛乱分子或者强盗,使全剧的矛盾冲突更加尖锐。作者对乱臣贼子极尽贬斥,最后让他们个个下层层地狱受尽万般痛楚,用这样的办法来教化百姓。但剧本并没有一味地威慑百姓,而是倡导人们过而能改,安分守己,做个好百姓。郑之珍本中有段戏写何氏兄弟游手好闲、吃喝嫖赌,将祖上遗产挥霍一空,但写得很简单,到《劝善金科》便发展为一段较为完整的情节,结尾是大家共唱“从前错把家业消,终日漂流没下梢。多蒙长者恩义高,败子回头便是宝。”可见除了用威吓的一手,剧中还兼用软的一手。
《劝善金科》编撰者并没有掩饰其宗旨的意思,在剧本的“开宗灵官先上扫台”一场,两位灵官有这样一段台词:
这本传奇,原编的不过傅相一门良善,念佛持斋,冥府轮回,刀山水火。善者未足起发人之善心,恶者不足惩创人之恶志。当今万岁爷,悯赤子之痴迷,借傀儡为刑赏,曲证源流。悬慧灯于腕底,兼罗今古;驾宝筏于毫端,删旧补新,从俚入雅。善报恶报,神栽培倾覆之权;去骄去淫,凛恶盈损满之戒。世纪升平……要使天下的愚夫愚妇,看了这本传奇,人人晓得忠君王,孝父母,敬尊长,去贪淫。戒之在心,守之在志……善恶必报,不昧毫厘……见世有不明之事,天无不报之条。借此引人献出良心,把那奸邪淫贪的念头,一场冰冷,如雪入洪炉,不点自化……台下的人,要把来当艳舞新声,寻常观听过了。[16]
在十卷二十二出,末扮的采访使者又进一步指出,是“当今万岁爷”即康熙皇帝下令编撰这部《劝善金科》的。编写的目的是要“让人们学做忠臣孝子节妇烈士,或生前功名显赫、福禄随身,或身后名留千古;如若反叛朝廷,大逆不道,不但生前不得好死,死后在阴间还要遭受种种酷刑”。[17]剧本末出的下场诗唱道:“金科劝善宣扬后,寰宇祥光五色开。”[18]这正是《劝善金科》编创的初衷。
经过《劝善金科》编创者的努力,目连戏这一在民间影响极大的曲目,被改写成一部宫廷大戏,从以宣扬“孝”为主旨改变为以宣扬对朝廷的“忠”为主旨,从民间意识形态载体改变为官方意识形态载体。这个过程无疑是一批御用文人与朝廷合作的过程,虽然我们至今无法查证这个群体的具体构成。
然而,朝廷与文人合作对目连戏的改造工作并没有就此停止。乾隆之初,又出现了一部张照奉旨修改的新版《劝善金科》(乾隆五色套印本,简称“五色本”)。[19]修改者张照曾在宦海中遭受很大挫折,不仅被革职拿问,而且到了“入狱几死”的地步。乾隆元年被释放,二年授内阁学士,入直南书房。几年后,张照修改的《劝善金科》和他编撰的其他几部大戏深得乾隆满意,于是又被提升为刑部尚书,兼领乐部。
乾隆之所以决心修改康熙旧本《劝善金科》,一方面可能是对旧本格调之粗俗感到不满,另一方面可能是感到他面临的形势已经不同已往。乾隆即位之初,距三藩平定已经过去五十多年,大清国比起刚刚统一之时,已经更加稳定和强大,所以,有必要更多地宣扬太平美景,显示朝廷的德政和仁政,而不必像康熙旧本那样强调惩罚叛逆。换句话说,朝廷的意识形态重心有调整的必要。
张照被重新起用后,心怀对“皇恩”的感激之情,仔细揣摩“圣意”,对康熙旧本作了小心的修改。共增加十八出,删除十九出,内容也作了修改,但新版的“五色本”保留了康熙旧本的主要情节,贯穿全剧的仍然是目连救母的故事,而颜真卿、段秀实为国尽忠,李晟平息叛乱以及陈荣祖、郑庚夫、李文道、莫可交等人的事迹也全部保留。全剧的基调没有发生变化。新版的五色本虽然刻意淡化了惩恶的宗旨,删除了揭露“赃官骗百姓”和“豺狼当道”之类不利于歌颂乾隆盛世的场面和话语,展现了国泰民安的大好局面,但是,新版和旧本一样,仍然体现了皇帝的“圣意”,这就是要巩固皇权的地位,对那些企图造反的人发出警告。从艺术上看,经过张照的加工,五色本的剧情合理顺畅了许多,人物性格也把握得比较准确,文字也干净得多,清顺典雅,与原剧的鄙俗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康熙旧本的修改中,张照小心地掌握了淡化惩恶宗旨、歌颂大好形势与坚持维护皇权的“主旋律”之间的平衡,完成了乾隆交给的任务,这一成功充分体现了汉族知识分子在协助朝廷调整意识形态方针的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刘祯认为,民间目连戏被改编为宫廷大戏“是目连戏发展中出现的一股逆流,是目连戏思想与精神的反动。宫廷改编与民间演出已完全不同”。[20]不过,宫廷目连戏,不论是康熙旧本还是新版五色本,对民间的影响都不大。宫廷目连戏毕竟是在皇宫的围墙内上演的,锣鼓声传不到遥远的乡村。在民间,目连戏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着,延续着。规模浩大的宫廷目连戏为国家仪式服务,民间目连戏为老百姓自己的仪式服务,分别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分别体现着官方和民间的意识形态。
五、民间目连戏与民间意识形态
我们之所以将民间目连戏称为民间意识形态的载体,是因为民间目连戏所包含的解释世界的方式、价值判断、法律观念、宗教观念既具有民间性,又具有系统性、权威性和排他性。
正如刘祯所说,“目连戏的思想是封建社会中下层群众的思想,虽然存在着宗教迷信、因果轮回等因素,但它反映的大多是民间朴素的思想感情。”[21]这种意识形态的民间性在目连戏中首先表现为“孝”的观念。报恩行孝是民间目连戏的核心思想,是全剧的主题。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和社会集团,对“孝”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标准,不同的要求。这是毫无疑义的。笔者在拙文《戏剧思维的三种基本方式》中曾经说过:“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价值等级体系中,道德价值高于审美价值,各种道德价值依严格的等级层次排列而成,道德价值结构制约着审美心理结构,成为导致公式主义的重要根源。”[22]“让我们看看在中国封建社会影响极大的“曲祖”《琵琶记》吧。男女主人公在说唱艺术和地方戏中原是一对双双死去、结局悲惨的人物,可是到了高则诚笔下就成了另一个样子。假如把《琵琶记》写成一个大悲剧,就宣扬了忠孝的不可调和,否定了三纲的有机整体性和合理性。在当时的历史社会背景下,这显然是不允许的。忠和孝是三纲五常的两个有机环节,家庭和整个封建社会是子系统和母系统的异质同构关系,忠与孝本来就应该是统一的。因此,只有把《琵琶记》写成一部五伦全备,全忠全孝的作品,才能符合封建伦理的法则。为此,只好违背生活的逻辑,牺牲人物性格的一致性。思维方式是理性的,然而却是被一定的规范扭曲了的理性。”[23]
目连戏和《琵琶记》截然不同,它不是一部宣扬“忠孝两全”的剧目。目连在自己的母亲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后,官封剌史不受,美满姻缘不谐,“真心救母无他向”,历尽千难万苦,终于把母亲从地狱苦海中拯救出来。为救母亲而不当官,不结婚,毅然出家,这样的形象是中国古典戏曲中少有的形象,闪烁着圣洁的光辉,和那些一心追求功名和美貌佳人的书生、才子们不可同日而语。目连拯救母亲,不但出自一片孝心,而且出自凛然正义。母亲刘氏遭受的苦难,是那个时代被压迫的劳动大众所遭受苦难的象征。地狱中的刘氏是受苦人的代言人,尤其是受苦的劳动妇女的代言人。一个“苦”字,在刘氏的念白和唱词中不知重复了多少次。最感人至深的是“三殿寻母”一出中“三大苦”的诉说:“人生莫作妇人身,做个妇人多苦辛。媳妇苦也是本等,且说做娘苦楚与世人听。”接下来的三段唱,最流行的是诉说“第一苦”即“乳哺三年苦”的唱段。这段唱特别感人,在目连戏的许多版本中都保留了下来(例如莆仙戏《目连救母》)。在郑之珍本中,“三大苦”唱段的最后一句是:“这是为娘三大苦,我今说与世人详。奉劝世间人子听,五更高枕细思量。从头说尽千般苦,只恐猿闻也断肠。”众人听罢,在场所有人物,包括狱官及其手下和夜叉等人在内,齐声唱道:“三大苦更可伤,越教人涕泪滂。”狱官说:“刘氏,三大苦楚,非你说不出来。为人子者,须当谨记,谨记!”[24]这场戏有力地突出了“孝”的主题。
刘祯先生指出:“可以看出,目连戏的孝主要是对母亲、自己亲人的孝,而不包括‘事君’的所谓大孝。它与以‘全忠全孝’相标榜的‘曲祖’《琵琶记》是不同的。”[25]这段论述强调民间目连戏在“孝”的观念上坚持了自己的民间立场。
其次,目连戏在法制观念上确立了自己的民间立场。剧中构建了一个完整而严密的法网,“掌理天曹是玉皇,人间敷治赖君王。天人两下皆兼理,地府阎罗独主张。”[26]不仅有明确的分工,而且有相应的空间布局。这一切在剧中都有形象的描绘:“但见天府巍巍金灿灿,有十大重的宝殿;地狱济济铁辚辚,有十八重的阴司。宝殿何为十大重?东二殿,西二殿,中二殿,南二殿,北二殿,十大重显显煌煌。阴司何为十八重?东四司,西四司,南四司,北四司,中二司,十八重深深隐隐。殿一殿天造地设,重一重鬼哭神愁。且论十殿天王,分理一十八重地狱,……十大殿统论纲领之尊严,十八重细数条目之周密。刑名虽备,刑实期于无刑;法纲虽详,法乃所以止法。但愿天多生善人,个一个不堕地狱;又愿人多行善事,件一件莫犯天条。使十殿虽设,千古常空。”[27]这张法网,可谓严严实实,任何罪犯都无法逃脱。但是,同时又希望法制的威慑能使人们多行善事,让天府地狱都成为徒然虚设。
剧中各殿各司,都是铁面无私的执法者。例如,城隍一上场就唱:“天地无私,神灵有职把阴阳理。阳世差池,阴司里难逃避。”接着道白:“山川处处有神灵,体察人间仁不仁。处事惟凭三尺法,加人不用半毫心。”剧中反复强调“阴间法度无偏枉”,“阴世法律无边外”,“阴司网密、有钱买不开”,从而与阳世徇私枉法、草菅人命的现象形成鲜明的对比,反映了民众对法律公正的强烈愿望。这种强烈的对现实的批判性和对法制公正性的向往,正是民间意识形态的一大特征,在民间目连戏中得到生动形象的体现。
第三,独特的人间、天上、阴间三界的思维模式,反映了解释世界的民间方式。
在目连戏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宗教思维对戏剧时空观和结构方式的影响。宗教思维是和理性思维相对立的。宗教幻想使《俄狄甫斯王》式的思维方式所特有的时空局限性化为乌有。黑格尔在谈到印度艺术的“形象的漫无边际性”时举剧本《沙恭达罗》为例。黑格尔写道:
剧本《沙恭达罗》就有这种情况。开始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温柔芬芳的爱情世界,其中一切都是按照人的方式在进行着,可是突然间我们发见这个具体现实界烟消云散了,我们被转运到因陀罗(Indra)天空的云霄里,那里一切都变了,都失去明确的界限,放大成为自然生活与梵的关系以及人凭刻苦修持所挣得的驾御自然神的威力之类普遍意义了。[28]
这里,黑格尔以再明白不过的语言描绘了戏剧思维在宗教思维的影响下是怎样从有“明确界限”的“人的方式”转化为完全“失去明确界限”的腾云驾雾般的宗教幻想方式。
宗教幻想不仅导致了艺术形象的“漫无边际性”,而且导致了艺术结构的漫无边际性。欧洲奇迹剧就是这样的产物。中世纪奇迹剧往往采取连环剧的形式,由一连串短剧组成,用以表现圣经故事,以创世纪始,以末日审判终。最长的一部叫“约克剧”(York Plays),作于14世纪,由48个短剧组成。15世纪的宗教剧继续向大型化发展,最长的《使徒行传》要演40天。这出连台本戏描写耶稣的十二门徒到东方传道,行经印度、西班牙、罗马、埃及等许多国家,经历种种奇事,遭受种种苦难,最后一个个殉教。全剧共有494名有台词的角色,规模极其宏大。
在东方,同样有类似奇迹剧的宗教戏剧,而且出现的时间更早。出土于我国新疆的《弥勒会见记》成书于公元8至9世纪,描写弥勒出家学道成为佛的弟子后降生人间,后又弃家寻道,得成正觉,下地狱解救受苦众生的全过程。全剧长达27幕,演出时间无从考查。目连戏这部中国式的奇迹剧早在北宋就发展成时空频频转换,可连演8天的连台本戏。
综观东西方的连台本宗教戏剧,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剧情发生地点在人间、地狱、天堂(或佛国)之间频频转换,而不是像希腊悲剧那样局限于单一不变的地点;时间跨度可以是数年、数十年,有时还具有“上天方一日,世间已千年”的相对性,绝不像希腊悲剧那样将剧情浓缩、集中于危机爆发到危机解决的短暂时日。这种时空转换、变化的极大自由,正是宗教思维影响的结果。如果说古希腊悲剧是表现危机以及对危机根源的高度理性化的剖析,那么基督教奇迹剧、目连戏和《弥勒会见记》之类的戏剧就是表现过程,直观地形象地展示宗教幻想的轨迹。
宗教思维对戏剧思维的影响即使在最伟大的戏剧家的创作中也有十分典型的表现。我国的汤显祖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牡丹亭》中“生—死—再生”的构思正是佛教“三世”之说影响的结果。所谓“三世”之说就是认为任何一个个体由于因果轮回只能存在一定的时间:过去、现在、未来;人死了之后,可以转生;人死后成鬼,人鬼可以相见。杜丽娘梦中见到柳梦梅,害相思病伤情而死;她的鬼魂三年后与柳梦梅相会,并得再生,这一“生—死—再生”与人鬼相见、人鬼结合的情节框架,正是印证了佛家的“三世”之说。
这种在观念上一反佛家学说,在思维方式上却与佛家暗合的矛盾现象,我们可以在但丁的《神曲》中找到相似之处:《神曲》一方面有反封建反教会的倾向,另一方面在总体构思上(地狱、净界、天堂三界的设置和七种罪恶的分类等)又遵循了中世纪基督教的说法。但丁是借宗教思维的先验模式来体现他的人文主义思想,探讨意大利民族复兴之路的。
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和汤显祖同时代的莎士比亚。有人把莎士比亚的悲剧称为“基督教悲剧”。海伦·加德纳在《宗教与文学》一书中指出,莎士比亚悲剧的“时间安排”是“非古典主义”的,“强调个人经验及其逐步的发展”[29];古希腊悲剧表现危机,而莎士比亚悲剧则表现过程:“过程和时间是莎士比亚悲剧的基本因素”[30]。这一转变正是宗教思维影响的结果:“它与《圣经》强调历史的意义,强调基督教经典包含着许多历史叙述和人物传记这一事实肯定是有联系的。”[31]基督教的观念“使得人的整个生活经历带有启示性,因而生活的意义被看成一条曲线、一个单一的命运的展开,而不是包含在一个死结里。”[32]莎士比亚深知浓缩在戏剧里的价值,但他的悲剧突出了叙述性因素,采取了叙述体结构,“从未遵循过三一律”。[33]歌德的例子也是不可忽略的。他的剧作在结构上是对莎士比亚的模仿,同时也是宗教思维影响的结果。《浮士德》第一部有一个“天上序幕”,通过上帝和魔鬼梅菲斯特的对白体现了对人类历史发展的预言,全剧的结局是上帝预言的实现。但歌德自己说过,他这样做并无宗教意义,而只是“借助基督教的一些轮廓鲜明的图象和意象,来使我的诗意获得适当的、结实的具体形式”[34]。这是借用宗教思维的方式表现非宗教、反宗教内容的一个典型范例。
作为一部典型的宗教戏剧,目连戏并不是反宗教的。相反地,剧本从内容到时空处理都打下了深深的宗教烙印。然而,它又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将目连戏和在元代一度十分流行的神仙道化剧相比,能够看出明显的不同。神仙道化剧虽有许多“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仙境,但少有地狱的场景。而目连戏则以地狱为重要的戏剧场景。正像郑之珍本“傅相救妻”一出中城隍所说,目连是“寻母到幽冥,把重重地狱都游尽。”从“一殿寻母”到“十殿寻母”,目连历尽千辛万苦,而他的母亲刘氏在地狱中则通过了金钱山、滑油山、望乡台、耐河桥、升天门等多层地狱,受尽种种折磨。剧中关于地狱情境和可怕刑罚的描写相当具体,具有震撼力,这在中国戏曲史上是少有的。
地狱场景在全剧占重要地位,这恰恰是目连戏民间性的一个表现。正如刘祯所说,地狱固然阴森可怕,但却是惩罚、苦难和死亡的象征。“科学地看地狱是不存在的,在民间却相信其有,相信它的存在……地狱是不存在的,但它的产生又是合理的。目连戏作者通过一个不存在的、虚妄的世界,运用对比手法批判和否定了这个现实中存在却不合理的有私社会,批判和否定了这个有私社会的制度及其存在。”[35]
六、小结
任何仪式都不可能自动地生成戏剧,必须经过漫长而艰难的转化过程,代言体意识(现在时意识)的形成与外部环境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古希腊戏剧是在高度发达的希腊文明中形成的,三大悲剧诗人的出现是戏剧高度成熟的标志。在漫长的中世纪,西欧戏剧走向即兴化与低俗化,新的大剧作家在文艺复兴之前没有出现,基督教对戏剧的歧视和压迫是重要原因。相比之下,中国戏曲受到的压迫不是来自宗教,而是来自封建统治者(中国的宗教生态不同于西欧)。历代统治者对民间戏剧的禁毁有多方面的原因,而最重要的原因是加强意识形态控制的需要。中国民间戏曲是民间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封建统治者一方面禁毁民间戏曲,另一方面改造民间戏曲,并且争取士绅阶层的合作。目连戏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经过文人改写的宫廷目连戏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载体,使目连戏的发展形成官方与民间两条截然不同的路线。官方与民间的意识形态斗争对戏剧的走向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全文完)
注释:
[1]戴云:《<劝善金科>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
[2]同[1],第15页。
[3]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9页。
[4]同[1],第23页。
[5]参见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八。
[6]刘祯:《中国民间目连文化》,巴蜀书社,1997年版,第324-325页。
[7]叶明生:《莆仙戏剧文化生态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7页。
[8]同[7],第356页。
[9] 刘祯:《中国民间目连文化》,巴蜀书社,1997年版,第44页。
[10]同[9],第60页。
[11][13]同[1],第47页。
[12]同[1],第42页。
[14]同[1],第36页。
[15]参见郑之珍撰、朱万曙校点《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黄山书社,2005年版,第二七七、二九四页。
[16]转引自戴云:《<劝善金科>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0页。
[17]同[1],第51页。
[18]转引自戴云:《<劝善金科>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2页。
[19]乾隆之前清内府档案不存,嘉庆时的档案大部不全,所以无法看到乾隆批复的关于修改《劝善金科》的圣旨。但从昭摙《啸亭续录》的有关记载中可以得知,张照是奉了乾隆之旨才去修改《劝善金科》的。
[20]参见戴云:《<劝善金科>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3页。
[21]同[9],第56页。
[22]同[21],第65页。
[23][24]陈世雄:《戏剧思维的三种基本方式》,《文艺研究》,1989年第4期。
[25]参见郑之珍撰、朱万曙校点《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黄山书社,2005年版,第三七二至三七六页。
[26]同[9],第68页。
[27]同[15],第二○一页。
[28]同[27],第三四七至三四八页。
[29]〔德〕黑格尔:《美学》第二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51页。
[30]〔英〕海伦·加德纳:《宗教与文学》,沈弘、江先春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2页。
[31][32][33]同[30],第76页。
[34]转引自余匡复:《德国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14页。
[35]同[9],第74页。
责任编辑 原旭春
——弋阳腔艺术保护中心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