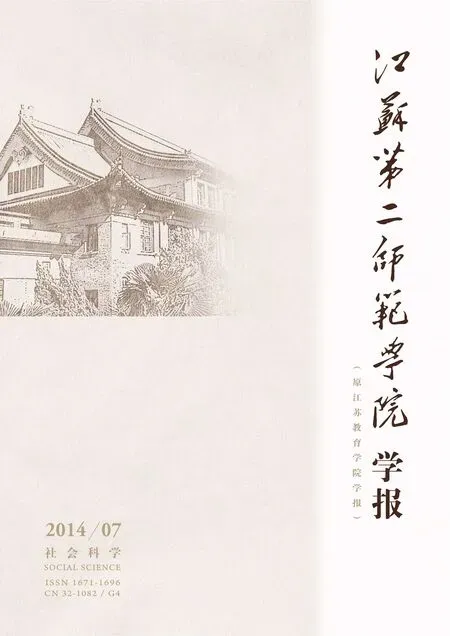大卫·哈维《后现代的状况》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径
陈 磊
(南京大学哲学系, 江苏南京 210093)
大卫·哈维《后现代的状况》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径
陈 磊
(南京大学哲学系, 江苏南京 210093)
大卫·哈维在其《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一书中,于空间化的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内,沿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路径,证明了“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这一命题。从政治经济过程分析了这种文化经验的形成、性质和内在机制,详细阐明了资本灵活积累的经济趋势和“时空压缩”理论,从而为总体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和文化提供了一种综合视角,也为我们认识后现代问题和当代中国的后现代风格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后现代; 政治—经济学批判; 历史地理唯物主义
20世纪7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相互冲突的意见和政治势力的战场”[1](P.56),无论是建筑规划还是小说创作,无论是哲学层面实用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的结合还是神学方面上帝与真理同在,都呈现出许森斯所表述的“有感受性、实践活动与话语构成方面的一种值得注意的转移”。[1](P.56)而如何评价、理解和解释这一变化却显得极为困难。后现代主义是“代表了与现代主义的彻底决裂”还是“只不过是在现代主义内部反叛某种形式的‘盛期的现代主义’”?是“一种风格”还是“应当严格将其看成是一种划分时期的概念”?是“反对一切形式元叙事”的革命性力量还是“只不过是对现代主义的商品化和通俗化”的折衷主义?是“破坏了新保守主义的政治”还是与之结合?后现代主义的崛起是该“归因于资本主义的某种彻底重建、某种‘后工业’社会的出现”还是该将其视作纽曼和杰姆逊所提出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1](P.60)面对这一理论困境,哈维在《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一书中以丰富的细节展开了自己的讨论。
一、哈维后现代理论的学术图景
哈维承认,哈桑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纲要性差异”列表式的图解为他理解后现代主义提供了“一个有帮助的起点”。相比哈桑所列的语言学、人类学、哲学、修辞学、政治学和神学等诸多领域的差异,哈维认为更为重要的是把握“一种对于差异可能是什么的感觉”。[1](P.62)他从后现代主义“完全承认短暂、分裂、不连续性和混乱构成了波德莱尔的现代性概念①波德莱尔在《现代生活的画家》(1863)一文中写道:“现代性就是短暂,流变,偶然事件;它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则是永恒与不变”。(参见[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的一半入手”,分析了后现代主义“强调现代生活深度的混乱及其在理性思想面前的难以应付”却又并不试图“超越它、抵制它甚或去界定包含在其中的‘永恒与不变’的各种要素”。[1](P.63)哈维认为,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思想中的分裂、短暂、不连续和混乱变化的状况的连续性比二者之间的差异性更加重要,应当“把后者看成是前者内部的一种特定危机,一种突出了波德莱尔所阐述的分裂、短暂和混乱一面的危机”。[1](P.155)在这里,哈维特别表达了对马克思将这个方面当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整体来分析的肯定与敬意。
在呈现自己有关后现代的评价之前,哈维梳理了福柯、利奥塔、阿洛诺维奇、许森斯、德里达、罗蒂和哈贝马斯等理论家的后现代主义思想。这里哈维给予法国哲学家、后现代主义者利奥塔以更多的关注。利奥塔在其代表作《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一书本来是利奥塔应魁北克政府大学委员会的要求撰写的一份临时性“知识报告”,作者因此将其称为“应景”之作;然而,它对后现代性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该书与哈维的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主标题一词之差却指向了不同的理论路径。笔者认为,哈维一书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利氏的回应。一书中指出,“后现代”这个词,“指的是经历了各种变化的文化处境,这些变化从19世纪末就开始影响科学、文学和艺术的游戏规则了。”[2](引言)利奥塔认为,相对于“现代”一词指称“依靠元话语使自身合法化的科学”,“后现代”可以被“简化”为“对元叙事的怀疑”。[2](引言)在利奥塔的语境中,后现代是否可能的问题转化为对后现代时期知识状况的研究。他认为,“后现代知识”,“可以提高我们对差异的敏感性,增强我们对不可通约的承受力”。[2](引言)他坚持把其各种观点“置于新的通讯技术的语境之中,把贝尔和图雷纳关于交流的命题运用于‘后工业’以信息为基础的社会,把后现代思想的崛起置于他认为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交流语言引人注目的社会和政治变迁的核心之中”。[1](P.71)但在哈维看来,只是由于利奥塔如同大多数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一样,受到了信息与知识生产、分析和传递的各种新的可能性的迷惑,“元理论不可能被破除,后现代主义者只不过把它推到了隐蔽之处,它在那里继续作为一种‘现在没有被意识到的功效’起着作用。”[1](P.157)
不同于利奥塔的后现代主义“画像”,哈维更多地站在了与杰姆逊相同的立场上。在哈维看来,首先是把后现代主义当作一种“历史状况”而不是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观念”。这与杰姆逊不把后现代主义当作“文艺或文化的风格来看待”,而采取一种“历史分期的假设”的论述方式[3](P.349)不谋而合。杰姆逊曾经明确指出“后现代主义时代的叙事及其同晚期资本主义的关系是全部问题之所在。”哈维援引后现代绘画和建筑的例证,重申了杰姆逊关于后现代主义中深度感消失、历史感减弱和情感缺失的主题,进而提出了后现代运动的所有问题中“最为艰难的问题”,“即它与日常生活的文化的关系,以及与日常生活的文化的结合。”[1](P.83)他通过对迪斯尼乐园、西铁城手表广告、电视的普及和博物馆文化的增长等日常生活中实例的分析,得出了后现代主义标志着“市场力量向整个文化生产领域合乎逻辑的扩展”的结论。[1](P.86)这一观点再次通达杰姆逊有关“美感的生产已经完全被吸纳在商品生产的总体过程之中” 的论断。正如杰姆逊所论证的,“在资本主义晚期阶段经济规律的统辖之下,美的生产也就愈来愈受到经济结构的种种规范而必须改变其基本的社会文化角色与功能。”[3](P.351)至此,哈维把我们带向了杰姆逊的著名命题——“后现代主义完全就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1](P.88)但他并非只从形式角度揭示后现代主义的特征,从而只是停留在意识形态批判上,而是从政治经济过程阐明了这种文化经验的形成、性质和内在机制,因而具有更强的说服力。[4]这一点我们将在文章的第二部分予以详细阐述。
对于如何评价后现代主义,哈维认为既应当看到它在“对差异的关注,对交流之困难的关注,对利益、文化、场所及类似东西的复杂性与细微差别的关注方面发挥了积极影响,”[1](P.151)同时也应当正视其存在的问题。哈维总结出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将后现代主义夸大成“战胜了被以为是现代主义的一切弊病的一场有意的而非混乱的运动”;二是“轻易地一笔勾销了现代主义实践的物质成就”;三是“与市场无耻地和解”,将其自身“牢牢地置于一种作为新保守主义标志的企业文化轨道之上”;四是“迷恋分裂和不和谐的声音”,“迷恋于解构一切论证形式并使之非合法化”;五是“否认能够把握政治—经济过程的元理论”并“剥夺了在一个不平衡的权力关系世界里的‘他者’的发言权”。[1](PP.154-156)据此,哈维总结道:“后现代主义的言辞是危险的,因为它避免面对政治经济的现实和全球权力的情景。”[1](P.156)在他看来,这是后现代主义与政治的“美学化合谋”,[1](P.157)产生这一状况的各种社会力量从而成为哈维关注的焦点和展开进一步论证的主题。
二、哈维后现代理论的分析范式
在《后现代的状况》一书的第二部分,哈维以“20世纪晚期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转变”为题,直接表明了他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剖析出发的研究路径。他深入分析了代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社会主要生产体制的“福特主义”,以及自1970年代以来出现的“灵活积累”的生产体制,指出正是这两种生产体制分别构成了作为文化现象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基础。[5]哈维认为“福特主义”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时间和空间形式的危机,由此把关注点引向了“对时间和空间的体验”,即“时空压缩”理论。正如他在该书的开篇论点中指出的那样,“1972年前后以来,文化实践与政治—经济实践中出现了一种剧烈变化,这种剧烈变化与我们体验空间和时间的新的主导方式的出现有着密切关系”[1](前言)。在哈维那里,无论什么新颖的观点,都可以将其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的探究之中。
哈维以大量详实的史料论证了“福特主义”发展演变的过程及其主要特征,提出“福特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明确认识到“大规模生产意味着大众消费、劳动力再生产的新体制、劳动控制和管理的新策略、新的美学和心理学, 简言之, 意味着一种新的理性化的、 现代主义的和平民主义的民主社会”[1](P.167)。在此基础上,哈维进一步总结道,“战后的福特主义必须被看成,更多地是一种全面的生活方式。大规模生产意味着产品的标准化和大众消费;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美学和文化的商品化”,“福特主义也以各种非常明确的方式建立了现代主义的美学并为它出了一份力”。[1](P.179)同时,哈维更加深刻地觉察“战后的福特主义也是一桩非常国际性的事件”,“福特主义国际性的进展则意味着在共产主义世界之外全球大众市场的形成和把大批世界人口吸收到新型资本主义的全球动力之中”,这“出现在国际政治—经济调节和地理政治结构的特定框架之内。”[1](PP.180-181)
面对“现存的政治—经济实践与战后繁荣时期的实践之间的反差”[1](P.165),面对1965-1973年间福特主义—凯恩斯主义没能遏制住的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日益突出,哈维提出了从福特主义向“灵活积累”体制转变的论断。哈维将“灵活积累”视作“依靠同劳动过程、劳动力市场、产品和消费模式有关的灵活性”而形成的“与福特主义的刻板的直接对抗”,其特征是“出现了全新的生产部门、提供金融服务的各种新方式、新的市场,首要的是商业、技术和组织创新得到了极大强化的比率”。“它导致了不平衡发展模式中的各种迅速变化,包括各个部门之间与各个地理区域之间的迅速变化”。[1](P.191)哈维进一步通过对劳动力市场的重构、区域经济的兴起、服务业就业的增长、企业规模的扩张、全球金融体系的重组等政治—经济领域一系列深刻变化的分析,得出了“福特主义的现代主义相对稳定的美学”已经让位于基于“灵活积累”的“后现代主义美学的一切骚动、不稳定和短暂的特质”的结论。[1](P.202)根据马克思的分析,“资本主义的危机趋势会产生过度积累的周期性阶段”。哈维认为,1973年以来周期性出现的种种状况就是其典型的表现形式。[1](P.228)在他看来,“通过时间和空间的转移而‘吸收过度积累’”,是一种更为有效的方式,“灵活积累就是两种基本策略的简单再结合”[1](P.235)。在这一分析中,哈维再次肯定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组织和积累逻辑的论述在“灵活积累”的现实下依然闪耀着理性的光辉,并试图采用马克思的理论工具来考察“灵活积累”的表现形式。
随后,在对全球金融体制创新的分析基础上,哈维强调了他的结论,一是“灵活积累必须被看成是资本积累的全面逻辑内部主要的旧要素的一种特定的、也许是新的结合”,二是如果说“福特主义的危机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时间和空间形成的危机”,那么“变化着的对时间和空间的体验,至少部分地构成了向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实践与哲学话语的冲击性转折的基础。”[1](P.248)这一论述恰好呼应了哈维在全书的开篇论点中所阐发的要义,“在后现代主义文化形式崛起、更加灵活的资本积累的方式出现,与资本主义体制中新一轮的“时空压缩”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然而,在与资本主义积累的基本规律进行对照时,这些变化在表面上显得更像是转移,而不是某种全新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甚或后工业社会出现的征兆。”[1](P.1)在全书接近尾声的部分,哈维制作了一张“福特主义的现代性对灵活的后现代主义”的“术语拼贴画”,用以阐明他把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两方面范畴融入一种总体性的结构性描述中,二者之间的鲜明差别被一种“当作一个整体的资本主义内部内在关系之不断变动的考察”。[1](PP.421-422)
在政治—经济背景的考察之外,哈维“更加仔细得多地考察了对时间和空间的体验”。在他看来,这样的体验“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历史—地理发展之动力与文化生产和意识形态上的转变的复杂过程之间重要的中介环节”[1](前言),这正是哈维理解后现代主义的独特视角。哈维指出,“空间和时间的各种维度”,在文艺复兴之后的西方世界里“都承受了资本流通和积累的持续不断的压力,在时空压缩破坏性的和分裂的较量中达到了顶点(特别是在19世纪中叶以来出现的周期性的过度积累的危机期间)。”[1](P.409)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变,与资本主义经济从福特主义向更为灵活的资本主义积累方式的政治经济转变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二者的重要的中介,就是哈维所谓的“时空压缩”。这一概念标志着“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品质革命化了”:一方面由于“花费在跨越空间上的时间”急剧缩短,我们甚至感到“现存就是全部的存在”;另一方面,空间收缩成了一个“地球村”,使人们在“经济和生态上相互依赖”。[1](P.300)“时空压缩”已经对“政治经济实践、阶级力量的平衡以及文化和社会生活具有了一种使人迷惑的和破坏性的影响”[1](P.355),“在很多方面都夸大了过去一次又一次困扰着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的各种困境”[1](P.385)。通过对商品生产领域“形象生产工业”和短暂性生产的盛行以及消费领域中大众市场时尚的充分调动和商品消费向服务消费的转变等经济、文化和政治回应的分析,尤其是通过对“时间消灭空间”这一资本主义核心动力的分析,哈维认为对时空体验的解释,“已经从物质与政治经济学的基础领域领域转向了思考自主的文化和政治实践”[1](P.410)。而通过对两部后现代电影的剖析,哈维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对于时空压缩的体验,在转向更加灵活的积累方式的压力之下,已经在各种文化形式之中产生了表达的危机”,而要应对这一危机,就“必须创造出思考和感受的各种新方法”,这也应当体现在后现代状况的任何部分中[1](P.405)。显然,哈维更加寄希望于转向“各种强大的美学运动”。在对历史概况的一系列描述之后,哈维明确提出要把对后现代状况的回应拉入到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和解释的框架之中,甚至可以用“马克思所提出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元叙事的方法”使之“理论化”[1](P.410)。据此,哈维将“后现代主义”总结为“某种历史—地理状况”[1](P.410)。
哈维从1971年前后开始研读《资本论》并开设讨论课,持续了30多年之久。在《后现代的状况》一书中,他多次表明自己所依靠的主要思想武器是马克思的《资本论》,“正是《资本论》,才十分丰富地洞见到了流行的思维状况的内容”[1](P.424)。哈维上述一系列分析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他表明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后现代主义”语境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武器并没有丧失有效性和锋芒, 依然可以用来解剖各种从表面上看来令人眼花缭乱和争论不休的现象”[5]。哈维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科学解释中的元理论不是对总体真理的一种陈述,而是与历史的和地理的真理妥协的一种努力。“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是一种无限制的和辩证的探究方法,而不是一种封闭的和固定的理解实体”[1](P.441),其复兴可以“促进坚持一种新的启蒙规划”[1](P.446)。
三、哈维后现代理论的当代意蕴
“哈维对后现代主义的考察走了一条全然不同于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们集中从‘观念’上进行的文化、政治和知识批判的政治—经济学考察路径”[5]。其后现代主义理论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展开,在空间化的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内,从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剖析入手,深刻阐明了由“福特主义”和“灵活积累”所分别构成的作为文化现象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现实基础,并且将时间和空间的体验贯穿其中,对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体验的形成机制和过程详尽阐述。哈维的理论特色就在于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角度来解释文化现象的变迁,实际上提出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解与马克思理论之间的关联问题。“他在特定的论域中提出具体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元理论充分展开于其中,深刻表现了马克思主义有所作为的多种可能性和当代价值,开掘了一条通往后现代世界独特的马克思主义路径”。[6]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参考,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时,应当首先坚持“马克思主义最为根本的出发点——对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全面考察”[5],在此基础上考察社会的意识形态。
如前文所述,哈维和杰姆逊的后现代理论在诸多观点上是相通甚至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位理论家均来自美国,他们的后现代理论更多地应该出自其作为一个美国人的经验和体会。这从《后现代的状况》与《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两部著作中援引的大量美国经济—政治社会的事例中可以得到明证。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认识中国近年来在文化艺术和思想学术领域涌现出的后现代风格问题。虽然后现代主义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是一种别样的经验,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对它的现实镜像视而不见。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文化的全球化传播、网络社会的来临等都为后现代主义的生长提供了生存的土壤。眼前的事实是,各种形式的后现代主义都无法避免受到‘文化产业’的诱惑和统摄。杰姆逊在1986年面对的由电视剧、商品广告、子夜影院和“每家机场书店都必备的平装本‘副文学’产品”[3](P.347)所构成的后现代社会的文化世界在今天中国已清晰可见。在学术研究领域,“后现代主义各种论点的喧嚷似乎与时俱增”[1]前言3,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遭遇的问题与西方有诸多相似之处,比如工业化对人性的压抑、文化的商品化和低俗化乃至道德的沦丧,这些都为后现代主义提供了批评的话语空间。但为了避免文化上的虚无主义,“中国文化的主流,依然需要沿着启蒙的轨迹,归根到底是要循着马克思主义所开创的轨迹,而非采取后现代主义无所畏惧的态度,去颠覆尚未实现的目标和尚未建立的价值”[7]。在此意义上,批判和镜鉴应该是我们的态度。
[1][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2][法]利奥塔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3][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4]胡大平. 从历史唯物主义到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哈维对马克思主义的升级及其理论意义[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4(5).
[5]闫嘉.后现代语境中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兼评戴维·哈维的后现代理论[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1).
[6]董慧.何种后现代——大卫·哈维对后现代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解读与建构[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
[7]张旭鹏.后现代主义无助于解决中国问题[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01-04(A07).
(责任编辑 南 山)
2014-06-10
陈 磊,女,江苏姜堰人,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南京政治学院科研部讲师。
A811
A
1671-1696(2014)07-00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