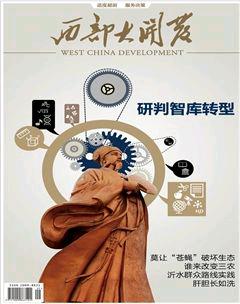也谈贾平凹的“凹”
●文/孟西安
文学
也谈贾平凹的“凹”
●文/孟西安
我和贾平凹交往已30年。去年春,我计划编著一本《人生如歌》的报告文学特写集,一天被誉为文学界“基辛格”的周明老兄从京来西安,与我一同见了平凹,我请他为此书写序并题写书名。他说,现在一般不为人的书写序了,但你出书我要写书名,又笑着说,可不收费用哟!
可不是,贾平凹的名气越来越大了,求他的一幅四尺的字,据说要花数万元!听说今年又涨价了。最近,我这本书即将交华夏出版社出版。去年7月22日,平凹得知后,他在西安永松路的书房中等我。我赶到,屋里坐着好几位等他在新书上签字的朋友。他把我请到阁楼上的书房,顺手拿了一张四尺斗方的宣纸,写了“人生如歌”四字,上注“西安兄正”,接着盖了印章闲章,同时在他签名上方摁了手印。接着他又应邀为我珍存的赵朴初先生30年前为草堂寺所作的佛诗原作(前我写了序,后附草堂寺方丈释谛性写的证词和省书法家协会原主席、赵朴初的学生雷珍民写的千字文跋)中的空白处,挥笔写了“珍品久藏”四个字。
其实,我向他求字,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还我一桩心愿,借机采访他想写篇文章。我们虽交往这么多年,我却没有专门写过他、宣传过他,一是写他宣传他的人太多,二是他太忙,我也忙,没考虑好采取什么角度去写,加上其他的因素,包括挚友、著名作家陈忠实等在内,我一直想写,也未能动笔,成了我的一块心病。于是,我趁他写字之机,询问了他近些年文学创作和获奖的一些情况,他简单地作了回答。接着他又送给我一本他新出版的小说《带灯》,并签名:“孟西安先生正”。我还要进一步细谈,这时他的手机又响了,朋友催他赴约吃饭。我只得说改日再谈吧,起身告辞。
过了两天,我给他发信息:“抽空再聊聊,想写篇介绍你的稿子。”他回信息:“有事回老家,不写我了,谢谢老兄!”我又回信息:“你谦虚,我内疚。任务还得完成……”
回家后,我从网上下载了些资料,又翻看他的新著《带灯》。我被这篇长篇小说反映的当前农村的实情、乡镇干部的甘苦以及生动朴实的情节和语言所打动。特别是看到他在这本书的后记中透露他的身世、写此书的起因和动机,尤其是他的姓名中关于“凹”字的破解引起了我的兴趣。于是我决定这篇文章就从他名字中的“凹”字谈起。
“凹”是对应“平”而言的。贾平凹原名贾平娃,“凹”是他后改的。“平”是指平坦的路,加上“凹”就不平坦了。实际上平凹走了一条不平坦而又成功的人生之路。他从小生长在陕南商州丹凤县棣花村,父亲是乡村教师,母亲是农民。父亲10多岁在西安考学,候榜时流落西安街头,八路军办事处曾介绍父亲到延安当兵,父亲没有去。平凹写道:“我埋怨父亲,你要去了,你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了,我也成了高干子弟了。”解放前夕,西安“城里响起了枪声,他又跑回老家丹凤。我又埋怨:哎,你要不跑,我不就是城里人吗,又何苦让我挣扎了19年后才成了城里人!”后来,因父亲历史“问题”,母亲又有病,平凹报名参军,没当成;招地质工人,招养路工,招民办教师,平凹虽然报了名,但不是没被选上,就是被人“掉了包”……1972年,一个偶然的机遇,他上了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从事文学编辑兼写作。当时他没有住处,就在西安北关方新村租了一间农村小屋。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西安晚报任社会部负责人,曾与年轻作家张敏(后任西安电影制片厂的编剧)及西安晚报的同事、文学编辑张月赓(他是贾平凹第一篇见报散文的编辑)等一同到方新村看望平凹,平凹当时在文学界崭露头角,他向我诉说了无房住的苦衷。我建议他给我写封信,过了几天他给我寄了一封信,我当即给市领导(主管文教和新闻工作的西安市委副书记丛一平)写了一封信并附上平凹的来信,不料一周后,平凹来电话说,市房地局的同志前来了解情况。一个月后就给他在南院门市委家属院一座新楼调剂了一套二室一厅的新房,这在当时是很令人兴奋和羡慕的事。之后,平凹与前妻韩俊芳成了我家的常客,1985年10月我调到人民日报工作,大约在90年代初,平凹又见我,说他现在来的客人太多,房子太小,不够用了,后我又给市委书记崔林涛反映,不久市委又在甜水井街附近给他又调整了一套四室二厅的房子。因为我忙,没有去他的新家看。1993年,他的小说《废都》出版发行,一天我与雷抒雁、陈忠实等人在钟楼饭店与贾平凹相见。平凹为我送新著《废都》一书,陈忠实在书的扉页上签字留念,陈忠实写:“此书关键在于一个‘废’字”。不久,这本书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批评者多,肯定者少,特别对书中过多的“性”描写和社会效果不好提出批评。我本来打算采写并宣传贾平凹,但报社领导接中宣部指示,近期不准宣传贾平凹。这是宣传纪律,不得违抗,这也是一段时间里我没能采访宣传贾平凹的主要原因。后来贾平凹一段时间情绪不好,还得了乙肝。我曾看望过他的病,希望他早日康复,但怕影响他的创作情绪,我没有向他透露人民日报不让宣传他的信息。后来市委书记崔林涛主动找贾平凹谈心,从关心爱护的角度,苦口婆心地劝说他今后多深入生活,多写些热情讴歌社会变革、积极向上、注重社会效益的文学作品。我想,这对贾平凹在文学创作凸凹不平的路上,一定会留下党和政府关心作家的深刻印记。当然,现在看来,贾平凹创作《废都》,也是想在文学创作上进行一次尝试和“突破”,也是对都市生活在变革时代认真思考和真实的反映。用他的话来说,文学作品生命如超不过50年,就不是有生命力的作品,我想这可能是他写作《废都》的初衷吧。之后《废都》一书不仅多版大量发行,而且还获得了法国费米娜文学奖。回顾平凹走过的人生路,可谓“历经三界苦,再求四季春”;“奋走平凹之路,体会黑白人生”。正如贾平凹自己所说的:“我的命运就是佛桌边燃烧的红蜡,火焰向上,泪流向下。”
“凹”字也像聚宝盆和金元宝。盆是盛水聚宝的容器,金元宝又象征财富。平凹出生在陕南农村,青少年是在农村长大的。当了作家之后,虽住在西安古城,但他热爱家乡,每年一半时间到农村体验生活和采风,晒农村太阳,吸农村地气,查农村民情。因此,他写的小说《秦腔》、《高兴》、《古炉》以及早年写的《浮躁》、《高老庄》、《怀念狼》等,都是他深入农村生活汲取民间营养加以深思熟虑提炼加工而写成的,特别是农村中许多生动情节和活生生的语言,都是他像端聚宝盆那样吸纳采集而成的。我没有机会陪他到农村体验生活,但一次相聚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1990年,我与陕西的一批作家、记者及文艺界朋友乘车到韩城党家村参观采访,途中有人讲了一个荤段子:一位农村小伙的父亲看见儿媳妇给孩子喂奶,孩子哭不吃,就对孙子说:娃呀,你再哭叫不吃,爷就吃了,说着就在儿媳妇的奶头上吮了一口。事后儿子就斥责父亲:“你咋能那样干!”父亲回答:“怎么,你吃了我媳妇多少年奶,我才吃你媳妇一口就不行?”大家听罢笑得前仰后合,而平凹却不动声色地记了下来,写进了小说,后来根据小说拍的电影《野山》还有这样的一个镜头。小说中关于农民缺钱他说:“人民币、人民币、我是人民咋没币?”说镇派驻村的干部,面对“毬咬腿”的人搅得选举无法进行,只好说:“我们都不是撵狼的狗,觉得很无奈”,以及催粮催款和刮宫流产生动的语言和描写,都是来自农村。不仅平凹在创作中善于吸收群众语言,“盆”中盛满生活中的智慧,而且他本人和家中也是个聚宝盆,盆中盛满了元宝。他喜欢收藏,他家中堆满了瓷器、陶罐、木雕、石雕、古木家具等等,有的是朋友送的,有的是他买的,有的是用字画换的。他的一个书桌上就放置了一个酷似“凹”字的秦岭山石。据知情人说,贾平凹是作家里最富有的人之一,光卖字画和稿费收入就很可观。20年前他抽烟是“大雁塔”牌,后改为“金丝猴”,现在桌上摆的是软盒精装“芙蓉王”。
“凹”字又酷似一个“火山口”。这是一个天津的文友来看他时说的。可不是吗?他近些年来创作就像喷发的火山口,火光冲天,岩浆四溅,佳作不断,颇为壮观。这次我会见他,询问他这些年创作获奖情况,他说现已出版文集23部,各种版本的书400多种,还不包括小说《古炉》、《带灯》和散文《天气》。接着他亲手在我的采访本上写下他的作品获奖情况。
虽然他著作等身,但他不善言辞,不喜欢热闹应酬。他也不喜欢西式大餐,喜欢农家饭;他为人忠厚朴实,绝无花言巧语,更不会哗众取宠。我想智者与愚者最大的区别是,一个充分利用大脑,一个充分利用舌头。贾平凹就是善于用脑思考,而不善利用舌头。“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如愚才是贤”用在他身上最为合适。字如其人,他写的书法虽不敢说是绝等佳品,但他的字拙朴敦厚,自成一体,形成独特的风格。许多人喜欢他的字,连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一本书封面都是他题写的书名。使我感动不能忘怀的是,我父母亲的墓碑就是平凹20年前应我之邀特意题写的。我每年清明回老家祭奠父母,在墓前对我敬爱的慈父慈母怀念和跪拜,同时也是对平凹的深情给予了叩谢,因为墓碑上留下了“贾平凹书”的落款呀!
“凹”字还像什么,我看还像中国的版图。中国版图就是一个东方破晓,迎着旭日引吭高啼的雄鸡。你看头仰尾翘,粗一看也是个“凹”字。平凹的作品也是具有中国风格,代表中国目前小说创作的一座高峰。他的作品不但在法国、美国获多项文学奖以及香港“红楼梦·世界华人长篇小说奖”,而且他的作品已用英、法、德、俄、日、韩、越等文字翻译出版了20多种版本。2008年,他的小说《秦腔》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古炉》自上市以来获得多个文学奖项,这次新出的小说《带灯》,国内多位文学评论家给予高度评价,新出版的《新华文摘》载文称赞:贾平凹的“每一部长篇小说几乎都与当代现实的难题相关”,《带灯》是“政治理论的困境与美学理想的终结”,在他的写作历程中不仅具有“总结性的意义”,而且有“强劲的突破性意义”。
的确,平凹在《带灯》一书中做了新的尝试和新的突破。多年来,他喜欢明清以至上世纪30年代的文学语言,他认为语言清新、灵动、幽默,有韵致。他模仿着,借鉴着,学的很像。近年来,随着年纪的增长和心性的变化,他文学的兴趣转向了中国西汉时期那种《史记》般的文章风格,它虽没有那么多的灵动和蕴藉、委婉和华丽,但它沉而不糜,厚而简约,用意直白,下笔肯定,以真准震撼,以尖锐敲击。《带灯》等作品有意学西汉风格,向粗犷浩瀚海风山骨靠近,因而更具有中国风格。
我们希望挚友、作家贾平凹,怀揣着聚宝盆,不畏艰险,勇于探索,沿着凸凹不平、崎岖蜿蜒的山路攀登,登上文学创作的险峰和高峰,遥看喷薄而出的东方红日,迎接“火山口”新的、更绚丽的喷发。我们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