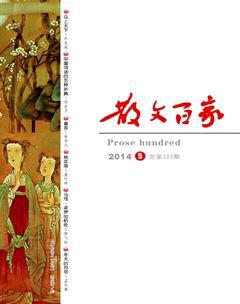稗米飘香
吕凤君
吉林市有个乌拉街古镇。离乌拉街不远,有个岗子屯,那便是我出生的地方。小时候,这一带盛产小米、高粱和少量的大米。还有一种特殊的米,叫稗子米。
近来读史,无意中了解到稗子米这种草芥一样的东西,竟然是皇家的最爱。据史料记载,吉林将军每年都要给皇帝上贡,除了野猪、鹿肉、鲟鳇鱼等近百种山珍野味和土特产外,还要送稗子米和铃铛米(一种燕麦磨成的米)。典籍中有一份标有“吉林属每岁进贡物产开列于后”字样的清单,上面清楚地记载着,这一年吉林将军进贡了七次,有三次赍送了稗子米和铃铛米,而没有送其他粮食。这还不包括恭贺皇帝过生日时送的稗子米和稗子米粉面子。从十月稗子成熟,到十一月新粮下来,吉林府三次一共送了六斛稗子米。这不知是皇帝钦点,还是妃子、格格们的私下索要?
稗子跟野稗草似乎没什么区别,只不过野稗草没有稗子高罢了。每到秋天,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都拎着筐到野地里捋草籽,男人们也会拎着镰刀跟在屁股后去割稗子,因为割得晚了那些稗穗就成了鸟儿的大餐。野稗草的籽粒用来喂鸡,稗子米用来喂人,两样都是好东西。每当母鸡下完蛋,“咯咯嗒”地正在兴头上,你抓把草籽扔过去,那可比月婆子吃鸡蛋还要补。
我曾经傻呵呵地问捋草籽的女人,这东西好吃么?那女人说傻小子,你又不下蛋,吃它干什么?男人要是能下蛋,这可就是好玩艺儿了。说完,便哈哈哈地笑,别的女人也笑。我想了想也是,男人们净会说扯淡,怎么可能会下蛋呢,又不是鸡。不过,我还是想弄明白这稗草的籽粒到底好不好吃。因为我始终也无法辨别野稗草的籽粒与稗子的区别在哪儿。
那时,稗子是常见的作物,除了正常种植外,哪块地涝洼了,大人们就会说补种点稗子吧,那东西不怕淹。种点得点,总比撂荒了要好。那意思是嫌稗子产量低,种得再多,也打不了多少粮食。没有特殊情况,一般是不会种稗子的。
稗子收回来了,晾晒完了还要摊放到席子下面炕,彻底炕干了才能去磨,磨米或者磨面。我没有吃过稗子面做的饽饽,稗子米饭却没少吃。雪白的稗子米,乍看上去跟白小米似乎没什么区别,可下了锅就不一样了,小米能煮一会儿,稗子米就不行了,时间稍长一点就炼汤,粘糊糊的,像浆糊似的,一点也不好吃。那时候,我奶奶是这村里最会做稗米饭的,无论是做干饭还是大米和小米两掺的二米饭,都格外松软,粒粒成形,吃起来香喷喷的。我至今还记得她老人家做二米饭时的情景:烧一锅水,待到把水烧叫唤时,先把大米下锅,过了一小会,等到米粒不软不硬八分熟了,再把淘好的稗子米倒下去。这段时间最难把握,时间稍长就成二米粥了,时间短了大米熟了、稗子米熟不了。每到这时,奶奶总是把火烧得旺旺的,再用笊篱在锅里搅一搅,然后赶紧把两样米粒捞上来,狠劲掂几下, 在确信控干了汤水后再放到瓦盆里。这还不算完,还要把瓦盆里的半成品放回到锅里蒸,在蒸的同时,锅里的汤就用来炖菜了。当再次烧开锅之后,雪白的二米饭和清淡的炖菜就可以上桌了。土豆炖茄子,大锅蒸二米饭,再炸碗鸡蛋酱,那种清香的味道实在难忘。
吉林是满族的发祥之地。乌拉街不仅是为皇家采集贡品的地方,也是出美女的地方。小时就曾听过一首歌谣,说“青皮萝卜紫皮蒜,乌拉街的格格最好看”。乌拉古镇曾经是一个古国,是女真人重要的部落之一。据说自从清太祖努尔哈赤进军中原之后,有许多妃子、福晋就都是乌拉古镇的格格出身。对于这些长年处在深宫大院的女人们,乌拉古镇的一草一木都寄托着她们的乡情。我曾想像过,在那老北风刮着、冒烟雪的冬天,当打牲丁经过千里跋涉把贡品运送到北京,当太监们打开纸包纸裹着的稗子米时,那些当年的格格们该是怎样的一种心情。
“格格”一词原为满语的译音,译成汉语就是小姐、姐姐、姑娘之意,在满语中原意是对女性的一般尊称,而在现代汉语中出现时则大多是对清朝贵胄之家女儿的称谓和对皇帝、亲王妾室的称谓。我的奶奶是土生土长的乌拉街人,我曾听老人们说起过她,说她在家当姑娘时如何漂亮,说漂亮得就像个格格。可我却想像不出奶奶与格格有什么区别,也不知道奶奶做稗子米饭的本事是从哪儿学来的,就像不知道那些稗子米进宫后是如何做熟、是如何端到餐桌上的一样。
我的奶奶是个大户人家的女儿,不知怎么就嫁给了我爷爷。我爷爷家当年也有许多房子、地,后来因为喜欢上了打麻将、推牌九,渐渐地家道就败落了。等到土改划成分时,我爷爷已经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成了名副其实的贫农。在重新分得土地之后,爷爷本该老老实实地过着“一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农生活,可这位老人家却因过于倔犟,酒后竟敢咒骂农会干部而进了牢房。
我没有见过我的爷爷。从我懂事起,这个家就由奶奶操持着。做饭、喂猪、种地,里里外外没有她做不到的。奶奶有五个孩子,父亲排行老二,是哥五个中最早结婚的。父亲结婚不到两年,我的母亲在产下我之后就病死了。当时,我的老叔才只有四岁。丈夫被关进了大牢,一个儿子刚刚丧妻,三个儿子还需要照顾,一个没有妈的孙子哇哇待哺,我不知道当初奶奶是如何面对这些的。
从一个大户人家的女儿,到一个被专政对象的老婆,奶奶经受了太多的磨难。为了让儿子能多学些文化、有个安身立命的本领,她让大儿子拜师学了中医,让二儿子到城里当了技工,三儿子被送进寄宿学校,四儿子被送到一个没有儿子的兽医家当学徒。送不走的,只剩下小儿子和刚刚会爬的孙子。那时候曾经有人找过奶奶,说把那个没妈的孩子送人吧,这年头你会饿死他的。我奶奶没有搭理那个人,因为他不知道自从妈妈死后,姨姨曾背着奶奶把我送了人,是奶奶逼着她把我从城里富有人家要了回来。
童年时有两样东西至今难忘,一个是摇车——一个红漆画着金色图案的摇车,还有一个硕大的笸箩。摇车是我睡觉的地方,里边残留着父辈的梦想;而笸箩则是个特殊的工具。那时,奶奶最大的心事就是养鸡和照顾孙子。秋天里,她把我放到笸箩里,然后再放些瓜果当玩具,让四岁的叔叔陪着我玩,然后再去捋草籽。那时的田野里、小河边野稗草连成片,是鸟儿的乐园,也是奶奶的乐园。当奶奶背着一满袋草籽回来时,常常看到两个孩子已经睡到笸箩里了。这时,奶奶就会把我抱进摇车,唤醒我的老叔,然后再把草籽摊放到笸箩里。
童年的乡村是没有音乐的,公鸡打鸣、母鸡下蛋的声音就是最好听的声音。每当那“咯咯嗒——,咯咯嗒——”的声音响起时,奶奶的脸上就会露出笑容。那时,我的家乡方圆几十里都见不到一只奶羊和奶牛,为了养活孙子,奶奶常把稗子米磨成粉、熬成糊当成牛奶喂我,而喂得最多的是鸡蛋糕,还有鸡蛋糕拌稗子米饭、拌小米饭。为了我这个可怜的孙子,也为了她那些背井离乡的儿子,我的奶奶不知付出了多少艰辛与汗水!
我的奶奶死在秋天,是在我从乡下抽回到城里之后死去的。奶奶至死也没有再见过她的丈夫,按照老人家的遗愿,我们把她和我爷爷的遗骨合葬在一起,埋在一个向阳的山坡上。那坡上有松树,还有蓬勃的野稗草。
几十年过去了,我从乡下来到城里,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可童年时吃稗米饭的情景却依稀可见。我曾想找回那久违了的感觉。走在家乡的田野上,仍然能看到野稗草在风中招摇,却找不到那和野草一样的庄稼,找不到那刻骨铭心的米香。
可是我相信,唯有我那草根的奶奶,那长眠在黑土下面的奶奶,她曾做出来的稗子米饭,才是这个世界上最香甜的米饭。这种香甜来自泥土,来自过去,只要野稗草还在,它便永远不会濒危。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