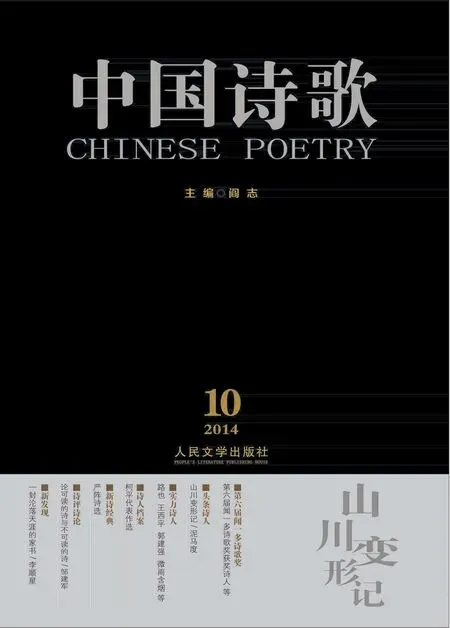严阵新诗导读
□田艳
严阵新诗导读
□田艳
“肩上一片月,两袖稻花香”、“五月江南碧苍苍,蚕老枇杷黄”,这些清新优美的诗句,出自诗人严阵。可能对于年轻的读者来说,严阵的名字有些陌生,但他曾是臧克家向毛泽东推荐的“五大开国青年诗人”之一。臧克家还专门为严阵的诗选《琴泉》做了一篇长长的序言,极度肯定其在诗歌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
严阵是一位多产的诗人,出版了许多诗集与文集。2008年,十卷本《严阵文集》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严阵的诗歌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他曾应邀出席过世界诗人大会,其作品也被译成了多国文字。值得一提的是,严阵不仅是一位诗人,更是一位画家,出版了三卷《诗人严阵绘画》及其他画册,并在北京和纽约等地多次举办个人画展。画是有声诗,诗是无声画,诗画在艺术境界上本就是相互沟通交融的。严阵认为绘画是一种精神的表达,是一种激情、发现、感悟与超越。诗歌更是如此。
1
诗心不老,诗魂不朽。六十年来,严阵一直坚持着用诗歌来表达自己对于生活的理解与热忱,其诗集《江南曲》 (1961)、《长江在我窗前流过》 (1963)、《琴泉》(1967)是其代表作,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其诗歌思想内容方面的特点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严阵创造了一种融“政治颂歌”与“牧歌情调”于一体的“新田园诗”。受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尤其是受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要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的观点的影响,严阵的诗歌在内容上必然以表现工农兵即劳动人民的新生活为主,以歌颂新时代、抨击旧社会为基调。但是,与当时占主流地位的直抒胸臆、浅白直露的“政治颂诗”不同,他选取了“江南”这一富含古典意蕴和田园牧歌情调的“地理空间”,描绘了江南水乡赏花、割麦、采莲、耘田的生活画卷,清新自然,飘逸灵动,赋予政治抒情诗以别样美感,形成了独特的“新田园诗”。如“五月江南碧苍苍,蚕老枇杷黄”(《耘田曲》),“江东:一轮红日,/江南:杨柳依依”(《桃花汛》),“二月的雨:红雨啊,/无声地,染红了江南”(《红雨》),“公社喜开丰收镰,/一曲唱遍了江南”(《开镰歌》)。这些诗句,包含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让人读来口角噙香、情思绵绵。正如臧克家所说,它们像朝霞在天,像花苞初放,像泉水涓涓,像月笼平沙。
在《江南春歌》中,这种田园诗意伴随着政治抒情发挥到了极致:
十里桃花,
十里杨柳,
十里红旗风里抖,
江南春,
浓似酒。
…………
阵阵笑声似江流,
妇女出村口,
幼儿园前招招手,
齐手巧把春田绣,
山花插满头。
…………
“桃花”、“杨柳”这类古典意象与“红旗”这一现代生活的意象结合在一起,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具有浓郁的现代气息。“新田园诗”新就新在古典意象与现代生活的融合。这首《江南春歌》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韦庄脍炙人口的《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画船听雨眠”成了“笑声似江流”,“皓腕凝霜雪”也变为“齐手巧把春田绣”。今日的江南已不再是昨日的江南,过去只有才子佳人才能欣赏的江南风光,已经进入寻常百姓家了。江南之美也不只在于画舫听雨、垆边赏月这类文人的风雅之事中,因为劳动创造美,劳动之中就有诗意。在这里,新时代的人民生活和政治风貌宛如浓烈似酒的江南春光,自然而然地十里飘香,无须直白地歌颂。
又如《开镰歌》:“是谁昨夜趁着人睡酣,/一笔染黄了江南?/呵,原来是麦子熟了,/麦浪在南风里撒欢。//多少春风春雨月明天,/多少人曾在田埂上转,/如今沙沙摇铃的麦穗儿,/终于把喜信送到了耳边。”这确实是一首政治抒情诗,歌颂了公社丰收增产的喜悦,但在明快欢欣的基调中,更蕴含着对生命本身的礼赞。开篇的“是谁”一句,直接叩问了生命的本质,歌颂的不只是劳动生产本身,而是自然造物主的神力,与“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类诗句有着相似的意味,是对大自然力量的肯定。“一笔染黄了江南”带有“春风又绿江南岸”的阔大境界与勃勃生机,“多少春风春雨月明天”中也能看到“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悦事谁家院”的影子。这类古典意象的呈现,使其诗歌具有曲径通幽之感,赋予单纯的劳动场景某种深远的境界。
事实上,严阵把“江南”(广义的江南)作为描绘的对象,是一个别具匠心的选择,因为“江南”不仅是一个真实的地理位置,更是一个特殊的“地理空间”,其中充满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它是一个诗意的乌托邦,是每一个中国诗人的精神家园和永恒的乡愁。海德格尔曾说“诗人的天职是还乡”。严阵这位农家子弟,书写着关于故乡“江南”的田园牧歌,但和传统的诗意已有了质的区别,它融合了现代的意象和生活场景。他试图在政治和审美的夹缝中进行自身的还乡之旅,而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这注定是一场并不轻松的旅行。也许,严阵的诗歌还无法达到古典诗词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但在那个政治先行的特殊时代,严阵的这种新田园诗就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他竭力捍卫“审美”的地位,使之不至于被“政治”完全吞没。在某种意义上,他的新田园诗是一种“戴着镣铐的舞蹈”,是在政治正确的前提下尽可能自由地、真诚地呈现诗意。可以肯定地说,严阵以自身独特的情思和笔触,将审美性与政治性完美地结合了起来。诗集《江南曲》和《长江在我窗前流过》中的《江南曲续编》里的大量诗歌,都是这种融合的结果。其后期诗歌如《竹矛》等就偏离了早期新田园诗的审美旨趣,沦为简单的政治抒情。

另一方面,严阵的诗歌反映了时代精神的变迁。黑格尔认为时代精神是“绝对精神”在每一个时代的具体化身,是每一个历史时代特有的精神实质和集体意识,体现了时代的发展方向。严阵在其六十年的创作中,恰如其分地把握住了每一时期的时代精神,从新中国建立到社会主义的建设,再到新时期国家的发展,他都以诗人独特的匠心慧眼进行了细致的观察、深切的感受以及诗意的言说。五六十年代的时代精神是一种歌颂新生活、人民当家做主的昂扬向上的奋斗精神,如在《老张的手》中,诗人通过“手”这一细节,“歌颂了新人的成长,赞美了劳动的光荣”(蔡其矫《读严阵的诗》)。事实上,这个时期的人们,都期待着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全新的生活,充满着理想主义的激情,恰如诗人所写到的:“波头蓼花红,/江南稻子黄,/稻穗一天一个样,/忙坏了农具厂。//公社党委书记,/一夜来三趟,/肩上一片月,/两袖稻花香。”(《麦收序曲》)又如“江南三月夜短,/谁肯舍得早眠?/挂起锄,放下镰,/小巷里细语呢喃……村外江潮在响,/村头读书声喧,/一颗颗心儿钻进了书卷,/像犁儿把泥土深翻。”(《夜读》)这些诗句既富于生活气息,又呈现了劳动人民创造幸福生活、相信未来的崇高信念。
进入八十年代,诗人告别了五六十年代的热情洋溢,转为沉潜深邃。八十年代的时代精神是历经磨难、重新发现美好事物的审美精神。如《桃花溪》一诗虽然继承了早期诗集《江南曲》中的某些审美趣味,但却更为深沉凝重。“一夜桃花雨,半溪胭脂水,千回百转,淙淙流过,/……/桃花开了,李花开了,荼蘼也白得像雪的旋涡”,这样的良辰美景,这样的姹紫嫣红,春的气息,跃然纸上。但在看似单纯的写景之中,寄予了诗人对于时代风云的深思,对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关怀:“不断地向前流啊,坚定不移,不管世间谈清说浊,/只管以胭脂一样的彩波,灌溉不断更新的生活”。不管世事如何变化,桃花溪永远坚定不移,向前流去,“把通向大海的道路疏凿”。这蕴含了诗人对动荡时期的某种深思。可将此诗与六十年代的《桃花汛》简要对比。“江东:一轮红日,/江南:杨柳依依,/长江儿女,迎着阳光;/千里江岸树大旗!”很显然,《桃花汛》是朝气蓬勃的直抒胸臆,简洁明快,充满昂扬的干劲与斗志,表现出诗人对于生活的无限期望,却少了几分令人回味的隽永意蕴。《桃花溪》则不然,充满了某种深邃的哲思,诗人赋予笔下美景以新的内涵,耐人寻味。这恰恰是八十年代时代精神的体现:告别五六十年代的热情昂扬,在经历了痛楚、磨难以后,人们有些困惑彷徨,但是仍坚定不移地寻找着方向,期望重拾信仰与美好!
二十世纪新时期的时代精神则表现为国家和民族的全面上升、创造美好未来的梦想精神。诗集《中国梦》正是这一时代精神的回响。100年的风雨沧桑,中华民族终于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的“梦”,现在中国需要新的梦想,重新审视自己、重新认识世界。“这个现代化的世界,/某些方面,还是一片荒漠,/等待着我们去开发的美丽,/还有/很多。/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梦,/需要一个/新的/中国梦。”《中国梦》虽然是政治抒情诗,但严阵并没有一味地歌功颂德,而是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与呼吁,对于许多不良社会现象进行了抨击与批判。因而,《中国梦》中既有澎湃的激情和对生命的赞叹,又有沉重的忧患意识和对苦难的思索。“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因为最成功的时候/就是最危险的时候。”但总的来说,严阵这一时期诗歌的艺术性不如六十年代的,政治色彩过于强烈。
最后,严阵的诗歌还具有一种对于宇宙、人生的哲理性思考。《江南曲》中的诗篇虽大多都热情昂扬,欢快流畅,但同时也“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具有某种深邃性与永恒性。如《月下的练江》:“船的咿呀声由近而远,/江水静了,船影渐渐不见,/只有那股茶香久久地留在江上,/月下的练江,一条金练。”营造了一种时间、空间的无限感,人声、船影都消失不见,只有江水亘古长流,颇有“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况味。又如《谁打碎了月亮》,寥寥数行却意味深长:“是谁打碎了/月亮//留下/满地/碎片//我将用它拼成/透光的/瓷瓶//盛满/世间迷人的/忘却”。破碎与完整,月亮与人间,留下与忘却,在这几组相反相成的意象中孕育着某种思辨的色彩,表达了某种于毁灭中孕育新生,于残缺中重铸美好的哲思。在长诗《天空》之中,诗人以“天空”的广阔性、无限性,与抒情主体“我”的有限性、当下性进行对照,进行了一种永恒的哲学思考。“我永远奔腾”,但无法走出“天空”的“平静”与“蔚蓝”。天空辽远而深邃,无始无终,没有诞生与死亡,却笼罩大地,滋养万物。“当我变得暗淡的时候/你的夜晚/便让我/发光/当我光芒四射的时候/你又会掩盖着/我的/辉煌”。天空虽然是更高的主宰,但是“天空”与“我”之间并非隔绝或敌对的关系,而是相互交融,“我”被天空所滋养,又与“天空”合而为一,“你在海天相接处等我/等我驶过/等驶过有着薰衣草香味的/梦的/小船”。“天空”需要“我”的存在来使之完满、圆融。诗人并不像科学家那样探求宇宙的无穷奥秘,也不似哲学家般以逻辑与思辨来探求终极问题,他以诗性的方式引导我们神游万里、心骛八极,思考瞬间与永恒、有限与无限、自我与宇宙如何交融与变幻。
2
“山坞三月夜,/一片梨花月,/簇簇梨花开得盛,/梨花和月色分不清。”(《山坞》)这样意境清幽、沁人心脾的诗句,表明严阵的诗歌已经形成了其独特的艺术风格。
严阵诗歌最突出的是具有一种古典化、民歌化的特点。“古典化”标示着新诗与传统的关系,“民歌化”则意味着新诗与民间生活尤其是工农兵生活的关系。实际上,毛泽东在1958年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要在民歌与古典的基础上发展新诗:“我看中国诗的出路恐怕是两条: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这两面都要提倡学习,结果要产生一个新诗。”严阵的《江南曲》,显然是实践这一指示所做的尝试。如前所述,严阵的“新田园诗”善于将古典意象与现代生活场景融为一体,他吸收唐五代的小令手法,使用短句,快节奏,借以制造欢乐气氛。他还借助古典诗词中的旧有意境和韵律,表现劳动的喜悦,一种时代的幸福感。如《红雨》是一幅典型的江南春雨图,雨在此被赋予一种清新、明秀、灵动的品质,它给不甚如意的人生以无限宽慰。“红雨”是古人惯用的意象,如李贺的《将进酒》:“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但是严阵赋予了其现代意味。“二月的雨:红雨/无声地,洒遍了江南,/一颗雨点染红了一个骨朵,/一颗雨点染红了一张笑脸。”本是花朵和笑脸映红了春雨,作者却反写,赋予了雨鲜活的生命力。李贺笔下的“红雨”是桃花的象征,带有一种生命凋零、时光易逝的况味,严阵则歌颂“雨”带来的无限生机,并进一步歌颂劳动人民的新生活:“抚摸着新铸的犁尖,/争着去开第一犁,/蓑衣都不穿。//只有拖拉机手,/把机子试了一遍又一遍”。在这里,古典的“红雨”意象与现代的“犁尖”、“拖拉机”等形象组合在一起,具有了一种独特的美感。《桃花溪》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唐代诗人张旭的《桃花溪》:“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矶西畔问渔船。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但同样也赋予了古典意象以现代意蕴。“一夜桃花雨,半溪胭脂水,千回百转,淙淙流过”,这是古典审美意蕴的接续,但是“果筐满了,粮囤满了,丰收车队像千百条金色的山脉”,则是对现代生活场景的描绘。
严阵十分善于化用古典诗词中的各类传统意象,甚至达到了黄庭坚所说的“脱胎换骨”、“点铁成金”的地步。如“半船红霞半船莲蓬”(《采莲曲》)脱胎于“半江瑟瑟半江红”,“别担心荷叶遮住了归路”(《采莲曲》)又带有“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的影子。又如“千山雪,一夜化尽。/一江水,也绿了几分。”(《梅信》)则化用自欧阳修的“雪消门外千山绿,花发江边二月晴”。而“万座潮头千层雪,涛声轰轰几十里”(《桃花汛》)也具有某种“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壮阔!正如T·S·艾略特在其著名的《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指出的,任何文学作品都必然置身于一定的传统之中,真正优秀的作家一定是“传统的”,具备一种历史意识。严阵自己也明确表示,其诗歌创作深受李白、李贺、李煜等古代诗人的影响(见《诗人的自白》)。他对古典意象的借用和化用,正体现了传统的影响。他一方面借助古典意象使其诗歌具有一种深邃的历史感和悠远的境界;另一方面,又赋予古典意象以新的时代精神内涵,使其焕发新的生命活力,延续了传统。
民歌化是严阵诗歌的又一特点。胡适曾指出,“中国新诗的范本,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外国的文学,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民间歌唱。”并强调民歌对于新诗创作的意义:“民间歌唱的最优美的作品往往有很灵巧的技术,很美丽的音节,很流利漂亮的语言,可以供今日新诗人的学习师法。”事实上,自五四以来,新诗一直以高雅化和文人化为特点,少有对底层大众生活的描绘,也与大众的阅读基础完全疏离。民歌体新诗则是诗歌大众化的一次尝试,体现了诗歌与劳动人民生活的连接,其特点在于用词口语化,意象生活化,节奏感强,富于音乐性,顺口易唱。许多民歌体新诗都取得了较好的艺术效果,如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张志民的《王九诉苦》、阮章竞的《漳河水》等,都将民歌形式与现代思想相结合,兼具了民歌的生动质朴和新诗的现代意味。严阵的诗歌亦是民歌化的典范,如“尘满脸,汗满脸,心头甜,/歌曲儿悄悄流到了唇边:/公社喜开丰收镰,/一曲唱遍了江南”(《开镰曲》),“坡上挂翠,/田里流油,/喜报贴在大路口,/山歌儿,/悠悠,悠悠”(《江南春歌》),“满树青桃红了嘴,/熟透了的杏子落成堆,/谁去理会?打麦忙得火烧眉”(《打麦歌》)等。这些诗句描绘了一幅幅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并将丰富多彩的口语、俗语入诗,讲求韵律节奏,易于吟唱,且诗歌内容贴近生活,明白晓畅,便于大众理解。
在严阵的《采莲曲》和《采菱歌》两首诗中,古典意蕴与民歌特色达到了完美的融合。如:“姑娘们笑着把莲篷采折,/惊动了水底的一朵红莲,/波纹里像有一块红色的宝石,/闪烁在一大堆翡翠中间。//……//七月的清晨风还没醒,/半船红霞半船莲蓬,/别担心荷叶遮住了归路,/公社的红旗正在飘动。”
又如《采菱歌》:
轻巧的手指向水底一捞,
就提上了一串串红色的玛瑙,
对着那淡淡的初月一眉,
尝尝新菱是什么滋味。
菱盆儿分开,菱盆儿靠拢,
采菱的歌曲儿忽西忽东,
而歌声好像向全世界说:
羡不羡慕我们这诗一样的生活?
这首先是承接了古代民歌“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的审美趣味,又有李白“若耶溪边采莲女,笑隔荷花共人语”的盎然生机,还依稀可见张籍“归时共待暮潮上,自弄芙蓉还荡桨”的悠然自得;其次又明显受现代诗人朱湘用民歌曲调创作的《采莲曲》的启发,“小船呀轻飘,/杨柳呀风里颠摇;/荷叶呀翠盖,/荷花呀人样娇娆”,将一些通俗的口语和节奏融进了诗里。这些诗既有古典的意境,又有民歌的韵味,别具新意,且朗朗上口,易于传唱。

此外,严阵一直勇于进行诗体实验,力图拓宽诗歌的表现形式。一方面,他尝试过多种诗律,如半自由体,《长江在我窗前流过》:“长江在我窗前流过,/翻腾着金黄色的浊波,/啊,这热情澎湃的河流,/横贯了我的祖国。”语言简洁直白,格律自由明快。同时,他化用古典诗词的格律和民歌小曲的节奏方式,创作了具有古典意蕴的《江南曲》,在当时广为传唱。严阵擅长运用长句,如“让我在你那云梯般的道路上探求终生吧,/让我在你的花朵中间去开拓你那芬芳的矿藏”(《莲花峰》);有时则又将长句打散,将一句完整的诗行分成几个短行,形断意不断,形成一种灵动的韵律美,如“此时此刻/中国的/每一个/被压弯的枝头/都结满了/沉甸甸的/辉煌”(《辉煌的秋色》),又如“花的墙。花的院。/花的小径。/整个的山坞都睡了,/月色。梨花。是它的梦。”(《山坞》)他十分注重排比和对偶,回环往复,层层渲染,营造出一泻千里、奔腾不息的恢宏气势,如“一天风露,万树香雪,布出江南白玉阵,/一枝出墙,千朵突发,少缺杏花不是春”(《杏花》)。另一方面,他还打破各种文学体裁的界限,融叙事与抒情于一体,如《江南曲》中的大部分诗歌都是自然景物与生活事件的结合。他更进一步打破诗歌与小说的界限,创作了长篇诗体小说《山盟》,这在新诗的历史上是里程碑式的作品。诗体小说属于叙事性、情节型的文学样式,重视和讲究叙述方式和结构艺术,不同于一般的散体小说,是一种诗性的叙述,往往在叙事中夹杂抒情。
3
严阵从青年时代起就有“山东才子”的美称。他出生于山东一个名叫“沐浴”的小村庄,这样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孕育了其无限的情思,故乡的一山一水、造化神秀,都成为严阵以后文学创作的直接源泉。对于严阵这样一个15岁就参加革命、只读完小学的人来说,能取得这样的艺术成就,不得不说是山东这片神奇的土地赋予了他无限的灵感和激情。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文学地理学”理论的又一明证。严阵的创作历时六十年,至今仍在笔耕不辍。他的诗歌具有自身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思想特征,其早期诗集《江南曲》、《琴泉》、《长江在我窗前流过》中的诸多篇章都言辞秀丽,意境清幽,将古典意象与民歌艺术融合于一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新田园诗”。对时代精神的显现,是严阵诗歌创作的灵魂,这使其诗歌具有了历史见证的意味。他的诗歌往往不是个人的玄思冥想,而是来自于劳动人民鲜活的生活,取材广泛,田间地头、工厂楼房、江海湖泊,无一事、无一物不可入诗。他的诗歌语言通俗凝练、明白晓畅,承接了杜甫、元白以来的“诗史”传统,使老少妇孺,皆可吟诵。
在充分肯定严阵诗歌所取得的艺术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指出其存在的不足。由于受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严阵的有些诗篇存在着“观念先行”的情况,为了歌颂而歌颂,语言直白、浅露。这种政治化的倾向,削弱了其诗歌自身的艺术性和感染力。如《欢呼啊!我的太阳》、《啊,六十年代》、《寄给古巴》、《遥望非洲》等,都只是简单的赞歌,缺乏深刻的内涵;有时为了配合主流意识形态,甚至歌颂一些存在问题的历史事件,如“杜鹃花开三月天,/江南万山红遍,/处处锣鼓,处处歌声/迎来大跃进的局面”(《杜鹃花开三月天》),欢欣鼓舞地歌颂了大跃进的到来。而诗集《江南曲》 (1961)、《长江在我窗前流过》 (1963)正创作于“三年困难时期”,全国性的大饥荒使人民的生活异常艰难,但严阵的诗中却只有花好月圆,没有民不聊生。当然,这些都是时代的政治思想造成的,是政治意识对文学艺术戕害的证明。诗人也只是时代洪流里的一粒微尘。
另外,由于受民歌化倾向的影响,严阵的有些诗歌语言过于口语化,缺乏诗味,且意象陈旧,缺乏全新的艺术感受。如“青年们顾不得把茶喝,/争着来读当天报,/谈论古巴日本南朝鲜,/为整个世界把心操”(《田间》),“听,钟声已经响了,大会就要开了,/县委书记说啦,他也马上就到,/看,太阳已经升得那么高,/快来听吧,毛主席的指示到了!”(《我的马儿,快跑,快跑》)这类诗句接近于大白话,诗意全无,没有令人回味的余地,也缺乏深度。正如周作人对民歌的批评,“言词贫弱,组织单纯,不能叙复杂的事实,抒微妙的情思”。口语化、民歌化也导致了严阵的许多诗作只有个别诗句精美,而整篇成就不高,名句易有,名篇难得。如《耘田曲》的开篇“五月江南碧苍苍,/蚕老枇杷黄”古意盎然、诗情勃发,但紧接着的“冬鸡子声声催薅秧,/快把新草帽儿戴上”,太口语化了,把原有的诗意完全破坏了;又如《丰收序曲》中的“肩上一片月,两袖稻花香”,简直可以追步古人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一畦春韭绿,十里稻花香”,但随后的“头一次来就问,/割稻机制得怎么样?/二回头又来催,/打稻机也要快赶上”就乏善可陈,诗意荡然无存。在其最新的《和谐的中国》一诗中,这类问题仍然存在,如“和谐是一双手/拉着另一双手/和谐是一颗心/贴着另一颗心”,过于概念化,略显空泛,在铺陈中重复,没有融入更深刻的思想内涵,且使用的意象也略显陈旧,将“和谐”比喻成用滥了的“高山流水”、“雪中红梅”,缺乏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