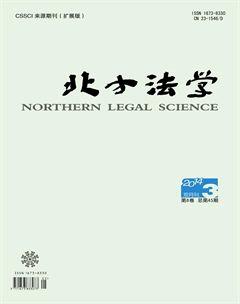对法国物权变动债权意思主义的再思考
董学立
摘 要:一般认为,《法国民法典》确立了物权变动的债权意思主义,即当事人间的债权意思引致了物权的变动。但深入研究《法国民法典》后却得出了并非完全一致的结论:所谓的物权变动的债权意思主义,是一定逻辑体系之“前见”下的结论。以权利生效的要件以及权利变动的过程和结果观之,债权意思产生物权变动的效果是荒诞的。“物权意思+公示对抗”应当被确立为物权变动的第四种立法模式。这一认识对于理解我国《物权法》关于物权变动的立法主义选择以及我国未来《民法典》的制定具有意义。
关键词: 物权变动 债权意思 物权意思
中图分类号:DF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330(2014)03-0005-06
物权变动的立法主义,就引致物权变动的意思要素而言,一般地认为,有债权意思主义和物权形式主义之分。前者以《法国民法典》确立的物权变动模式为其典型;后者以《德国民法典》构建的物权变动模式为其范本。所谓债权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是指除了当事人的债权意思之外,物权变动无须其他要件的物权变动模式。以买卖合同为例,标的物所有权的移转,以当事人之间的买卖合同为根据,纯粹取决于当事人的自由意志,既不需要交付或登记行为,也不需要独立于买卖合同的物权行为。①在对《法国民法典》进行一番研究之后,笔者不禁要问,难道《法国民法典》真的确立了物权变动的债权意思主义吗?或者,对于那个物权变动的结果而言,难道其真的是由债权意思所引致?对这一问题的追问,不仅有助于理解我国《物权法》中的物权变动立法主义,也有助于我国未来民法典的体系设计。
一、实然与应然——对《法国民法典》物权变动规则设计的解读
关于“特定物”的买卖,《法国民法典》第711条规定:“财产所有权,因继承、生前赠与、遗赠以及债权的效果而取得或移转。”第938条规定:“经正式承诺的赠与依当事人间的合意而即完成;赠与物的所有权因此即移转于受赠人,无须再经现实交付的手续。”第1583条规定:“当事人就标的物及其价金相互同意时,即使标的物尚未交付、价金尚未支付,买卖即告成立,而标的物的所有权亦于此时由出卖人移转于买受人。”②根据《法国民法典》的这些规定,“特定物”买卖契约以契约当事人的合意而成立,标的物所有权于契约成立时发生移转而无需履行任何外在形式。故而,一些学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标的物所有权依当事人之间纯粹的债权意思即可完成移转,由此可见,《法国民法典》所贯彻的是债权意思主义原则。③但是,在这些规定之外,关于“非特定物”的买卖,《法国民法典》第1138条又规定:“交付标的物的债务依缔约当事人单纯同意的事实而完全成立。”“交付标的物债务的成立从标的物应缴付之时起,即使尚未现实移交,使债权人成为标的物的所有人……”可见,在“非特定物”交易中,标的物所有权并非自合同成立时起就发生移转,而是从标的物“应该交付之时起”发生移转。④对此例外之规定,需要悉心研究。
就《法国民法典》的规定而言,其第1583条之规定以“特定物”交易为规制对象,在解释上被认为是该法典关于标的物所有权移转的一般规则;其第1138条则是包括种类物、未来物等在内的“非特定物”所有权移转的特别规则。从这两条规定中唯一可以明确的是,“特定物”所有权移转的时间是在“当事人双方就标的物及其价金相互同意时”,“非特定物”所有权的移转时间是从标的物“应该交付之时”。这样看来,与其说《法国民法典》第1583条和第1138条是关于所有权是依“何因”移转的规定,倒不如说是关于所有权于“何时”移转的规定。如果说在“特定物”买卖中,物权变动可依据债权意思而发生的话,则在“非特定物”的买卖中,就不仅需要有债权意思,还需要其他条件。在非特定物特定化之前,当事人间的约定没有产生物权变动效果。当然,其约定仅在当事人间产生债权法律效果:一方享有债权,另一方负有债务。而此时,因缺乏“特定物”条件,所有权无法完成移转。所谓的“应当交付之时”,依本人的理解,即是“非特定物”已经成为“特定物”之时。这样一来,所谓的法国债权意思主义物权变动立法主义要件构成就是:债权意思+特定物。
在这种情况下,说《法国民法典》单依凭债权意思即可引发物权变动,肯定不妥。相对于单凭债权意思即可产生债权效果而言,“特定物”必要条件的加入,使得直接关乎所有权变动的意思表示,名其为物权意思以与债权意思相区别并相对称,是再恰好不过的道理。⑤只是,在《法国民法典》起草和颁布之时,限于各方面要素的影响,尚不能在理论上更不能在立法中提炼出有别于债权意思的物权意思。一般地,物权意思在民事法学理论和立法中被债权意思吸收了,尤其是在“特定物”买卖为法典规制的一般对象的情况下,为实现交易便捷的时代追求,更没有区分出一个物权意思的社会需要。由是之故,在“非特定物”买卖,《法国民法典》也非是如后来的《德国民法典》那样类分出一个有别于债权行为的物权行为,而只能是在立法技术上将其转化为“特定物”买卖来处理。所以,在“特定物”之即时买卖,在债权意思与物权意思同时生效的情况下,物权意思被遮蔽于债权意思,物权变动被理解为“因债权的效果而移转”;而在“非特定物”买卖,受物的非特定性所限,物权意思之即时作成受到了阻碍,债权意思作成后的债权效果并不生物权变动之结果,只有在“非特定物”特定化后,物权意思才得以作成,所有权才得以变动。置身于特定的时空条件下思考,认定《法国民法典》为物权变动的债权意思主义本也不会造成理论上的困惑和实践上的混乱。但是,笔者认为,这只是农业社会背景下以“特定物”买卖为社会经济生活常态的法律制度构造。所谓的债权意思主义,是以债权意思的形成机制和存在形式掩盖了其中必然存在的物权意思内容的结果。法制的实然与法制的应然之间的矛盾,在《德国民法典》确立物权行为理论之后,才得以浮出水面并加以彻底解决。
二、过程与结果——依法律行为物权变动全程之扫描
依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也即是依当事人意思的物权变动,只是关于此一“意思”,在《法国民法典》“作者”的眼里,被视为了债权意思,即债权意思引致物权变动。在笔者看来,这一在当时十分正确的规则设计,以债权与物权生效的要件衡量,则问题大矣!债权意思对应物权效果,风马牛不相及也!
(一) 民事法律行为与物权变动的意思
民事法律行为,指以发生私法上效果的意思表示为要素之一种法律事实。⑥先看这一概念里的“私法上效果”,就笔者的理解,所谓“私法上效果”,即通过当事人的自治行为获得何样的民事权利。民法上的权利,依据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类型划分,但有一种类型划分最具有意义,这就是把权利划分为绝对权和相对权。民法以权利为核心,以法律关系为构架。关于权利与法律关系的内在联系虽不是本文着重探讨的问题,但关于两者关系的一个基本判断是:权利总存在于法律关系之中;权利也只有被放诸法律关系之中,才可以更好地被理解。⑦法律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⑧以法律关系所及主体的范围为标准可以而且只可以将其划分为两类:特定主体间的法律关系和特定主体与非特定主体间的法律关系。⑨与法律关系的分类相对应,权利以其效力所及的范围为标准,可以划分为相对权(请求权)与绝对权(支配权)。而实际上,法律关系主体的范围与权利效力所及的范围是一回事——即纳入法律调整的主体的范围而已。在这里,两者实现了统一。所谓绝对权,即得请求一般人不为一定行为之权利也,其特征在于义务人之不特定及请求内容之限于不作为,绝对权以物权为其典型;所谓相对权,即得请求特定人为一定行为或不行为之权利也,其特征在于义务人之特定及请求内容不限于不作为二点,相对权以债权为其典型。⑩就权利实现的机制来看,绝对权之实现仅凭权利人的自由意志即可,不需要其他人的积极行为;相对权之实现非借助于有法律上有义务的相对人的给付不可。就此区别,法学理论上认为绝对权为支配权,相对权为请求权。请求权为特定主体间的法律关系,在财产法领域其抽象的法学术语即债权;绝对权为不特定主体间的法律关系,在财产法领域其抽象的法学术语典型即物权。
再看这一概念里的“意思表示”。依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总是发生于特定的主体之间,但是,发生于特定主体之间的法律行为,其意思表示之内容却并非就是建立一个仅仅拘束当事人自己的债权法律关系。主体的特定性并不能限制意思表示内容的多样性。质言之,特定主体间的意思表示,既可以是指向建立债权法律关系的意思表示,也可以是指向建立物权法律关系的意思表示。这样一来,就有了区分“意思表示”类别的标准:将意欲建立债权法律关系的意思表示定型化为债权行为;将试图建立物权法律关系的意思表示定格化为物权行为。这样的法构造理念,就促成了物权变动“区分原则”的基础。一个目的在于物权变动的法律行为,其行为主体的特定性、相对性,极易掩盖主体意思表示法律效力范围的非特定性、绝对性。这一发现和牛顿研究苹果落地一样:现象是早就存在的,但是从一种现象中发现法科学规则,却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法国民法典》将物权变动视为“债的效果”的规定,就显示了该法典在这一问题上缺乏学理洞见。
(二) 物权变动的过程
依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总是表现为一个当事人就与物权变动有关的问题不断磋商的过程。过程本身同样是具有法律意义的。其间具有法律意义的意思表示,当然也要形成而且也只能形成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锁”。正是此过程中产生的这些“法锁”,构成了物权变动目的实现的法律保障。当主体间的意思表示之法律效果指向对另一方当事人的请求权时,这就是一个债权行为。而且,在公示生效主义立法体例下,办理公示完毕前的“合同行为”中的所有意思表示,都只能产生债权法的法律效果;即使是公示对抗主义立法体例下,物权变动之效果的获取也会因为主观方面原因如附条件,或者客观方面如“物”的非特定性等,而不能成就物权变动效果,但这并不妨碍债权效果的成就。尽管有学者认为“所谓移转物权的合意,是包含在债权合同之中的”,或者“物权行为所包含的意思表示在法律意义上是对债权行为意思表示的重复或履行”,或者“物权行为不过是原来债权行为意思表示的贯彻或延伸,并非有一个新的意思表示”等等。但笔者认为,尽管债权合同中有一些内容是以物权变动为目的的,但这些意思表示的法律效果均只能在当事人间产生债权、债务关系。总之,尽管债权合意都是围绕着移转物权这一目的而展开,但其法律意义是给付请求权的设定,法律从来没有赋予其物权变动的法律效力。有学者曾指出:“盖债权契约仅发生特定给付之请求权而已,债权人不得依债权契约而直接取得物权,故应认为债权契约以外,有独立之物权移转之原因即物权契约之存在”。《法国民法典》的不足就在于,其将物权(所有权)变动的结果作为“债权的效果”,混淆了物权变动的过程与变动的结果的关系。
(三) 物权变动的结果
物权变动的结果,就是作为权利的物权——支配权,在主体间发生了移转。由此,形成了一个新的物权法律关系。显然,这一结果受到前面具有法律效力的过程的推动。过程与结果的区别,在《法国民法典》关于“非特定物”的买卖中已有所发觉,遗憾的是,《法国民法典》最终也没有把因“物”一方面的特定或者非特定而导致的法效果之不同区别开来。产生这一缺憾的原因在于,《法国民法典》没有如《德国民法典》关于权利分类的支配权、请求权的区别,没有物权与债权的区别,也没有《德国民法典》法律行为的概念和理论,因而,在《法国民法典》中也不会产生物权行为概念和理论。虽说这是《法国民法典》的缺憾,但就《法国民法典》的内在逻辑性、体系性来说,也属情理中事。将结果从物权变动的过程中区分出来,将合意所产生的对交易相对人的法律拘束效果,与物权变动所形成的新的物权人与其他人包括原物权人的物权法律效果分裂开来,以不同的法律效果对应于不同的当事人意思,以此形成债权意思与物权意思的法律分野。这样一来,相对于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而言,就有了物权行为的存在。这其实不仅是一个逻辑的问题,也是一个生活实际的问题。在特定物之买卖的意思表示之中,既可仅有引发债权债务的效果意思,也可以同时兼具引发债权债务的效果意思与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意思。因此,在立法上就有了两种选择的可能,一是可采德国民法的“析分”方法,把一项交易解分为一个债权行为,两个物权行为;二是可采法国民法的“综合”方法,把一项交易作为一个行为,例如一个买卖合同,把发生债权债务的效果意思与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意思一起纳入到这一个行为中。但是,特定物买卖是农业社会的常态现象,在商业社会,未来物、种类物买卖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会占有更大的比例,并日益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之常态。因此,在进行法律制度的创造和法律政策的选择时,就不得不因应社会变迁。法国法确立的债权意思主义没有在后来的德国法中得以延续,就是一个例证。德国民法确立的物权形式主义更能迎合作为社会常态的“非特定物”交易。
三、继承与创新——我国《物权法》确立的物权变动立法新模式
我国1949年以前的民事立法,移植了《德国民法典》确立的物权形式主义;1949年以后至《物权法》的颁布,我国民事立法照搬了俄国的债权形式主义。通说认为,我国2007年颁布的《物权法》就物权变动立法模式确立了公示生效主义为主,公示对抗主义为辅的立法主义。其中的意思要素究竟是物权意思还是债权意思,学界在解读《物权法》时的回答则模棱两可、意见不一。笔者倾向于认为,我国《物权法》确立的是物权意思。这一认识主要来自于《物权法》第15条所确立的区分原则,即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物权变动的结果相分离。
从法制史的角度来看,我国物权立法关于物权变动立法主义可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以前,采物权意思+公示生效主义;1949年以后,我国大陆民事立法采债权意思+公示生效主义;2007年颁布的《物权法》采物权意思+公示生效主义为主、物权意思+公示对抗主义为辅的二元主义。自1949年后的民事立法关于物权变动的立法主义是债权形式主义,即引致物权变动的因素包括有债权意思与公示形式两个方面。这一立法模式,既不属于法国模式,也不属于德国模式。在赞同债权形式主义体例的人士看来,债权形式主义既结合了法国意思主义的优点,又截取了德国物权形式主义的长处。但在笔者看来,情况恰恰相反,债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是一个物权变动立法要素上“拉郎配”的产物:就我国现有民事立法体系所采取的德式逻辑体系来说,债权意思只能产生债权效果(如果这句话没错的话),而在物权变动的债权形式主义,债权意思却成了物权变动的意思要素;公示要素在物权观念化后本仅可作为动态物权安全制度体系中表彰某人享有某特定物所有权的外观形式(没有公示,也并不代表不享有物权,这就是公示对抗主义),而在债权形式主义,其却又成了某人获得所有权的生效要件。
当然,法律制度可以被人为地任意建构,只要已经“拉郎配”了,并且只要人们已经按照“拉郎配”塑造的行为模式安排自己的法律生活了,这个法律制度也是可以践行的。对于法律制度这种人造规范来说,人们不曾想象到的东西就是不存在的并也是对法律实施不产生什么影响的,或者事实上产生了却不被人们所认知。但民法典本是一个体系化、逻辑化的制度,是在一定前见指导下的体系。我国民法理论已经引进并采纳了德国民事法律行为理论,已经将民事权利类分为绝对权和相对权并有物权编和债权编的立法体系结构,那么,将物权变动的意思要素理解并置设为债权意思,从民法理论体系和逻辑的角度来看,是不能被接受的。
物权观念化后,物权变动的充分条件得以完全奠基于当事人变动物权的意思合致之上。物权公示在谢却其物权变动要件地位之后,良性地恢复到了其本有的功能之上——以解决物权利益冲突和宣示物权状态从而促进交易安全为己任。在交易相对人之间,单凭当事人的物权合意,就足以实现物权移转。只是,《法国民法典》将其没有能够发掘出来的物权意思以债权意思遮掩或替代了。在近百年后的《德国民法典》中,物权的观念性没有改变,但物权变动的立法模式却显有不同,确立了物权变动的物权形式主义,这似乎以回归的方式将前罗马—日耳曼法上的要件性公示制度又搬移回到了现代法的物权变动模式之中,以将物权变动固定于一定的物质形式之上,来谋达物权变动另一制度价值——物权变动的内外法律关系的清晰与交易安全。《德国民法典》为何选择公示生效主义作为其物权变动的立法主义?除了萨维尼从交付的研究中发现的物权行为理论并再也没有走出交付对物权变动表现形式的局限以外,再者就是公示生效要件主义本身被人们认为所具有的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优点。
在物权变动二要素——意思要素与形式要素中,债权意思引致物权变动的理论和制度是荒谬的。相对于权利体系的类型化以及民事法律行为理论的确立,在物权观念化的今天,引致物权变动的意思要素只能是物权意思。再者,是否在物权变动的必要条件设计中须有公示要素的加入?不论是从社会实践的角度还是在理论建构的层面,都只能是一个价值上的政策选择问题——可以择其为必要条件,也可以不这样安排即选其为对抗要件。这是一个与法律制度建构所要设定的目的有密切关系的问题。就公示制度在物权观念化的制度体系中所能够担当起的角色而言,它只能对交易安全的实现起到物权享有的标示作用。所以,笔者认为,物权变动的直接原因来自于当事人的物权意思。当然,此物权意思绝非是《法国民法典》的债权意思,已属昭然;此物权意思在构成上也非属《德国民法典》的物权行为,则应需注意。因为,此物权意思(没有形式主义的要求)就是产生物权变动法律效果的充分条件,不需要德国法上的公示要件。由此形成了物权变动的物权意思主义:即物权意思+公式对抗主义。
四、结 语
要问《法国民法典》是否规定有债权意思产生物权变动,答案应是肯定的——法律有明文;再要问债权意思能否引致物权变动,答案则又是或然的。乍一听两个矛盾的判断之间其实并不矛盾,因为,前者是个实然的问题,而后者是个应然的问题。实然的东西一定有其存在的理由——“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应然的东西也必定有其可以存在的价值——“合理的也应是存在的”。在我国正在谋划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之际,审慎地反思和检讨各项法律制度的优缺点,大胆地进行法律制度借鉴和创新,既要照顾到民法典体系固有的逻辑性、体系性,又要远观民法典各项法律制度的科学性、前瞻性。在传承与创新中,完成“制订一部二十一世纪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国民法典”宏伟目标。就物权变动的原因而论,物权变动之“物权意思+公示对抗”立法主义之确立,应是我国未来民法典编纂中值得认真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