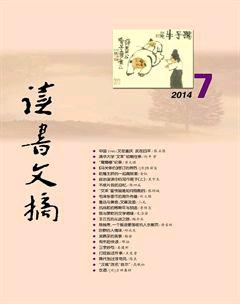政治漩涡中的写作班子(上)
吴中杰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帮”垮台之后,与之有关的写作班子,如北京的“梁效”写作组、上海的市委写作组,立即受到审查和清理,并被责令交代问题。当时要他们交代的主要是与政治斗争有关的问题,在一系列批判文章的写作过程中,“四人帮”都下达了哪些指示等等。总之,这种审查,意在通过写作班子成员的交代来挖掘“四人帮”的罪证,同时也理清这些成员各自陷入政治阴谋的程度。至于“写作班子”这种运作方式本身,却并没有受到质疑。不但没有质疑,并且还被认为是有效的斗争工具而接过来使用。据上海市委写作组文学组后期负责人陈冀德在她的回忆录《生逢其时》里说:“中央工作组刚刚进驻写作组的时候,工作组组长车文仪曾明确表态说,这支队伍是有战斗力的。正本清源之后,这支队伍今后我们还是要用的。”这就明显是把写作班子当作一种写作工具,只要能掉转枪口,原班人马即可为我所用。虽然后来由于形势的发展,车文仪未能如愿保留下这套人马,但写作组的形式还是承续下来了,只是人员和归属有所不同罢了。好在中国不缺遵命文人,组建几个写作班子并不是难事,像上海出版系统就如法组建了大批判写作组,写出了批判“四人帮”的系列文章,在当时很有影响(把胡风与“四人帮”一锅煮的文章,就是他们所写)。复旦大学重新掌权的领导干部也积极网罗写手,重组写作班子,有的教师过去受压受排挤,此刻能参加写作班,也感到无上荣光,在接受任务时向领导表示:这点任务“吃不饱”,意在表示自己有更大的能量,希望能进一步受到重用。
写作的内容虽然随形势而变,笔锋所指有时会截然相反,而写作班子这种组织形式却在中华大地传承不绝。这说明了一个问题:“文艺必须服从政治”的口号虽然不提了,但此种理念却仍然深入人心,而且,用来“服从”的东西,早已从文艺扩大到各个社会领域,如历史、哲学、经济学等等,甚至还把自然科学也包括进来了,当年不是还有“自然辩证法写作组”和“理科大批判写作组”吗?后者还准备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当作哲学上的相对主义来加以批判。
写作班的组织形式之所以受到广泛的青睐,因为它适应了上下两方面的需要:对上而言,它是权力者手中的工具,服从权力者的指令而行事,当然受到权力者的欢迎;对下而言,中国文人一向廊庙意识很强,而进入写作班也就是受到领导重视的表现,有些人还可借此作为晋升之阶,所以乐而趋之。
但是,知识分子贵在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这是文化创造的基本条件。中国文化之所以多所因袭而缺乏创造性,就是因为有着太多的从属观念而缺乏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之故。因此,我们不但要批判当年那些官方写作班子所写的文章内容,而且还应该看到他们那种写作方式的弊病,从而否定写作班子的组织形式本身,使写作脱离权力意志,获得真正的独立。
当然,我这里指的是一种卷入政治漩涡的评论性写作,而不是机关文秘写作。文秘(文字秘书)本来就是听从领导人调遣,为领导人服务的,他们(无论是个人或班子)的写作,无论是工作报告、政策文件或者什么讲话稿,都是代领导人立言,即使有些自己的见解,也需获得领导人认可,才能作为官方意见而融入文章,这与本文要说的写作班子的文字操作是两码事。
评论写作与文秘写作虽然是两种路子,但以写评论为主的写作班子却与文秘工作有着渊源关系。
在我国,文秘制度源远流长。过去,皇帝有中书舍人、南书房行走之类,地方长官有文案师爷,都是代拟文稿的;现今的一些领导通知,手下也都有秘书班子,其中必有文秘,就是他们的笔杆子。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中特别提出:“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可见书记们即使向中央写报告,也大都不是亲自动手,而是由秘书代劳的,否则党主席不会有此叮嘱。这些南书房行走、文案师爷和文字秘书们,虽然本身还不是写作班子,但却为日后的写作班子开启了一条写作道路:放弃自由思想,禀承上意写作。
在秘书代劳写报告的基础上,就必然要发展到由秘书代劳写文章。政客和武将的文章,大抵是由秘书代写的,有些大文章一个人写不了,就组织一个班子来写,领导人或者先口授一个提纲,或者连提纲也没有,由秘书班子先写,不中意的再修改。政客武将大都不习文墨,请秘书代劳还情有可原,最奇怪的是,有些文学家也不肯自己动手写文章,而要别人代写,这就有点看不懂了。当年的中国文联副主席、文艺理论权威周扬,他的一些重要理论著述,如《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等,都是组织班子写的,这大概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吧。难怪文坛奇才聂绀弩要嘲笑他说:“自己在各方面都拿不出一本书来,一部安娜(按:指译作《安娜·卡列尼娜》),大半是别人干的。人生几何,笑话太多。”(1979年12月7日致胡风信,见《聂绀弩全集》第9卷)
但这种为写某一篇文章而组织的写作班子,是临时性的。文章写好,班子也就解散了。相对稳定的专业性写作班子,是为了要长期反对资本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需要而建立起来的。一九六二年九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在这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还批判了小说《刘志丹》,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从此,各级党委对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就特别重视起来,写作班子也就应形势的需要而生。
这时,写作班子已有一个现成的模式,这就是北京钓鱼台的写作班子。钓鱼台写作班子是一九六〇年中苏关系紧张之后成立的,专门撰写反对“苏修”的文章。这个写作班子由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负责,由书记处书记康生主持,参加的成员有:《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红旗》杂志副主编范若愚、中联部副部长王力、中宣部副部长姚溱等。复旦大学有一位熟读马列经典的教授,借调到那边只是做个资料员,可见这个写作班子级别之高。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就是他们的杰作。接着,因为赫鲁晓夫的下台,中苏论战的大文章没有再发下去,这个写作班子也就无形中解散了,但是影响却一直存在。复旦大学党委宣传部长就常常以这个写作班子为范例来进行宣传,并教导文科师生:只有像“九评”这样的文章,才能称为好文章!这之后所成立的各种写作班子,大抵也是仿照这个模式而组成的:从各单位抽调一些写手,集中在一个地方,听命于领导的指令而写作,即所谓“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endprint
当时最有代表性的,是上海市委写作组。它成立的时间较早,存在的期限很长,产生的影响也甚大。我们不妨以它为麻雀来进行剖析,同时也兼及其他同类写作班了。
上海市委写作班是根据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意见成立的。柯庆施的政治敏感性特别强,对毛泽东的新思路跟得特别紧。八届十中全会开后不久,他就在一九六三年一月四日上海市文艺界迎春茶话会上发表谈话,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号召,并说:不写十三年的戏,我就不看。这种褊狭的题材决定论,在全国文艺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不但作家们难以接受,就是许多文艺官员也表示反对,但因为此论符合当时的政治方向,它还是占了上风,硬是把反对意见压了下去,使得反对的文艺官员变换腔调。接着,上海《文汇报》的版面也有了重大改变。政策调整时期所推出的争鸣之作消失了,代之以各种大批判文章。最明显的标志性作品,是五月六日、七日连载的长文《“有鬼无害”论》,它批判了孟超的新编昆曲《李慧娘》及廖沫沙为该剧叫好的杂文《有鬼无害论》,震动很大。这篇文章是江青通过柯庆施组织的,署名梁壁辉的作者是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俞铭璜。江青称赞它是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俞铭璜学养丰厚,议论务实,并非一个偏激的批判家,这篇文章是奉命而作,大概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据说稿子出来后,柯庆施嫌它学术性太强,要张春桥加以修改,以加强其政治批判性。
而这之后不久,毛泽东对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出来了。第一个批示写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九日,就批在《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的简报上,说是“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又说:“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这个批示下达后,中国文联开始整风,但毛泽东认为他们是在应付,即后来所谓的“假整风”,所以才会有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的第二个批示,而这个批示就批在文联整风报告的初稿上,措辞就更加尖锐了:“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柯庆施是得风气之先者,在这场斗争中已经占了先机。而在毛泽东作出第一个批示之后,他更加紧了战斗的部署,所以要在上海成立两个舆论机构:一个是写作班子,一个是《未定文稿》(一般称之为《内刊》)。这两个机构很快就建立起来,据写作班子文学组的人回忆,他们报到的时间是在一九六四年夏天。
上海写作班子初由市委文教书记石西民具体领导,先后有过五个组:文学组组长叶以群,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书记处书记兼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所以组员大都从作协文学研究所调来,也从三所大学中文系调人,华东师大和上海师院各有一名教师参加,只有复旦中文系不肯放人——所以就没有复旦的教师参加。副组长徐景贤又从电影局带来一个写作小组,一起并入,叶以群下乡参加“四清”工作后,即由徐景贤接任组长之职;历史组组长金冲及,他是复旦大学教师,从复旦历史系带来一个写作组,主要笔名是罗思鼎,意即要做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一九六五年金冲及调北京工作后,由朱永嘉接任组长;另外,经济组由钦本立负责,自然辩证法组由李宝恒负责,哲学组由郭仁杰负责。这个写作班先与《内刊》一同设在丁香花园,文学组的主要笔名丁学雷,就有身居丁香花园学雷锋之意,后来写作班迁至武康路十八号,又迁至武康路二号,但这个笔名仍旧沿用。不过迁到武康路之后,写作班只剩下了文学组和历史组,其余各组人员都陆续回到原单位去了。而且,市委直接领导写作班的人也改换了。一九六五年国务院文化部改组,石西民调到文化部任副部长,临行前他召集写作班开了一次会,接任他主管上海文教工作的市委书记张春桥和华东局宣传部部长夏征农分坐在他的两边,他明确将写作班的工作交给夏、张二人。但后来夏征农并未插手写作班的工作,写作班就由张春桥主管了,从此就成为他手中的一支政治力量。而在石西民领导时期,华东局宣传部倒还过问一些写作班子的事。据文学组早期成员吴立昌回忆,他当时有两篇文章,一篇由石西民修改过,另一篇则去俞铭璜办公室听取过意见。
写作班子本来就是跟着权力者所指的方向出击的,当时正在批判热潮之中,从《北国江南》、《早春二月》开始,接着是《舞台姐妹》、《林家铺子》、《不夜城》、《逆风千里》、《兵临城下》、《革命家庭》、《红日》、《聂耳》等,批了很多电影,还有京剧《谢瑶环》、昆曲《李慧娘》等。被点名批判的文艺界大人物,则有田汉、夏衍、阳翰笙、邵荃麟等。当然,文艺只是个突破口,很快就扩大到其他文化领域,如美学界的“无差别境界”论和“时代精神汇合”论、史学界的“让步政策”、哲学界的“合二而一”论、经济学界的“利润挂帅”论等等。一路批判下来,好不热闹。丁学雷和罗思鼎,也就在这一轮批判中大显其名。
不过这些批判,由于有统一的部署,所以全国各写作班子或非写作班子的写作积极分子们,差不多全都卷入了,只是影响不及丁学雷与罗思鼎而已。但这个写作班子在一九六五年却得到一个特殊的任务,使它的地位突然显要起来。这就是协助姚文元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姚文元这篇文章,是江青布置他写的,江青的背后当然是毛泽东。毛泽东是位谋略家,每个重要动作都有战略意图。组织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要从《海瑞罢官》的作者——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打开一个缺口,直接通向市委书记兼市长彭真,而彭真的背后则是刘少奇。这是他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关键一着,因此,这篇文章也就显得特别重要了。endprint
吴晗是位明史专家,学有专长。但他的写作有个严重缺点,就是喜欢以历史研究来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搞的是影射史学。他早年所写的朱元璋传《从僧钵到皇权》,就是影射蒋介石的,这次写有关海瑞的史论,并“破门而出”写起《海瑞罢官》这个京剧剧本来,也是由于受到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的鼓励,为配合毛泽东提倡海瑞精神而作。但政治家谈历史故事总是从一定的政治需要出发的,当政治需要发生变化时,他的提法也就不同了。于是吴晗当初为一定的政治需要而写的史论和史剧,转眼间也就成为新的政治需要的靶子。
姚文元是文学评论家,对于历史是门外汉。现在是奉命写作,批判《海瑞罢官》的基本调子是上峰定好了的,他要做的是根据这个调子写出批判文章来。但对于不熟悉史料的人来说,这也是难事。这个时候,写作班子就起作用了。张春桥立即从“四清”工作队中调回罗思鼎小组,关起门来帮他查找史料。这时上海市委写作组已经搬到武康路二号一幢小洋房里,姚文元和罗思鼎小组关在二楼炮制批《海瑞罢官》的文章,连住在一楼的丁学雷成员也不准进门,不准打听他们在干什么,简直神秘至极。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江青的掌控下几经修改,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在《文汇报》发表,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这篇文章所署的作者名字是姚文元,但罗思鼎亦有功焉。接着,罗思鼎、丁学雷又为姚文元批“三家村”做了很多的资料工作,并将这把烧北京市委的火延伸到上海,丁学雷批判了周信芳主演的京戏《海瑞上疏》,罗思鼎则批判了李平心和周予同,他们都跟得很紧。
上海市委写作班子本来就是张春桥领导下的班子,在“文革”发动期间又协助姚文元做了许多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当然会受到他们的重视。此后,随着张春桥、姚文元政治地位的上升,这个写作班子也就日益显要起来。到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徐景贤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授意下,率领写作班子集体造反,并与《支部生活》编辑部等联合成立了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接着,这个联络站联络了各路造反队伍,夺了上海市委的权,从而使自己的性质也起了变化。它一方面是中央文革成员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的办事机构,同时也直接参加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班子。当张春桥、姚文元成为上海市委和市革会一、二把手时,写作班子的支部书记徐景贤就成为第三把手,市民称他为“徐老三”——那时,王洪文等工人造反派还未蹿上来,而马天水等老干部也还未解放和结合。罗思鼎小组组长朱永嘉则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指挥,并进入市委和市革会的常委会。还有些人出任“调查组”、“农村组”和“政宣组”等组织的负责人。
但这样一来,写作班子也就没有时间再写文章了。再加上“市革会”里面各派人物的权力斗争,这个写作班还能否继续存在,也就成了问题。不过,徐景贤深知笔杆子的作用,他不肯轻易放弃这支自己的队伍,在一九六七年全国“革命批判”高潮中,又在宛平路华东局机关大楼内重新成立上海市大批判写作组,同时还在康办(市委康平路办公楼)旁边的荣昌路上成立了一个专题写作组,成员都是党员,要比大批判写作组高一档。但似乎没有写出什么大文章,不久就解散了。一九六八年,毛泽东因清华大学的武斗,派遣工宣队进驻全国高校,徐景贤就趁机将写作班子的人分派到工宣队中去,借以保存这支力量。后来姚文元接管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要上海成立《红旗》组稿组,上海写作班的人马就以这个名义重新组织起来,继而又成立了新的上海市委写作组。
这个新的上海市委写作组,或者遵照张春桥、姚文元的指令,或者自觉地根据当时的形势而写了具有很大冲击力的文章,如对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体系的批判、对于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大学的调查报告等,将文艺界和教育界冲得稀里哗啦。但在全国,这个写作班已不能起领先作用了。因为不久,北京就出现了“梁效”写作组——清华和北大两校联合成立的写作组。
既然写作组是权力者的工具,那么文章的威力也就不在于写作者笔力的健弱,而取决于掌握写作班子领导人的权位。上海写作班子背后是张春桥和姚文元,而向“梁效”发指令的却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文革”结束后清查“梁效”写作班子时,重点是清查它与江青的关系,大概为了撇清这一点,“梁效”写作组组长范达人在《“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里说:“尽管江青与‘梁效来往不少,但是,在我看来,‘梁效应是毛泽东通过谢静宜、迟群掌握的写作班子。毛泽东直接向谢静宜下达指示和要求,然后再由谢和迟向‘梁效头头传达、贯彻。”同时还引用了谢静宜的谈话为证。谢说:“江青在一次会上把‘梁效称作她的班子,我当时反驳说,这个班子是毛主席提议建立的,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工作的。江青听后马上改口说,那就更好了。”毛泽东是号令全国的最高统帅,大家都要跟着“最高指示”转。所以当时老百姓有句顺口溜说:“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于是“梁效”也就占尽风光了。此外还有听命于江青的文化部写作班子“初澜”等,也很霸道。
上海写作班子有一点比较特殊,它直接与上海的权力机构相结合,所以它又发展出“梁效”、“初澜”那些写作班子所没有的功能。当时各省市新成立的中共省委、市委都设有宣传部,唯独上海没有,因为写作班子就代办了宣传部的工作。“文革”后期,上海创办了文学刊物《朝霞》丛刊、《朝霞》月刊、《外国文学摘译》和理论刊物《学习与批判》,还设立了《鲁迅传》编写组(石一歌)、文学概论编写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编写组、《哲学小辞典》编写组等等,都从属于写作班子,电影组虽说是由市委书记徐景贤直接领导,但也与写作班子有着联系,可见写作班子在上海权力机构中的作用。
正因为上海写作班子掌握着这样大的权力,所以新的权力斗争也就要冲着它而来。“《朝霞》事件”,就是这种斗争的表现。《朝霞》事件发生在一九七四年四月份,其时王洪文已被毛泽东作为接班人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地位远远超过徐景贤,他手下的工总司(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头头们,也都一齐鸡犬飞升,窃据要津。他们在上海已掌握了党、政、财各方面大权,唯独文权不在他们手中,所以势在必夺。一九七四年三月下旬,王洪文在上海的主要代理人王秀珍到北京去和王洪文密谈之后,回到上海就提出一份要《朝霞》停刊整顿的决定书,要另两个市委书记马天水和徐景贤共同签字。理由是《朝霞》上发表的《初试锋芒》和《红卫战旗》有严重政治问题:污蔑民兵组织,影射攻击工总司,丑化一月革命。马天水一向主管工交,不懂文艺,而且又是结合进领导班子的老干部,在“文革”中腰杆子不硬,不敢拂逆造反司令的意见,自然就签字同意了。徐景贤主管文艺,自己又是作家,作品是否有问题自然不会看不出来,而且写作班子是他的嫡系,王秀珍此举耍的是什么把戏他当然很清楚,只是对方来头很大,他实在顶不住压力,也只好签字表示同意。三个市委书记联合签字,事情就算定局了。这时朱永嘉为了保住写作班子这支队伍,就采取政客们惯用的丢卒保车方法,把《朝霞》负责人陈冀德抛了出去。据说,这时工总司方面已经预备好一套编辑班子和作者队伍,随时准备接管《朝霞》等刊物。endprint
但后来事情有了一个戏剧性变化。因为陈冀德实在接受不了眼前这个突发事变,就写了一封信给在北京的萧木,汇报《朝霞》此刻的情况,悄悄跑到负责往北京送文件和稿件的机要交通站发出。萧木原来也是上海市委写作班子成员,《朝霞》就是在他创议下办起来的,此时在北京做王洪文的秘书。萧木倒不怕得罪王洪文,他拿着信去向张春桥汇报。张春桥马上作了批示,说《朝霞》这两篇文章并没有什么错,而且他是市委第一书记,责令《朝霞》停刊整顿的事情,他怎么不知道?并明确表示,以后凡属工作中的差错,不要把责任推给下面。责任在市委,首先在他。张春桥还要萧木马上接通朱永嘉的电话,他在电话中立即对朱永嘉下达指示。于是第二天一大早,王知常就带人将所有揭发陈冀德、批判《朝霞》的大字报统统撕下,而王秀珍则一再声明:我怎么会炮打春桥同志呢?事情终于以喜剧的形式落幕(据陈冀德《生逢其时》、燕平《我在〈朝霞〉杂志工作的回忆》)。
人们或许以为张春桥此举颇为费解:此时王洪文地位已在张春桥之上,他为什么敢于下达这样的指示?这不是冲着王洪文来的吗?其实也不难理解。因为王洪文毕竟是个草包司令,在江青、毛泽东面前,张春桥还是比王洪文更受信任,王洪文过去是张春桥提拔起来的,以后也还要仰仗他的力量,才能生存和发展,所以对张还有所忌惮。而张春桥之所以不顾王洪文的态度而要保存《朝霞》,倒也不是什么主持正义,而是出于政治权谋。须知张春桥是一名政客,在政客心中首先考虑的总是利益,《朝霞》事件的处理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平衡术。盖因张春桥虽然志在掌握中央权力,但上海毕竟是他的基地,他深知这个后方基地对于他在中央掌权的重要性,非要牢固地掌控在自己手中不可。而要掌控这个基地,则必须平衡各种政治力量,使他们都要依赖于自己。“文革”初期,他依靠的是写作班子,但在中国,文人是成不了什么大气候的,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这一点他看得很清楚。所以他抓住中央文革派他处理安亭事件的机遇,先斩后奏,签字同意了工总司的要求,扶植起这支工人造反队伍,王洪文等人当然要唯他的马首是瞻。后来毛泽东要求各地革委会必须结合老干部,他又拉出马天水、王少庸等人来为己所用。现在,工总司的力量无限膨胀,要想吞没一切,将来难免要失控,所以他在一封信中将《朝霞》事件比作当年“四一二”(4月12日)红卫兵对他的炮打,就是这个道理。他不能让工总司的势力独大,而要用老干部和写作班这两支力量去平衡,否则他就难以控制了。王洪文、王秀珍之流毕竟是老大粗,暴得大权,而不懂政治,所以才会如此肆无忌惮地扩张,犯了政治上的大忌。而徐景贤、朱永嘉虽然读过不少书,也从政多年,但毕竟是书生见识。他们想丢卒保车,而一旦丢掉这枚卒子,对方岂能得一小胜就止手乎?朱永嘉要求王秀珍不要让《朝霞》停刊,不是马上受到了王秀珍的嘲笑吗?
只是文人做到了成为别人政治棋局中的一枚棋子,却失去了独立意志,也是够可怜的了。有些人至今还以自己当年的写作是接受某领导的指示为荣,实在是很悲哀之事!
(选自《书城》2014年第2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