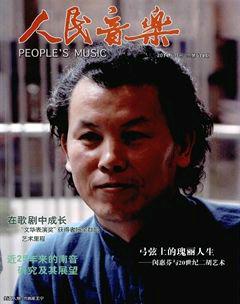“水”之意象的音乐表达
一
水孕万物之灵,“水”似乎在中国国民心中一直有着特别的情感投射。自古以来,在中国的哲学、绘画、音乐、文学中,水都是最重要的命题之一。而与西方同类命题的磅礴气势相比,中国的“水”有更多的人文涵义——“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上善若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在这无数的骚人墨客的作品中,汉民族特有的“低调”、“圆融”、“中庸”以及“至善”等的道德诉求与人生旨趣似乎都在对“水”之不厌其烦的描述中借水喻情中表达出来。
水是中华传统精神之灵粹,而在20世纪这个以东西交汇融合的大时代里,华人音乐家们同样没有忘记“水”之意象。“水”或以典型的形象?熏或以特性的音质成为二十世纪诸多华人作曲家们笔下的宠儿。而在新千年之后,我国当代作曲家朱世瑞同样以“水”为命题,创作了一部关于“水”之意向的作品——《水想II》。
这部《水想II》创作于2010年,并于2010年10月的上海音乐学院当代音乐周首演。之后分别献演于2010年12月于天津召开的“中华乐派论坛”、2011年6月的“上海之春·民乐新作专场”音乐会、2011年12月西安音乐学院学术讲座、2012年上海音乐厅李志卿独奏音乐会、2012年11月上海文汇大厦演出并由电视与网络实况转播、2012年12月北京首届胡琴艺术节闭幕式音乐会以及2013年8月上海城市剧院等等。值得重视的是2012年获得“TMSK刘天华奖中国民乐室内乐比赛”一等奖(前四届“一等奖均空缺”),并开始作为中央音乐学院以及上海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考试备选曲目以及“金钟奖”等比赛曲目。在目前这个现代专业音乐创作与学院派创作普遍受“冷遇”的大环境下,《水想II》的这种受欢迎程度确实引人注目。
按照作曲家的解释,《水想II》是“着意于对水的思绪、想象和情感表达”。相较于其他新创作作品,《水想II》的音乐相当入耳,全曲传统意味十足,通过采用二胡与古筝两件传统乐器的组合诠释出了中国文人对于“水”之意象的认知与理解。这首作品给人的第一印象即在于“融合”:一方面这是一部严肃的学院派作品,作品之“形”中有精确的创作构思,但并未凸显太多现代的技法观念。而另一方面,作品之“神”又传统意蕴十足,同时又不是传统意义上民间曲调或音色的简单拼贴挪用。当古筝与二胡进行亲密的对话,筝的古雅之声与二胡的洒脱情怀融合萦绕之时,一种新的音乐风格进入耳朵。这即是一种传统的复现,又是一种现代的创新。或者说,这是在21世纪的今天,一种“中国之声”或“传统情怀”的音乐表达。
二
作曲家在《水想II》中有意识地对“水”之意象进行描绘。这种描绘展现于作品整体与局部、自旋律构建延伸音色使用的各个层面,作品的各个层面中都凸显着水的形象流转。而在这种描绘的背后,展示出的是作曲家对传统的意蕴及现代观念的比较、借用、思考以及拓展。
作品的整体层次已然体现出了这种“融合与独立”兼具的特质。首先是乐器组合,自民乐创作形成的那一刻,两件乐器的组合形式似乎就是常规的做法之一。不管是二胡与扬琴、唢呐与笙、琵琶与三弦还是琵琶与古筝,当两件传统乐器结合在一起,必然呈现为一件乐器主奏,另一件乐器伴奏的状态。然而这部作品却颠覆了这种传统的主奏伴奏模式:二胡与古筝在不同的时刻各自占领着主奏的位置,处于各领风骚的样态。这缓解了以往一件乐器主奏的单调性,呈现出变幻多姿的音色交织、在音乐发展的过程中,模仿与对比复调的运用同时在纵向上勾勒出丰富的立体层次。
同时,在作品的整体结构中也存在对“水”形态进行的勾勒。首先,《水想Ⅱ》采用西方音乐常用的四乐章套曲结构形式,但同时可以发现其于结构层面上存在一种将西方的结构概念与中国传统音乐结构模式自由结合的特征。四乐章速度上“慢快”—“快慢”的对称式设计其实源于对于“水”的不同状态的理解与阐释:水可以缓行可以激进,可快可慢,可动可静也。同时,这部作品乐章顺序可随机安置、自由组合。这种构思更符合水之形态自由变化、居无常形的特点。“水”之势无常态,因此,《水想II》在独特的结构模式之中已经触及到了中国传统艺术的最核心特质——一种与西方立体“透视结构”,具有明确边界完全不同的东方式的“自由、随意”的散点艺术特征。这恰恰是中国艺术的最本质特征。正如同浩浩汤汤之流水一般,无相无形,随性自然。
而在作品内部,为了追求传统音乐理念之中所谓“中和”的至高追求,作曲家有意选择了具有明确五声性特征的音程素材进行发展。全曲四乐章统一采用由D—A构成的纯五度。作为核心音程的五度音程的选择不仅使全曲的音程旋律变得协和有序,同时也使旋律写法更接近中国语言腔调的变化。这一动机因此成为了统摄全曲结构层面、旋律层面甚至是精神意境层面的核心要素?熏甚至可将此音程动机理解为“水动机”,即一种纯净、平稳的动机形象。
在全曲的陈述中,这一动机经历了从明确展现到被掩盖再回复逐渐明朗化的过程:第一乐章呈现出明显带有核心音调的旋律扩散。第二乐章核心音程的展现伴随加入古筝的泛音与其他音型,核心音程的出现变得不再特别明显。第三乐章核心音程几乎已经被掩埋,失去核心位置。第四乐章核心音调又回归至清晰、明朗的状态。这种变化过程一方面是技巧上避免单调的构思,同时这种从明确到掩饰再到复现的过程也与“水”之清洁、明澈意境相吻合?熏即所谓“源情流洁”、“楚水清若空”。
在旋律构建及音色安置层面,在聆听中同样可以感知到作者对于“水”之画面感的强调。全曲在点与线交织的织体布局支撑下有效地塑造了水流的动态画面。在聆听过程中,可以不断地听到类似以二胡主线,古筝点状跟随的手法展开。古筝在二胡线条每次气口的连接部分插入进行点状润色,二胡的横向线条与古筝随后的模仿恰巧形成一种类似单一线条在纵向音响空间中扩展。而在作品中不断呈现出的单音滑动①音色特点,则形成一种具有“音腔化”②的带腔音的特点。这种以单音为主的持续线条在“准”与“不准”之间的音色中滑动,充分传递着东方音乐“以滑动的声音追求余韵的神似”的审美观。同时在音色设置上,作曲家则追求一种共性带来的两件乐器统一的完美配合,而非强调两件乐器独特的特点,这种通过使两件乐器在两个声部交错中所展现出奇特意境的创作风格,正是作曲家所说的“强调我国传统音乐中的‘随意性?熏追求一种实中有虚、虚而寓实的境界”。
三
作曲家在创作中不断进行着针对“水”之范式的思考。这种思考则构成了桥梁,接通了具体抽象的现代音乐作品创作与平和古雅的传统艺术的审美意蕴。作为一部以“水”为主题的作品,作曲家首要表现的自然是“水”的形态与精神。作曲家自己在谈到这部作品的创作时就提到:“水想”想的是什么?想的是——老子的上善若水,无形亦随形。它是艺术之水、生活之水、历史之水,更是生命之水。水最坚强也最随性,水可以摧毁一切,水也孕育生命。水无色却可映照出斑斓色彩……因此在这部作品中,作曲家想要表现的是远比自然之水更多的东西?熏是一种古老文化对其精神层面的感召。这种感受是自古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感受得到的?熏即所谓“智者乐水”。
在我国传统器乐曲中,这种情怀曾一次次被揭示:《春江花月夜》中以静态的水描绘出山河景象,《潇湘水云》中对水之意境动态主观的特景描写,在《江河水》中是悲伤绝望的旋律诉说,到《流水》中则转化为气势磅礴的姿态展现。
《水想Ⅱ》中体现出的正是这种对古老文明精神力量的感知与回馈,是一种当代作曲家对于已然逝去的传统因素的追寻。虽然当代作品已经不能从标题来判断作曲家的用意,但是通过对作品谱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作曲家对“水”的精神、水的意象、水的禅意、水的画面用音响来诠释。正如李吉提说到:“中国现代音乐与西方的现代音乐的不同,首先表现在精神内涵方面。中国当代音乐家创作中集体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寻根意识……对中华民族文化(历史、哲学、诸子百家)各层次的深入理解……对中国山水意境的苦苦追求……中国情结。”
当代作曲家对于中国哲学、美学上的追求也正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寻找中国传统之根的最本真做法。作品标题的“水想”展现出的正是对我国哲学、诸子百家的致敬。这种心灵流露,其风骨极似我国古代的“文人音乐”,作品中所展现出的注重个人内心体验的细腻、含蓄与韵味。虚实相间的意境和音色变换,自由松散的结构等特点都与西方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水想II》表现出的意境正与传统意义上的文人音乐相印合,在自由松散,若虚若实的音乐笔触之下,展现一种动则力若万钧,静则悄无声息的模糊美感。而在音乐的背后,则是个人情怀的极致抒发。这也正是当代作曲家对于中国古代文人雅致的一种崇敬,一种模仿。进而在对古代文人音乐意境模仿的过程中不断地出新变化,即作曲家林乐培所说的“从古思中寻根,从前卫中找路”。
同时,在实际创作中,每位作曲家都会赋予其作品独特的涵义,然而当聆听者无法探知作曲家赋予作品的涵义时,聆听者的理解与审美势必会与作曲家产生一定的错位。作为作曲家,朱世瑞所要表达一种关于“水”的随想,他将作品的四个乐章定性为水的四种状态,而且认为乐章之间都可以任意组合。而作为一个聆听者,在不知作曲家用意的情况下,所听到的却是严密的四个乐章阐述了水从初始的平淡到后来的汹涌澎湃,后来又渐渐平静恢复原始状态。在这种聆听经验基础上,四乐章位置是不可颠倒的,如果颠倒势必失去整体上的秩序感。由此引出另外一个存在于目前诸多当代作品中的问题:聆听者如何在针对当代作品的意义理解上与作曲家达成同一?抑或是否需要存在这种同一?
或许,我们的确需要从标题与作曲家对曲目的题解当中去理解作品,在作曲家的标题指引与乐谱的分析指引下,甚至在作曲家亲自撰文的引导下,我们必然会产生一种纯粹的“正确”的建筑于理性之上的审美体验。然而同时,如果我们仅仅去聆听作品,或许同样可以感受到一种直观的、建筑于感性之上的审美体验。当我们从感性的聆听中感知到一种听觉体验,同时又从理性的体验中感知到另一种音乐表达。当这种理性与感性产生错位时,哪一种才是我们应该遵循的?哪一种又是可以被接受的?而我们的批评又应建筑于何种标准之上?
四
作曲家叶国辉经常提及一句话?押“我们远离了传统,因为我们不够现代。”从《水想II》这部作品种可以看出我国当代作曲家对于传统文化的领悟与吸收,以及对传统的再造。中国大量当代优秀音乐作品不断涌现,尤其是21世纪以来的新作品,作曲家们不仅仅开始有寻根意识,而且出现一种多元化的寻找传统意识。无论是对传统曲艺形式的进一步探寻,抑或对中国民族乐器本身的音色发掘,或者,体现如同朱世瑞的《水想Ⅱ》,强调一种中国意蕴的诠释。
对于这种当代作曲家追寻传统根源,并形成创作的过程,朱世瑞认为,(这种行为)“可以说这是一种传统的延伸”。立足于传统,将自己对于音乐的理解融入到自身创作中,同时对音乐文化“汇流”做出贡献。
黄翔鹏先生曾经说过:“传统是一条河流。”传统应该是包容的,是流动的。正如中国文化特有的“水”的形态。不断地流动,且无常形。在不断地向前流动的过程中,卷入一切,消化一切,并形成新的一切。而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员的当代的作曲家,同样应当在这种流动的过程中感知、创作。找到自己的定位。今天的传统是过去的创新,当下的创新是未来的传统。当代作曲家音乐创作中的“传统回归”也可看做是一种“新传统‘主义”的体现。当我们不断地学习外国的技法和理论而有点迷失方向的时候,或许能从“传统的回归”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或许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不需要拘泥于何谓“西方”何谓“东方。只要是中国人创作的,能够展现出中国传统意蕴的音乐作品,均可视作是传统音乐的代表之作。或许当我们形成如此开放的观察角度之后,我们才能够更好地解释:“何谓传统?”抑或“何谓当代?”
参考文献
?眼1?演李西安《走出大峡谷》?熏安徽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眼2?演李西安、军驰《中国民族曲式》,人民音乐出版社1985年版。
?眼3?演李吉提《中国音乐结构分析概论》,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
?眼4?演程兴旺《价值显在:学术音乐与音乐学术——“朱世瑞室内乐作品音乐会创作研讨会”综述》,《人民音乐》2007年第11期。
?眼5?演王安潮《跨文化视野下的综合美显现——朱世瑞室内乐作品音乐会评述》,《人民音乐》2007年第11期。
?眼6?演徐天祥《新世纪中华乐派?押理念与路向——首届“新世纪中华乐派论坛”侧记》,《人民音乐》2007年第1期。
?眼7?演郭树荟,《探索与困惑——20世纪下半叶上海民族室内乐为我们带来了什么》,《音乐艺术》2007年第4期。
?眼8?演郭树荟《当代语境下的中国民族器乐独奏音乐——传承与创作双向路径与解读》,《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①单音滑动:作曲家将该技法定义为“揉-颤-滑-泛音”,即四种技法结合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演奏技法。
②音腔:广义来说,凡带腔的音,都可称为音腔。所谓腔,指的是音的过程中有意运用的,与特定的音乐表现意图相联系的音成分(音高、力度、音色)的某种变化。所以,音腔是一种包含有某种音高、力度、音色变化成分的音过程的特定样式。(沈洽《音腔论》,《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
(本文在第六届上海音乐学院当代音乐周“第三届中国当代音乐作品评论比赛”中获一等奖)
姜小露 上海音乐学院2011级硕士研究生
?穴特约编辑 于庆新?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