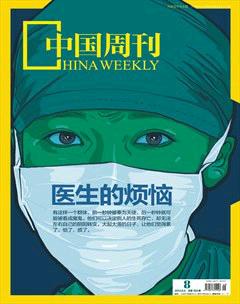纪克宁:“退休”是一种解放
夏华东



学医是一个历练的过程
五十八年后,77岁的医生纪克宁依然清晰记得南开中学的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1956年,她从那里高中毕业,考取河北医学院(今河北医科大学)。
“允公是大公,惟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正己教人,发扬集体的爱国思想,消灭自私的本位主义。允能者,是要做到最能,要有现代化的科学才能,同时要具有实际工作能力。而所谓日新月异,不但每个人要能接受新事物,而且要成为新事物的创始者;不但要能赶上新时代,而且要能走在时代的前列。”南开中学的老校长张伯苓先生留下这番校训解读。
在以后的日子里,纪克宁都以此为准则。比如选择学医那一天,她唯一的想法就是“治病救人”。 “我们家基本算是商人家庭,没有人从事与医生相关的工作,只是爷爷和父亲患有肺结核病,父亲又爱读大众医学及相关的科普知识,我便对医生很感兴趣。”作为家里的长女,纪克宁从小就很独立,她明了自己的选择。
“学医跟别的专业不一样,要有一个历练的过程,就算都学了,最后还得通过思考,通过总结,才真正有提高。只看书本是不够的。”她解释为什么学医需要五年时间。
1961年,纪克宁面临分配。那时候,人人争先恐后要去最艰苦的地方锻炼,同学们天南海北。她被分到了河北省张家口阳原县医院,做综合性病房医生。
两年后,纪克宁到北京天坛医院妇产科当起了住院医。二十五六岁的年纪,纪克宁像鱼儿进了大海一般,对工作充满了热爱,尽情吸收着养分。妇产科多被认为又苦又累,但她并不在意。“那时候主要看工作需要,上学时没有学费和书费,就觉得国家培养了医生,一定要再回馈给国家,回馈给人民。”
回忆起天坛医院的时光,让纪克宁印象深刻的是那里的教授、讲师很有经验,能够非常规范地培养出一个医生,教会了她很多。
“那时好些年不兴提升,以至于我离开的时候仍是住院医。那个年代,医生就是累积临床经验,回顾病例。”纪克宁说,“现在学医更注重的是影像、化验、科研,是名气,不像我们那会儿一个病例一个病例地总结。”
在纪克宁看来,一代人跟一代人不一样。她们这一代承上启下做了好多,都是从最基层做起,从什么都没有开始摸索,所有东西都是慢慢地从实践中磨出来的,所以比较有耐性。 “心中无缺叫富,被人需要叫贵”,这是纪克宁的座右铭,也是这么多年来的感悟。
从业53年来,纪克宁积极响应国家各项政策,参加过上山下乡,深入民情,这让她走得也更踏实,不仅积累和更新了专业知识,也注重理论结合临床实践。
“我很感谢这个职业。感谢病人通过自己的病痛,成就了医生治病救人的梦想。每例急救成功,更加坚定了救死扶伤是医生天职的信念。”
在医生这一职业变得如此敏感的今天,纪克宁也从未后悔过踏入这一行。“我觉得每个人的病都是一本书,过程、结果都是不一样的。医生这个职业会让原来感性的自己变得更理性。这样也比较能宽容别人。”
谁是强势?谁是弱势?
从医的人往往对家庭付出很少。纪克宁的先生也是医生,夫妻俩都缺席了儿女的成长。“小时候女儿在北京归奶奶管,儿子在天津归姥姥管,这也是为了学业。”虽然如此,纪克宁并不遗憾,“医生就是没有自己的时间啊。那个年代我也是觉得自己要多进步,多为病人解除病痛。”
从业这么多年,纪克宁深深体会到,医护人员已经成了尚未成功的医改道路上的牺牲品。“医学是有风险的行业,目前国内医护人员多超负荷工作,活多、钱少、高危已成为中国医生的标签。最严重的是执法不公,法律往往将患者视为弱势群体,将举证责任倒置,使得医生成为戴罪之身,作为执业医师深感屈辱。”
1990年代以前,纪克宁从未意识到医患矛盾这一问题。“1990年以后只是个别现象,根本构不成整个社会的大问题。但2000年以后再加上医闹,一下子就出现了‘不打医生打谁,不打护士打谁,打的就是他们的普遍现象。”这种把对社会的不满、对医院的不满发泄到医生身上,让医生当替罪羊的举动,让纪克宁内心很是不舒服。
“医闹就是流氓,就得严厉打击。像在美国,一般就得收监,还会让他们赔偿很多钱。”纪克宁说得认真。在她看来,虽然现在国家也投入了很多人力保护医院,但却缺少相应制裁的法律。
“到底谁是强势?谁是弱势?哪一行都有风险,但就是医生这一行不允许有失误。每一次发生一些事故或者误诊的时候,很多医生出于职业道德都会有负罪感和不安,但依然有很多人坚守在这一岗位上承担很多。”纪克宁说。
制度缺失与保障无力,让医生成为了面对矛盾时非常具体的一个对象,悲剧也就一次又一次地发生。
“三甲医院人满为患,医生不可能给每位患者提供良好的诊疗、帮助和安慰的服务,这是我们的体制造成的。如果让80%-90%的患者,在门诊服务上能够下到社区,医生们才有精力和时间,建立医患相互信任的这种关系。”原北京市卫生局干部王双琴曾这样提到。
“很多时候不是说医生失误,现在不论是环境污染,还是食品安全等诸多复杂情况,如果没有化验和精密仪器检测,一旦有情况真是百口莫辩,没有证据。”从业多年,纪克宁没有任何医疗事故,但是也曾经历过同科室的一些意外。从中,纪克宁也吸取了很多教训。
“现在好多医生常常会觉得忐忑,跟病人说完话,赶紧就走,不敢多待,确实都有一个防范的意识。”纪克宁谈到几年前同仁医院医生徐文被患者砍数刀的事情,感慨道:“每个医生在学医的时候都以救死扶伤为目的,但现在,他们更注重保护自己。”
“谁都愿意做个好人,不愿意做个死鬼。”纪克宁很直白。在她看来,医生和患者事实上是平等的,治好了病,两人也是共赢。“所以如何分辨强弱势?很多时候还是社会带出了这个问题。”
医生在中国到底是什么?
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曾说,在一个社会中,医生和律师的劳动报酬应该比较高,因为我们把健康委托于医生,而把财产委托于律师。endprint
纪克宁曾多次出国访问,她的观察是,“除中国外,各国都十分尊重医生。有的国家,医生的地位超过官员,甚至超过律师。在中国,医生以前的地位虽然不算高,但会觉得在治病救人中得到快乐,并没觉得受到屈辱。现在,完全就成了替罪羊。”
“中国医生的执业环境太糟了!”一位医生曾向《医学界》杂志痛陈,“医疗环境和医疗工作强度是我现在面临的最大困难,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撑下去,真的是在撑着,硬撑着,工作中没有乐趣。”
“医生在中国到底是什么地位?有没有发挥他们的所长?是不是能真正地人尽其能?”纪克宁觉得这些问题非常需要思考。
“很多现象特别能说明问题,比如SARS发生的时候,医生被称赞为‘白衣天使。包括汶川地震,医生也是奋不顾身地向前。但是,远离这些危险时,人们就反过来给医生挑错。各行各业都有出错的人,但对医生却是普遍挑错。可以说,医生的地位正在下降,这对中国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与高强度的工作节奏相比,医生们的回报明显偏低。《医学界》此前发起的一项6150名医生参与的调查显示,中国医务人员的工资收入非常不容乐观。“我得说句公道话,现在的付出和薪酬确实不成正比。”纪克宁说。
在中国,医生究竟该不该拿高薪,一直存有争议。《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叫做《医生子女为何不学医》的文章中提到,给医生高薪,也是想让他们脑子里只考虑看病,而不要考虑如何赚钱养家。事实上,让医生有尊严地拿到合理合法的高薪,表面上是增加了人力成本,实际上是变“以药养医”为“以技养医”,最终减少不合理的医药费用支出。
在纪克宁的记忆里,35年前随中国援外医疗队在马达加斯加的两年零八个月,是她作为医生幸福感最强、安全感最足的时光。
“马达加斯加是真正的全民医疗,所以就不会有不平衡的心理,医护关系非常好。在那里也真的得到了不一样的待遇,总统和夫人设家宴款待医疗队,卫生部长时不时就会来慰问一下。”
那种工作环境让纪克宁深深地感到患者对医生的信任。此后,每次出国,她发现在那些国家都是医生说了算,患者和家属会非常配合。医生没有杂念,没有烦扰,剩下的只是互相交流和学习。
对于医生当下的敏感处境,纪克宁说:“无论是私底下,还是会议上,大家并不交流这些事。对于医生们而言,明摆着的事,只能装不知道,装看不见,装麻木不仁。”纪克宁说,“事实上,现在很多医生都有一种屈辱感。”她强调。
“我理想中的医生,是面对病人可以只考虑他的病情需要怎么处理,怎么与病人做好沟通,然后全力以赴地救冶病人,而不是首先去想我怎样做才不会被骂,被打,被投诉,惹上官司。”一位医生这样说道。
如今已77岁的纪克宁面对当前的形势,觉得“退休”对自己来说是一场解放。她现在在北京生生医院及北京美兆健检中心坐诊,也经常到全国各地进行以女性不孕不育为主的会诊。
对于中国未来的医疗,纪克宁没有想过,也没有过多的期待。“我不是那种爱纸上谈兵的人,我是那种非常讲求实际的人。且行且珍惜。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我喜欢这样。”末了,她说,“我希望中国能够走自己的道路。”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