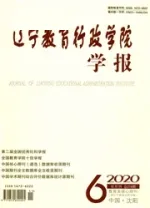《祝福》与《金锁记》叙述视角变迁——祥林嫂与曹七巧母性叙述视角之比较
张 衡
广西民族大学,广西 南宁 530006
鲁迅和张爱玲都是有着经久不衰的艺术生命力的作家。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到来,经历了辛亥革命的鲁迅,将自己置身于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之中,致力于整个民族的国民性的思考,试图用文艺救治愚弱的国民;而张爱玲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光辉影响下,把个体的人作为其文学创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去思考和言说现实。可以看出,无论是针对群体的人还是个体的人,鲁迅和张爱玲都把对“人性”的深度挖掘与演绎作为作家观照社会、展现特定时代文化语境的凝聚点。尤其是在表现封建婚姻制度和礼教制度之下的女性形象上,二人在对“人性”的体认上达成了一种批判意义上的共识。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从《祝福》中的祥林嫂和《金锁记》的中曹七巧这两位有不同生活境遇却在经历相同命运的母亲形象入手,来管窥母性叙事视角下的迥异的“母性”,进而发现母性叙事视角本身由“神性”到“人性”的演化与变迁过程。
一、深沉的母性与狠毒的母性
从祥林嫂和曹七巧身上,我们能感受到母爱的不同的表达方式。尽管二人都将孩子视为自己唯一的精神依靠,但是,一个是失去后的绝望,一个是绝望后的失去,呈现出两个女性迥异的母性品质。从鲁迅到张爱玲,母爱由单纯的爱子到有着复杂人性的虐子,体现出不同的描写母性的视角。
在《祝福》中,儿子阿毛的死,使祥林嫂唯一的希望破灭了,她变成了一个值得同情和怜悯的弱者。尽管有着凄惨的经历,但在鲁镇人们的心中,她仍是一个“再婚丧夫”的失节之妇,是不祥之物。她感到的是众人冰冷异样的目光,处于被孤立的状态而无所依凭。死去的阿毛成为祥林嫂精神生活中唯一可以维持她求生意志的灵丹妙药,“我真傻,真的……”她不断叨絮着阿毛被狼叼走的故事,希望能用阿毛的死、用自己的不幸能博得众人一丝的同情。但这种骨肉分离的痛苦却没能在众人面前得到丝毫的安慰,反而一次次地反刺到祥林嫂沉重的内心。鲁迅抓住了这一细节,在批判愚昧落后的封建迷信和伦理道德观念的同时,以沉重的笔调刻画了一位失去儿子的母亲的悲伤与绝望。虽然在《祝福》中并没有出现任何对祥林嫂母爱的褒扬之词,但正是在祥林嫂神经质地不断重复着“阿毛被狼叼走的故事”而被别人当成笑料的过程中,祥林嫂这一具有愚昧麻木的国民劣根性的女性形象,似乎并不应完全成为受批判对象;由母性视角来看,作为一个失去儿子的母亲,人们有理由从怜悯和尊重的立场客观地分析这一母亲形象。“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启蒙中逐渐走向人性的苏醒,而鲁迅在揭露丑陋的国民性的同时,似乎并未将所有黑暗面都覆盖其上。在祥林嫂身上,我们似乎看到了源自于女性内心深处最执着、最真挚的母爱。后来的研究者大多从批判国民性的角度分析祥林嫂这一女性形象,却看不到祥林嫂身上闪烁着的具有伟大爱子情怀的深沉母性。这一时期的其他代表作家如冰心、陈衡哲、苏雪林等人都在其作品中表达了他们对于母亲的赞美,母性成为五四时期“人性”启蒙的重要组成部分。
曹七巧继承了姜家父权式的教育方式,自觉成为父权制度的维护者与压制女性的代理者。她对于儿子长白和女儿长安使用不同的教育方式。对于女儿的未来,她严加干涉并强硬替其决断,完全是封建大家长对待子女的粗暴教育方式。在父权替身面前,在无法改变的命运面前,长安不挣扎不反抗地接受了母亲的摆布,逐渐变成了七巧的模样,在外人眼里长成了“活脱的一个七巧”。或许是处于对金钱的保护,或许是出于对女儿的嫉妒,曹七巧以牺牲女儿终身幸福为代价,以各种疑虑的心态不断干涉和破坏长安的恋爱与婚姻,泯灭了长安追求恋爱自由和婚姻自由的可能;相对于教育女儿时的严厉与刻板,曹七巧在对待儿子上却处处溺爱、放纵,纵容“长白在外面赌钱,捧女戏子”。直到长白“渐渐跟着他三叔姜季泽逛起窑子来”,曹七巧才慌了神,手忙脚乱地给儿子定了亲,娶了老婆。儿子的婚姻唤醒了曹七巧沉寂已久的被压抑的“性”意识。正如文中写到“这些年来她的生命里只有这一个男人……可是因为他是她的儿子,他这一个人还抵不了半个……现在,就连这半个人她也保留不住了——他娶了亲。”长期以来,儿子便是曹七巧性爱世界里唯一的精神情人。由于这种掺杂性爱成分的母爱,曹七巧对儿子长白怀有一种强烈的占有欲。儿媳的介入分享了儿子的部分情感空间,使得她在精神上产生了强烈的排他情绪。她津津有味地打探儿子与儿媳之间的闺房隐私,又肆无忌惮地向外人宣扬,活生生地将儿媳折磨致死。正是这种强烈的占有欲和排他性,使她毁坏了儿女的幸福,也葬送了自己的一生。
在封建的父权制度下,女性寻找自我和人格独立的尝试往往遭受到失败的厄运。祥林嫂丧子后的悲惨遭遇,曹七巧对儿媳的压迫,实际上是男权制束缚女性、维护男权秩序的制度延伸。在深深地悯惜祥林嫂和曹七巧这两位母亲之死的同时,我们必须做出理性的审视,过多的精神压力会使母亲逐渐丧失女性意识和原始母性,完全沦为父权主义的牺牲品或帮佣。
二、畸形社会下造就的相同悲剧命运
不得不说,对祥林嫂与曹七巧母性的异样表达是有深刻的社会原因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封建制度的沉闷呆滞习气笼罩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不断地吞噬着生活在这一时空下的每一个个体,每一个遭受不幸的人都是旧社会里深受压迫和剥削的劳动人民的缩影。祥林嫂就是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摧残下的牺牲者。正因为祥林嫂是封建礼教的忠实信徒,她自觉遵守和维护封建礼教加诸妇女身上的各种准则,所以才会在封建买卖婚姻制度下,在被卖去给卫家山的人做童养媳而失去人身自由和婚姻自由中走向了个体的毁灭。祥林嫂也试图反抗:她逃出婆婆家到鲁镇做工,在被婆婆绑回家时的嚎、骂,在拜天地时头撞香案……但这些反抗也只是表面的、暂时的,甚至只是象征性的。她本属被压迫、被凌虐的一群,但是她又习惯了被压迫的状态,很快就坦然接受各种安排,将社会的畸形看作命运对自己的惩罚。因此,可以说祥林嫂是封建宗法制度的受害者,是一名受尽残害但安分守己的未觉醒的劳动妇女形象。
相对于祥林嫂,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有一定的女性主体意识。曹七巧自幼生长在一个开着麻油店的普通小市民家里。在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下,她不仅有青春少女的活泼萌动,其暴躁泼辣的性格亦迥异于当时传统女性的温良沉默,这些都是我们难以从习惯逆来顺受的祥林嫂身上看到的。尽管如此,她依然难逃封建买卖婚姻的噩运。他的长兄曹大年为了钱把她卖给了残废但家境优渥的姜家二少爷。但是这个患有骨痨的丈夫无法给予曹七巧完整的爱,她时常因不满而在姜家大院里口无遮拦、大吵大闹。不完整的婚姻使她陷入无比的空虚和绝望中。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她拒绝了姜季泽的“爱情”,却将自己长期的性欲与情感期待推向了绝灭的边沿。欲望的无法满足与对金钱的渴望造就了她畸形的人格,她反过来成了欲望的压抑者和金钱的守护者。曹七巧代表的,是在性欲和物欲中沉沦的个体,她与祥林嫂是相同命运下的两种被扭曲的灵魂。祥林嫂是婚姻被包办、被买卖的产物,她无所谓性和爱,她的生活空间是封闭的、自足的小农经济。而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曹七巧已经有了独立的、鲜明的个性,她婚后生活的空间更多的是在“金锁”之中。但是,她们的命运有共同点:她们都是像商品一样被“卖”出去,自己没有选择权。她们都无力操控自己的婚姻,无论是祥林嫂的呆滞,还是曹七巧的多疑,其悲剧命运的起点都是残忍的封建包办婚姻。
三、母性叙述视角变迁的时代意义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在以文学呼唤人性解放的潮流中,在作家几乎不约而同地用彰扬女性解放来反叛父权主义的同时,更通过对纯朴的原始母性神话的颠覆叙说女性话语,赞扬的格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出现了对母性进行客观审视的作品,也出现了各种生活状态下丰富多样的母亲形象。在《祝福》中,鲁迅塑造了祥林嫂这个被封建礼教和麻木无情的社会共同摧残得失去了个体意识的母亲形象。祥林嫂完全被千百年来积淀下来的封建集权无意识地操控。在强大的社会机器面前,她无法抗争。但是在母亲这个身份的塑造上,祥林嫂仍然具有单纯而温暖的神性:母亲形象仍然是美好的,只是背负着无法摆脱的道德枷锁。
近20年之后创作的《金锁记》(1943年),其中的曹七巧这一母亲形象和祥林嫂相比有巨大的差异。鲁迅所关注的是封建礼教的“吃人”问题,虽然也是曹七巧不幸的根源,但是张爱玲显然更加重视物欲对人性的异化。在张爱玲笔下,母亲的神性被完全剥夺了,母性不再是神性,也不是德性,而是复杂人性的一部分,是文化心理塑造部分外化的结果。母性回到人间本位,母亲这一本体也成为被审视、被批判的对象。
这种对母亲形象的深入剖析,除了本文提到的《金锁记》中的曹七巧,还有《风景》(方方)中“一见男人便做少女状的”的母亲,《你是一条河》(池莉)中的辣辣以及《不谈爱情》中的梅莹等。这些母亲已经不仅仅是作为母爱的化身出现,她们有了自己的欲望,但又因为这种欲望始终是被禁锢的,最终呈现出女性怪异甚至是变态的生存面目。
张爱玲和鲁迅关注母性的角度存在差异,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是由于张爱玲作为女性其关注方向和鲁迅作为男性的思考方向之间存在的不一致。鲁迅是把国民性放置于封建大环境下进行整体性思考,祥林嫂是其“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后的代表,形成对于整个国民性的一种批判张力;而张爱玲则善于从个体、家族出发,展现个人情感与家庭生活的复杂性;另一方面是由于张爱玲身处沦陷区,而当时中国较发达的官僚资本主义和民间资本大都集中于此,这种经济制度对人性的异化更加吸引张爱玲的注意力。于是,她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揭示了在资本主义浪潮冲击下,人们对于金钱、物欲的追逐。而鲁迅则是集中刻画了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存在于农们身上愚昧、麻木、落后的劣根性。
从女性主义角度分析,鲁迅和张爱玲的创作存在两种话语趋向:一种是将母性上升至超伦理的个人化与审美化叙述对象,从而达到对伦理化主流话语的反叛;另一种是在社会伦理结构中以反向的话语方式来重新结构母性的伦理内涵,从而树立女性特有的价值标准。但是毫无疑问无论是哪种书写形式,五四时期的作家都要面对母性的历史书写与现实重写相悖逆的文化语境,而且母性自身的矛盾性与复杂性都必然导致重写的模糊性与歧义性,女性主义最终无法找到一种理想化的母亲形象来作为母性关怀的文学表述。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母性关怀作为一种性别叙述策略是成立的,但是在具体的文本实践中却只能是以被批判和被怀疑的面目出现,以母性关怀来作为一种文化拯救的策略也在人性的启蒙中遭受了遮蔽。
[1] 梁云.论鲁迅与张爱玲的文化关系[J].社会科学辑刊.1997(6).
[2] 西北大学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丛刊 [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
[3] 常彬.中国女性话语流变(1898—1949)[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4]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5]李乐平.为女性命运的呐喊——祥林嫂春宝娘悲剧形象之异同比较 [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5(3).
——曹七巧形象的另一种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