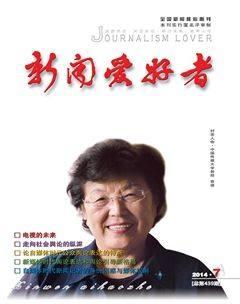人鬼情未了
李彬
在今人的印象里,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仿佛解放区明朗的天,听听当时的歌曲,也能感受到那种生机勃勃的时代气息:《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在希望的田野上》《青春啊青春》……当此时,文化领域更觉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春潮,使蓄积经年的精神活力喷涌而出,一泻千里。在蓬蓬勃勃的热潮下,新闻与文学形成相互冲击,彼此激荡之势。尤其是兼容新闻与文学的报告文学,在80年代一直广受青睐,以诗人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为开端,涌现出一批名家名作。解放军报记者钱钢的《唐山大地震》、中国体育报记者鲁光的《中国姑娘》、中国青年报记者麦天枢的《西部在移民》、光明日报记者理由的《李谷一与〈乡恋〉》、人民日报记者刘宾雁的《人妖之间》,以及作家赵瑜的《强国梦》、张正隆的《雪白血红》、黄济人的《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等,都如当年梁启超的报章文字“一纸风行,海内视听为之一耸”。
黄济人的《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起初就是1980年在《时代的报告》上连载的,而这份专门刊发报告文学的期刊,由时属公安部国际关系学院的新闻系系主任、军旅记者与报告文学家黄纲主编。王蒙评价这部作品是“用文学的方式更新了人们对历史的看法,参与了中国思想解放的大合唱”。2013年,《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原国民党将领大陆新生始末》(完全本)问世,将80年代的版本作为“上部”,将补充内容扩展为“下部”,再度引起关注。
现为重庆作家协会名誉主席的黄济人,属于十年“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代大学生,学生时代即完成这部蜚声海内外的纪实名作。如同当时诸多文学以及非虚构作品一样,《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也突破了一个敏感禁区,真切、细致、生动地讲述了国民党战犯的改造故事,揭开了一页曾经不为人知的历史内幕。黄济人是国军将领的后代,父辈与这些战犯或有密切交往,或有通家之好,故以得天独厚的条件接触到这个领域和题材,扉页书名的题字即出自杜聿明——淮海战役被俘的名将,毛泽东还曾留下一篇经典的广播稿《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1984年,连载的“将军”结集成书,在解放军出版社付梓时,这个题签还曾引起一点麻烦,按照当时的观念,解放军出版社岂能用一位国军将领的题字。
了解现代史,谙熟革命史,对书中各色人物及其背景当不陌生: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廖耀湘、郑庭笈、李仙洲、黄维、杨伯涛、陈长捷、杜建时、王陵基、王耀武、康泽、文强、沈醉、徐元举、罗历戎、张淦……至于杜聿明是杨振宁的岳丈,王耀武是大孝子,文强是文天祥的后人和毛泽东的姑表兄弟,廖耀湘、郑庭笈是远征军名将,宋希濂是处死瞿秋白的当事人,沈醉、徐元举是残害红岩烈士的元凶,黄维是痴迷永动机的“怪人”一类轶闻,更是流行。确实,他们各自连着波涌浪翻的历史,从北伐到剿共,从抗战到内战,惊涛裂岸,大浪淘沙。而自从他们战败被俘,一道铁门就此落下,外界对他们的情况便一无所知或所知甚少了,除了传闻在北京功德林监狱反省历史,接受改造,最后逐批获得特赦,成为共和国公民。《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初名《功德林》),就是通过他们从“战犯”到“公民”的复杂改造过程,让人真切领略了战场上的硝烟炮火虽然渐行渐远,但一场“灵魂深处的决战”同样跌宕起伏,扣人心弦。
作品的主人公是国民党被俘将领的群像,而推动故事情节的核心人物是邱行湘,国民党青年军整编二〇六师少将师长,在洛阳战役中战败被俘,其对手则为共和国“十大将”之一的陈赓。当年,由于看到黄埔同学黄剑夫忠厚老实,邱行湘将妹妹许配于他。平津战役期间,黄剑夫率部把守德胜门,后在四川阆中宣布起义,而他的次子正是黄济人。于是,不难理解,在“将军”一书里,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作者,便以舅父邱行湘的前世今生为叙事主线,穿针引线,勾连历史,旁逸横出,展现主题,通过采访所得的一手的、鲜活的、引人入胜的丰富细节,完成了一项本该新闻记者或历史学家承担的工作。
作品的内容是改造战犯,而主题是再造新人,这也体现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宏图伟略——既善于打破一个旧世界,也善于创造一个新世界,正如毛泽东1949年所言“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对此,作为1959年首批特赦的十名战犯之一,邱行湘多年后终于明白了陈赓的临别赠言,懂得了“解放”的含义:
如今我们解放了洛阳,解放了这里的人民,也解放了你。共产党的宗旨就是这样: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所以,我们要把你送到解放区,希望你在那里接受教育,认识过去,求得人民的谅解。[1]
不用说,对被俘将领来说,接受教育,认识过去,谈何容易。他们可都不是等闲之辈,内战中固然“有罪”,但北伐、抗战期间也曾“有功”。身为壮烈殉国的中国远征军戴安澜师长的长官,杜聿明在昆仑关上曾指挥击毙日寇旅团长中村正雄中将。更何况,他们的信念早已定型,甚至成为“花岗岩脑袋”,战败被俘后往往一副士可杀而不可辱的架势,若想让他们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也不亚于蜀道之难。淮海战役中全军覆没的“黄维兵团”司令官黄维,起初就一直拒绝认罪,以成王败寇的逻辑认定自己“最大的罪恶,就是把仗打败了”。1935年瞿秋白就义前,时为国民党三十六师师长的宋希濂曾与他有过一番思想交锋,也表明他们并非仅仅是一介赳赳武夫:
宋希濂:“我这次回来,从龙岩到长汀这一段数百里间,人烟稀少,田地荒芜,有不少房舍被毁坏了。我想以前不会是这样荒凉的。这是你们共产党人搞阶级斗争的结果。我是在农村里生长的,当了多年军人,走过许多地方,知道有五百亩以上的地主,在每一个县里,都是为数甚微。没收这样几个地主的土地,能解决什么问题?至于为数较多,有几十亩地的小地主,大多数是祖先几代辛勤劳动积蓄起来几个钱,才逐步购置一些田地,成为小地主的。他们的生活水平如果同大城市里的资本家比较起来,简直是天壤之别。向这样的一些小地主进行斗争,弄得他们家破人亡,未免太残酷了!因此我觉得孙中山先生说中国社会只有大贫小贫之分,阶级斗争不适合于我国国情,是很有道理的。”
瞿秋白:“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来的专制统治,这是对于国家的伟大贡献。但中山先生所搞的三民主义,把中外的学说都吸收一些,实际上是一个杂货摊,是一种不彻底的革命。中山先生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大城市里,对于中国的社会情形,尤其是农村的情况,并没有认真调查研究过。中国的土地,大部分都集中在地主富农手里,只有地区之间有程度的差别而已。我们共产党人革命的目的,是要消灭剥削。不管是大地主还是小地主,不管是大资本家还是小资本家——他们都属于剥削阶级——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有地主,就有被剥削的农民;有资本家,就有被剥削的工人,怎能说阶级斗争不适合于我们的国情?显然这种说法是错误的。”[1]102-104
经典歌剧《白毛女》,催人泪下地演绎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故事。《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的主题,展现了类似的历史逻辑与思想蕴含。即使骨鲠之士,正人君子,在一个鬼蜮世界,效命一个腐朽政权,身处魑魅魍魉之中,身心也难免妖魅出没,鬼气氤氲,更不用说数千年封建文化与近百年殖民买办文化对人心的奴役了。看看郭沫若在《女神》中的“上海印象”,也不难想象牛鬼蛇神的“民国范儿”:眼儿泪流/心中作呕/游闲的尸/淫嚣的肉/满目都是骷髅/满街都是灵柩……由此可见,对战犯而言,再造新人的过程也无异于把鬼变成人,必然充满戏剧性的矛盾冲突与精神痛苦。当然,战犯不都是康泽、沈醉似的杀人魔鬼,而不乏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之士。尤其是邱行湘所属的“青年军”,更不同于一般国军,他们多为抗战中应征入伍的“学生兵”,在“一寸江山一滴血,十万青年十万兵”的感召下,投笔从戎,奔赴国难,包括西南联大学生、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的公子。这样的部队有文化、有知识、有思想,自然不同于绳捆索绑押赴前线、稀里糊涂投入战场的壮丁。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将他们编成“青年军”,作为蒋家王朝的御林军,用于生死存亡关头,如邱行湘“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指挥“青年军”二〇六师固守洛阳。而二〇六师的“政委”——政工少将处长赖钟声,还是杨振宁西南联大的同班同学。书里有这样一处闲笔,杨振宁回国后,想方设法联系他,希望见上一面:
赖钟声左思右想,结果拒绝了杨振宁。拒绝的理由有两点:其一是自惭形秽,有可能杨振宁看不起自己;其二是孤芳自赏,自己有可能看不起杨振宁。前者不言而喻,后者需要解释,赖钟声在信中这样告诉邱行湘:“此生最大的慰藉,便是国难当头,日寇猖獗之时,我能够挺身而出,愿以血肉之躯,报效国家。以后卷入内战,为蒋家王朝卖命,实为身不由己。而在相同的时刻,杨振宁选择了出国,虽不算逃兵,至少也算懦夫,懦夫是叫人看不起的!”[1]394
由此说来,让这样一批“诚既勇兮又以武”的将帅,心悦诚服正视历史,放下包袱重新做人,岂不更甚于再打一场淮海战役或洛阳战役——“人民解放战争中,夺取大城市的第一次硬仗”(毛泽东)。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啊!“将军”一书,情节曲折生动,故事引人入胜,笔法灵动,叙事鲜活,而令人感触最深的还是中国共产党人壮志凌云的一腔豪情。他们坚信自己既能解放全中国,也能改造旧世界,包括改造旧军人、旧官僚、大特务、侵华日军、末代皇帝等;既能从头收拾旧山河,也能攻心为上收拾世道人心;既能席卷自然的版图,也能攻取人心的领地。这种自信不仅仅来自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实力,更是源于一种高远壮美的理想,也就是北京大学政治学教授强世功概括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际主义和‘天下大同(人人平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构成三位一体。”[2]换言之,共产党、新中国的抱负不在于改朝换代,更不在于冤冤相报,而在于建设一个新的、风清气正的社会,没有剥削,没有压迫,自由平等,公平正义,就像一位新中国开国将领给女儿的信里诗情洋溢写到的:“让爸爸们,把新民主的地基铲得平平的,让你们后一代,能够在我们的国土上建筑起一座自由、快乐、文明、进步、庄严、华丽的世界。”显然,这是一桩前无古人的伟业,也是一项艰难复杂的工程。仅看功德林的故事,就知道共产党人的旷古雄心,也知道再造新人的复杂艰难。
那么,这批或血债累累或声名赫赫的国民党战犯,最终如何完成由鬼到人的蜕变,内心的鬼气又是如何一点点驱散的呢?黄济人采访了父执辈的诸位将领,用大量生动有力的事实,揭示了一个简单无敌的武器——真理。他们不怕死亡,但怕真理。诚所谓全世界的黑暗,也无法掩盖一支蜡烛的光芒。正是真理之光,照亮了他们的内心,驱散了身心的憧憧鬼影。1936年,坦然走上刑场的瞿秋白,曾给监刑的国民党“鹰犬将军”宋希濂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象,也成为后来促使他走上新生之路的思想契机:
上午9点,国民党三十六师警卫连长将这位共产党人从牢房押出,宋希濂和司令部一百多个军官都站在台阶上,目送瞿秋白缓缓离去,直到附近的中山公园。宋希濂没有想到,这位身体单薄、面部清瘦的中年人在死神面前竟能如此神态自若,更没有想到,行刑前的十五分钟,面对警卫连三十多个官兵,瞿秋白竟能这样继续着前几天与宋希濂的话题:“我知道,你们都是农民抑或工人的儿子,因为吃粮当兵,地主、资本家的后人用不着这样做。可是,我得告诉你们,你们父母被剥削的是血汗,你们自己被压榨的是生命,让你们永世不得翻身的是代表大地主大资本家利益的国民党反动统治。”
昔时,宋希濂佩服瞿秋白的人格,却并不赞同他的观点;而今,当这位共产党人的理想已变成现实的时候,宋希濂不得不冷静下来,对自己的信仰进行反省。[1]318
中共高级“卧底”赵炜,颇似电视剧《潜伏》中的余则成。1940年,他毕业于黄埔军校,毕业典礼上还见到蒋介石,得到“中正佩剑”,后在第五战区绥靖组效力,而绥靖组实为特务组织。当时,他们缴获了很多进步书刊,包括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等。闲着无聊时,赵炜也随便翻翻这些文字。结果,看着看着,他的人生观就开始发生转变,寄希望于中共了。杜聿明掌管国民党东北军政时期,赵炜已经成为中共中央安插在国民党军东北司令部的一张王牌,送出颇有价值的情报,为解放战争做出历史性贡献(见《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9期《一道假命令改变东北战局》)。与此相似,在功德林,除了廖耀湘一字不落背诵《哥达纲领批判》等特例,听听国民党第四十一军中将军长胡临聪在一次学习讨论会上的报告《我对自由与民主的体会》,也同样可以看到驱除黑暗的真理之光如何在他们的心灵深处闪耀,而且“即令是纸上谈兵,也显示出战略地带的开阔”:
第一,民主与自由服从阶级利益:民主与自由是有阶级性的,民主与自由只有具体的没有抽象的。资产阶级民主与自由的口号在18世纪起过骗人的作用,直到《共产党宣言》问世,才将它揭穿。第二,民主与自由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在英国第一次出现议会,就是资产阶级派代表监督英王对金钞如何用法。民主与自由不可能离开经济基础,资本主义的民主与自由是为私有制服务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与自由是为发展公有制服务的……[1]166
共产主义真,党是引路人。而所谓“真”,既体现为人间正道的真理,又体现为实事求是的道理。一次,杜聿明写自传,没有写他的抗战胜绩,主管人员让他加进去,说昆仑关战役加淮海战役才叫杜聿明,杜聿明感慨道:“我是今天才被俘虏的!”而黄维后来发自肺腑的朴素言语,更是实实在在的道理,也道出了大家的心声:“旧社会不讲生产,不搞建设,国民党把大量的物力人力用于内战,用于巩固政权。共产党掌权以后,虽然也有内部斗争,但是头等大事是老百姓的穿衣吃饭,是发展国民经济而非发展官僚经济。由此发生的巨变我们有目共睹,我一个人也不可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呀!”[1]396光明正大的真理与天翻地覆的变化,不仅一点点化开了他们的板结心田,而且还使流落天涯、名列蒋介石之后的“二号战犯”李宗仁,也禁不住冲破重重险阻,辗转万里,于1965年回到了祖国大陆。
书中着墨颇多的军统头子沈醉,即《红岩》里严醉的原型,更细腻地展现了一个由人变鬼、由鬼变人的典型,蕴含了意味深长的道理。沈醉的母亲罗裙是南社诗人,她认为传诵千古的诗词,首推李清照的《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这里“沉”与“沈”相通,于是,她为自己心爱的儿子取名“沈醉”:
沈醉的母亲这样对自己的儿子说过:“一个人可以不做官,但是要做人。”沈醉并不是生下来就要做鬼的——我们没有理由否认:他也曾偶然良心发现,在力图做人。
江竹筠。沈醉称之为“女中豪杰”。当年在中美合作所最西端的渣滓洞看守所里,沈醉和徐元举一起审讯过这位共产党川东地下工作者。江竹筠被带进审讯室的时候,虽然披头散发,却是神态自若。她昂起头,侧身对着壁头上的窗口。徐元举勃然大怒:“你傲慢什么!今天不说,我当场扒掉你的衣裤!”江竹筠慢慢回过头,望着徐元举冷笑道:“我连死都不怕!”沈醉正欲说话,江竹筠上前走了一步,涨红着脸颊,以不可遏制的愤懑,指着徐元举说:“我告诉你,你侮辱的不是我一个女性,侮辱的是我们民族女性的全体,其中包括你的母亲和你的姊妹!”江竹筠的声音缓慢、低沉,但却像闪电一样轰击了沈醉,他条件反射似的垂下了头。就在徐元举果然唤进打手的时候,沈醉在桌子下面踢了他一脚……
国民党战犯大集中前,《红岩》的作者罗广斌就审讯江竹筠一事在重庆白公馆采访了沈醉。说来奇怪,沈醉宁肯把自己建议将十根竹签打进江竹筠手指的暴行告诉对方,也不愿披露徐元举下令“当场扒掉衣裤”的细节。[1]173-174
长江上游的巴山蜀水、中游的洞庭鄱阳、下游的江浙苏杭一线,自来云蒸霞蔚,才人荟萃,黄济人也属此类。“将军”一书,谋篇布局,匠心独运,叙事遣词,活跃跳荡,仿佛快速切换的电影镜头,令人目不暇接,欲罢不能。其中特别有趣的一点,是“下部”每节的结尾与下节的开篇,都用同一词语或词组过渡衔接,环环相扣,好似行云流水的音乐旋律。这一“音乐”笔法让人想起米兰·昆德拉的小说,如《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感觉气韵悠长,一气呵成,与灌注全书天新地新的气息一脉相通。不过,黄济人当初曾是一位“小愤青”,由于受“国民党将领”牵连,“文化大革命”中命运坎坷,更觉气息难平,不免满腹怨恨。1978年,当第一次见到舅父邱行湘时,他忍不住大发牢骚,冷嘲热讽。不料,邱行湘一番拍案怒斥,始则令他不解,终则成就了他的“将军”之作:
出乎黄济人的意料之外,舅父哭着哭着,突然一巴掌拍在饭桌上:“你以为我在哭你的父亲么?不是的!自从离开你父亲的坟头,我就不想他了。我现在哭的是你,是你这个不懂事的毛孩子!你懂什么?你什么都不懂。你不懂国民党,所以你不懂共产党;你不懂蒋介石,所以你不懂毛主席。不懂可以问呀,可以看呀,我邱行湘有今天,你父亲有今天,我们全家有今天,这都是看得见的事实呀!”黄济人的眼睛怔愣得大大的,不过瞬间便眯成一条缝,那上翘的嘴角,挂着挑衅般的讪笑:“舅舅,这里没有外人,连窗户也是关紧了的,你不必装腔作势。不晓得的人听了你的宏言谠论,还以为你是共产党高官,可是你不就是一个国民党战犯嘛!”
邱行湘气得脸色铁青,牙齿咬得咯咯作响……[1]402-403
这一场不欢而散的家宴,对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青年黄济人触动很大,使他开始冷静深思,最终不仅“改变了题材,也改变了体裁,他想把国民党将军从战犯到公民的改造历程记录下来,而且只有这样,他才能读懂别人,诠释自己”[1]403。如果说30多年前采写“将军”上部时,他还更多地在探究再造新人的历史过程,那么如今在下部里,已经读史阅世数十年的黄济人,对前辈的心路历程则有了更深的理解与体悟。如果说邱行湘最终是被共产党的真理击败的,那么黄济人也是被邱行湘的新生折服的。从下面一段动情文字里,不难窥见这一点:
怀揣着特赦证,拥有了公民权,邱行湘就这样走出了人生阴影,看见了生活的阳光。七天后的那个下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了十一位获赦人员,除了来自抚顺战犯管理所的那位三十五年前的清末皇帝,便是来自北京战犯管理所的这十位十年前的国民党将军了。周恩来慈眉善目地望着大家,语重心长地讲完事后被获赦人员称为“四训”的爱国主义观点、阶级观点、群众观点以及劳动观点后,便和颜悦色地逐一问起他们的志向来。
爱新觉罗·溥仪说,他想在植物园当园丁,因为他对果树嫁接颇感兴趣;杜聿明说,他想当木匠,功德林的好些桌椅都是他维修的;杨伯涛说,他想当农民,从小在农村长大,犁田插秧收谷割麦,样样在行;邱行湘说,他想当工人,最好是搬运工,肩宽体壮,有使不完的力气……
周恩来笑了:“你们的志向都很好,从自身的情况出发,非常实际。不过,我还有一个更加实际的想法,那就是你们都是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你们有义务也有责任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要知道,历史并不是胜利者写的,更不是歌功颂德、树碑立传。历史是一面镜子,它由正面和背面组成,没有正面就没有背面,反过来,没有背面也就没有正面。这,我想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这是邱行湘在记录这段讲话时所作的眉批。共产党人的胸襟,让他心悦诚服,共产党人的高远,让他感佩不已……[1]283-284
读着这些“人鬼情未了”的故事,不由想起电影《末路》(2010)。这部差不多属于80后导演执导的影片,取材于大陆最后一位落网的国民党将领郑蕴侠的逃亡经历,是一部真实、紧张、充满悬念的佳构。郑蕴侠原为中统重庆地区最高负责人,曾经经历了台儿庄战役中艰苦卓绝的滕县保卫战、国共重庆谈判等重大事件,也曾一手制造了重庆校场口血案、捣毁《新华日报》等暴行。解放后,侥幸逃脱,如丧家之犬东躲西藏,一天到晚心惊肉跳,直至1957年落入法网,在校场口血案发生地重庆受到公审,先被判处死刑,后改为15年有期徒刑。影片就是根据他口述的经历改编的。片中的郑蕴侠,本是一位怀抱理想的热血青年,大学毕业后热望为国家建设服务,不料稀里糊涂落入中统魔窟,一步步沦为冷血动物,抓捕进步学生,迫害民主人士,凶神恶煞,无恶不作。入狱后,经过教育改造,他反省了自己的前半生,晚年以政协委员身份为两岸的和平统一尽心竭力。影片末尾的一段道白尤为感人。2009年6月23日,年届102岁的郑蕴侠老人,在摄像机前用四川方言,亦吟亦咏地絮谈自己的一生及新生,而说完这番话后不久即离别人世: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亲人半零落,逝者长已矣。人生自古,相聚少,离别多,存者休戚说,提起来泪满江湖,来表达中共给我的再生啊!我对共产党的深恩厚德没有忘记……
黄济人:《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原国民党将领大陆新生始末》(完全本),中国青年出版社/重庆出版社,2013;溥仪:《我的前半生》(全本),群众出版社,2007;沈醉:《沈醉回忆录:我的特务生涯》,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
参考文献:
[1]黄济人.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原国民党将领大陆新生始末(完全本)[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重庆:重庆出版社,2013:282-283.
[2]强世功.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M].北京:三联书店,2010:104.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编校:郑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