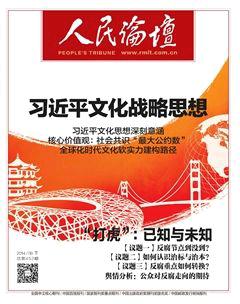存在与时间
一
近些年来,不知不觉,参加葬礼的时候多了。
一代人又正在离去,不是一个或几个,而是一代,是一批,是一批人的思想情感以及故事和生活。
随着参加葬礼的渐多,我也强烈地感觉到:死亡并不代表结束。人们所送别的人们正去新的地方生活。他们虽然已经离去,却又似乎仍在身边,还在关注此地的亲朋,还在指点他们继续走完此地要走的人生。
离去了的是他们的肉体,留下来的是他们的心。
天上一颗星,地下一个人。我记得在八岁的时候,乡下的大舅病入膏肓。大舅死的那天晚上,我在屋外仰望夜空,确有一颗星子落下。那星,那么倏忽一闪,随即灭了,只剩划痕,就像大舅闭上的眼睛。
外婆到死都极坚信,如果一个生命没了,另外一个新的生命就会在新的地方诞生。新的生命比逝去的一定更加坚强漂亮。外婆相信一个人只要有人记住,有人懂得理解他,那他不管遇到什么,只要他曾在世活过,他就不会完全逝去。
外婆说的,当然不错。问题是在这个世上,谁又能够记得住你?你又能够记得住谁?对于父母,对于儿女,对于你最好的朋友,你当然是记得的了,他们对你也是一样,你存在于他们之中,存在于他们的生活之中,存在于他们的心目之中。对于他人,就不同了,你就可说不存在了,你是死去,还是活着,都无关乎他人的痛痒,他人于你也是一样,是死,是活,你也不想,你要想也无法去想(当然,我这是就一般而言,特殊的情况应该除外,比如某位英雄的逝世,或者某个罪人的下场,均不在我所说的范围)。
事情不是这样的吗?事情就是这样的。
二
我老了。
越老,我就越问自己:“你了解你自己吗?清楚自己是谁吗?”
每当这样问着自己,同时我也警告自己:“你这是中了希腊哲学的剧毒了!”
希腊哲学总是问:你是谁?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我曾看过一本书,是写花豹和羚羊的,它们从不反省自己,对自己也一无所知,所以也就过得幸福。
我应该向它们学习,以使自己过得幸福。
这样想了,就轻松了,有关自己是谁的问题,也能坦然回答了:
“一个人是谁重要吗?”
“重要的是这个人曾经做过什么事,还将要做什么事!”
我曾做过什么事呢?有好事也有坏事。有时是好心办好事,有时是好心办坏事。我总怀着一颗好心。我可不像有些人,总是怀着一颗坏心,做好事也怀着坏心。我是这样看自己的。
我还将做什么事呢?我还能像有些人那样老有所为吗?人能学成一样的吗?人能置换彼此吗?这样想着,我一定睛,又清晰地看到自己,又中希腊哲学的毒了。
我还是要向花豹学习,要向受花豹威胁的或被花豹吃了的那些懵懂的羚羊学习,那样——我就能平静了,就能过得幸福了。
这样想着,抬起头来,我又看见那轮落日,斜晖脉脉,染红窗台。
我又想起了那句古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三
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常常梦见自己躺在一个巨大的死人坑里,所有的灵魂都在骚动,都在叫我快快尖叫。于是,我就拼命尖叫,结果一声也没叫出。
现在,我已长大了,变老了,还是照旧,害怕做梦,因为我知道即使尖叫仍没能力叫出一声,我必辜负那些灵魂,那些活在我血中的长满古老青苔的灵魂。
我碰见的大多数人都是低着头颅的。每天早上,每天晚上,我都碰见这些人。他们走路总弯着背,像在灰里寻找意义。他们若是对我说话,我就觉得自己成了很久以前的一具僵尸。
我想自己若不说话,天空真的会塌下来,但我若是开口说话,他们又都笑我忧天。我盼自己能变成树,能够长成擎天之柱。有时,我真觉得天空距离我的头顶很近,就像我的头发一样紧紧贴着我的脑袋。
这个不声不响的天空不时总会吓我一跳。沉默比那成吨的钢铁更能将人压成肉酱。有些时候,我在梦中能够听见自己的心跳,但这真的只是有时,更多时候,我听到的是那战鼓一样成千上万的咚咚心跳。这些心跳都要比我早活几百或几千年。这些心跳总是使我要冷的血重又沸腾。
四
那些打铁的日子里,我常坐在炉膛口上。炉膛里的熊熊火焰,烤着我的黧黑的面庞,让我感到自己这堆由椎骨所支撑的皮肉,由脖颈和头部相连、四肢对称配置的躯干,竟也能够接受产生一些与众不同的思想,或者说是某种精神。这种精神驱动着我运用自己的眼睛观察,展开自己的动作探索。这种精神使我知道无论自己多么能干,也会因为时间有限而不可能走得更远。假如真的给我时间,我会不惜自己的力量,就像此刻,我存在着,我也就在行动着。我知道,这力量,还常使我左顾右盼,主意不定,甚至使我错误判断世界已经给我的教训。我羡慕有些人,那些学识更多的人。当然,同时,我也知道,他们也跟我一样,也会失误和犯错,也必须从错误之中学会如何才能正确。我从来都没有因为缺乏某种观念而深陷入惶恐之中,我也不会固执于某种植根于脑的观念。我从来都不曾在真实的食物之中掺入谎言的添加剂,以使食物更新鲜,以便自己好消化。我是梦想过,我喜欢梦想,梦想着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我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把自己的梦想当成梦想以外的东西。我时刻都告诫自己莫把真理当成偶像。我宁肯让真理直到不是真理时仍然能够保持着它这朴实准确的名字。我经历过的成功危险并非他人说的那样,但若要我说,我又懒得说。我知道我死的时候不会像我出生的时候,那样纯洁,那么傻。
五
过去的人,过去的事,总是浮在我的眼前,被我看得凋萎得成了灰白的老话旧话。
以前读过一篇文章,写的是在南美的一个印第安人的部落所持有的时间观念。他们往前看见过去,依靠后背感知未来。据文章的作者介绍,这种体验时间的方式至今还能在他们的语法结构里面找到。发现这种现象的是个细心的语言学家。经过研究,他揭示了这种惊人的方向颠倒。endprint
这有什么惊人的呢?我倒真不这样看。我倒觉得他们这种颠倒了的时间观念才是符合自然的。过去,你能看得见,当然就在你前面,一般来说,你的眼睛也是看着前面的。而未来,你不知,欲知也只能感知,当然就在后面了,后面没眼睛,感知只能靠后背,也是非常自然的。
过去成了老话旧话,谁都不会再有兴趣,未来总是无比新鲜,要人不想都不可能。
而我作为一个老人,眼前满是过去的老人,每天带着过去醒来,拽着过去走来走去,多少难免有点沮丧,就是非常自然的了。
我还会有未来吗?我的未来什么样呢?有时,我也闭上眼睛,感知一下我的未来。
我的未来在我身后,无比温柔,紧贴着我。
她的胸部非常柔软,她的腹部也很柔软,她的大腿也很柔软。
她的双臂紧搂着我,将我身子转了过来,她也跟着转了过去,然后,带我往后退去。
我想看看她,却又看不见,始终看不见。
我想能够停在原地,却又觉得身不由己,只能随她向后退去,离开眼前所心爱的,去那不想去的地方。
我的眼前,仍是过去,仍是飘来飘去的过去。
这些过去都看着我,恋恋不舍,看我离去。
六
我儿时玩耍的地方如今已经不存在了。
那个山坡,那棵大树,那道小坎,那条老街,即使十年二十年前人们心目中的地标,也有很多突然消失,就像从未有过一般。
每当路过这些地方,看着焕然一新的一切,我就觉得自己也在渐渐消失变成幽灵,面对时间,口呆目惊:那个孩子哪里去了?那个孩子早消失了。女大十八变,男大就不变?男大也在变,不知多少变,变得再也不像自己,变得再也不是自己,变得遇见儿时的朋友也不相识、目光迷离。
没有什么是永远的。
再好再美也会消失,再丑再坏也会消失。
能回顾的只有废墟,只有废墟中的遗骨,只有废墟中的遗物,有的甚至无迹可寻。
有时,我在街上走着,越走越是觉得孤单,跟在身后的流浪狗们也咆哮得令我胆寒。
每当这时,我就觉得再新的大楼也在褪色,平坦宽敞的沥青路面也在皲裂长出草来。
“这里的一切多么过时!不是陈旧,不是古老,不是样式,而是过时!”我又想起布罗茨基,想起这位俄罗斯的美国诗人随着同伴走在伊斯坦布尔的曲里拐弯的街头巷尾说着这话的那个样子。
那是个什么样子呢?一副永不过时的样子。
虽然,样子只是样子。
七
像猫一样小心地伸了一下手,床头灯就灭了。
寂静跟着变黑了,只有窗户上有光渗进来,很细小,极微弱。
我看不到家具了。它们摆脱了我的视线,静静地进入了自己的世界。但我心里很明白,它们还在那,还在这屋里,还是那样一动不动呆在原来的那个地方。
座钟嘀嗒着,计算着时间,耐心又执著。
我也静卧着,等待着睡意,但我心里更明白这等待的结果终归还是白等。
小的时候,我觉得每天晚上都钻进这条毫无意义的床单和这愚蠢至极的被窝真的就是浪费时间。到后来,长大了,自然也就认识到人能躺在被窝里(特别是与心爱的人)那就真是一种幸福。现在,老了,我又觉得这般毫无睡意地躺在这个被窝里简直就是度日如年。
你是否能想象一下如果我们不用睡觉我们会多出多少时间?我们在这些时间里会做一些什么事情?我对自己说,对自己所想象的无所不知的那个人说。
小时候,我会说:那就可以玩个饱啦!
现在的我只会想:如何打发这些时间才会多少有点意思。
八
我看到了一些什么?我正走在一条街上。
前面稍远处有两男两女正在朝我慢慢走来。对面的那条人行道上有一个老妪牵着一条狗正在无所事事地散步。咔嚓,我拍了一张照片,流行语说是在“扫街”。街上有多少活着的生物?彼此的距离又有多远?我之所以会这样想又是受了书的影响。那本书叫什么名字,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但那书里曾经这样向人提出这个问题。
很显然,是六个。不,不,不,应该说一共九个才算对。我还看到一棵树上有三只鸟正蹦跳着(砰的一枪,打掉一只,还有几只?父亲曾经这样问我)。
两男两女在走着,离我越来越近了,多少米?
老妪的那条狗正在蹦蹦跳跳地越蹦越远越跳越远,多少米?
鸟儿也在树上蹦跳,它们又相距多少米?
我目测着,估计着,说不准。
其实,若是讲事实,我根本就没有看到这条街上正拥挤着数十亿个活着的生物,其中只有五个是人,一条是狗,除了树上的三只鸟,还有很多很多的鸟正暗暗地坐在树上,躲在密密的枝叶之间。还有那树也是生物,树叶树皮树根里面还有数不尽的昆虫。鸟的毛里也有小虫。狗的毛里也有小虫。我自己的皮肤上,我自己的毛孔里,也有无数无数的细菌,爬动着,拥挤着。还有无数无数的病毒随风飘荡在空气之中,形成一张有机的网。这些生物彼此之间所有的距离等于零。
我看得到这些吗?我根本就看不到。
九
小的时候,我病过,但它没有使得我改变看待世界的态度。
青年时候,我病过,它也没有改变我看待人事的态度。
中年时候,我病过,这次它却使得我看世界看人事多多少少有了些变化。
老年了,我再病,每病一次,对世界,对人生,对事情,都会有些不同的看法,总的来说,是越来越淡,感觉一切不过如此。
天大的事,不过如此。
地大的事,不过如此。
无论何人,不过如此。
人说:好时光还会回来的(人生再糟糕也有好时光)。
我问:是吗?
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过这么一句话(或许这话不是我的,而是某人某本书留在我的脑壳里的):
好时光,对于人,一生只会有一次,所剩下的只有回忆,回忆那段好的时光。
十
关于时间,我的耳旁响起的是这句话:“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跟着,我的脑壳里浮现的是这幅画:孔子立在一条河边,看着那条河水发呆,看了好久,忽感叹道:时间的流逝就是这样吧?倘若真的就是那样,时间确如河水流逝,如何测量也是问题,因为河的流淌速度每时每刻并不一样。有时,河会流得极快;有时,河又淌得很慢。为了能够被人测量,河须流速均匀才行。你说河能做得到吗?河当然是做不到的。我的心里非常明白,但我就是爱瞎琢磨。虽然我的这种琢磨,无法写出《时间简史》,也就只是琢磨而已。然而,就在前不久,我去旅游了一次,时间也就两个星期,我却觉得对于时间突然有了新的认识。什么认识呢?说来也简单,那就是我突然觉得旅游时的新鲜有趣居然能使时间变长,当我回家再回顾时,我竟觉得那些场景仿佛已是很久以前同时却又如在目前。而先前,对时间,我不这样认识的。先前,我总以为新鲜能够驱逐时间快跑,也就是使时间变短,让人感觉“转瞬即逝”。反之,陈旧则会使人时刻感到“度日如年”,觉得时间长而无聊。现在看来,并非尽然。陈旧的生活,习惯的生活,周而复始,一成不变,实际是使时间萎缩,时间再长也是短促,稍不注意,便已逝去。如果天天都是一样,一天也就等于天天,天天也就只是一天,习惯会使时间入眠。年轻时你觉得日子过得慢而且很难捱,年纪越大你越觉得日子过得就像一晃,都是习惯惰性使然。长期而有规律的生活会使你的肌体松弛会让你的精神迟钝。你一定要更新生活,不管你以何种方式,用你自己喜欢的方式,才能保有敏锐触角,才能继续生机勃勃,日子才会变得年轻,时间才会长而有力。否则,你的时间意识会因年事高而疲惫,疲惫的它,容易入睡。入睡的你,只会觉得自己从未离开过家,旅游于你也不过是夜里的一个小梦而已。
周实,作家,现居长沙。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性比天高》、长篇随笔《无法安宁》等。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