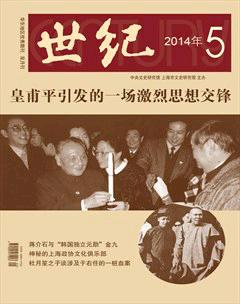我所知道的[龙潭后三杰] 及其他
张林岚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共历史上出现过许多深入龙潭虎穴,在敌方卧底的情报人员,被周恩来誉为“龙潭三杰”的钱壮飞、胡底、李克农,是出色的一批;潜伏在反共前沿“西北王”胡宗南身旁十余年之久的陈忠经、熊向晖、申健是“龙潭后三杰”。由于他们的工作,保卫了党中央、毛主席。毛、周等领导人两次演出“空城计”①挫败了蒋介石的内战阴谋,最后摧毁了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了全中国。毛主席表扬他们,说你们保卫了党,一个人抵得几个师。
笔者曾是新闻记者,现在是旧闻记者,虽然没有赶上前三杰的岁月,但与“后三杰”相识,那些年曾在西安朝夕相处,成为朋友。本文所记是我亲闻亲见的一些与他们有关的故事。
一、卧底胡宗南帐下
我于抗日战争开始从事救亡运动,并参加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为它的一名小干部。1939年秋天,因为难以在浙东家乡立足,跋涉万里,到达西安。已是岁末,很想经八路军办事处转赴延安,没有成功。原因是陕甘宁边区已被胡宗南的几十万军队封锁,凡是有意北上“投共”的知识青年和进步人士,一经查获立即投入集中营或关入黑牢,受尽折磨,迫害致死的不计其数。
也真是祸福无常,黑暗深处,忽见爝火在前:我的一位四川籍难友李恭贻,获释不久,正在奉命筹备一张名为《青年日报》的三青团机关报。由于李恭贻的援引,我开始进入新闻界,做了这家报纸的记者。这年我刚二十岁。
李恭贻是四川自流井人,出身小盐商家庭,北京大学经济系学生,参加过“一二·九”运动,也是民先队员,后经同学陈忠经介绍入党。抗战开始,北平和华东各大中学校师生纷纷南下,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湖南长沙设立临时大学,招辑流亡,得二三百人。在敌人飞机日夜空袭轰炸、兵荒马乱中,草草复课。1937年12月13日南京弃守,日军屠城,灭绝人性的残杀我国军民三十万人。消息传来,长沙和各地学生、民众痛心疾首,悲愤填膺,纷纷罢课、罢工、罢市,要求上前线杀敌,为死难同胞复仇雪恨。临大学生听说从南京撤退出来的中央医院一部分青年医生护士正在与当地湘雅医院的医护人员一起组织战地服务,经清华大学同学郭健恩(后更名郭建,中共党员)和湖南著名女作家谢冰莹介绍,双方合作,组建战地服务团。开始时有近百人,但有些人因家累、体弱或随校迁往昆明,继续就读西南联大而退出。
1937年、1938年的爱国青年“从军热”分流三股:一股经武汉去了陕北,入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和鲁迅艺术文学院(包括去八路军的学兵队);一股去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和阎锡山的部队,参加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和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一股参加中央军的正规部队,或考入中央各军事性的短期训练机关和军校,受训后去前线部队。临大这批人推清华学生洪绥曾(后改名洪同)为代表,与中央医院护士长李芳兰商量后,决定去新从淞沪会战前线撤至长沙休整补充的第一师胡宗南部。因为他们听说胡在“八一三”抗战中作战骁勇,屡立战功,已由第一师师长升为第一军军长。胡是黄埔第一期毕业生中最受蒋介石器重的学生,一般人都认为“前程远大,未可限量”。胡宗南见有如此一批男女青年前来帐下效力,十分高兴,与他们见面,一一谈话。他说:“你们都是将来的国家栋梁之材,今天暂时不要匆忙上前线,还要锻炼锻炼,再派你们大用处。”根据胡宗南的意见,“战地”两字改为“随军”,服务团从此随他的部队南征北战,哪里需要到哪里去。服务团员工编制三十余人,由李、洪两人任正副团长。
不久,胡部开拔,直奔西北。一部分驻守黄河的风陵渡、潼关一线,防御日寇。一部分赴宁夏、甘肃、陕北,以“邠洛区”、“商同区”两个“民众动员指挥部”的名义,构成绵亘千里两道封锁线,包围陕甘宁边区。
服务团的大学生们大多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思想比较激进,甚至有共产党员,胡宗南不是不知道,但他有自己的一套政治哲学:青年左倾比右倾好。左的往往胸怀大志,有革命性,有作为。“只要对我忠实,为我所用,我就要用他,重用他们;我怕什么!”他不喜欢点头哈腰,逢迎拍马,蝇营狗苟,只想升官发财的人。他自己也很能吃苦耐劳,身先士卒,作风朴素;这一点名记者范长江写的《中国西北角》、《塞上行》中也有所记述。
胡宗南的部队布防周密后,由平凉、天水、凤翔而西安,最后以西安为总司令部。这时他已由第一军军长晋升为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随后,蒋介石再一次表示荣宠,给他加了第十战区副司令官的官衔(长官是老一辈的蒋鼎文、朱绍良)。随着军事形势的变化,他又改任第八、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节制西北五省军事,兼任军委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蒋介石兼校长的中央军官学校,胡是第七分校主任,统一培训政治工作的战时干部训练团第四团(以下简称战干四团)也是老蒋自任团长、由胡主持,最后训练干部有数万人。
我与“三杰”、李恭贻等人都曾在这个“战干四团”受训。此团的前身是军校七分校的政治大队(或各政干部训练班),后因无所不训,日益扩大,而独立设于张学良办的东北大学原址,即今之西北大学所在。
1938年蒋介石宣布组建以黄埔系军人的复兴社为骨干的“三民主义青年团”,企图为派系林立、日趋腐败的国民党换血,苟延残喘。陕西省三青团地方组织的筹备工作,由随军服务团的人担任是顺理成章的。于是陈忠经做了组训组组长、洪同任宣传组组长、申振民是视导室主任。省支团部书记杨尔瑛,榆林人,二十年代与刘志丹、高岗等同时从事革命活动,参加过共青团、共产党,曾就读于上海大学,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西安事变后做了胡宗南的苏联顾问团俄文翻译。《青年日报》创刊,杨自任社长。后来陈忠经一再升官,继任省支团部书记,国民党省党部执委。于是,地下党控制了三青团的大部分组织,建立庞大的情报网。
胡宗南指示,《青年日报》由战干四团出人,总编辑由高级教官兼任。但大多挂名,五日京兆,半年数月换一个。实际负责人是编辑部主任李恭贻。李恭贻有肺病,干了两年不到,告假养病,编辑部由我“小鬼当家”。我们这张报纸最大的特色是不反苏反共。李恭贻定下方针:讲团结,反对分裂;主张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支持进步,反对倒退、消极、落后和黄色腐朽的东西。这样的编辑方针和言论,自然要引起同业和国民党的非议,但因为这张报纸挂三青团的招牌,是胡宗南出钱,战士四团出来的人编的,他们不好公开指责。
毛泽东也说,“西安的三青团与别处不同;这个我知道”。
这张报的另一特色是简陋之至。虽有编辑部,却没有报社社址。报纸创办时只在西安东大街的西北大旅社租两个小房间作为宿舍。编辑除李恭贻外只有我们两三个实习生,每人一支红笔,一碗浆糊,一把剪刀就上阵了。新闻用的是中央社的通稿和自己记者采写的稿子,办公室借用旅馆隔邻的私商《新秦日报》。“一仆二主”,我们帮他们编报,他们给我们室印报,先印“新秦”一两千份,换个报头,再印“青年”一两千份。
这种合作方式,维持了一年多,后来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先后爆发,我国政府“正式”对德、意、日轴心国宣战,西安土地庙什字的天主教堂主教和神父都是意大利人,教堂被视为“敌产”,由《青年日报》占用大部分建筑,才有了报社社址。后来形势变化,《青年日报》停办,又由延安拨款收购《新秦日报》,做了党的西安情报机关。
作为记者和《青年日报》的负责人,三青团支团部是我常跑的地方。一则为了取得杨尔瑛信任,得不时为他个人宣传,向他报告报社社务。洪同虽非共产党,也不是民先,他是服务团的头,陈忠经、申振民他们许多事情并不避他。对于我来说,陈、申两位是我的“双重领导”,对我的政治情况是了解的,除了他们的秘密活动我不能参与,平时吃喝玩乐、公开的事包括服务团开会都邀我加入。
二、“后三杰”陈忠经、
申健、熊向晖
后三杰之首,是陈忠经。他做事沉着稳重,不动声色,很有点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气概。他不时骑一辆重型进口自行车“上东仓门”或是向胡宗南请示汇报;或是时与潜伏在司令部担任胡的随从副官和机要秘书的熊向晖等人接头。在胡的司令部,我估计还有几个服务团出身的地下党员在做搜集情报的工作。熊向晖的姐姐熊彙苓(解放后周恩来为之更名:光晖)做过我受训的艺术班的女生队长,一度盛传要与胡宗南结婚,后来大约因戴笠的干预,没有成功;改由宋美龄出面为干女儿提亲,胡与美国留学回来的叶霞翟结合。而这个叶霞翟,原是军统老特务文强的助手,原名霞娣。这一来,做了胡的女监军。熊彙苓则退而嫁自己人,与申振民缔婚。
申振民(后更名申健)是北师大学生;民先队员。他先做西京市(西安曾筹建陪都)三青团分团部书记,后任省支团部视导室主任,又打入军统,持有可调动军警的红色特务证。他以视察、指导三青团团务为名,跑遍了陕西各地和外地,还代表胡的司令部出席国民党“党政军特联席会报”。
至于他视察到了什么?不说自明。我亲身经历有他出场的事有两起:一是率领大批宪兵军警抄查西安天主堂,搜出了意大利神父们使用的秘密电台,说是有间谍活动。一是支团部新建大会堂“青年堂”,落成庆典上抓到一个人。此人名卢敦生,是国民党中统特务,新任青年书店总经理,又是洪同的清华同学。洪是清华同学会会长。申振民以“军统”的身份连夜拷问,真相大白。原来是CC系派他打进三青团机关来侦查陈、申、熊等地下党活动的。洪同与申同住一室多年,竟被瞒过,浑然不觉。
三、无名英雄
洪同手下的宣传组组员潘裕然,是北大名教授,老翻译家潘家洵的儿子。1942、1943年间,我去陕西城固西北大学借读时,我们同住一室。他当时的公开身份是三青团城固县分团部书记。他的下手鹿崇文田競存夫妇,分管组织、宣传组,明里是三青团,暗中是地下党情报小组,做西大等院校和汉中一带的秘密工作。那里靠近鄂豫皖和川北,蒋介石亲自上火线指挥“剿匪”军事,山中有他的指挥所。三青团以办夏令营为名公然前往参观,连老蒋的住处也查看了。潘裕然今年已九十又八,他回忆往事,还笑着说:“那时候我还不是党员,陈忠经他们有意不叫我入党。这是何意?万一败露被捕,我只要说是‘经济上有困难,给陌生人送个信,赚几角小钱,那样招供,罪名就轻了。”西安时的老朋友到老了也叫他“小潘”。1947年夏天,西安出了王石坚一案。西安的情报工作由小潘接手,站了最后一班岗。
陈、申、熊等人出国前路过上海,我和报社的服务团老友周光楣在清华同学会设宴饯行。对西安脱险的事,一字不提,而且谈笑自若,十分从容,直到解放以后一年他们回国,才公开此事。而台湾方面,掩耳盗铃、至今保密,不敢公开此事。
服务团的小妹妹陈顺遂,原来也在西安工作的,后来去武功西北农学院上学,学农林经济,可惜英年早逝,因肺病不治,殁于校中,才二十二三岁。绰号“武老头”的武果,是洪同的清华校友,他是西安新生活运动委员会的总干事,也是申健的“总干事”、联络员。他年长几岁,老成持重,“新生活运动”搞得热热闹闹,很有些成绩,得到总会的通报全国嘉奖,但只有我们自己人明白:大家实际上在建设的是怎样的一种新生活。
关于获取胡宗南1943年7月闪击延安作战方案从而摧毁蒋介石扩大内战阴谋的故事,熊向晖已在1991年1月《人民日报》的《在周副主席领导下工作的十二年》一文中首先“曝光”,后来又在1997年、1999年出版革命回忆录《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活》。陈忠经也有纪录片《卧底“西北王”》在电视纪实频道播出,不用我来多说了。我这里说的只是他们“后三杰”以外的一些旧闻。毕竟大家都已到风烛残年,有的已经作古,今后恐怕不会再有人提起这些老话,特别是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无名英雄。为革命奋不顾身,不计个人荣辱安危利害得失的人,又岂止前后三杰?
毛泽东所说的以延安西安划分革命与反革命,只是从大处着眼,但延安西安之间实际上是犬牙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打了几十年仗,你死我活,后来又会和解,握手言欢。
一个世纪的历史,又将翻开新的一页。
2014年5月 上海
(作者为《新民晚报》原副总编辑)
责任编辑 殷之俊
注释:
①1943年6月1日晚,蒋介石亲自召开官邸会议,决心取消中共武装和根据地政权。蒋随即密电胡宗南闪击延安。胡宗南完成布置后,于7月2日正式确定7月9日为进攻边区的时间。胡宗南的作战方案被熊向晖盗得。熊立即报告党中央、毛主席。此时延安只有留守部队在从事大生产运动,一时来不及调兵抵抗。只得由朱德出面抢先予以“公开化”,揭露蒋介石扩大内战破坏团结的阴谋,蒋介石、胡宗南见事已败露,只得收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