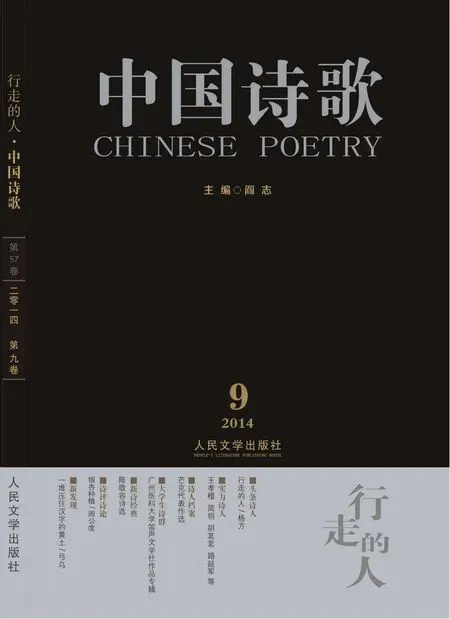行走的人(组诗)
杨方
行走的人(组诗)
杨方
这些年,我看到了诗人杨方的不断进步。从她的第一本诗集《像白云一样生活》,到第二本诗集《骆驼羔一样的眼睛》,她的诗从简单走向丰富,从稚嫩走向成熟。她诗中源自生命深处的忧伤没有消失,她诗中对少年时代生活的那片土地刻骨铭心的爱没有消失。生命的痛感,发自心底的真挚的呼唤,对文化的敬畏和对大自然的爱,以及对他者的理解与同情,这些构成了杨方诗歌作品的基本品质和感人至深的力量。
在杨方的许多作品中,我们看到了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吸收和对其他艺术门类及西方现代诗歌的借鉴与融会。正是这些,让她的诗歌有了诗歌艺术情感的深度,语言的根底和文化的价值。也正是因为这些,我们看到,她的诗歌近些年在不断地变化与上升。
——林莽
寻鹿记
我见过那只鹿,十几年前
被一根粗绳子拴着,在河洲上吃草
谁能相信,那么大的河洲
只有一只鹿在那里吃草
只有一只鹿顶着森林一样交错的鹿角
低下头吃草
有一次,我看见它以绳子为半径,一圈圈奔跑迎着风向嗅着远山的气息,呦呦地鸣叫
别离那头鹿太近,那是危险的事情
养鹿人这样对我发出警告
他用钢锯锯下鹿角
鹿茸切成片泡酒,鹿血掺着白酒喝下
而受伤的鹿,被破布包扎
养鹿人不懂,那庞大的鹿角
是繁星和一座森林组成的,回家的路
在长出新角之前,那只鹿是多么忧伤和愤怒后来它挣脱绳索,狂奔而去,无影无踪
我一直在寻找那只鹿,那只无视时空法则的鹿
想象它停留在羊齿叶与飘忽不定的铃兰花之间
走在空气流荡,清泉潺潺的山谷
它所去的地方,无疑是世界凹坑那样静谧的地方
比如远在天边的乔尔玛
黄昏时分我一转头就看见了那只鹿
它穿越一切的目光正和我静静地对视
它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吗?是我生命中的那只鹿吗?
新疆时间七点半的风吹着
人们永远不懂,它站在那儿的姿势,它的森林一样的鹿角
骆驼羔一样的眼睛
我来到并且停留,仿佛空气进入陌生的庭院
旷野气质的年代,春风在不毛之地温柔地吹拂
宣礼塔在高处召唤着信徒
大地像一张刚刚剥下的羊皮铺展开来
我走在温热的死亡之上
不会有什么令我感到惊讶和不安
无疑,我还会再次遇见你
像一个孩子那样从头开始
耳朵长成无花果叶的形状,清凉,多汁
倾听大气层缓慢移动的声音
我用湖泊的肺叶呼吸,用柔软的蛇腹走路
广场上飞起的那只鸟是我自身孵化的鸟
有五只翅膀,三双眼睛
它们追寻,超越,黑夜的羽毛一去不复返
而落日,我把它想象成一匹有长长毛发的红马
正悄悄穿越这座已被盗空的城市
我有时停在道路的中途
无法记起自己曾到过什么地方
仿佛我是一只禀性多疑的食草动物
是去年的草,去年的路
我在自己的身体里旅行,沿着弯曲的血管,心,肺经历着风暴,迷途,沉醉,累累伤痛
我的脚步,是胸腔里恐怖的回声
当我终于沿着一滴鲜血从指尖走出自己
安拉,我就会成为新世界苏醒过来的一部分
我就是那双骆驼羔一样的眼睛
我是故乡的
我的眼睛是凹陷的,我的语言,是西域的
我的鼻梁和身体起伏,是天山山脉的
我的脸庞,是阿力麻里的(阿力麻里意即苹果城)
我的名字和出生,是出生地的
我的身体,是奶牛和馕养大的
我的星空,是博格达峰之上的
我的羊毛披肩和方格裙子,是伊犁绵羊的
我的胃口,是孜然和胡椒粉的
我不是维吾尔人,不是蒙古人,不是哈萨克人不是锡伯人,不是塔塔尔人
我和这里所有的人一样
把安睡和吃饭的地方当作故乡
把一棵开花的苹果树当作童年
它曾给我怎样的幸福和光亮
在青草的牧场,我和一匹年轻的昭苏马奔跑
我的青春被一根细细的鞭子抽打过
被一双骆驼羔一样的眼睛温柔地追逐过
我的爱情,是新疆的,没有谁能把我半路抛弃
我有祖国,有父亲母亲,有混血的出生地
我在那流血和开花的地方生活了很久
我在那流血和开花的地方还将生活很久
我的情感,伤害,边界线,是国家的
我的热爱,悲伤和思念,是故乡的
我,是故乡的,我的死亡,是故乡的
没有谁能把我分离出去
黑走马
我看见过一匹黑走马
在河洲,冬天的榆树林
疏离的枝条上,月亮像狙击步枪的瞄准圈
黑走马,戴着绊马索,黑夜的皮毛洗得发亮鬃毛披散下来,像夜晚的歌
它可是邻居家拉车的那匹马?
白天被鞭子抽打,在尘土的马路上
拉着高高的麦草垛奔跑
夜晚在低矮的马棚,被结实的拴马桩拴牢无声地嚼食着夜草
不,它一定不是那匹温驯的马
它一定是一匹想在枪口下,走遍大地的黑走马像个穿越黑暗的旅行者,像个诗人,流亡者
不安,动荡,追寻
笼头上的铁扣子,闪闪发光
马蹄铁清脆,给大地留下马蹄形的伤口
它带来什么消息?
被无尽而广阔的空间,囚禁的黑走马
怎么走,都走不出去的黑走马
我要用风中的无花果树,摇曳的叶子和果实
用牛奶和露水洗干净,喂饱它
让它去往无知的途中
让它永远是一匹陌生之马
让它戴着绊马索,走遍大地
让诵经者的祝福,追上它,贴着影子和它一起走
让它在自己的故乡被流放
让故乡在山脉的另一侧,沉睡如山脉
天鹅来到英塔木
听,冬天里,遥远的英塔木
飘荡的温泉水和白色雾气缠绕的苇草间
天鹅的叫声多么清亮
那是我从没有去到过的偏远乡村
眼帘之上的冰雪之国,白天鹅大雪一样降下崇拜天鹅的哈萨克人
从不知道天鹅会在冬天飞临
一群遗世的贵族,带来宇宙惊讶的美
它们起飞的时候,引颈高叫
这声音仿佛是对人类发出的邀请
我不是一个感伤主义者
我记得阳光下积雪的山脉
巨大,闪光,风琴架在绵延的山冈
伊犁河,在最冷的日子里拉长冰冻的脸
洁白的乌托邦,惟一没有冻僵的,柔软的湿地
我一直在小心地靠近一群天鹅
为什么天鹅留在英塔木?
为什么我留在英塔木?
为什么单纯而细碎如羽的时光,留在英塔木?
有一年春天,天鹅过早地飞走
屋檐耷拉下悲伤的翅膀,想带空房子飞走
捻羊毛的人,手里命运的光线
越捻越细,越捻越长,天鹅飞走的路线一样长
仿佛那些天鹅,是一根细细的羊毛线放飞的
是从一堆蓬松的羊毛里面,一只一只飞走的
之后,纺锤飞走,冬天飞走,白色飞走
惟有我,春天来的时候
还穿着白色羽绒服,代替一只死去的天鹅
脖颈低垂,孤独地留在英塔木
请给我一颗萨尔布拉克的星星
戈壁之后是沙丘起伏
疲惫的旅途似乎永无止境
但愿我穿过这座尘土中的小镇
就能把故乡的荒凉彻底原谅!
夜风的手掌已将命运的面纱掀起
缭绕的青烟飘荡在黄土的村庄和麻扎
往事闪现,亲人的脸庞
如薄薄的月浮现西天
沉寂的山冈就要落入黑暗
胡大啊,世界是如此空茫
我仿佛住在一粒微小的尘埃里漂浮无定
当我掩面哭泣
请给我一颗萨尔布拉克的星星,一颗就够
在头顶,在东天,在楚鲁特冰雪皑皑的山峰
它泪水般硕大,深情
带着光束冰凉的疼痛洞穿我的心肺
就算背转身,也能感觉那小小的发光体
对人世永恒,慈悲的安慰和护佑
遇羊记
羊群出现在我的路上
像一些属于高空的事物突降人间
散漫,蓬松,不着边际
在唤醒它们之前,它们是执迷不悟的
做梦一样穿过公路,走向高高弓起的山脊
仿佛穿过薄薄的世界,就是命运的尽头
那只带头的山羊,有着令人惊讶的傲慢
对人间的事物漠不关心
冰雪的楚鲁特山,不允许一只山羊长出翅膀
但一只山羊充满质疑的脑袋可以长出犄角
有智慧的眼神,长者的胡须
它熟知分散的湖泊,百草的气味和养分
分瓣的偶蹄敏捷地跳跃,掠过混杂的植物
我无法确定一群羊飘过之后
撒落的是羊粪还是青草的幼儿
在我的描述中那是彗星尾巴上凋落的闪光
一群魔幻的白色影子,曾漫游于天边
漫游于人类生活之外
在那些缥缈而虚无之处,杳无人迹的地方
被风穿透,成为离群的事物
我们不得不相信,真的有一个那样的时刻
世界的群羊,在我们眼前稍纵即逝
去往了那片并不存在于大地上的辽阔草原
我是臆想的,可疑的种族
不能沿着一座山脉的走向
在最低的盆地,河流的两岸
找到多年前热爱的居民,那些
石头上的居民,草叶间的居民,尘土中的居民
农闲时节敲打着手鼓在打麦场上跳麦西来普
几个世纪以来一条河流冰冷的岩浆
替他们喂养着亚麻和小麦
河流是他们的元素和背景
是一条哗哗流淌的伤口
而马车店是一个临时驿站悲伤的遗物
一个陌生女人取下遮面的黑盖头挂在铁丝上
两只乌鸦,是被风吹上天的一双黑鞋子
让它们替我去走遍天空吧
没有地方可以把我留在任何地方
地表的条条大道都不能通往虚拟的故乡
宰杀羔羊的屠刀在博格达峰的冰雪之巅高举
倘使我是被拒绝的命运
诵经的伊玛目就是我的福祉
人们可以把我当作外乡人,光着脚,没有姓名
他们埋葬我的时候,用清水洗脸,用白布裹身
淡灰色的眼珠
他们不知道我有自己的领地和王座
有养育和生死,最边远的墓地从不被人惊扰
我曾存在,或不存在,那些疑似古代的波斯人
和我一样有着深陷的眼眶,忧伤的,淡灰色的眼珠
惊蛰
响雷鸣动之时,请回答:你是谁?
你不住在鸟巢,你的眼睛是洄游的两条鱼
萌芽的植物,昆虫的振翅,狐狸飞奔
和你有关吗?
你触动了一些被禁止的事情
庞大的交响乐中那支孤独的银笛
是一条被惊醒的银环蛇
自你的胸腔飞蹿而出
它一直上天空,遁入星星冰凉的窟窿
此时风变换着方向吹来,地气通,凌丝断
大自然隐藏着许多秘密
一个洞穴在你身体里越挖越深
我想钻进你身体里去,牙齿发出摩擦的声音
分叉的舌头在你口中嘶嘶地吹吐着凉气
令人不安,又多么愉快!
五百年来了又去,春日生长,冬日睡眠
无论你是谁,出来吧
打开声带吧,尽情繁殖吧
不要像躺在坟墓里的人与电波失去了联系
那早已逃走的时光,为你又回来了一次
有着山林和湿地的南方又回来了一次
胆小怕光的我又回来了一次,铃兰花又回来了一次整个世界,都为你又回来了一次
两棵杨树
两棵杨树为什么不动?十年了
距离不动,生活姿态不动,崇高理想不动
主心骨不动,树影横斜不动
树杈上的鸟不动
乌鸦是乌鸦,喜鹊是喜鹊
不混在一起,不飞,不叫,不为食亡
也不怕被别的鸟占了巢
如果飞,它们飞的路线不动
沿着风向,气流,光线和山脉的起伏
如果叫,它们的明亮不动,爱情不动
恨别时的惊心不动,一只鸟分身为两只
飞往秋天的高度不动
明年飞回来绕树三匝,栖落的枝丫不动
动一下会死吗?那么多东西在动
蜗牛在动,动车在动,冰山在动
宇宙间的漂浮物和不明飞行物都在动
一个人,从南跑到北,从东跑到西
不停地在地球上移动
但两棵杨树不是人,有进有退,有所思,有所不思
如果一棵杨树对另一棵杨树心生爱慕
暗暗钟情,暗结连理
它们表达的方式就是永远不动
百步穿杨,秋风扫落叶,都没什么可怕的
它们一味地树干正直,不要结果
一味地坚持着,介于飞和不飞之间
翅膀展开,羽翼丰满,只欠东风
——就算东风来了它们也不动
它们知道,哪怕稍微挪一挪身子,世界就变了
冰糖的月亮就会从树丫间掉下来,摔成人间碎片
树梢之上正是孤独的群星
秋天,当你独自生活在某个陌生的地方
没有人认识
也没有悠长的钟声和缓慢的马车
阳台,空中楼阁般远离地面
只有两棵杨树的手臂,轻抚着玻璃的脸庞
不发出一点声响
当黄昏,金色光线穿过树洞
叶片闪闪烁烁,和梦见的一样多
鸟巢像挂在树丫上的草帽
连理枝上的双飞鸟,争鸣,振翅
在空气中呼啸而过
它们有时东南飞,有时各自飞
也不发出悲切的鸣叫
你不定的目光,从不会追随,不会
跟从它们的心停留在别处
染上暮色忧伤的气息
你,只是慵懒,散淡地
长久注视灰白的树干和枝丫
命运分岔的小径,越往上越细
仿佛探寻宇宙的天线
接收着来自蓝色天宇的微波和光亮
地球之外,星云,水,也许另一些生命和花朵多少年来从不曾熄灭
黑暗之中也熠熠生辉
它们把庞大的沉默,撒满天穹的
冰凉种子,传递给人类
那树梢之上,正是孤独的群星
一个哈萨克牧人和他满天的星斗
他习惯把北斗星叫作铁橛子星
晚上看守畜群
他根据铁橛子星的方位确定换班时间
然后踏着青草上的露水回毡房
冬天,看见绊马索星出现
他将畜群赶进棚圈
并在三只山羊星淡出时起身给马喂夜草
他知道杀毛驴星最亮的时节,可以剪羊毛
如果两颗红色的星开始挨近
就应该让公羊交配,母羊怀孕
他把天狼星叫作苏木比列
此星出,黎明凉爽,水变冷
对牲畜有害的虫子即将死去
人们开始割麦,打草,准备过冬的柴火和牛粪
他把滑过头顶的流星叫作尾巴星
尾巴星落进水里,雨多
落在干燥的地方,风多
落在石头上,气候炎热
秋天看见尾巴星,这时节植物的根不再往下长
茎秆开始结出果实
人们宰羊熏肉,准备去往冬牧场
一个哈萨克牧人,就是这样把万物生长和消亡
跟天上的星星联系在一起
把自己的作息和迁徙,跟天上的星星联系在一起
如果有一天他死去,他一定是像星星一样死去
蓝色的,落入水里,红色的落在石头上
毫无疑问,他是最后一个热爱星星的人
他对远古星辰的怀念,高不可及
似乎那冰糖渣子一样又甜又亮的星星
只属于一个又偏远又孤独的牧羊人
他用哈萨克语一一叫出它们的名字
像叫出每一个,眼眸明亮的姑娘
行走的人
一个人,在地球上某处走
缓慢地从球体的一点移动到另一点
经历无数陌生的省份,河流,天气
不同的语言,地貌,植被和肤色
一条大路认得他,一条小路也认得他
还有一条水路越走越亮
他将沿多雨地带,丘陵地带,高山地带
无止境的黑色地平线和拧弯的金属海岸线
甚至危险的国境线
在如此苍茫的地球上他是孤零零的
他再怎么走也走不出地球
他不能走到沉静的土星和木星上去
不能走到水深火热的水星和火星上去
他只能往高处走,越走越高,越走越坚定
在一座孤独的山头,他是受伤的狮子
流着夕阳的血,披着风的披风
如果有一天他不在地球上某处走
只是坐在自家低矮的门口看地图
喜马拉雅和乞力马扎罗压住了他的两只脚
密西西比河和亚马逊河蟒蛇一样缠绕双腿
他四十二码的旧鞋子,大草帽,尘土满面的脸
以及八尺长的影子,仍在地球上某处走
夜行北雁荡
是夜,雁荡山有犬牙交错的起伏
树木有老棺材的厚重和漆黑
一行人,在一座山的体内行走
像不出声的猫头鹰,怀有黑暗之心
有人突然停下,在合掌峰的指缝间
划亮一根火柴为大家点燃香烟
光之队列,星星点点
在山体开裂的缝隙,在事物隐秘的纵深
他们一一穿过缺口,就像白驹过隙
但他们只是低头急走,从不抬头
不能看见,黑暗中的山就像大地上的孤儿
每一个孤儿都有一枚仇恨的尖牙
暴烈的黑色花朵,把他们撕碎,吞没
凶狠的打击,雷电,雨雪,还有冰川的痕迹
火山的痕迹,大地震的痕迹
人类开山凿石的痕迹
都不能够使它悲伤和遗忘
山峰上千年的睡眠,也不能够移动一寸
那隆起的,思想的峰顶
脊骨曾驮负着整个宇宙的深蓝
多少次,我独自落在最后
听见了冰凉洞穴里,睡蛇的响尾
头顶群星不时掠过,石头和风刮擦的声音
给我带来巨大的痛楚
我的灵魂正被万物的灵魂所带走
自此夜起,它将停留在山峰永恒的孤独中!
山下夜行人
夜,一辆老旧三轮摩托车像小型坦克隆隆驶过
之后,小镇显得异常安静
她弃路走向荒野
立刻被眼前一轮大大的圆月所惊呆
仿佛看见巨灵,一声不吭地从茫茫中升起
天庭的光泽,也是这般静止
她不能知道在空幻的,山的另一面
是否有另一个光亮的世界
有另一个人,身披月光,独自行走
看见了光,影,山,色
普天下贫穷的心,赤裸的神迹
看见月亮被卡在山的缺口,永远不能沉落
发光的崖壁上,爬藤从深渊爬上来
仿佛一个死去的人从幽黑的坟墓中爬出来
横躺在人间的光亮中
她无端端地,就失去了语言
也许她曾生活在无声的月亮上
金灿灿的桂花落了一地,一年又一年
现在她想要走回到那里去
经过发白的河流,萧索的矮树丛
和一片遗址般废弃的荒园
一只狗跟在她身后,当它停下
仰天嗥叫的时候,影子也跟着拉长了嗥叫
世界因狗的嗥叫更加寂静
那么,晚安吧,剪刀峰就耸立在头顶
月亮在那里发出十倍的光亮
群峰正如寒冷的,金属堆积的山尖
如果她走到那里,是否就算回到了来处?
如果她折返人间,是否就是我回到了自己?
他山之石
置身山外,我听不见音乐隐藏在山的肺腑
流水的怒吼在最坚硬的岩石中沉睡
落日,环形山镶嵌在指间的一颗红宝石
奇异的光让我看见了痛苦的美
在天空交叉的路口,人间冷暖的屏障
雁过之后,有的留声,有的一死成名
隔着一千座雁荡山
我宁愿像一只雁一样孤绝鸣叫,折颈而亡
也不要一个人孤独地行走在这充满欢爱的人间
如果你是孤独,是青黛,是永恒的忧伤
天黑下去,你就是另一个时代
众多夜晚,我看见人们漫长地生活在群星下
缝补,浆洗,织锦,做梦
他们从不知道,黑暗能像愚公一样搬走一座山
而我却不能搬动体内最小的顽石
如果你是隐匿,是消失,是无形
是开门不见的山,被掏空了所有的矿石
压在我身上的沉重就会荡然无存
最后,如果你是寂静,是深邃
在山的这一边,或山的另一边
在这个星球,或那个星球,我就是对应的虚空和遥远
黛力新
野蛮而悲伤的高原,今夜,我只是个病人
孤独,焦虑,弹尽粮绝
有谁能给我一片救命的黛力新,我不是不知道
这紫堇色的糖衣片,小毒,大瘾,致幻
必须一张医生的处方才能买到,我不是不知道
它的危险,只是今夜我比它更危险
骑在高原耸起的屋背上
脚下河流奔走,额头乌云越压越低
我就要被它挤爆,我就要被自己压碎,不能呼吸
那堵乌云的墙壁已经越堆越高
湿,重,厚厚的,密不透风
我恨不能用钢镐去刨,去掘,直到流出鲜红的血
饮马街
这么晚了,那个人还在陌生的城市寻找一家通宵的药店
她将在饮马街下车,从东走向西
她将遇见两个说藏语的人,她将跟着他们
经过一排孤单的丁香树,一些明亮的广告牌
她将看着他们消失,她将被剩下
被许多店铺关在门外,被一辆飞驰的车溅一身雨水
她将扶着湟水,看见水中青丝的芦苇
脆骨,空心,飘零半世,草莽一生
她将随着它们,风一吹就那么固执,那么紧地抱着自己
她多想躲藏在小小的,哭泣的丁香里哭泣
多想从一条街的口袋
翻出止痛片,止血片,解毒片,安神片
她正经历的痛,是一生最小的痛
她将走过的饮马街,被天上的雨水洗得干干净净
她将在这条街的尽头停下,手里捏着空空的药瓶
裙子上的葵花黄,被一万华灯薄薄地照亮
雾灵山,风朝一个方向吹
许多日子我坐在山顶,看见风从远处吹来
踩着老梨树,山楂树,玉米叶子哗哗地走
它们弄出流水的声音,仿佛另一条河流流过
带走了人间芦荻纷飞,黄叶翻卷
最后,它们去了哪里?
飞鸟去了哪里?真正的流水去了哪里?
拉萨河,红河,额尔古纳河
或者更远的多瑙河,印度河,密西西比河
我从未去过的地方,有谁看见它们日日空流
奔波在绵延的归途
就像我来到雾灵山,或者去别的什么地方
都只是路过,我最终要去的
是今生无法依托的故乡,和死后的故土
当我看见落日西沉,晚星淡出
珍珠梅在风中雪一样飘落
它落在无人的小径
僻静的山谷,虚空的时间,寂静,冰凉
我想不出别的事物是怎样飘落的
在看不见的地方,那些风
走在分叉的树枝上,走在分支的河流上
它们朝一个方向吹,它们又是怎样
像一群人,走着走着,突然消失的
石榴树下
不,那些不是花朵,不是火焰
不是六月,不是明暗分割
当我跑近,又突然止步
一棵石榴树的气息多么血腥和狂放
让我产生腹痛的感觉,腹腔,满是红色的回音
对我来说,它们真的就是一场流血
血色罗裙,红,接着更红,往死里红
要么辉煌,要么寂灭
要么拯救,要么分裂
看,又一朵火红的石榴花坠落泥尘
就像坠落在一个人荒凉的额头
面容闪烁,气息奄奄
是世界化为灰烬的声音
是凉下去的声音,是绝望,震颤,威胁和恐惧
这个夏天,石榴花仿佛开也开不完
仿佛要一直这样开下去
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这样的一棵石榴树
烈火中永生,或永不再生
风中的芦苇
当我们来到,风中的芦苇林立着
像一堵植物的城墙坚不可摧,我相信
在我们没来之前,它们就一直在这里认真地绿着
把脆骨熬成空心,把草莽飘零成半世
这些芦苇,应该是一些有思想的芦苇
懂得择水而生,就像古人择邻而居
它们喜欢在四月发芽,五月展叶,七月孕穗
八月开花,九月纷飞,自此白鹭一样渺无音信
此时是六月,芦苇像一个瘦瘦的孩子正在长高
如果停下,可以听见它们吮吸清水的声音
如果一直往前,会迎头遇见一艘蓬松的运草船
那年轻的运草人站立船头
明亮,葱绿,像是从水中长出来的
而船尾霜雪满头的老人
会随手指出一枝芦苇里深藏的光芒和呼啸
嘉峪关,西北望
自古险要从无宁日,打来打去
一道血肉筑成的关,究竟能阻挡住什么?
箭羽,流沙,碎石
还是一只受伤大雁脚上的书信?
十几年前,我曾和一列绿皮火车孤独地经过
天黑前它还有几千里路要赶
那旷野气质的时代
宇宙洪荒,前路未卜,前路无知己
多少年,嘉峪关土黄的颜色在我记忆里
是剪影般壮丽的图画
落日有点残忍的明亮,仿佛刀光空悬
仿佛大厮杀之后的大沉静
没有什么能像一座砖石的关口一样
一声不吭
他的沉默是三尺城墙亮晃晃的沉默
死去之前,他是活着的
一夫当关,守住道路上的真理,信念
时光的缺口
就像古人在死地里养育出月牙和柳树
西北望,任谁都会生出一副悲愁的心肠
草木缺水,妇女没颜色
风跟河流已经不再出声
鸟跟牲畜不知踪迹,只要再等一会儿
嘉峪关就要孤独地安睡在旷野里
那荒凉泥土之下,沉睡的人永远比地面上多
清明上河图
我将穿过画里的闹市
算命的,杂耍的,卖烧饼的,卖笑的
都在为生计奔波,是我熟悉的愁苦
酒肆挨着茶坊,花街柳巷,风流韵事仍然在
管弦和丝乐把一个朝代弄得乱纷纷
转个弯,那条拱起的虹桥就泊在水里
年代久了,水色也憔悴
只有丝绸庄里堆积的布匹还算明亮
潮湿的下午,二八女子倚着门框,吐气如兰
美貌让她孤寂丛生
一顶素轿抬着扫墓归来的妇人
汴京的人都看见她口含杏花,一路飘洒
比清明灰白的雨水还要哀伤
我终将来到一堵断墙的庭院
玉树开花,青苔渗着旧梦里的冰凉
听说,一口废弃的古井里常常闹鬼
又是一个无处诉说的女子
在黑夜里击鼓鸣冤,惨白地唱
我还将记起当铺,卖身契,一张宣纸上欠下的债
宋朝的江山破碎后,我是惟一
从州府的公堂和刑具里抽身溜走的
我将和市井的吆喝一起消失,找不到来龙和去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