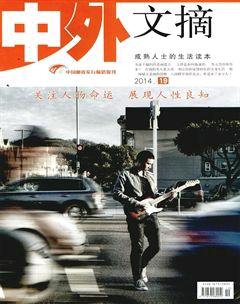历史的注脚(二篇)
叶永烈
毛泽东和秘书工作
为了写作《毛泽东的秘书们》这本书,我详细考证了毛泽东历年来任用的秘书。经过多年查证,到2005年,我查找到的毛泽东的秘书为26位。经过这几年的继续查找,又找到毛泽东的ll位秘书。这样,毛泽东一生任用的秘书为37位。
毛泽东曾经是中共中央局秘书
在就《毛泽东的秘书们》一书进行多年深入探讨的时候,我还发现,毛泽东本人早年既担任过中共中央局秘书,也出任过国民党上海执行局秘书。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山恤孤院后街31号一座简陋的两层民居楼内秘密召开。40位代表出席了会议。毛泽东以湘区党代表的身份出席。大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谭平山、王荷波、毛泽东、朱少连、项英、罗章龙9人为中央执行委员,邓培、张连光、徐梅坤、李汉俊、邓中夏5人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中共“三大”闭幕的翌日,即1923年6月21日,新当选的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在中共中央驻地广州新河浦路24号春园二楼召开会议,推选产生中央局。这时,陈独秀提议中央设立秘书一职。会议选出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谭平山(后由于谭调职,改为王荷波)、罗章龙5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任中央局秘书,罗章龙为中央局会计。中央局下设组织、宣传、妇女等部门,毛泽东负责组织工作,蔡和森、罗章龙、瞿秋白负责宣传工作,向警予负责妇女工作。
这是中共中央局首次设立秘书。不过,毛泽东所担任的中央局秘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秘书,而是中共中央局的领导人之一,相当于后来的中共中央秘书长。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由此可见,毛泽东所担任的中央局秘书相当重要。
毛泽东有很强的档案管理意识。他担任中央局秘书以后,要求所有党的文件,除了保留印刷件之外,还必须保留原件。此前,中国共产党处于草创时期,党的文件随发随烧。陈独秀在中共“三大”的报告中指出:由于“中央委员会人员太少,不能搜集很多文件。又由于遭受迫害,许多文件材料遗失了”。毛泽东担任中央局秘书之后,扭转了这样的不严密的状态,开始注重保存中央文件,尤其是保存原稿,建立“发文留底稿”的制度。中共“三大”的决议、宣言、章程、报告、通告等都得到很好的保存。后来这些文献保存于中共中央地下档案库。从现存的中共中央地下档案库目录中可以看到,1923年7月至1924年7月这一年间,中共中央积存了300余份重要文件的原件。这些重要文件躲过严重的白色恐怖,至今仍完整地保存在中共中央档案馆中。
1923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第5号通告,宣布中央局自广州迂回上海后的人事变动。“中局组织自迁沪后略有变动,即派平山同志驻粤,而加入荷波同志人中局。又润之(即毛泽东)因事赴湘,秘书职务由会计章龙同志兼代。”
毛泽东也曾是国民党秘书
2009年1月,台北的国民党中央党史展览厅举行国民党党史展览,内中国民党上海执行部1924年3月的决算书上记载,毛泽东任国民党秘书,每月领取120元大洋。这份文件原稿首度曝光,引起参观者的莫大兴趣。
这里所谓的“国民党秘书”,准确地说,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
身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毛泽东,怎么会去当“国民党秘书”?
事情还得从中共“三大”说起。
中共“三大”的中心议题,就是讨论国共合作问题。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指出“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会议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形式实现国共合作。大会期间,毛泽东曾和陈独秀、李大钊、徐梅坤先后两次去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财政部长廖仲恺家,恳谈国共合作事宜。
根据中共“三大”的决议,毛泽东加入了中国国民党,成了一位“跨党分子”,即既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又是中国国民党党员。
在中共“三大”决定实行国共合作的同时,孙中山在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推动下,决意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榕树低垂,一条长长的老街越秀路从树下穿过。街边的人行道上方是骑街楼,这种便于躲雨的旧房一望便知是20世纪上半叶的南洋建筑风格。2008年10月,我在广州越秀中路与文明路交叉口,见到高高的围墙抱住一个偌大的院子,门口高悬郭沫若题写的“广东省博物馆”六个大字。国民党“一大”会址就在大院之内。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一大”就在这里召开——这“一大”是按照中共党史的习惯简称的,而按照国民党的用语则简称为“一全大会”。中国国民党的创建早于中国共产党,而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则晚于中国共产党。步入礼堂,主席台上悬挂着中国国民党党旗和孙中山肖像。主席台下是一排排深褐色木长椅,前排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座席,后面为会议代表,再后面是列席代表。正式代表对号入座,座位上贴着代表的姓名。我看到许多熟悉的名字,如廖仲恺、戴季陶、于右任、谭延间、程潜、叶楚伧、孙科、何香凝、陈璧君等著名的国民党人士,我也看到李守常(李大钊)、谭平山、林祖涵(林伯渠)、王尽美等著名的共产党人士。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第39号毛泽东。国民党“一全大会”代表196人之中,有24人是中共党员。经孙中山提议,“李君守常”为大会主席团五名成员之一。会议洋溢着国共合作的良好气氛。39号“毛君泽东”是相当活跃的代表,几度在大会上发言,并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1月30日下午,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时,孙中山亲自拟了一个候选人名单,交付大会表决,其中就有毛泽东。经过大会表决,毛泽东当选中国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国民党“一全大会”结束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派毛泽东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在上海,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执行委员、组织部秘书和文书科代理主任。endprint
在上海毛泽东身兼国共两党秘书
2008年12月19日,我陪同毛泽东的儿媳刘松林(刘思齐)在上海茂名北路威海路参观毛泽东旧居。1924年2月中旬,毛泽东从广州来到上海,就住在这里。当时的毛泽东,身兼国共两党的秘书:既是中共中央局秘书,又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
这是毛泽东第九次来到上海,住在威海卫路云兰坊7号(今威海路583弄7号)。那是一幢两层楼砖木结构的石库门房屋,迄今仍保存完好。当时,毛泽东在这里住下之后,端午节前后,杨开慧和母亲带着两岁的毛岸英和刚出生不久的毛岸青也来到了这里。当时,毛泽东一家住在楼下,毛泽东的挚友蔡和森、向警予一家住在楼上厢房。
前八次来到上海,毛泽东都只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这一回,由于他在上海身兼国共两党的中央执行委员,国共两党的秘书,所以是他住得最长的一次;而且由于妻子杨开慧、岳母和两个儿子的到来,也是最富家庭生活气息的一次。
杨开慧来到上海之后,除了料理家务,还帮助毛泽东整理文稿。
毛泽东在上海,由于同时在国共两党工作,相当忙碌。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以叶楚伧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反对国共合作。毛泽东跟叶楚伧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24年11月17日,孙中山应冯玉祥等人的邀请北上,途经上海。毛泽东向孙中山面呈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上海执行部14人致孙中山的信,信中反映:“自8月起经费即未能照发,近来内部更无负责之人,一切事务几于停顿,希望派员解决。”当时,孙中山因北上事务繁忙,而且又身染重病,未能处理此事。1924年12月,毛泽东因工作过于劳累患病,于12月请假回湖南老家养病,结束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的秘书工作。
此后,1925年9月,毛泽东从湖南前往广州。10月5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111次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当时身兼国民党宣传部部长,他声言自己公务繁忙,无法顾及宣传部部长工作,提议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部长。这样,毛泽东出任国民党宣传部代理部长。10月7日,毛泽东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就职,并主持召开宣传部第一次部务会议。
然而,国共两党渐行渐远,合作濒临破裂。1926年5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毛泽东在20日的会议上作了《宣传部工作报告》。这次会议通过的《整理党务案》,规定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职务的共产党员必须辞职。从此,毛泽东离开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
在北伐胜利之后,国共分裂。特别是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政变之后,血腥屠杀中国共产党人。这年秋天,毛泽东在湖南举行秋收起义,带领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踏上以枪杆子推翻蒋介石政权的漫漫征程。
从首任秘书谭政到末任秘书张玉凤
1928年,在井冈山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有了秘书。
由于毛泽东自己做过秘书,所以他要求秘书除了收发文件、起草文件之外,还必须具备强烈的档案意识。
在井冈山上,由于处在战争的流动环境之中,毛泽东无法用档案柜保存文件,就用文件箱保存文件。毛泽东对秘书贺子珍、曾碧漪说,她俩的任务就是保管好文件,保护好文件箱。那时,战斗频繁,说走就走。在行军时,文件箱在哪里,她俩便在哪里。
毛泽东的首任秘书是谭政,末任秘书是张玉凤。从1928年直至1976年毛泽东去世这48年间,毛泽东先后任用了37位秘书,依照他们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时间顺序排列如下:
谭政(1928-)
江华(1928-1929)
贺子珍(192-1937)
谢维俊(1928-1929)
古柏(1930-1933)
曾碧漪(1930-1933)
李井泉(1930-1931)
郭化若(1931-)
谢觉哉(1933-1934)
黄祖炎(1933-1935)
王首道(1933-1934;1937-1944)
李一氓(1935-)
童小鹏(1935-1936)
叶子龙(1935-1962)
吴亮平(1936-1937)
张文彬(1936-1937)
周小舟(1936-1938)
李六如(1937-1940)
和培元(1938-1941)
华民(1938-)
江青(1938-1976)
陈伯达(1939-1970)
张如心(1941-1942)
胡乔木(1942-1966)
柴沫(1941-1945)
王炳南(1945-)
田家英(1948-1966)
罗光禄(1948-1963)
王鹤滨(1949-1953)
高智(1953-1962)
林克(1954-1966)
徐业夫(1957-1974)
李锐(1958-1959)
谢静宜(1959-1976)
戚本禹(1966-1968)
高碧岑(1968-1974)
张玉风(1974-1976)
毛泽东慧眼识人才
在毛泽东的众多的秘书之中,有的秘书兼做各种各样的秘书工作,也有的秘书有所分工,诸如陈伯达、胡乔木这样专门为他起草文件的政治秘书,有江青这样的生活秘书,有高智、罗光禄、徐业夫的机要秘书,有郭化若这样的军事秘书,也有林克这样的国际问题秘书,还有像王炳南这样只在重庆谈判期间担任他的秘书(因为王炳南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熟悉重庆各阶层人士)。此外,也有李锐那样的通讯秘书,即通过通讯表达自己对一些问题的见解,供毛泽东参考。endprint
毛泽东很善于识别人才、发现人才、培养人才。谭政在井冈山上成为毛泽东的首任秘书时,不过22岁。经过毛泽东的培养,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副部长。同样,在井冈山,江华担任毛泽东秘书时只有21岁。经过毛泽东的培养,后来成为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毛泽东挑选秘书,当然很注意秘书在政治上必须绝对可靠。他挑选谭政当他的秘书,是知道谭政乃陈绍纯先生的女婿。毛泽东不仅认识陈绍纯先生,而且认识陈绍纯先生的长子陈赓,因此谭政在政治上当然可靠。毛泽东在1937年选用刚刚出狱的李六如作为秘书,是因为他早在1921年就认识李六如,并介绍李六如加入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勤于读书看报。他挑选政治秘书,往往是从读书看报中发现的。
毛泽东注意到陈伯达,是在听了陈伯达在延安关于孙中山思想的讨论会上的发言之后,发现陈伯达关于孙中山思想的见解有独到之处。毛泽东又仔细读了陈伯达1939年发表在延安《解放》第八十二期的《墨子哲学思想》,于1939年2月1日给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的陈伯达写了一封二千字的信,谈论《墨子哲学思想》。此后,毛泽东又于1939年2月20日、22日写了两封信给张闻天转陈伯达,评论陈伯达的《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这样,在1939年春,陈伯达调到毛泽东主席办公室工作,从此成为毛泽东的秘书,为毛泽东以及中共中央起草了许多重要文件,直至1970年,前后达31年。
陈伯达向毛泽东推荐了胡乔木。陈伯达说,胡乔木在《中国青年》1939年第1卷第2期上发表了《青年运动中的思想问题》,写得不错。毛泽东仔细看了这篇文章,说:“乔木是个人才。”这样,1941年2月,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增加秘书处人员时,毛泽东提名胡乔木。从此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直至1966年“文革”爆发,前后达25年。在担任毛泽东秘书期间,胡乔木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起草了大量重要文件。
毛泽东注意到田家英,是在1942年1月8日。那天,田家英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从侯方域说起》一文。毛泽东读后,颇为赞赏。1946年,毛泽东请田家英担任他的长子毛岸英的家庭教师。1948年,经胡乔木推荐,田家英成为毛泽东秘书。
逐步形成毛泽东稳定的秘书群
从毛泽东任用秘书的时间来看,早期处于战争环境之中,不论是在井冈山、瑞金,还是长征途中,毛泽东的秘书任期都很短暂,变动频繁。
进入延安之后,毛泽东的工作环境相对稳定,这一时期也是毛泽东完全确立中共领袖地位、工作繁忙、著述甚多的时期。毛泽东身边的秘书增多,秘书班子逐渐稳定,形成了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叶子龙、江青这样的秘书群。这个秘书班子从20世纪30年代末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文革”前夕。1956年,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正式确定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叶子龙、江青为毛泽东秘书,被人们称之为毛泽东的“五大秘书”。
叶子龙在1962年被调离中南海,田家英在1966年5月23日自杀于中南海,胡乔木则在“文革”初就遭到“批判”,毛泽东这“五大秘书”中三人离开秘书工作岗位,而陈伯达、江青则分别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和第一副组长,后来分别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委员。1970年,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被打倒。“五大秘书”之中,只剩下一位并不与毛泽东生活在一起的生活秘书江青。
在毛泽东晚年,1974年机要秘书徐业夫病重住院之后,毛泽东身边的秘书只剩下一位张玉凤,陪伴着他直至1976年9月9日病逝。
田家英之死
离世的前夜
我于1989年9月16日、17日在北京采访田家英夫人董边,录了7盒磁带,她很详细地回忆了田家英之死。我至今仍保存着她的谈话磁带。
董边说,有件事给了田家英沉重的一击,那是在1966年5月22日星期日。
下午三时,中南海“喜福堂”田家英家门口,忽然来了一辆轿车。从车上下来三个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王力以及那个在走红的戚本禹。
他们进屋,不巧,田家英和秘书逢先知外出。董边在家,告诉他们,田家英很快就会回来的。
于是,安子文、王力并排在长沙发上坐定,戚本禹坐在旁边的单人沙发上。三个人神情严肃,看来,“无事不登三宝殿”。董边不知来意,又不便问。
在沉闷的气氛中等了一会儿,田家英和逢先知回来了。看样子他们要谈重要的问题,董边站了起来,打算避开。这时,安子文对她说:“董边,你也是高级干部,坐下来一起听听。”逢先知也留了下来。
安子文对田家英的谈话要点,据董边回忆,是这样的:“我们是代表中央的三人小组,今天向你宣布:第一,中央认为你和杨尚昆关系不正常(当时杨尚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田家英任副主任,在工作上有许多联系),杨尚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要检查,第二,中央认为你一贯右倾。
“现在,我们代表中央向你宣布:停职反省,把全部文件交清楚,由戚本禹代替你管秘书室的工作。你要搬出中南海!”
田家英几乎屏着呼吸,听完安子文的话。安子文很明确地说,他们三个人是代表中央来的,显然并非安子文的个人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北京举行。显然,已成为新贵的江青、陈伯达借批判“彭、罗、陆、杨”的势头,要拔掉他们早就想拔去的眼中钉——田家英。
关于“三人小组”,我在访问王力时,他是这样说明的:“当时政治局决定成立一个小组,下面分为处理彭真、陆定一、杨尚昆、田家英问题的四个分小组(罗瑞卿问题已在上海会议期间处理)。田家英分小组的组长是安子文,组员是王力、戚本禹。”
安子文是奉命而来,因为他的职务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诚如董边回忆此事时所说:“安子文同志在1966年7月也被批斗、关押,遭受到严重迫害,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到平反。他在病重期间,还关心地询问田家英和我的问题是否已经平反。”endprint
在安子文作为三人小组组长传达了中央意见之后,田家英的眉间皱起深深的“川”字纹。他竭力克制自己内心的激愤,冷静地问道:“关于编辑‘毛选的稿件是不是也要交?”
“统统交。”安子文答道。
这时,戚本禹问道:“毛主席关于《海瑞罢官》的讲话记录,在你那里吗?”
戚本禹所说的记录,当然就是指毛泽东那次杭州谈话的记录——他非常关心那份原始记录,想知道内中的究竟。
“没有。”田家英很干脆地回答道。
谈话就这么结束了,开始点交文件。田家英把手边的文件,一份份移交给戚本禹,成本禹逐份登记。安子文和王力在一旁看着。
大约到了下午五时多,安子文和王力走了。戚本禹仍留在那里,一直点交到天黑才走。
戚本禹走后,田家英像塑像一般,一动不动坐在那里。董边劝他吃晚饭;他也不吃。看得出,他陷入了极度的痛苦和愤懑之中。
夜深,电话铃声响了。是谁来电话?戚本禹!
“你到秘书室来一趟,在文件清单上签字。”戚本禹仿佛一下子成了他的上司似的,对他颐指气使。
啪的一声,田家英挂断电话。
他满脸怒色,对董边说:“戚本禹是什么东西?!他早就是江青的走卒,我不去签字!”
过了一会儿,田家英咬牙切齿道:“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人有好下场!”
董边听不出他话里有话,但是知道他心里如割似绞,便坐在一旁默默地陪着。
人在最痛苦的时候是无言的。田家英一声不响,木然坐着。
董边呢,心中也反反复复想着安子文在下午代表中央所说的那些话。她当时并没有把事态看得那么严重,以为像往常的政治运动——《五·一六通知》通过才几天,谁会料到这场“文革”会那般惨重、残酷。
夜深了,十二点了,田家英要董边先去休息。
那时,他们所住的“喜福堂”,是个小院子,中间的正房住家,右边的是毛泽东的图书室,左边是逢先知的办公室。田家英那时坐在图书室里。
董边因为翌日一早还要去上班,回正房先睡了。
她迷迷糊糊一觉醒来,一看手表,已是清晨五时,图书室里还亮着灯。
董边赶紧下床,到那里去看田家英。他竞一夜未眠,未吃,仍呆呆地坐着。
董边知道他心里难受,可是没有往坏处想。她要他赶紧去休息。
“今天你上班吗?”田家英问她这么一句话。
“上班。”董边答道,“七点就得走。”
“你管你去上班,别管我!”田家英说道。
董边依然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她以为,这一回大约是要他检查检查“右倾错误”,要他离开中南海下乡劳动。她去找逢先知,要逢先知帮助他作检查,如果要下乡的话,就跟他一起下去。
吃过早饭,快到七点,董边像往日一样,跟丈夫打个招呼,上班去了。与往日不同的是,她又一次劝他早点休息。
田家英呢,朝她点点头,一点也没有流露出异常的情绪。
董边走出了院门,上班去了。她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一回竟是与他生离死别!
自杀的经过
5月23日上午,挂着清朝乾隆皇帝手书“喜福堂”的小院,格外的安静:逢先知写材料去了;勤务员陈义国也有事外出了。
“喜福堂”格外安静,还因为隔壁的“增福堂”无声无息:那里原本住着陆定一一家。陆定一夫人严慰冰已于1966年4月28日被捕。陆定一于5月8日从合肥回京之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受到林彪的责骂,当即被逐出中南海,软禁于北京安儿胡同一号,一个班的士兵看守着他。
“喜福堂”格外安静,也由于离此不远的毛泽东住处不再人来人往:毛泽东在杭州住着,有时他在上海,就连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样重要的会议在京举行,他也没有回京。正忙于发动“文革”的他,行踪隐秘,百倍警惕着“现正睡在”他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要借助“文革”打倒的“中国赫鲁晓夫”,此刻正在北京主持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呢!
就在这一片安静之中,田家英在“喜福堂”小院里,独自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一个上午。
安安静静,电话铃声未曾响过,也未曾有过一个来访者——他已接到逐出中南海的命令,还有谁会给他挂电话,还有谁敢登门拜访?
直到中午,小院外才响起了脚步声,打破了这里的沉寂。那是勤务员陈义国回来了,找田家英吃中饭。
正房里没有人影。
图书室的门紧闭着。陈义国在门外大声地喊了几下,没人答应。
咦,田家英到哪里去了呢?
陈义国试着推了图书室的门,那门反锁着,推不开。
他等了一会儿,又喊了一阵子,屋里仍没有任何反响。
这时他觉得情况有点异常,找人拿钥匙开了门。
陈义国朝里面看了看,见不到人。他走了进去,走过几排书架,顿时像触电似的尖叫起来:“啊哟……”
原来,他在两排书架之间,看到田家英吊死在那里。
陈义国急急抓起电话,向上报告。
下午三时光景,正在上班的董边,忽然接到了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的电话:“你马上到少奇同志西楼办公室来一下!”
董边觉得诧异,平素很少交往的安部长,怎么会直接打电话来?会不会发生了什么突然事变?
董边急急赶回中南海,来到刘少奇西楼办公室。她一走进去,安子文已在里面等她了,旁边坐着汪东兴。当时,汪东兴主管毛泽东的警卫工作。
等董边坐定,安子文这才直截了当地把不幸的消息告诉她:“田家英同志自杀了!”
董边顿时懵了,脑袋仿佛在一刹那间剧烈地膨胀,全身发冷,两行热泪涌出了眼眶。她万万想不到,在她清早离家时,丈夫还是好好的,一转眼就隔着生与死的鸿沟。endprint
等董边的情绪稍稍安定,安子文问道:“他临死前跟你说过些什么话?”
“我一点也不知道他会去死。如果我稍微察觉他有死的念头,我就不会去上班了!”董边如实回答道。
安子文也长叹一口气,心情显得非常沉重,对董边说道:“我陪你一起去看一看他。”
在安子文、汪东兴的陪同下,董边一脚高一脚低地朝“喜福堂”走去。那里跟刘少奇西楼办公室只一箭之遥。
董边一走进家门,便看到院子里站着三四个解放军战士。显然,因为家中发生了意外事情,解放军战士来看守现场的。
董边走进图书室,田家英已被放下来了,躺在两排书架之间的地上,身上盖着他平时用的灰色的被单。董边弯下身子,看见他双眼紧闭,但舌尖伸出嘴外。
“你立刻离开中南海!”董边正处于心灵的巨创剧痛之际,接到了这样命令式的通知。
董边无法在丈夫的遗体旁再多看几眼,便只好来到正房。一走进去,就看见桌子上放着丈夫的手表——他在离别这个世界前,从手腕上取下,留给妻子的。
田家英留下了遗言。他写下振聋发聩的话:“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
董边以为是要她暂时离开这里,匆匆拿了牙刷、手巾和一点零用钱,就像平常出差似的,拿着一个小包上了汽车。她压根儿没有想到,她从此就永远离开了这个地方。
“曲生何乐,直死何悲。”田家英“直不辅曲,明不规暗,拱木不生危,松柏不生埤”的浩然正气,贯长虹,惊天地。他的死,是对那正在席卷全国的“文革”狂澜的强硬抗争。虽然英年早逝,可悲可叹,但是他“直如朱丝绳,清如玉壶冰”,永远活在千千万万人民的心中。
田家英是一个没有城府,喜怒形于色的人。他因为接到久别的妻子的一封信,会当众高兴地哭起来。当他蒙受诬陷,他又一怒而以死相抗。他不会掩饰,不会屈膝,也不会忍耐。他离世之际,不过44岁,正值年富力强、生命之花最为茂盛的时候。
田家英夫人被逐出中南海
逝者撒手离去,生者备受煎熬。
汽车离开中南海,在北京城里东拐西弯,驶入了丰盛胡同,把董边送入中央直属机关宿舍。董边一进去,吃了一惊,她的三个孩子已经在那里!
本来,董边和田家英住在中南海“喜福堂”,那里属于乙区,是首脑人物的住地。他们的孩子则住在中南海东八所。孩子们正在上中学。可是,如今连孩子也被逐出中南海,临时搬入中直机关宿舍。
孩子们不知道家中发生了什么事情,董边也不便对他们说。孩子们住在一间屋里,董边被安排在另一间屋里。
董边失去了行动自由,处于软禁状态。
孩子们觉得奇怪:“妈妈,你怎么不去上班?”
“我在家里写文件。”董边搪塞道。
在那些痛心疾首的日子里,先是安子文在他的办公室里,单独约见过董边;接着,安子文、王力、戚本禹这三人小组,又找董边谈了一次。
在万分郁闷之中,在孤寂烦乱之中,董边的心灵受着折磨。据告,田家英是犯了“篡改毛主席著作”的“大罪”。据指示,她必须彻底“揭发”田家英
手中的笔重千斤,董边没法写“揭发”材料。幸亏她向来豁达、乐观,这才没有被逼疯、逼死。
如此这般过了一个月,董边接到通知,让她回原单位——全国妇联去。当时,她担任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中国妇女》杂志社社长。
就在董边准备去全国妇联的时候,一大群人来“请”她了!她被拉上汽车,直奔全国妇联。
呵,全国妇联可热闹,从一楼到四楼,全是大字报。更准确地讲,全是批判董边的大字报。
董边被软禁在全国妇联的一个小房间里。每天,她要拿着一个本子,一边看大字报,一边摘录。她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中国妇女》杂志上“贩卖封、资、修黑货”。
在大字报所揭发的种种董边“罪行”之中,最耸人听闻的一条是:让外国人侦察中南海的地形!
那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董边在国外访问时,一家妇女杂志的主编在家中宴请她。后来,那位主编访华,董边以同等的礼节相待,在家中宴请她。于是,那位主编来到中南海,被说成是“侦察”中南海的地形。事先,董边向领导部门请示过,何况那位外宾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当时与中国关系十分友好。再说,中南海也并非外国人莫入的“禁区”。
在那荒唐的岁月,一张又一张荒唐的大字报编造着荒唐的谎言。董边被关在一间黑洞洞的汽车库里,三天两头接受批斗。
最为荒唐的一幕,发生在1968年6月,董边遭到了激烈的批斗。这一故事,简直足以收入“‘文革笑话集”。
那时,“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即“军宣队”)要进驻全国妇联。“军宣队”队员大多数是男的。在全国妇联,“文革”中女厕所常用,而男厕所几乎关闭。因为妇联工作人员是女的,关起门来搞运动。董边是“牛”(即“牛鬼蛇神”),干最脏的活,打扫厕所成了她每日的“任务”。为了迎接“军宣队”的到来,董边奉命清扫男厕所。打扫毕,董边为了让“军宣队”来到时厕所千千净净,就把小便瓷斗用报纸糊上,到时再取下报纸。糊的时候,董边只留意报上有没有照片。
糊好之后,董边闯下大祸——因为有人发觉,报纸上印有“红太阳”字样!
于是,“军宣队”进驻后的头一炮,就是批斗董边!十年“文革”,董边过了十年非人的生活。
(摘自中华书局《历史的注脚》)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