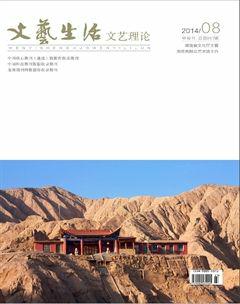悲情城市的印象
曾岚
(国际关系学院基础部科技与文化教研室,江苏 南京 210039)
悲情城市的印象
曾岚
(国际关系学院基础部科技与文化教研室,江苏 南京 210039)
读着朱天心的文章,总能想起王安忆来,在她们的小说中你都会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历史忧郁感。两位作家如同法国现代作家玛格丽特·杜拉丝在她的小说中创造的那个“令人不安、具有传染性的病态世界”一样,描绘出两个病态的城市——台北和上海。贯穿两位作家近期作品的忧郁和哀悼之情,揭示的正是他们共同承担的政治文化潜意识,是她们对历史经验与记忆极其相似的探寻和挪用。因此将朱天心和王安忆关于城市的作品放在一起阅读,尽管都浸透着对故都的哀悼悲情,尽管都有一种摆脱了青春期的宽怀和细密,但还是能分辨出她们各自的历史渊源和思考纬度来。
朱天心;王安忆;悲情;台北;上海
读着朱天心的文章,总能想起王安忆来,在她们的小说中你都会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历史忧郁感。她们“也许都在书写一个不再年轻、不复有激情的时代;中年人那种日渐压抑下来的对向往的向往,成为这两位作家几乎同龄的作家共同的叙事视角和抒情缘起。她们同样以一种兼叙兼议的笔触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当代城市(台北和上海)同样成为她们探索历史和记忆的一大契机,甚至连她们的创作历程,都可以说有某种相互映照的同步变奏。”①两位作家如同法国现代作家玛格丽特·杜拉丝在她的小说中创造的那个“令人不安、具有传染性的病态世界”一样,描绘出两个病态的城市——台北和上海。
90年代王安忆写出了很多很棒的小说,在《香港的情与爱》里,王安忆细腻地探讨消费大都会里的情感生活,叩问真正的依恋是否可能,“在貌似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世界下面,常常涌动着一股视现在为已经发生了的过去的哀伤”。②1977年就以短篇小说集《方舟上的日子》而成名的朱天心,作品却不多,可是每一部都能引起很大的反响,近年来,最成功的应该是她1997年写得中篇《古都》,朱天心晚近的小说除了被形容为“都市人类学”或“新人类学”外,又被称为“百科全书小说”。这一特点在《古都》里尤为明显。的确,朱天心自己想做的,似乎更是一个人类学家。
王安忆在《长恨歌》中写道:“只有鸽子看见了。这是四十年前的鸽群的子息,它们一代一代的永不中断,繁衍至今,什么都尽收眼底……它们盘旋空中,从不远去,实在向着老城市致哀。在新楼林立之间,这些老弄堂真好像一艘沉船,海水退去,露出残骸。”③她仿佛已经找到了一个借助悲伤或忧郁进入历史深度的通道。历史忧郁是王安忆所创作的伤心故事的根源和内容,看她的《伤心太平洋》,就能很明显的体会到这一点。它表达了作者在意识到一个世纪即将结束和新世纪即将开始时,对20世纪中国历史,尤其是人文历史,所抱有的深刻复杂的矛盾感情。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即是一篇对知识分子的角色和文化使命的重新追问的文本。作者自称包含着“对一个时代的总结与检讨的企图”。在小说中,王安忆残酷得粉碎了“五四”以来传统的对知识分子的表述,层层拨开了一个神话般的知识分子的偶像。叔叔的“现实生活不再是真实的,而是为小说创造素材,艺术才是他全部的真实的生活。”她尖刻的将启蒙的知识分子幻想加以击破。
既是文学评论家,亦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及比较文学研究所教授的王德威曾经描述王安忆创作的三个特征,分别是对历史与个人关系的检讨;对女性身体及意识的自觉;对“海派”市民风格的重新塑造。其创作和探源的据点很多时候选择在了上海,一个由外来者汇聚而成的都会,一个不断迁徒、变易和遗忘历史的城市。
在朱天心的作品中,往往会关注现代都市的发展对传统生活空间的破坏。朱天心在她的《古都》中写:“那时候的天空蓝多了,蓝得让人老念着那大海就在不远处好想去……那时候的体液和泪水清新如花露,人们比较愿意随它要落就落……那时候的树……存活得特别高大特别绿,像赤道雨林的国家。”在《古都》里这种“超现实”与“现实”的巨大落差,让故事的主人翁不胜感慨,放声大哭。小说中对比日本京都与台北两个城市,叙事者(也可当作作者自叙)对于永恒不变的京都的情感认同竟然要强过对于生长地台北,只因台北的变幻莫测(地理空间以及政治方面)并且善于将过往的种种历史痕迹毫不留情的予以摧毁。书中以《匈牙利之水》和《古都》两篇浮现出朱天心对于族群问题的思考。《匈牙利之水》里描述两个中年男子——我和A如何以味道为索引,回忆出被埋没久远的往事。两个人原本只是夙面之缘,却因为A对“我”身上香茅油味道所勾引起的亲切回忆,而结成共同忆旧的好友,有趣的是A是本省籍,而“我”则是外省籍,两人的回忆因此交织结构出台湾过去农村与眷村的历史。中年男子不再是能够习惯和别人吐露心事的年纪,他们意外的因为共享了过去的记忆而成为莫逆之交,并共同为了彼此最为记挂的事情做约定,A在报上悬赏绝版香水以求能回忆起婚前女友的模样,“我”则是写好了一份广告寻找小时候眷村的童党,以备发生不测时能刊登。《古都》的内容约可分为三部份,先是“我”对于少年时期以及和此时期分不开的台北地景记忆,中间一段“我”为了和多年未见的友人A会面而在京都盘桓数日,后则叙述提前返台的“我”拿着日本的台湾殖民地地图,假装自己是个游客在重访台北同时也温习了台湾近代历史发展。
青春是至高无上的,中年逐渐腐败,那么生命的终点站死亡在朱天心笔下又是什么情景呢?在《匈牙利之死》的A念念不忘探讨死亡的主题,就像“我”对A会产生的疑问一样,读者不禁也要问为什么朱天心对于死亡是这么的念念不忘,小说中引用某个作家的说法,“死亡,就是我加上这个世界再减去我”,如果死亡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回事的话,那么A为什么念念不忘死去的舅妈,甚至努力的保存能够想起舅妈的香味,也就是说人死了不是干干净净一走了之,没有了具体的物质性的存在,但还有留给生者无限的记忆啊!《古都》中处处流露着对于似乎永恒不变的京都的依恋,隔着几年没去,清凉寺还在那里,甜食店的老板一样亲切的招呼,甚至连池里的鲤鱼也还在。所以京都对叙事者的意义超过了台北,“因为唯有在你曾经流下点点滴滴生活痕迹的地方,所有与你有关的都在着,那不一定它们就会一直一直那样在下去,那么你的即将不在的意义,不就被稀释掉了吗?”
贯穿两位作家近期作品的忧郁和哀悼之情,揭示的正是他们共同承担的政治文化潜意识,是她们对历史经验与记忆极其相似的探寻和挪用。朱天心所探寻的是台北这座见证了荷兰殖民者、明清朝廷、日本人半个世纪的占领、国民党统治,同时她以内心对白反照出一个都市人层层叠叠的生存空间,一个不断引起伤痛、激起想象和回忆的现代大都市。王安忆在1993年反思道,在商业化的浪潮中不是所有的人都该作弄潮人,面对下海的喧嚣,应该有一些孤独的灵魂,他们对社会的反应是沉思性的,而不是出自本能的或自发的。因此将朱天心和王安忆关于城市的作品放在一起阅读,尽管都浸透着对故都的哀悼悲情,尽管都有一种摆脱了青春期的宽怀和细密,但还是能分辨出她们各自的历史渊源和思考纬度来。
注释:
①唐小兵著.英雄与凡人的时代——解读20世纪.上海文艺出版社.
②朱天心著.方舟上的日子.上海文艺出版社.
③朱天心著.威尼斯之死.四川文艺出版社.
I206
A
1005-5312(2014)23-001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