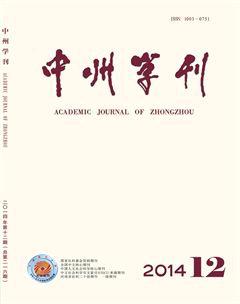海峡两岸女性家族小说的叙述者干预与叙事伦理
王萌
摘要:在中国海峡两岸女性家族小说中,叙述者干预主要分为对话语的干预和对故事的干预两种方式。二者最基本的区分在于“是否削弱小说之结构”。叙述者干预是一种极为常见的叙事技巧,大多受到中国古典传统戏曲和小说的影响,且部分地融合了西方现代小说和电影的理论与技巧,与所讲述的故事往往密不可分。叙述者干预对小说伦理意蕴的展现和读者的伦理取位均起到重要导向作用,有助于读者更好地把握与理解故事和人物。
关键词:海峡两岸;女作家;家族小说;叙述者干预;叙事伦理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4)12-0163-04
一
在中国海峡两岸女性家族小说中,叙述者干预主要分为对话语的干预和对故事的干预两种方式,二者最基本的区分在于“是否削弱小说之结构”①。先讲第一种方式,即叙述者对话语的干预。这一干预方式是最悠久、也最常见的干预方式,在中外古典小说中被普遍使用,通常较为简单、直接,多是为了烘托氛围,或预设价值立场和伦理判断,以引出故事。如蔡素芬《烛光盛宴》第一节的开场白,除了能够营造出一个让叙述者与读者直接交流的叙事场和为故事预设一个感伤的情感基调之外,最重要的一点,是由落叶引出叙述者“我”八岁那年去大姑家吃喜酒的故事:
深秋,叶子很轻易离枝飘落。也许你走在路上行经一棵树下,枯黄的叶子从你耳边飘过,落在你肩上,又弹滑到脚尖。你盯着那行进的脚尖闪过一缕枯叶的影子,已经这些年了吗?②
盛宴之后往往是长久的孤寂,而年幼的“我”在热闹喧嚣的盛宴之中已经备感寂寞,因而离开宴席,独自去林中看树叶。其后陆续出现在故事中的人物菊子、白泊珍、刘德、庞正大陆的妻子,等等,无一不是在孤单落寞中去迎接生命的终结。从故事的大幕拉开直到结束,“我”始终无法摆脱孤寂的心情,故事也因而一直伴随着一份感伤情怀。
置于作品开头或作品章节开头的卷首引语,更是一种常用的对话语的干预方式。表面上它似乎游离于故事之外,但实际上它与故事和人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与叙述者的价值立场和伦理判断密切相关。
徐小斌《羽蛇》开篇所引用的“世界失去了它的灵魂,我失去了我的性”③这句话,源自德国剧作家恩斯特·特勒的悲剧《亨克曼》。该剧讲述亨克曼由于战争失去了性功能,因不堪忍受社会的压迫和友人的羞辱,最终自杀身亡的悲剧故事。澳大利亚女权主义运动家杰梅茵·格里尔在其代表作《女太监》一书中,选用此句作为综述部分的卷首引语。该书指出,女性时刻被传统男权思想囚禁于精神牢笼之中,逐渐丧失了原有的活力,从而变成“被阉割的人”,即“女太监”。如此一来,《羽蛇》对此句的引用就有了双重意义:既有原作所蕴含的悲剧意味,又带有鲜明的女权主义色彩。书中所讲述的是一个家族五代女性曲折跌宕的命运故事,她们的悲剧无不与性爱有关。而更为可悲的是,在历史风云的变幻中,家族内外的男性都是在缺席者或者无能者之间进行选择,是女性用生命撑起了家族和男人的天空。同时,这句话也是女主人公陆羽悲剧命运的写照。充满灵性、与俗世格格不入的她,后被切除脑胚叶而成为一个符合家族期望和社会规范的所谓“正常人”。她用生命爱着烛龙,但烛龙却没有勇气也没有力量回应她的爱。陆羽最终的离去,或许不是死亡,而是从无望尘世的一种彻底解脱。显然,这一引语高度概括了故事的核心内涵,为读者指引出一个明晰的理解方向。
方方《祖父在父亲心中》的开篇引语,出自屈原的《天问》:
何阖而晦,何开而明?
角宿未旦,曜灵安藏?
天门关闭为什么会天黑?天门开启为什么会天亮?东方角宿还没放光,太阳又藏在哪里呢?或许每个人在年少时都曾有过类似的疑问,这是一种非常古老原始而又简简单单的问题,将其与叙述者对中国两代知识分子的成长困惑相联系,则格外发人深省:“我”的祖父和父亲都是才华横溢、清高迂阔的知识分子,祖父悲壮英勇地牺牲于日本鬼子的刺刀之下;而父亲却在一次次政治运动的挤压之下,成为一个谨小慎微、战战兢兢的庸人。引语反衬和强化了故事中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退化的悲剧性与荒诞性,给读者更为强烈的震撼力。
在张抗抗的《赤彤丹朱》中,从第十五章到第二十章,每章开篇都引用了真实作者的父亲张白怀(故事中化名为张恺之)在民国时期担任《当代晚报》总编时,为专栏《朝花夕拾》所写的时事杂评。叙述者试图以此方式混淆虚构世界与真实世界的界限,以强化故事的真实感。
张洁《无字》(第一部)的开篇方式也与之相似,将故事人物吴为与真实存在的、读者正在阅读的小说相联系,从而营造出一种亦真亦假、真假难辨的阅读氛围:
尽管现在这部小说可以有一百种,甚至更多的办法开篇,但我还是用半个世纪前,也就是一九四八年那个秋天的早上,吴为经过那棵粗约六人抱的老槐树时,决定要为叶莲子写的那部书的开篇——
“在一个阴霾的早晨,那女人坐在窗前向路上望着……”
只这一句,后面再没有了。④
此外,脚注也会被叙述者用来对话语进行干预。如铁凝《笨花》的脚注主要涉及历史人物和方言的解释;陈玉慧《海神家族》中的脚注多是把故事正文中的闽南语翻译为普通话,其目的都是为了方便读者阅读。
二
第二种干预方式,是叙述者对故事的干预。叙述者对故事的干预通常有解释、判断和概括三种形式。“解释”是对主旨、关联性或某故事要素之意义的公开说明;“判断”表示道德的或其他的价值观点;“概括”则从虚拟世界向外指向现实世界,无论是指向“宇宙真理”还是指向实际的历史事实。⑤由于叙述者对故事的干预常常散布在作品各处,直接与人物和事件相关联,所以对读者伦理取位的影响较大。
与其他类型小说相比而言,家族小说中人物的伦理境遇一般更为复杂多变。为了达到“控制读者的反应,消除读者理解方面的不必要的障碍,努力使读者心甘情愿地认同和接受自己所叙写和表现的一切”⑥的目的,叙述者解释性和判断性的干预在海峡两岸女性家族小说中常常会大量出现。
丁玲的《母亲》在讲述守寡后的曼贞不满并尝试改变自己的生活现状时,多次使用叙述者干预,反复叙述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对她的禁锢和戕害:
……尤其使她不甘服的,就是为什么她是一个女人。她并不怕苦难,她愿从苦难中创出她的世界来;然而,在这个社会,连同大伯子都不准见面,把脚缠得粽子似的小的女人,即使有冲天的雄心,有什么用!……⑦
以此突出曼贞从“三从四德”的旧女性到求学革命的新女性转变历程的艰难,使读者更能深刻地感受到其挑战世俗、勇于进取之心。
於梨华《梦回清河》中的叙述者干预则偏爱在定玉和美云之间形成强烈对比,使两个反差巨大的少女形象鲜明立体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以此造成读者情感的跌宕起伏。比如美云的形象基本上都是由叙述者“我”,也即女主人公定玉眼中呈现给读者:
……她是可以为她所要的、为她所爱的对象做任何事。可以为它而死,这是她的专诚,她的高人一筹的品质,是我所做不到的,所没有的东西。我能了解这种高贵专一的品质,但是我不能了解为什么她会有。因为我知道她有,而我自己没有却也永远不会有。所以我才恨她,恨得想把她立即置于死地。⑧
从仇恨者的眼中,更能凸显美云的善良和忠贞。美云被残害致死的悲惨结局,当然也使读者感到格外痛惜和愤怒。与此同时,定玉的心理畸变也在此中暴露无遗。原本只是刁蛮任性的她,因为自己家庭的不幸和大家族的黑暗,无法向上提升自己的人格,也不能容忍别人拥有完美人格和高贵品质。于是,她便一厢情愿地以为将其毁灭就能换取自己生活的舒心,结果却是铸成大错。当她感到后悔时,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
蒋韵《栎树的囚徒》在为范氏家族四代女性谱写的一曲绚丽而又悲惨的命运咏叹调进入尾声时,叙述者指出了从陈桂花到段金钗、关莨玉,再到苏柳、贺莲东,最后到悯生、天菊,这些女性抵御男权社会压迫和历史风云变幻莫测的两种生存方式:
……我想起我们家族的女人,她们有多少是用“死亡”这种方式摆脱了生命的困境。她们选择了死来保存了生的自尊。她们是一些美丽而易折的乔木,构成了我们家族树林的重要景观。而我们,苟活者和幸存者,则是她们脚下丛生的灌木和蒲草。我们永没有她们那种身披霞彩的千种风情;而她们,则不如我们——坚韧。⑨
无论是惨烈而刚强地拥抱死亡,还是坚韧而卑微地活着,虽然都是无法摆脱的悲剧命运,但是叙述者的总结为其染上一抹亮色,凸显范氏家族女性的勇气和力量,使故事避免陷入悲惨的泥淖,或能部分地调整读者压抑和悲伤的阅读情感。
与此同时,叙述者判断性干预还会以一种反讽的口吻,出现在海峡两岸女性家族小说中。如此一来,读者就需要从叙述者相反的角度去理解。
在施叔青的《风前尘埃》中,叙述者对和服所代表的一种战争暴力美学的判断性干预,也是颇为典型的例子。“二战”期间,日本政府将战争宣传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服也未能幸免,沦为宣传军国主义的工具之一。枪炮、轰炸机、坦克、战舰,以及日军在中国大陆、南洋各地的侵略战争场面,等等,都被设计成逼真的图案,织在和服上,从而“将战争美学化,枪炮机关枪的焰火,兰花一样点缀在烧焦的草原上,轰炸机投下的炸弹升起螺旋状的浓烟,也被处理得如烟似幻”。在这些细致的描述之后,叙述者紧接着一句:“战争是美丽的。”⑩此话原本出自法西斯作家之口,仅从字面意思来看,叙述者好像是赞同此话,其实不然。综观全书,叙述者的态度与此话所表达的意思截然相反是显而易见的。叙述者引用此话,意在让当下的人们关注和警惕战争暴力美学对普通民众的裹挟与洗脑,警惕军国主义借助各种形式再次复活。
除此之外,叙述者的概括性干预在海峡两岸女性家族小说中也颇为常见。这是一种超越虚构作品的世界而进入现实世界的一种哲学言论,它将故事中的事件与现实世界中的事件的某一面加以比较,所说的属于人所共知、普遍认同的“一般真理”。这一干预尽管是由故事所引发的,却都可以从故事中单独抽离。
王安忆《伤心太平洋》中由“我”父系家族成员的漂浮感和孤独感,推及全体人类的生存和精神困境:“地球上的所有陆地,全是海洋中的礁石,供人类栖身。人类其实是一个飘流的群体,飘浮是永恒的命运。”如此概括,故事就从具体的人物和故事上升到抽象的哲学思辨,令读者强烈地感受到超越时空的历史沧桑感和浓厚的哲学意味。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里,维克特打猎时误杀了弟弟安道尔之后,痛苦不堪。叙述者以“世界上没有哪一道伤口是永远不能愈合的,虽然愈合后在阴雨的日子还会感觉到痛”来做总结,在平实语言的背后,隐藏着无以言说的内心伤痛。任何有过创伤体验的读者可能对此都会感同身受,唏嘘不已。而萧丽红《千江有水千江月》在贞观丧父后、失踪多年的大舅即将返家之时,叙述者借贞观之口表达了一段有关生死的慨叹:
死生原来有这样的大别:死即是这一世为人,再不得相见了——而生是只要活着,只要一息尚存,则不论艰难、容易,无论怎样的长夜漫漫路迢迢,总会再找着回来。
质朴的语言简单明了地点出生与死的根本不同,悲痛感伤和无可奈何的情感溢于言表,直抵人的灵魂深处,强化了故事的情感力量,势必能引发不同时期不同地域读者的共鸣。
三
在海峡两岸女性家族小说中,还有一种干预方式,介于话语和故事的干预之间,就是括号加注。单就这一方式本身来说,它属于话语干预的形式之一,但是其内容又往往与故事和人物密不可分,类似于叙述者的解释性干预。如萧红《呼兰河传》中括号加注的使用。括号里的内容多是与故事发展密切相关,其中有解释的意味,但更重要的是叙述者为了强化反讽的效果。老胡家为小团圆媳妇治病、在大庭广众之下给其洗澡事件中的括号加注就是如此:
(这种奇闻盛举一经传了出来,大家都想去开开眼界,就是那些患了半身不遂的,患了瘫病的人,人们觉得他们瘫了倒没有什么,只是不能够前来看老胡家团圆媳妇大规模地洗澡,真是一生的不幸。)
该处如果没有括号,其实根本不会影响故事前后的衔接,也不会影响文本的协调;但是加上括号却使此段内容显示得更为突出,更为强烈地传达出叙述者对冷漠看客的嘲讽之意。
当代海峡两岸女性家族小说中,括号加注的方式使用更为普遍,尤其是台湾的女作家对此较为偏爱。李昂的《鸳鸯春膳》和陈玉慧的《海神家族》比较有代表性。在《鸳鸯春膳》中,括号加注的方式频繁出现,如以“蕃薯”影射台湾地位变化:
……蕃薯被岛屿住民普遍认为是十分低贱的食物,穷人用以果腹的主食,蕃薯叶子用来养猪,蕃薯吃后容易放臭屁极为不雅。由于多年来的外来政权统治,岛民称外形近似蕃薯的台湾岛屿为“蕃薯仔岛”,自称作“蕃薯囝仔”。
(半个多世纪后,有卫生组织经三年研究,认为蕃薯含丰富的维生素又能抗癌,评选为“十大健康食物”之首。)
括号里的内容是由故事所引发,但是又与正在发生的故事本身无直接关系。若直接出现就显得故事行文颇不协调,采取括号加注的方式既能够避免这一弊端,又可以达到叙述者的目的。而且括号内外的内容形成强烈的反差,令读者极易产生世事无常的慨叹。
《海神家族》中静子自幼对母亲绫子的偏心就极为不满,直到母亲去世之后依然不能释怀:
……静子母亲说,哪有,她只打我,她从来不打别人,不打她的心肝儿子,也不打她的心肝小女儿,只有独独打我(静子母亲说时连自己也忘记她曾多么用力地打过我)。
括号里的内容提到静子打女儿“我”的事情。静子记恨母亲绫子,而她不知不觉中又让悲剧在自己的女儿身上重演,母女之间的恨意远远超过了爱。静子年少时即叛逆出走,一生遭际坎坷,而“我”也步了母亲的后尘,离家出走,远渡重洋,直至20年后才返家。此处采取括号加注,在不中断故事连贯性的前提下,揭示出林家女性悲剧命运的一再重演,但可悲的是悲剧的制造者自己却不自知。叙述者“我”对林家女性命运的无可奈何之感,就此清晰地呈现给读者。
叙述者干预在海峡两岸女性家族小说中,往往融合了中国古典传统戏曲、小说以及西方现代小说的理论与技巧,是作品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好地承担了建构作品叙事伦理的责任。此外,它还起到了修辞手法应有的装饰性目的,使作品叙事结构更为独特与合理,也更能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进入21世纪之后,海峡两岸女性家族小说中的叙述者干预的形式更为灵活多样,成为一种越来越受创作者和研究者重视的叙事策略。
注释
①⑤[美]西摩·查特曼:《故事与话语:小说和电影的叙事结构》,徐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33、213页。②蔡素芬:《烛光盛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第4页。③徐小斌:《羽蛇》,《徐小斌文集》(第1卷),华艺出版社,1998年,第3页。④张洁:《无字》(第1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页。⑥李建军:《小说修辞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65页。⑦丁玲:《母亲》,《丁玲文集》(第1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65页。⑧於梨华:《梦回青河》,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162页。⑨蒋韵:《栎树的囚徒》,《收获》1996年第5期。⑩施叔青:《风前尘埃》,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243页。王安忆:《伤心太平洋》,《王安忆自选集》(第3卷),作家出版社,1996年,第383页。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214页。萧丽红:《千江有水千江月》,漓江出版社,1987年,第117页。萧红:《呼兰河传》,《萧红全集》(上),哈尔滨出版社,1998年,第223页。李昂:《鸳鸯春膳》,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7年,第61页。陈玉慧:《海神家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1页。
责任编辑:行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