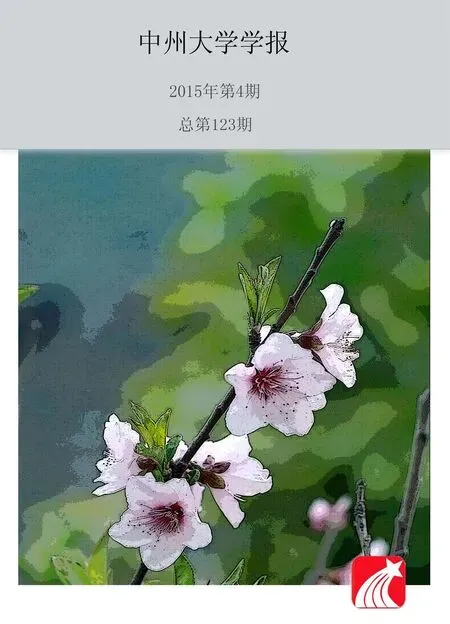《革命之路》:通向人性与政治的乌托邦
《革命之路》:通向人性与政治的乌托邦
陈演池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中文学院,广州 510420)

摘要:《革命之路》通过惠勒夫妇的浪漫爱情和人生追求,巧妙地展示了“美国梦”的内在悖论以及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社会的危机:社会现代性的负面效应给人带来了新的异化和奴役,使其无法在既定秩序同质化的生活追求中获取个人独特的存在意义。作品预示了1960年代席卷整个西方的激进运动的来临,同时也深刻地揭示了现代人的存在困境与社会政治革命之间的内在关联。
关键词:《革命之路》;“美国梦”;乌托邦;现代性
收稿日期:2015-05-20
作者简介:陈演池(1986—),男,广东怀集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文艺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学批评、文学观念史研究。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5.04.010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5)04-0050-05
《革命之路》是小说,也是电影。小说发表于1961年,作者是理查德·耶茨;电影于2008年底在美国上映,导演是山姆·曼德斯。虽然时间相隔了近半个世纪,但电影仍忠实于小说,并删繁就简,更集中地表现了小说主旨。因此,本文将小说和电影视作同一个文本,皆以《革命之路》名之,并在电影和小说之间互相阐释。[1]
故事发生于1945年后的美国。二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对抗苏联,援助欧洲,成为资本主义最令人向往的国度;而“美国梦”也再次成为美国人孜孜以求的最大梦想。不过,《革命之路》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却不是“美国梦”的组成部分,相反,是对“美国梦”的唾弃和反抗。
我们看看热恋中男女主人公的一组对话①:
弗兰克:你去过巴黎吗?
爱波:我哪儿都没去过。
弗兰克:那么或许有一天我带你去。只要一有机会我就会回去。那里的人都朝气蓬勃,不像这里。我最想做的事,就是感受这个世界,真正地感受,你懂吗?这个雄心壮志怎么样?
爱波:弗兰克·惠勒,你是我见过的最有意思的人。[2]
富于浪漫蒂克的表演系女生爱波,热烈地爱上了同样富有幻想的哥伦比亚大学男生弗兰克。后者不仅和她有着共同的理想,而且机智风趣、洒脱不羁,更有着奔赴欧洲参加二战的光荣经历。“你是我见过的最有意思的人”,吸引爱波的不是附着在弗兰克身上的“美国梦”,而恰恰是他对“美国梦”的抵制,是他的那个“雄心壮志”——“有一天我带你去(巴黎)”。然而,后来爱波的意外怀孕,打乱了他们原来整个的生活节奏。从那一刻开始,生活就由一连串他们不想要的事情组成:他们不得不安顿下来,最终搬到了郊外“革命路”上的“革命山庄”一带的小区。
“革命路”上的“革命山庄”,生活安宁、温馨和富足,是标准的“美国梦”的一个缩影,正好与“革命”的精神相悖。这种强烈反差一方面表达了作者对当时美国社会现实的批判,另一方面也承载了1776年的“革命”记忆,象征着新时代“革命者”的再出发之地。当然,对于弗兰克和爱波来说,“革命”已远离了战火硝烟,甚至远离了集体生活,而是他们对“美国梦”的离弃。这当然不是他们两人的孤立行为,而是那个时代追求个人价值和变动不居生活的年轻人们的普遍要求。诚如耶茨所说:“20世纪50年代,人们对循规蹈矩有着普遍的渴望——一种盲目的、不惜代价的对安全安稳的依恋——这不只发生在郊区而已。艾森豪威尔的执政和麦卡锡主义就是这种渴望在政治上的体现。然而,很多美国人对这一切感到不安,认为这是对美好与勇气的革命精神毫无疑义的背叛——这种精神就是笔者试图注入爱波这个人物的。这个书名想要说的是,1776年的革命之路,到了20世纪50年代就仿佛走到了尽头。”②
而住在“革命之路”、怀有“革命”梦想的年轻的惠勒夫妇,恰恰经历了这种始而离弃、终而回归的过程。婚后,像其他所有人一样,弗兰克不得不找一份稳定的、但对他来说是无聊至极的工作来养家糊口。令人讽刺的是,他任职的公司正是当年他父亲所供职的公司,一向鄙视并反叛父亲的弗兰克,正轮回到父亲那循规蹈矩、呆滞无趣的生活之路上。同样,爱波也沦为相夫教子的全职家庭主妇,在抑郁之中脾气越来越坏,夫妻俩经常莫名其妙为一些很琐碎的事情吵架。追求浪漫、变动和独特的爱波明显感觉到,他们这对“特别”的情侣也如千千万万人一样,被淹没在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之中,个性、激情和理想也逐渐被日常的琐碎所消磨。为了挽救他们岌岌可危的婚姻,重拾热恋时期的理想,爱波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让弗兰克把工作辞掉,把房子卖掉,全家人移居巴黎,由她来工作养家,到时候弗兰克就有充分的时间和自由去寻找真正的自我,去从事他最想做的事情。
就在时候,曾经感觉彼此特别一致而一见钟情的惠勒夫妇,开始暴露了他们之间的分歧和“错位”。一向洒脱不羁的弗兰克听了爱波这个异想天开的计划之后,虽然表面上嘲笑它不切实际,但“其实他是在向她掩饰——或许也是在向自己掩饰,他对这个计划感到强烈的恐惧”[1]96。接着电影中出现了这一幕对话:
爱波:让一个才华横溢的男人做着他无法忍受的乏味工作,下班后回到一个他无法忍受的地方,还有和他一样无法忍受这一切的妻子,这才是不切实际的!你知道最糟糕的是什么?这一切都是基于一个前提:我们认为我们与众不同,我们比他们强,但我们不是,我们和别人一样。看看我们,我们都陷入了同样荒唐的错觉:一旦有了孩子,就安定下来,就不能再享受生活。我们也一直为此深受折磨。
弗兰克:听我说,是我们自己决定搬来这里的,没有人逼我去诺克斯工作。而且,谁说过我将来就一定是个大人物?
爱波:我刚认识你的时候,这个世界上没有你不敢想不敢做的事情。
弗兰克:你刚认识我的时候,我不过是个爱吹牛的人。
爱波:不是这样的,你怎能这么说呢。
……
爱波:目前的生活,让你束缚了真正的自我,让你真正的自我一再被否定。
弗兰克:我是谁?
爱波:你不知道吗?你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你是个男子汉。
弗兰克被打动了,同意了这个计划,但这也让他陷入恐惧之中——恐惧承认自己“无能懦弱”,恐惧爱波对他的崇拜发生动摇。弗兰克的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当初正是这一点,深深吸引了追求“革命”(拒绝循规蹈矩、追求变动不居)生活的爱波。然而,没有让爱波发现的是弗兰克的“有意思”,他的“特别”,只是他追求的一种效果。他喜欢“特别”的姿态,喜欢让别人感觉他“有意思”,他的“叛逆”和“革命”热情,也只是在一个崇尚“叛逆”和“革命”的青年学生圈子里的精神时尚。这是一个年轻人情不自禁的追求,与其说是叛逆和“革命”(当然有这方面的冲动),不如说是显示一种让人看得见的自我的“重要性”而已。
小说特别表现了这一点。十四岁的时候,弗兰克就曾雄心勃勃地秘密“计划”坐火车去西海岸,但他更按捺不住的是,把秘密告诉了同伴,结果未成行却换来一番奚落。大学毕业后,他偶尔去打一些奇奇怪怪的零工,混迹过格林威治村③,但他的离经叛道主要是为了向他父亲“示威”,因为父亲一生平庸、失败的阴影从小笼罩在弗兰克的心头。有了孩子之后,他选择了这份无聊至极的工作,然后租进高档公寓,再生一个孩子,最后在郊区买了房子,走了一条实现“美国梦”的道路。从“叛逆”到“回归”,似乎循着一个共同的内在逻辑:他要首先满足他在世界上的“重要性”。而无意中回归“美国梦”也不过是为了证明:他是一个有能力、负责任的男人。甚至,他们决定放弃稳定、舒适的生活而移居巴黎,也即放弃“美国梦”时,弗兰克也是迫不及待地把整个计划告诉周围的人——邻居谢普夫妇、房地产经纪吉文斯太太以及他的同事(却不包括上司),因为如此重大的事情只有别人知道了,他才会感到有意义,感到真实。向别人证明自己的重要性和独特性,似乎成了弗兰克生活的全部理由。结婚七年来安稳、优裕的中产阶级生活,实际上慢慢悄无声息地消磨掉了弗兰克当初本来就不太坚实的“个性”和锐气。
但这个决定,却让他们仿佛重获新生,家庭生活出现了久违的和谐与欢乐。不过,焦虑和恐惧很快就把弗兰克从飘飘然中拉回到现实。就在他们筹划移居巴黎的时候,弗兰克获得了一个绝佳的职业发展机会,而爱波又意外怀孕了,他不禁开始了“背叛革命”。于是人们看到,第一次去见总经理的弗兰克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他表现出爱波从来没见过的恭顺神色和孱弱的一面。爱波只看到了他的洒脱不羁和嘲讽一切,他的上司却抓住了他非常渴望得到外界认可和权威赏识的心,他告诉弗兰克:这是一份充满挑战性和满足感的工作,前途无量,非常适合他这样一个出色的男人;也是对他父亲最好的纪念和礼物。这的确对弗兰克构成了致命的诱惑,假如他投入这份工作,将会完全实现他童年以来一直未能实现的“弑父”动机,虽然实际上不过仅仅是在父亲的道路上更加“出色”而已。于是,他不再三心二意,而是彻底地投向了那个曾经被他所唾弃的“美国梦”的怀抱。
是的,“美国梦”在这里受到了挑战。这个原本意指在平等、自由、民主的社会环境中通过个人的不懈奋斗便能实现自我、获得更美好生活的理想,此时则意味着另一种东西。当然,“美国梦”仍然被解释成一种理想,吸引着许多底层人,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人们,“美国梦”对于他们依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然而,对发达工业社会的许多年轻人来说,追逐“美国梦”就意味着对现存秩序的接受和容忍,意味着把自己局限在社会既定的目标和规范里面。接着便是,在看似多样但实则千篇一律的追求中,人逐渐丧失了真正的个性,走向彻底的异化。而且“美国梦”的现实版,又往往指向物质财富的获取和享受,最终完成了“梦”=“物”“梦想”=“物欲”的大众普及过程。
这也迎合了当时美国的社会现实。1950年代,在“二战”的可怕阴影和“冷战”的国际格局之下,正如前面耶茨指出,艾森豪威尔的上台和连任,以及麦卡锡主义的兴起和蔓延,意味着当时美国的政治状况和社会文化在整体上趋于保守,人们普遍在精神和行动上都失去了“革命”的勇气和能力,只会在现存体制的既定秩序之下追逐社会主流文化所提供的目标与理想,不再去想象或追求与现实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生活。这就是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社会”和“单向度的人”[3]。对于当时社会的沉沦、文化的衰朽以及人们的盲目,在小说中作者多次借弗兰克之口表达了他敏锐的观察和深刻的批判。
其实,“美国梦”的内在悖论典型地反映了现代性的两面性:近代以来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一方面将人们从传统和自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极大限度地给予了人们自由和个性的权利和空间,赋予了人们普遍平等的身份地位;但另一方面又会再度把人异化为一个庞大的、高度理性化同时也意味着高度等质化的社会机器的一个工具零件,使人们重新走向了另外一种更为精致、舒适的奴役,再度丧失了个性自我。当时弗洛姆就直截了当地说:“今天所说的‘平等’指的是机器人的平等,也就是失去个性的人的平等。”[4]20身处于这种现代性的桎梏之中,不能不让人感到绝望并且产生逃离、反抗的念头和行动。
爱波这个角色凝聚了小说作者(也包括导演)极大的同情和热切的期望,对比起弗兰克,她是否具备了真正彻底的“革命精神”?其实并不尽然。表面上爱波好像是一个执着于追求理想生活的“革命者”,她向弗兰克强调:人无论多平凡也要寻找自我,过你想过的生活才需要真正的勇气。但她说这话时并没有包括自己。爱波自幼父母离异,被寄养在不同的亲戚家庭,自知没有当演员的天赋,上大学只是为了逃离家庭。她从小就强烈渴望像身边那些学姐一样出类拔萃,但现实却是越来越感到真正的人生正在离她而去。所以,她从一开始就在弗兰克身上投射了过度的想象,把自己的命运和自我超越的任务完全交予了弗兰克。爱波并不把弗兰克的自我实践看作是他一个人的事情,因为它包含着爱波自己的“拯救”。总而言之,弗兰克与爱波之间处于一种想象的“错位”,这样发展下去似乎无可避免要发生悲剧的。
巴黎计划被取消之后,本来彻底幻灭了的爱波只想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平静地与弗兰克扮演一对有名无实的夫妻,但一次激烈争吵之后,爱波痛彻地觉悟了:她没有理由去恨弗兰克,因为他一直没有变,还是原来那个“最有意思的人”。她唯一的错误和不诚实之处,就是在错觉之中让两人的关系一直发展下去。她终于明白,像很多人一样,能够充分展现自我的工作和温馨安逸的家庭生活才是弗兰克最想要的,他非常适合于目前的工作,于是真诚地鼓励他去做好它,不再勉强他携带自己去改变、逃离。爱波痛彻地领悟到一个身边的人从没告诉过她的道理:“如果一个人想要做一件真正忠于自己内心的事情,那么往往只能一个人独自去做。”[1]227这也印证了耶茨的看法:“如果我的作品有什么主题的话,我想只有简单一个:人都是孤独的,没有人逃脱得了,这就是他们的悲剧所在。”[1]6
在作品中,唯一对现实的感受和洞察最为清醒深刻、能够真正理解惠勒夫妇移居巴黎的想法的,是吉文斯夫妇的儿子、疯子数学家约翰。电影中他们之间有一幕精彩的对话:
约翰:像你们这样一对夫妻,怎么想起来要逃离这里了?
弗兰克:我们不是逃离。
约翰:那巴黎有什么地方吸引你们?
爱波: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
弗兰克:或许我们确实是在逃离。逃离这里无望空虚的生活,对么?
约翰:无望的空虚?现在你们终于承认了,很多人都处在空虚之中,但要承认那种无望,确实需要真正的勇气。
……
爱波:你知道吗,他似乎是第一个了解我们想法的人。
弗兰克:是啊,也许我们和他一样都疯了。
爱波:如果疯狂意味着过有意义的生活,我不在乎我们是否完全疯了,你呢?
弗兰克:不在乎。
当弗兰克说到“无望空虚”时,约翰感到相当的震惊,他提到:“在我以前工作的地方,在西海岸,空虚是我们唯一谈论的话题。我们会整晚整晚坐在一起谈空虚。不过没有人说过它‘无望’,这会使我们感到恐惧。”[1]169后来也是他一针见血地揭穿了弗兰克“退缩”的真正原因,并指出了爱波其实还带有孩子的天真和幻想,之后引发了那场激烈的吵架。让人感慨的是,约翰当初只是因为一次与母亲吵架时情绪过于激动,被他的母亲叫来的警察直接强制扭送到精神病院,让他失去了任何的申辩可能和机会。作者把他这样一位清醒而深刻的智者塑造为一个精神病人,极其鲜明地反衬了这个社会的病态和疯狂:为了维持社会的“正常”运作,只好把真正正常的人视为“病态”,从而把他隔离开来。
故事的结局是,爱波因自行流产而死亡,弗兰克带着极为悲恸的心情搬回了市区,虽然如愿以偿得到了新工作,但完全失去了精神活力犹如行尸走肉一般。悲剧过后,父母也基本不带约翰从精神病院里出来,“革命山庄”一带再度恢复了昔日的安宁与和谐。
《革命之路》不单单是巧妙地呈现了“二战”以后美国人“革命精神”的丧失与否以及如何丧失的问题,它还有另外一些更耐人寻味的深层意涵——为何惠勒夫妇不在此时此地、而要通过出走巴黎(浪漫之都、革命圣地)去寻找“特别”的生活、有意义的人生?人为什么期望过一种“特别”的生活,而这个“特别”又要寓于“变动”(“革命”)之中?在前现代,一个人在哪个阶段应该去做哪些事情,基本上都是被外在的传统习俗规定好了的、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人们按部就班地做好这些事情,就实现了他的人生意义。然而,进入了现代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除了前述“现代性”在社会层面的两面性(获得自由与失去个性),它在文化和精神层面的“祛魅”也同样产生了一种两面性的效应,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人的存在条件。上帝死了和天道隐没之后,不再有任何外在先验的超越性力量可以为人的存在意义提供稳定、客观的基础和来源,“近代文明的这个转折,一方面具有强大的解放效果,使人在自然与社会两个领域均摆脱了天赋道德秩序的指导羁绊,另一方面却也赋予个人沉重的责任,因为现在个人必须自行建构价值与目的,为自己的生命找到意义。可是在除魅后的世界里,当宗教之类的传统救赎力量失去作用之后,个人又有什么资源处理这么沉重的课题呢?”[5]88总而言之,当神性或天道从日常生活退出来以后,现代人的生命感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
韦伯对比了古代人和现代人生命感受上的巨大差别,指出:“文明人的个人生活已被嵌入‘进步’和无限之中,就这种生活内在固有的意义而言,它不可能有个终结,因为在进步征途中的文明人,总是有进一步的可能。无论是谁,至死也不能登上巅峰,因为巅峰处在无限之中。亚伯拉罕或古代的农人‘年寿已高,有享尽天年之感’,这是因为他处在生命的有机循环之中,在临终之时,他的生命由自身的性质所定,已为他提供了所能提供的一切,也因为他再没有更多的困惑希望去解答,所以他能感到此生足矣。”[6]29-30因此,像浮士德那种永不安宁、永无止境的追求⑤[7],正是“现代情景”中人的普遍状况,在这种处境下,现代人所追寻的“终极意义”就只能在永远无限的“进步”(变动、革命)之中。惠勒夫妇,尤其是爱波对日常生活感到极度的沉闷无聊,一心追求独特、新异的生活体验,以此获取个人的人生意义,恰切地反映了现代人的存在状态。《革命之路》的精彩之处,就在于它深刻地揭示了现代人的存在困境与社会政治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
如果说惠勒夫妇接受“美国梦”意味着接受现状,忍受空虚无望的日常生活,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假若要否定“美国梦”,“革命”的未来又在哪里?“革命”要指向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才可以让人们心满意足地安顿下来?假设他们真的移居了巴黎,承诺养家活口的爱波整天为工作、家务奔波劳碌,而弗兰克则无所事事地看看书、写写东西,这对他们来说真的有意义吗?巴黎真的是梦想之地,而不是另一个“革命山庄”?当他们的生活在巴黎也进入“新常态”后,他们又会去哪里寻找新的“远方”呢?有意思的是,就在耶茨出版《革命之路》的七年后,巴黎,惠勒夫妇的梦想之地,爆发了“五月风暴”。无论耶茨自觉与否,《革命之路》还是预见了1960年代席卷整个西方的学生运动的来临。
19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是在形而下和形而上双重危机的背景之下爆发的。一方面,反对种族歧视、越战、旧的教育体制,要求更广泛的自由与权利等,这些都是当时人们在现实层面直接具体的诉求。另一方面,在这场运动中,西方原有的价值观念、社会规范以及生活方式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和批判,这说明年青人不再能从原有的价值规范中感受到人生的意义,他们是带着强烈的存在焦虑走上街头和广场的,背后无意识的动机是想通过革命的行动来排遣内心的苦闷和空虚。通过《革命之路》以及其他形式的艺术表现,还有当时人们的一些极为浪漫的口号和行为,都可以看出这一点。马尔库塞成为了这场激进运动的精神领袖,他那本《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也成为青年学生追捧的“圣经”,对这场运动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但是,马尔库塞以及1960年代西方的激进运动继承的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反资本主义”传统,代表的是一种生命情调,没有发展出一套具体可行的社会分析和政治纲领,因此最终受到了现实逻辑的嘲弄。但它在文化价值上的超越性取向,却深深地把握住了当时那些怀有强烈的存在焦虑的年青人的心。[5]26-37《革命之路》的悲剧收场,似乎预见了那场运动最终的黯淡落幕,弗兰克最后的“退缩”,也似乎预示了这场运动过后人们又重新认同和回归了社会主流。
社会政治领域的革命,反抗现实的苦难与不公,改造不合理的社会秩序,往往被人们赋予崇高和神圣的意义。但是当人们投入到革命之中时,往往会在无意识中将自身的存在焦虑投射到其中。因此,近代以来形形色色的乌托邦追求,不仅是出于苦难与不公的抗争,也部分来自于现代人的存在焦虑。后者的功能是企图从整体上回应和超越现代性状况,通过社会的根本变革来一并解决个人的存在问题和社会的正义问题。即一方面通过融入革命组织和集体,参与伟大神圣的正义事业来获得不朽的意义;另一方面,通过社会革命建立一套公平合理的社会秩序,并在此岸创造一个圆满和谐的意义世界,可以让人们最终地安顿下来。无论是1960年代西方的激进运动,还是20世纪的其他革命,在不同程度和层面上都带有这些特征。也许,比起具体的价值观念或者意识形态,现代人的存在困境对于人们的种种抉择和行动的影响更为强烈而根本,也更为隐秘。
因此,《革命之路》对于今天的人们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无论是追求理想生活,还是投身社会运动,首先要求当事者对自身的处境和现实的逻辑有恰切的把握和体认,慎重思考如何才能为个人的生活理想或社会革命理想注入实质的内容,在特定的现实条件下为它们找到可以落实的形式和途径。
注释:
①参见电影中译字幕和剧本,略有改动,下同。
②详见小说《革命之路》的封面。
③美国反主流文化的大本营,聚集着各色各样的艺术工作者、理想主义者等,代表着另一种生活方式。
④转引自小说《革命之路》译序,第6页。
⑤此处援引了诺尔曼·布朗《生与死的对抗》一书的基本观点,此处只是强调布朗所说的“浮士德精神”作为受压抑的人的普遍症状,到了“现代”之后,才成为了人普遍突出的精神特征。
参考文献:
[1]理查德·耶茨.革命之路[M].侯小翊,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
[2]贾斯廷·海西.革命之路[J].张颖,译.世界电影,2010(3).
[3]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4]艾瑞克·弗洛姆.爱的艺术[M].赵正国,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2004.
[5]钱永祥.纵欲与虚无之上:现代情境里的政治伦理[M].北京:三联书店,2002.
[6]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M].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7]诺尔曼·布朗.生与死的对抗[M].冯川,伍厚恺,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刘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