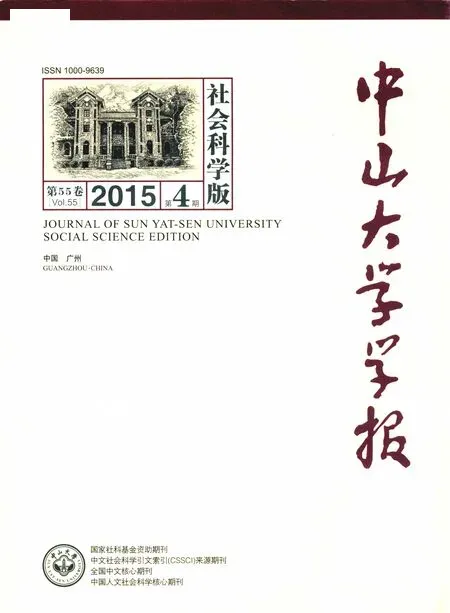晚清岭南学派《论语》诠释特点论*
冯晓斌, 柳 宏

晚清岭南学派《论语》诠释特点论*
冯晓斌, 柳宏
摘要:晚清岭南学派因独特的时代背景、地域文化、学术传承的浸润,其《论语》诠释视野开阔、独树一帜,呈现出融合汉宋、平心求是、开新改制的鲜明特征。岭南学派《论语》诠释铸成古今传承、中西交流的亮丽风景,开启了传统经学转型的风尚,推动了晚清学术现代化的进程。
关键词:晚清; 经学; 岭南学派; 《论语》; 诠释特点
岭南学派源自明代,由著名哲学家陈献章(1428—1500)创立。陈献章是明代心学大师,他创立的“白沙学派”,打破程朱理学原有的理论格局,在明初一潭死水的思想界荡起涟漪,开启了明代学术的新风尚,享有“广东第一大儒”“岭南一人”之誉。
陈白沙开创的岭南学派,由湛若水(1465—1560)等众弟子发扬光大,清代以后经朱次琦(1807—1881)、陈澧(1810—1882)开发崛起,由康有为(1858—1927)推向全国。岭南学派《论语》诠释不别汉宋,平心求是,开放创新。梁廷楠(1796—1861)《论语古解》“毕取汉唐古说”“与宋儒相发明”*[清]梁廷楠:《论语古解·自序》,严灵峰:《无求备斋论语集成》第293册,台湾:台北艺文印书馆,1966年,第1页。,桂文灿(1823—1884)《论语皇疏考证》“证其所长、考其所短”*[清]桂文灿:《论语皇疏考证》,《丛书集成续编》第13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第847页。,潘衍桐(1841—1899)《朱子论语集注训诂考》“窥先圣之微言,穷义理之所归”*[清]潘衍桐:《朱子论语集注训诂考·叙》,严灵峰:《无求备斋论语集成》第245册,台湾:台北艺文印书馆,1966年,第1页。,简朝亮(1852—1933)《论语集注补正述疏》“综合汉、宋,择善而从”*钟肇鹏:《序言》,[清]简朝亮:《论语集注补正述疏》,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第4页。,康有为《论语注》将孔子思想廓清提升为变法思想,用西方进化理论、民主制度等,对《论语》进行创造性的诠释。岭南学派的《论语》诠释适应社会变动,体现出开拓创新精神。
一、融合汉宋
岭南学派源自程朱理学。然而在明初的文化危机中,程朱理学由于居于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而逐渐僵化,故白沙、甘泉遂开辟了有别于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心学传统,但欲与程朱理学彻底疏离显然是异想天开。毕竟宋学在宋元明七百年间趋于极盛,有清以来依然衰而不竭,而乾嘉以来兴盛百余年的汉学已现衰象。
有清一代,从清初诘难宋学空疏,至乾嘉朴学繁荣,经方东树(1772—1851)《汉学商兑》挑起汉宋之争,迄晚清则走向汉宋合流之势。这一趋向与晚清岭南学派近乎一致。朴学是岭南学派的强势传统,阮元(1764—1849)开设学海堂,尽管其实质是以汉学为中心而兼取宋学,但毕竟采取调和汉宋的态度。“东塾学派”虽被认为集岭南朴学之大成,然陈澧中年以后逐渐走出汉学旧辙,强调经世致用,成为晚清汉宋调和思潮的代表人物。朱次琦既反对清中叶汉学考据的繁琐和门户之见,也反对宋明心学的空疏玄谈,体现出鲜明的疏离汉学、融合汉宋的经学思想。
梁廷楠《论语古解》自序云:“毕取自汉迄唐三十余家之说,摘与朱子《集注》异者,依次排纂,汇得十卷,名曰《古解》……”*[清]梁廷楠:《论语古解·自序》,严灵峰:《无求备斋论语集成》第293册,第1页。梁氏为何无视宋代及宋代以后注家之解,独独毕取唐代以前三十余家注疏之“古解”,显然是要提醒人们《论语》之诠释,除了朱熹(1130—1200)之《论语集注》外,还有自汉迄唐的诸家古解,无疑是欲呈现出汉学与宋学互参比勘的诠释版图。故梁氏专辑与《集注》相异之汉唐古解,将《古解》作为朱熹《集注》的对照注本,以倡兴古注、融合汉宋。
梁氏《论语古解》可与《集注》相发明。如,《卫灵公》“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句,《集注》云:“尹氏曰:‘卫灵公无道之君也,复有志于战伐之事,故答以未学而去之。’”*[南宋]朱熹:《论语集注》,《四部要籍注疏丛刊·论语》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644页。梁氏辑录:“郑氏曰:‘军旅末事,本未立则不可教以末事也。’韩氏曰:‘俎豆与军旅,皆有本有末,何独于问陈为末事也,吾谓仲尼因灵公问陈,遂讥其俎豆之小尚未习,安能讲军旅之大乎?’李氏翱曰:‘俎豆,宗伯之职,军旅,司马之职,皆周礼之本也。’”*[清]梁廷楠:《论语古解》卷8,严灵峰:《无求备斋论语集成》第294册,第1页。两相比照,《集注》的解释简洁明白。梁氏《古解》引郑玄(127—200)、韩愈(768—824)、李翱(772—841)三家注解,则显得丰富幽远。俎豆与军旅,皆为《周礼》之本。李氏持论出自经典,可考可稽。而俎豆、军旅,其本身皆有本有末,故韩氏之诘问当为有力,但贬抑俎豆之事、夸大军旅之事,恐未必允当。郑氏言“军旅末事”,应是相对于俎豆即礼义而言。在郑玄看来,孔子崇礼,强调礼治,安邦定国,当礼为本,兵为末。可见,朱熹《集注》与梁氏《古解》,比较互参,确能起到增广见闻、互相发明的效果。
梁氏《论语古解》可补《集注》之不足。朱熹《集注》虽不废古注,然集宋人之说较多,古注容量有限。《集注》虽重考据,但义理分析是其所长。故《集注》与古注相比,自有其长处,也必然有其不足,如未解处、不当处、空疏处、附会处等等。梁氏所撰《论语古解》,对《集注》之不足,有补救之用。如《里仁》“门人问曰何谓也”句,朱注未解。梁氏引皇氏曰:“门人,曾子弟子也。”*[清]梁廷楠:《论语古解》卷2,严灵峰:《无求备斋论语集成》第293册,第9页。邢氏《论语注疏》亦从此说。此为补朱注未解者。
凡此,足可说明梁氏《论语古解》融合汉宋的辑佚意图和实际效果。梁氏站在汉学的立场调融宋学,旨在提醒人们理解《论语》等儒家经典,除了宋学义理一途,还有汉学考据之路径,且只有这样,才能兼听则明,更全面地敞开经典的文本意义结构,更科学、更深刻地理解先圣的微言大义。
岭南学派另一位大儒潘衍桐融合汉宋的路径则迥异其趣,其《朱子论语集注训诂考》完全站在宋学的立场,爬梳剔抉,考镜源流,充分说明朱熹之注解源自汉魏诸儒之古解。潘氏在群经子史、汉魏古注的浩瀚典籍中,编采寻绎,细加搴采,乃迄今考察朱熹《集注》注文之依据较为重要的文本之一。细读朱熹《集注》,则可发现朱熹诠释经义时,分几种情况:征引前人之说并标引姓氏者;标明“就说”“一说”“或曰”字样者;在前人训诂基础上稍做变易者;未予指明出处而在他书中指出者。如《学而》“习,鸟数飞也”,此未标出处,然朱熹在《论语或问》中已经指出:“习之为鸟数飞,何也?曰:《说文》文也。”*[南宋]朱熹:《四书或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03页。由此,只读朱熹之《集注》,只能大致明义,或有时是懵懵懂懂、囫囵吞枣式的理解,或有时是一知半解、只知其然式的认知。潘氏《训诂考》,会让人对朱熹《集注》注文之源头依据有最为详备的了解,不仅能知其然,还能知其所以然。如《学而》朱熹释“悦,喜意也”*[南宋]朱熹:《论语集注》,《四部要籍注疏丛刊·论语》上册,第487,505页。,潘氏辑:“《广雅·释诂》:悦,喜也。”*[清]潘衍桐:《朱子论语集注训诂考》,严灵峰:《无求备斋论语集成》第245册,第1页。朱熹何以将古解“喜”变为“喜意”,加一“意”字有何考量?经义有何拓展?可见,朱熹在接受汉学熏染时并不拘泥墨守。潘氏《朱子论语集注训诂考》实为证明朱子“覃精著述,博极群书”*[清]陈澧:《与徐子远书》,《陈澧集》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55页。,充分凸显其融合汉宋、比勘发明的价值和意义。
此外,岭南学派简朝亮、刘明誉(生卒年未详)也积极倡导和践行汉宋融合。简朝亮本朱子及其师九江之师法,使汉宋互补,相得益彰。其云:“朱子之为《论语集注》也,自汉迄宋皆集焉。终身屡修之,欲其叶于经也。其未及修之者,后人补之正之,宜也。”*[清]简朝亮:《序》,氏著:《论语集注补正述疏》,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第1页。明确指出朱子并没有汉宋学的疆域壁垒。刘明誉有感于汉宋之学各守门户,各执己见,各有所偏,故作《论语注解辨订》,欲加兼采融合。其序云:“其治此者弊凡两派:一汉学派非真汉学也,苟焉于博洽之名而已,拾取一训诂之讹,剔抉一制度之颐,嚣嚣以驳朱子。艾千子有言,学莫陋于厌薄集注,骄语汉疏,遂欲驾马郑王杜于程朱之上,不知汉儒于道十未窥其一二也。宋大儒之所不屑,今且尊奉其弃余乎!诚哉斯言!其弊一也。一宋学派非真宋学也,漫然以为制艺而已。试观坊塾讲章,不曰某理某事也,而曰某字若何,某语气若何,某虚神若何。噫!抑未已具此两弊,安得有实学真材耶?”*张清泉:《清代论语学》,台湾:私立逢甲大学硕士论文,1992年,第232页。为纠偏汉宋二弊,刘氏全书于汉学取《集解》,于宋学取《集注》,采其正,辨其偏,择其精,订其陋,且旁采古今先儒诸说,综合训诂名物义理阐发而详加辨订。凡宋儒考据有讹者,取汉学辨之;汉儒义理不当者,资宋学订之:汉宋合流之特征十分鲜明。
二、平心求是
(一)平心互参
桂文灿的《论语皇疏考证》主要通过比较互参的方法,或先引他注,或先述皇说,考订详实,论据充分,屡屡在比勘参订中自然显示出皇疏的允当确切,常常云之“皇本是也”“皇说是”“皇说是也”“皇氏为得也”“皇说得其意矣”“皇说与某某说合是也”。
如解《尧曰》“兴灭国继绝世”时云:“皇氏云:‘兴灭国者,若有国为前人非理而灭之者,新王当更为兴起之也。云继绝世者,若贤人之世被绝不祀者,当为立后孙之使得仍享祀也。’”然后引郑玄、何休(129—182)之意旨,最后结论曰:“皇氏之说,与郑、何合是也。”*[清]桂文灿:《论语皇疏考证》,《丛书集成续编》第13册,第863,849,857页。又如考《八佾》“射不主皮”,最后云:“皇氏之说,与郑君《礼注》合是也。”*[清]桂文灿:《论语皇疏考证》,《丛书集成续编》第13册,第863,849,857页。此为指出皇疏持论与诸家相合者。如《先进》“赐不受命而货殖焉”条,按语曰:“……皇氏引殷氏、江氏之说,得其意矣。”*[清]桂文灿:《论语皇疏考证》,《丛书集成续编》第13册,第863,849,857页。此是指出皇疏之解释得诸家之意者。
梁廷楠《论语古解》,虽有为汉学正名的意图,但能够超越个人好恶,从学理出发,做到平心求是。其对所辑录之古解引史实或经文再加旁证。如《八佾》“八佾舞于庭”句,《集注》云:“佾,舞列也,天子八,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数如其佾数,或曰每佾八人,未详孰是。”*[南宋]朱熹:《论语集注》,《四部要籍注疏丛刊·论语》上册,第487,505页。梁氏辑之:“马氏曰:‘佾,列也,八人为列。’服氏虔曰:‘每佾八人。’按:佾,《说文》从八,月声,以八为义。《集韵》云:‘古文作佾,从八人,象形也。’”*[清]梁廷楠:《论语古解》卷2,严灵峰:《无求备斋论语集成》第293册,第1页。此条马融(79—166)、服虔(东汉,生平不详)皆明确指出“每佾八人”或“八人为列”,梁氏再引《说文》《集韵》等进一步加以佐证。梁氏按语中所引史实或经文几乎不存于《论语集解》《论语义疏》《论语笔解》《论语注疏》中,由此不难看出梁氏强调古解之价值的良苦用心,显示出其在文献典籍中辛勤钩沉、平心求是的治经精神。
(二)平心纠偏
桂文灿《论语皇疏考证》,共拈出《论语》经文约80条,对皇氏之疏文予以考证。其中以皇疏为是,证其所长者,约24条;以皇疏为非,考其所短者,约51条;余则或考订其篇章,或考版本之异文。无论是就篇幅还是条目而言,桂氏此书无疑以纠皇氏之误为主。桂氏纠谬之主要方法仍然是取参众注,择善比勘,在比较中简洁议论,自然地凸显意义,由此指出皇疏之错误,最后常常以“皇氏误已”“迂曲甚矣”“其说误已”“皇说失之”“皇氏载此无稽之事亦误也”作结。
桂氏平实的考证文字,常能彰显皇疏失误的原因。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是理解偏颇,导致失误。如《学而》云:“《论语》名篇,多因其分篇在是,即取章首二三字以为篇名,惟《学而》第一,皇氏谓以《学而》最先者,言降圣以下皆须学成,此书故以《学而》为先也。此言极为近理。皇氏又云‘而者因仍也’。夫‘学而’二字本截此章之文,岂有因仍之义,失之已。至《为政》以下诸篇,皇氏必于篇名求出相次之理,如以《八佾》名篇为深责季氏之恶,季氏恶不近仁,宜居‘仁里’,故以《里仁》次之,凡若此类皆非也。”*[清]桂文灿:《论语皇疏考证》,《丛书集成续编》第13册,第847,863页。今观皇侃《论语义疏》,于《论语》二十篇各篇之下,皇氏皆先解篇名,次解篇旨,再解其所以续前篇之缘由。但深入推敲,确实过于牵强,乃至无稽不经。《论语》是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记录孔子言行的文本,初始时没有篇名,只是在传播过程中因其分篇,“即取章首二三字以为篇名”,且《论语》之主旨、结构、层次,没有严密的逻辑体系。当然,不排除后人在整理分篇时有这些方面的思考,此应该成为诠释家注解经文时的考量因素。但要权衡应变,不能机械僵化,生搬硬套。皇氏强调学之重要,以“学而”为先,言之近理。“学而”之篇名当截章首之二字,可皇氏又凭空横来“而者因仍也”“学必因仍而修”*[南朝]皇侃:《论语义疏》,《四部要籍注疏丛刊·论语》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59页。等释语,令人诧异!皇氏显然将“学而”当作篇旨之提炼或概述,这种对篇名理解之“首失”带来了整体上的“此类皆非”。皇氏之篇旨说以偏概全、断章取义,其篇次说更是穿凿附会、难以成立。皇氏之失,盖因其对经文篇旨认识之偏颇,或因其对篇目相次之理的预设先见,导致其疏解失之于主观。
二是不辨真伪,导致失误。如《尧曰》:“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桂文灿云:“孔安国曰:‘亲而不贤不忠则诛之,管、蔡是也。仁人谓箕子、微子,来则用之也。’皇氏云:‘虽有云云者,《尚书》第六《泰誓》中文,言虽与周有亲而不为善,则被罪黜。不如虽无亲而仁者,必有爵禄也。’文灿谨案:上云‘予小子履’云云,孔氏注曰:‘墨子引《汤誓》,其词若此也。’若‘虽有周亲’数语,果为《泰誓》之文,孔氏岂犹不知之?且孔注《论语》以周为殷周之周,而引管、蔡、微、箕以释之,岂注《尚书》遂以周为至?言纣至亲虽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而商之才又不如周。其相悬绝如是,是岂出于一手乎?此乃东晋梅赜所献伪书之确据。皇氏不辨而反称之,失之已。”*[清]桂文灿:《论语皇疏考证》,《丛书集成续编》第13册,第847,863页。应该承认,皇侃之疏与孔安国之解,其意义相近。但皇氏认为“虽有周亲……”之经文为《尚书·泰誓》中文,被桂氏抓住了破绽。因为与此经文同章、在此经文上节有“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句,孔安国注云:“墨子引《汤誓》,其辞若此也。”*[南朝]皇侃:《论语义疏》,《四部要籍注疏丛刊·论语》上册,第300页。果若此经文出自《泰誓》,孔氏岂能不知?岂有不说之理?况孔氏注《论语》时言“周亲”,为何注《尚书》时“以周为至”而云“至亲”*李学勤主编:《尚书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77页。呢?显然孔氏所见之《尚书》非皇氏所见之《尚书》,皇氏所引之《尚书》为梅赜所献之伪书。皇氏不加辨别,反而称是,失之可惜。
三是仅凭孤证,且以附会之史实为据,实难信服。如《宪问》“卞庄子之勇”句,皇氏释曰:“(卞)庄子能独格虎。一云卞庄子与家臣卞寿途中见两虎共食一牛,庄子欲前以剑挥之。家臣曰:‘牛者,虎之美食,牛尽虎之未饱,二虎必斗,大者伤,小者亡,然后可以挥之。’信而言之,果如卞寿之言也。”*[南朝]皇侃:《论语义疏》,《四部要籍注疏丛刊·论语》上册,第259—260页。桂氏证云:“周生烈曰:‘卞,邑大夫也。考卞庄子,即孟孺子速也。’《左氏》襄十六年齐侯围郕。孟孺子速徼之齐侯曰:是好勇去之以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还。庄子当时有勇之名。故子以为言。文十五年齐人归公孙敖之丧,卞人以告。卞本孟氏私邑,庄子宰之,故称卞庄子。皇氏乃据格虎一事为证。文灿谨案:此事见《史记·陈轸列传》与《韩诗外传》,所载获田首事,皆傅会不经,无足信也。”*[清]桂文灿:《论语皇疏考证》,《丛书集成续编》第13册,第858,858,862页。此联系当时背景,子路问如何才能称得上人格完善的人,孔子认为:要有臧武仲那样的智慧,要有孟公绰那样的清廉,要有卞庄子那样的勇敢,要有冉求那样的才艺,再加上礼乐的修养,就可以称为人格完善的人。按照周生烈之解释,则孔子所云四人皆为大夫,孔子以四位大夫的突出优点归纳出完善人格的理想特点较为真实自然。且周生烈所云之卞庄子,其人其名,有记载,有事迹,有勇名,可查可考。皇氏所云之卞庄子,仅据“格虎一事”之孤证,且为史书不经之附会,既无从查考,又似不如家臣,实在让人“无足信也”。
我们亦能在梁廷楠的《论语古解》中发现平心纠偏的例证。《乡党》“不时不食”,《集注》云:“不时,五谷不成,果实未熟之类。”*[南宋]朱熹:《论语集注》,《四部要籍注疏丛刊·论语》上册,第586,487,572页。梁氏引郑氏曰:“非朝夕日中时也。”*[清]梁廷楠:《论语古解》卷5,严灵峰:《无求备斋论语集成》第294册,第8页。此解“不时”,二者明显不同。朱熹解为“不时之物”,郑氏释为“不时之饭”。从语境上看,《论语》文本中,“不时不食”前有“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数句,后有“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两句,盖言身边饮食之事,强调饮食卫生,应符合礼仪。且当时科技还没有发展到能够产出“不时之物”,即使有,孔子也未必能够享受。故郑氏之解更为确切。从思想角度分析,孔子十分重视日常伦用之事,强调行为规范,故郑氏之解更符合孔子思想实际。况皇侃疏曰:“不时,非朝夕日中时也。非其时则不宜食,故不食也。”《吕氏春秋·尽数》云:“食能以时,身必无灾。”*[东周]吕不韦:《吕氏春秋·季春纪第三》,《诸子集成》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6页。今人杨伯峻(1909—1992)等亦从此说。《学而》释“有朋自远方来”句中之“朋”字,《集注》云:“朋,同类也。”*[南宋]朱熹:《论语集注》,《四部要籍注疏丛刊·论语》上册,第586,487,572页。梁氏汇集各家之说:“包氏咸曰:‘同门曰朋。’郑氏玄曰:‘同师曰朋。’皇氏曰:‘同处师门曰朋,同执一志为友。’”*[清]梁廷楠:《论语古解》卷1,严灵峰:《无求备斋论语集成》第293册,第1—2页。两者互参比较,朱注无疑显得模糊,“同类”指称什么?且以什么作为分类标准?粗疏无当,旁生歧见。梁氏《古解》辑录诸家之说,则具体恰当,“朋”与“友”之区别一目了然。此外,简朝亮《论语集注补正述疏》亦能对朱注加以辩证。如解《子罕》“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句,朱注云:“道之显者谓之文,盖礼乐制度之谓。不曰道而曰文,亦谦辞也。”*[南宋]朱熹:《论语集注》,《四部要籍注疏丛刊·论语》上册,第586,487,572页。简朝亮认为“《集注》言文者未恰也”“文者六艺之文也”“故以文王既没为统称焉”*[清]简朝亮:《论语集注补正述疏》,第248页。,明确指出朱注之不当,并予以纠正。
(三)平心陈述
桂氏《论语皇疏考证》之主要目的是“证其所长,考其所短”,但亦有不论“短长”,只作陈述者。如《子路》“吾不如老农”句,释曰:“皇氏云:‘农者,浓也。是耕田之人也。言耕田所以使国家仓廪浓厚也。’文灿谨案:《礼纬·含文嘉》云:‘神者,信也;农者,浓也。始作耒耜,教民耕种,美其衣食,德信浓厚若神。故为神农也。’《书》农用八政,郑君农读为醲。《说文》凡从农得声之字,如醲为厚酒,禯为衣厚。盖字义生于声者,乃最始之义。耕田之人使衣食浓厚。故曰农先有浓厚之义,后名为农夫也。犹田夫谓之啬夫,先有爱濇之义,后名为啬夫也。皇氏之说古义也。”*[清]桂文灿:《论语皇疏考证》,《丛书集成续编》第13册,第858,858,862页。又释《子张》“虽小道必有可观者”句云:“何平叔曰:‘小道谓异端也。’皇氏云:‘小道谓诸子百家之书也。’文灿谨案:郑注云:‘小道如今诸子书也。’见《后汉书》注。皇氏本诸郑说也。*[清]桂文灿:《论语皇疏考证》,《丛书集成续编》第13册,第858,858,862页。以上二例,均是客观陈述,或为古义,或本郑说,至于孰是孰非,孰优孰劣,则不置可否,不做评判,充分体现了桂氏治经能平心客观,不妄加判断、不随意议论。
梁廷楠的《论语古解》专辑与朱子《集注》相异之汉唐古解。汉唐诸儒相异于朱子《集注》之注解可能有一解或多解之分,梁氏均将注解之具体内容简要列出。对于有可能出现汉唐诸儒之说与朱注相异而本身相同或相近之情况,梁氏盖取“某说与某说同”之方法。如“按皇氏、邢氏说同”“按郑氏、邢氏说并同”“按包氏、邢氏说并同”“按包氏、马氏、皇氏说并同”等等,此类按语较多。按理,《论语古解》仅列出异说即可,为何不厌其烦地指出“某说某说并同”呢?这类按语实为举例,具有论据之功用,无形中增强了梁氏所辑古解之代表性和说服力。汉唐古解去古未远,自有其真实性和可信度,而且这些古解并非一家之言,不仅汉儒如此说,魏晋诸儒也如此说,甚至唐乃至北宋之大儒还如此说。由此,人们不禁要问:《集注》相异于汉唐古解之说出自何?据之何?梁氏生活在晚清时代,清初反对宋学之潮流已被汉宋合流所取代。
潘衍桐以考证为主,对朱注之当否,不做判断,只是考出异文。如《先进》“柴也愚”章:“《家语》记其足不履影,启蛰不杀,方长不折,执亲之丧,泣血三年,未尝见齿。”潘氏按语:“《家语·弟子篇》文,无‘泣血三年’四字。”*[清]潘衍桐:《朱子论语集注训诂考》,严灵峰:《无求备斋论语集成》第246册,第3页。平心陈述,表面上不做判断,但实际上体现出求是的倾向。孔子虽“述而不作”,但却隐含微言大义。
三、开新改制
岭南大儒陈献章为了摆脱明代初期文化危机、打破程朱理学逐渐僵化之格局而开创了“白沙学派”,体现了强烈的创新精神。“东塾学派”代表人物陈澧中年以后提倡一种具有近代科学精神的“新学风”,被公认为汉宋调和的主将和集大成者。朱次琦敏锐地察觉到了当时主流学说的种种弊病,渴望出现大批操守高洁、才干卓越的通才,以应对当时的内忧外患,担当起天下的重任。“岭南学派”经世致用、改制图强的文化精神一代代传承发扬。最终,朱次琦将他的学生康有为等人推上了新旧思想交汇的风口浪尖。
康有为18岁拜广东著名学者朱次琦为师,施教以修身与读书并重,由此确立经世思想。1888年,康有为31岁时上书变法,为守旧派所不容。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康有为联络18省举人上书朝廷,要求拒和、迁都、变法,受到光绪帝的赏识,但被守旧势力排挤,不得已回广州谋生,在万木草堂执教,其间著成《孔子改制考》。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逃往香港,转赴日本。1899年赴加拿大,转往英国。1901年赴马来亚。1902年居印度大吉岭,时康氏45岁,成《论语注》,欲张孔学大道,绘改制蓝图。
(一)否定守约之学
首先,康氏指出孔学被曾学遮蔽,曾子之学皆守约之学。《论语》“盖出于曾子门人弟子后学所纂辑也”*[清]康有为:《序》,氏著:《论语注》,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1,2,2,2,2页。,但“曾子之学专主守约”*[清]康有为:《序》,氏著:《论语注》,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1,2,2,2,2页。,“其为一家之学说,而非孔门之全”*[清]康有为:《序》,氏著:《论语注》,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1,2,2,2,2页。,“曾学既为当时大宗,《论语》只为曾门后学辑纂,但传守约之绪言,少掩圣仁之大道,而孔教未宏矣”*[清]康有为:《序》,氏著:《论语注》,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1,2,2,2,2页。,“故夫《论语》之学实曾学也”*[清]康有为:《序》,氏著:《论语注》,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1,2,2,2,2页。,“不足以尽孔子之学也”,“不足大彰孔道也”*[清]康有为:《序》,氏著:《论语注》,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1,2,2,2,2页。。
康氏贬抑曾学专主守约,并非否定守约之学。因为守约不仅有利于修身,还能保证少犯错误。只是康氏认为守约之外还有其他更丰富的内容,更重要的担当。他在解释《子路》“苟有用我者”章时云:“孔子改制仁政,以拨乱反正,若行之一年,则规模可立,三年则治教大成……自信自任,而言之如此,确有把握可守,确有条理可行,所谓乐则行,则行在。此圣人不妄自任,其次序期限可玩也。愚尝诵之,然用我必三年乃可,十年有成,益叹圣人之神化也。圣人日以天下纬画于中如此,固非兢兢守身守约之儒所能窥矣。”*[清]康有为:《论语注》,第194—195页。康氏认为孔子此言在卫灵公不用之时,康氏注释《论语》也在变法失败后,共同的命运、共同的理想十分自然地将康氏和孔子联系在一起,故康氏尝诵之玩之,圣人之自信亦即康氏之自信,圣人之自任亦即康氏之自任,圣人之不妄亦即康氏之不妄。康氏确实不妄,自觉与圣人拉开了距离,圣人能“一年可立”“三年大成”,而康氏则“三年乃可”“十年有成”,但康氏毕竟能窥出可守之把握、可行之条理、可变之规律,远非一般守身守约之儒并论比拟。可见,康氏贬讽守约之儒,寄寓其社会变革理想。
其次,康氏对宋儒尊奉曾学提出批评。他认为宋儒仅仅发明了孔子言行,未能弘扬孔学之大道。《论语》辑自曾门,而曾门之学专主守约,笃谨狭隘。孔子之学假颜子、子贡、子木、子张、子思辑之,方显其博大精深;又假仲弓、子游、子夏辑之,方知其微言大义。然宋儒对孔门之学的把握缺少宏观的视野,对曾学“其为一家之学说,而非孔门之全”*[清]康有为:《序》,氏著:《论语注》,第2页。没有足够的认识,常常聚焦在曾门守约一隅。康氏不仅对宋儒尊奉曾子过甚提出批评,还对宋儒妄议子张予以鞑伐。如解释《子张》“执德不弘”时指出:“子张此言,真为治世传教之要。无志者不足论。”“真所谓德弘信笃者,迥非曾子、子夏所能及。后人误尊曾子,遂抑子张,是目迷白黑,颠倒高下,此孔道所以不明也。”*[清]康有为:《论语注》,第286,291,209—210,130,192,233页。又如,解释《子张》“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时云:“记《论语》者当为曾子后学,而非子张之徒,故记本师之言,犹荀子之非思孟耳,未可为据。” 进而指出:“朱子误尊曾子过甚,于是不考,而轻子张为行过高而少诚实恻怛之意,则大误矣。”*[清]康有为:《论语注》,第286,291,209—210,130,192,233页。
综上,稍加思考则可发现:康氏批评宋儒盖因其诠释理念和认知视域上的极大差异。此在康氏与宋儒对管仲的评价上可以做出清晰的判断,康氏认为宋儒鄙薄事功,攻击管仲,遂至宋朝不保,生民涂炭。此从康氏解释《宪问》“问管仲”时可以得到最直观的说明。康氏云:“人也,犹言是可谓之人物也。不关当时之治乱,不足谓之人;不系一世之安危,不足谓之人,所谓焉能为有,焉能为无者也。若举世变动,举世注仰,功名不朽,可谓之人,与下章成人相类,惟管仲可当之……管仲真有存中国之功,令文明世不陷于野蛮,故虽夺人邑,而人不怨。言功业高深,可为一世之伟人也。孔子极重事功,累称管仲,极词赞叹。孟子则为行教起见。宋儒不知,而轻鄙功利,致人才苶尔,中国不振,皆由于此。”*[清]康有为:《论语注》,第286,291,209—210,130,192,233页。
可见,康氏强调“守约”不是孔子思想之大宗,《论语》不是孔学之全部,孔子思想的核心是“大同小康”“托古改制”,故《论语注》之目的是弘扬孔学大道,是经世致用、经邦救国,为其变法维新开辟路径。
(二)提倡托古改制
在康氏心目中,孔子兼备万法,与时变通,是有法无法、有形无形之人,是亦虚亦实、若有如无之人,是知天感地、玲珑完满、不可度测之神人化人。其在解释《子罕》“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章时指出:“宰我称孔子贤于尧舜,子赣称其百王莫违,子思则称发育万物,峻极于天,庄子称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颜子则称其仰弥高,钻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然此五子虽极力铺写,终不若颜子之形容矣。“颜子深知夫子之道无穷尽,无方体,而叹之也。”“若颜子之所形容,所谓圣而不可测之谓神。”*[清]康有为:《论语注》,第286,291,209—210,130,192,233页。
康氏崇拜孔子,盖因其为托古改制,开新变法。“盖今中国一切名号,皆孔子所正也。”*[清]康有为:《论语注》,第286,291,209—210,130,192,233页。康氏认为孔子所定历法,不仅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而且对后来的欧美社会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乃至后来有些国家皆从孔子所定之历法。“今大地文明之国,仍无不从孔子之三正者。若印度,则与中国同行夏时矣。”*[清]康有为:《论语注》,第286,291,209—210,130,192,233页。
康氏认为孔子盖因改制贤于尧、舜。孔门弟子中即有孔子贤于尧舜的议论。此在其解释《孟子·公孙丑》章能够得到进一步揭示。如“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曰……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朱子谓孔子贤于尧、舜,在事功似矣。然不知孔子改制,治定百世,乃为功德无量。”*[清]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99页。显然,康氏更加侧重和强调其改制之无量功德。
康氏对孔子之赞美还在于其对后世社会的影响和意义。孔子不仅令古代“赞者”不可测之,孔子更有“无穷无尽新理”令后人包括康氏不能测之。康氏云:“今者,于《春秋》得元统三世,读《礼运》知小康大同,读《易》而知流变灵魂,死生阴阳。二千年钻仰未得者,今又新出,尚不知孔子更有几许无穷无尽新理,为我所钻仰未得之者耶?……天生大圣,以庄子、颜子之聪明不可测,知吾亦只得曰不可测知而已。”*[清]康有为:《论语注》,第130,229—230,129,197,249—250,250,250页。
不仅如此,康氏认为孔子改制之思想影响到欧洲之政体。此在解释《卫灵公》“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时得到印证。康氏云:“舜任官得人,故无为而治。盖民主之治,有宪法之定章,有议院之公议。行政之官,悉由师锡,公举得人,故但恭己,无为而可治。若不恭己,则恣用君权,挠犯宪法,亦不能治也。故无为之治,君无责任,而要在恭己矣。此明君主立宪,及民主责任政府之法。今欧人行之,为孔子预言之大义也。”*[清]康有为:《论语注》,第130,229—230,129,197,249—250,250,250页。
可见,康氏称赞孔子之目的,意欲藉孔子之道变革社会现实也!“素王受命懺……必有所制法垂教,而天瑞又必应之。”*[清]康有为:《论语注》,第130,229—230,129,197,249—250,250,250页。“圣人事穷而更为,法弊而改制……以救弊扶衰,黜淫济非,以调天地之气,顺万物之宜也。”*[清]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第197—198,198页。孔子之学的核心或精髓是托古改制。
(三)描绘改革蓝图
康有为宗奉孔子,提倡改制,其目的在于通过诠释《论语》阐述自己的变法改制思想,描绘清代社会的理想画图。
第一,康氏描绘了拯救衰败社会的政治体制,即实行君主立宪制。其解释《子路》“近者说,远者来”时,十分巧妙地将远近与新旧关联起来,指出:“器莫若旧,政莫若新。”并对新与旧大加对比铺陈:“盖旧则塞滞,新则疏通;旧则腐坏,新则鲜明;旧则颓败,新则整饬;旧则散漫,新则团结……旧则形式徒存,人心不乐,新则精神振作,人情共趋。”*[清]康有为:《论语注》,第130,229—230,129,197,249—250,250,250页。康氏对旧制、旧俗深恶痛绝,对新政、新变大加渲染和赞美。
康氏认为人类社会就是由乱而治、愈演愈进的发展进化过程。所谓“十世之失”“百世之失”,盖由“乱世而至升平,则君主或为民主矣”*[清]康有为:《论语注》,第130,229—230,129,197,249—250,250,250页。。当今世界各国竞相开议院、立宪法,实行君主立宪,而中国当变不变,必生后乱。因此,变更政体已成为中国生死存亡的关键。为了描绘自己托古改制的变法蓝图,康氏不惜改动经文。其在疏解《季氏》中“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时,武断地认为该句中的“不”字纯系不明孔子真意的后人妄增,因此必须删去,并解释说:“政在大夫,盖君主立宪。有道,谓升平也。君主不负责任,故大夫任其政。”“大同,天下为公,则政由国民公议。盖太平制,有道之至也。此章明三世之义,与《春秋》合。”*[清]康有为:《论语注》,第130,229—230,129,197,249—250,250,250页。
康氏将西方进化理论与汉代今文派“三世说”关联起来,深入阐述社会发展与变革的自然性与必然性。康氏引《说苑》认为:“夏道不亡,殷德不作;殷道不亡,周德不作;周道不亡,《春秋》不作。以此证之,继周者春秋也。百世以俟圣人,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以《春秋》治百世也。百世之后,穷则变通,又有三统也。此改制之微言也。”*[清]康有为:《论语注》,第130,229—230,129,197,249—250,250,250页。《公羊传》留下了“统三世”“张三统”“受命改制”的微言大义。“三统”意味着夏、商、周三代不同,当随时因革;“三世”指明了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愈改愈进步。所谓“十世之失”“百世之失”, “三千年皆大变,亦自然之数也”*[清]康有为:《论语注》,第130,229—230,129,197,249—250,250,250页。。康氏事实上讲的是当时社会的现实,指出清政权要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进行改革,才能维护统治的局面。
第二,康氏不仅提出了君主立宪的政体,还对君主立宪之社会关系做出具体描述。他所说的变法改制,字面上讲的是孔丘和孔丘学说,实际上指清政权统治下的中国,需要由封建主义的衰乱世,改为他所设想的资本主义的升平世。故将资产阶级的民主、平等、议院等等都纳入了孔子思想体系。其解释《尧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时指出:“为政者,但代民经理而已。孔子此言,尽为政之法矣。为国事而自行保护,为公众而自享利益,虽人人为兵,亦不敢怨……小大众寡,皆天所生,人人平等,不须严卫。故‘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符表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义存;仁义存,故盛德著;盛德著,故可以为法象。’今美国利民之道,仁民之制,劳民之方,平等之制,皆行孔子之政。言简而该,以此继帝王之道,可为平世民政之法也。”*[清]康有为:《论语注》,第303,182,226,174页。康氏认为美国之利民仁民之制,皆行孔子之政,虽有牵强夸大之嫌,但却具体勾画了康氏心目中理想社会的结构图景。
康氏将社会改制与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思考。其解释《颜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时云:“人道纲纪,政事之本。据乱世以之定分,而各得其所安,上有礼而下输忠,老能慈而幼能孝,则可以为治。否则,君骄横而臣抗逆,父寡恩而子悍悖,则国乱而家散矣。《礼运》小康之义,以正君臣,以笃父子是也,二千年间可以为鉴。时,齐家国皆乱,故夫子以此告之。若夫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人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此须待大同之世。苟未至其时不易,妄行则致大乱生大祸。”*[清]康有为:《论语注》,第303,182,226,174页。
康氏对大同社会自由平等问题都有较为深刻的阐述。他解释“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时云:“安人,小康之治也;安百姓,大同之治也。而必始于修己以敬,自明其明德,而后明明德于天下也。为治无论如何,务在安之,而已安之,必养其欲,适其性,因其情。束缚压制,则不能安,自由自立,而后能安。圣人所以为圣,日思所以安人者而已。”*[清]康有为:《论语注》,第303,182,226,174页。康氏解释“公西华侍坐”章云:“曾点之学,入皆自得,到处受用。”“随时行乐,与物偕春。”“乐其日用之常,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清]康有为:《论语注》,第303,182,226,174页。康氏强调自由平等问题与人格修养的关联,重视自强自立,顺天应人,注意人己之界,做到“无加诸人”,创造出“自得受用”“悠然行乐”的理想境界。
四、小结
岭南学派由陈献章、湛若水开创,至清代发扬光大,近四百年来一直保持经世致用的实学传统,重视学术与社会的关联。加之岭南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源地,有最早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独特的地理位置有利于岭南学者在接受、融合中原文化各种形态时,大量引入域外文化。
道光四年(1824)两广总督阮元在广州创建学海堂,开设地理科,比1867年京师同文馆设地理为必修课早四十多年。1840年前后,经世致用之学倍受重视。一些视野开阔的学者从古籍考据、八股科举中超越出来,关注务实“新学”。梁廷楠编纂了中国第一部海关志——《粤海关志》;写下《海国四说》等我国近代第一批介绍欧美的著作,其中《合众国说》是我国第一部介绍美国历史、地理和政治制度的著作;另著《东行日记》,体现了对自然探索的实学精神;戊戍新政之初的1898年2月10日,他在广州与黎国廉创办《岭学报》,较早介绍西学西政,成为了解西方文化的重要窗口。1884年潘衍桐上《奏开艺学科折》,虽被当时守旧势力奏驳,但为推广制造、算学、舆图等新学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环境、探索形成了岭南学派兼采包容的开放境界,故在经学研究上不拘一端,能够融合汉宋,平心求是。
岭南学派之《论语》诠释,经梁廷楠、桂文灿、潘衍桐、刘明誉、简朝亮、康有为诸家爬梳剔抉,取舍演绎,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在汉宋融合的视野下整合建构,多元探索,终将汇聚成与常州学派呼应、对接西学文化制度的现代思想浪潮。其在清代《论语》诠释版图上独树一帜,成为古今传承、中西交汇点上的一道风景。岭南学派代表人物康有为开启了传统经学近代转型的风尚,使古老经学焕发了青春。
【责任编辑:杨海文;责任校对:杨海文,许玉兰】
中图分类号:B24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5)04-0112-09
作者简介:冯晓斌,扬州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扬州225002);
*收稿日期:2014—10—09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清代地域学派《论语》诠释研究”(13YJA751031);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文化传承与区域社会发展”(PAPD)
柳宏,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扬州225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