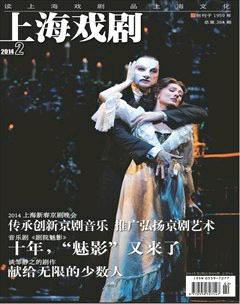跑赢了观念,未必跑赢共鸣
徐煜
孤独的守望者是现代戏剧常见的人物形象,比如《咱们死人醒来的时候》中的鲁贝克、《萨勒姆女巫》中的普罗克托、《沉钟》中的海因里希等等。剧中的主人公或者以信徒般的道德虔诚,或者以近乎偏执的精神追求,对抗着世界的堕落、平庸和麻木。这类主题的反复出现,表达着人类想要探寻被现代社会功利性异化的心灵本真的强烈愿望。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推出的新作《老大》也塑造了一个在物欲膨胀的背景下,坚持自己精神归宿的守望者形象。该剧以一个现代寓言式的故事,表达着对人类毁坏自己的生存之根的忧思。在当代一个渔村里,面对即将被改建成浴场的渔场,一个几十年以大海为寄托的老渔民,不甘心接受家园被毁的现实,以无力却又顽强的方式进行着近乎绝望的抗争。他倔强地固守着居民已都迁走、等待拆除的渔村而不撤离,最终却眼睁睁看着家园被经济开发的脚步毁于一旦。
一个人的坚守,这是一个很有力量的戏剧情境,对观众可能产生的震撼很值得期待。然而,从现场观众的反映来看,演出中几次创作者精心设计的高潮场面,似乎都没有引起足够的回应。有些地方,舞台气氛很强烈,但观众的情绪却并不高涨。这不完全是观众没有理解作品的内涵所致,而是作品中还存在着一些值得推敲的部分,影响了审美体验的完整性和连贯性。
《老大》是个象征感非常强的戏,大海是灵魂净土和生命本真意义的承载符号。剧中象征意义的完成,无疑需要强化大海这一精神符号的纽带作用。冯国良从一个苦命少年,成长为发祥号渔船的老大,海洋对他的磨砺,给予他的感悟,是他性格的主要促成因素,也是日后冯国良将大海视为圣殿的重要心理依据。剧中的情节主线,应该是冯国良和大海的相互作用的对手戏。然而从目前呈现来看,却给人一种避实就虚的感觉,剧本对于冯国良的人生经历的描写,恰恰回避了他对大海的搏击、抗争与领悟。在作品中,以追忆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冯国良的人生轨迹,除了一段当年的老大林阿龙和老轨林国章为了救他而死外,其余基本围绕他与两个女子的感情戏展开。冯国良为了赎罪而娶了林国章的遗孀阿兰,以及为娶阿兰而放弃了与女演员戚瑞云的感情,这些经历对于冯国良守望者形象的形成,并没有多大的促进作用,这种错位的爱情可以发生在任何人物身上。由于这两条感情线的喧宾夺主,人物的主要故事既形不成一个精神守望者的基本面貌,而且也要冒叙事上的风险。冯国良在现实中要捍卫曾经有过的精神家园,而那个家园在现有的框架中,对他来说就是两段遗憾的感情,这在守望主题应具有的人生气魄上打了不小的折扣。戏的基干部分成了普通的忍痛割爱的情感纠葛,冯国良守望的海洋和灯塔反倒成了陪衬,对海洋的怀恋只能是个空洞的标签,以至于剧中冯国良多次为大海的被糟践而呐喊,总让人产生差一口气的感觉,情绪很难充分调动起来。
情节侧重点的失误,除了造成对主题的削弱外,还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叙事上的风险。比如,冯国良与阿兰结合的情节就显得突兀和勉强,初看起来惊天动地,仔细推敲却觉得缺乏可信性。阿兰作为在海上挽救过冯国良的老水手的遗孀,冯国良对她有负罪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以一个未经世事的少年,而且还顶着“黑五类”的帽子,是否具备这样的勇气,着实需要斟酌的。即便冯国良有意,阿兰作为一个农家女子,又如何敢于接受小辈这样的要求,这中间要克服多大的民风、伦理甚至还有时代的障碍。这些障碍的克服无疑需要巧妙的叙事策略,然而剧中显然省去了必要的纠葛过程,轻而易举就达成了两个人的结合,这样做固然避免了缜密构思的麻烦,但是直接呈现结果的代价是,预期的效果必然会受到损害。
总体上,作为一部探讨生命价值和人文关怀的作品,《老大》的艺术追求是值得肯定的,而且不乏诗意的场面和语言,在时空设计上尤其值得称道。如果说跨时空、多时空结构的运用,在当代戏剧并不罕见,但是创作者在此依然发掘出了新意。比如戏中的闪回部分,往往让现在的冯国良直接走进历史画面,与当年的自己进行对话,这样的处理,既洒脱自由,又不乏穿越历史的哲理意味。当然,如果作品所表达的类似情怀、守望、灵魂家园的主题,能够有更贴切的人物命运折射出来,而不是通过演员的演说来转达,可能艺术效果会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