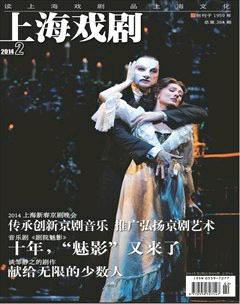凝历史中国艺术精神,塑当下社会心智形态
李伟
问:赵耀民的新作《志摩归去》在上海首演,引起了话剧界和媒体的关注。我们看到关于《志摩归去》的评论,大多都是就戏论戏的。您觉得从社会的层面来看,这个戏有怎样的意义?
答:现代中国艺术文化氤氲生成的历程中,徐志摩是具有深度创造性的意象和存在之一;沿着这一意象存在的脉络,可以重访古典中国的生命底蕴、现代世界的文化源流。两者在相遇、碰撞、互动中,激起灵动恣肆的精神气象。我看剧场里不少是年轻的观众,无论他们由于什么契机、带着什么期待来到剧场,无论由于商业性层面或艺术性层面的原因,他们对这出话剧有着亲切的兴趣,令人高兴。演出有商业性或者说市场定位,并不减少其中明晰地对话剧艺术的理解和把握,这在当下,十分不易。从社会的层面来看,这出剧带来了一系列人生命题,内涵既是中国的,又不仅限于中国。
我们正在经历经济全球化的巨大变迁,所有地区和人们都处于一种人生把握、价值寻求的湍流期。中国经济的大规模发展,中国社会的急速变化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都是世界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我和同行学者曾谈到:一般而言,“市场经济”是指现代社会里通过市场组织的经济生活;现在我们感到正在出现某种可以被称作“市场社会”的现象,即“社会”整体本身正在成为一个市场。在“二战”后的世界环境中,这是一种非常态的状况。我们可以说美国是一个最以市场为标准的国家,但美国的社会并不就是一个市场社会;亚当·斯密以来对经济、市场与社会、人生的经典阐述,就更非如此了。一个社会,把经济市场的逻辑扩展到所有的方面,就出现了可持续性的问题:包括人们之间的联系、情感维系的属性。从这个角度跟当下结合起来思考,《志摩归去》所携带和传递的历史时效信息是丰富的。从历史的维度和中华文明的特征谈,话就可以很长了。
简言之,我们经常讲中华文明的传统,是“一个世界”的世界观,即我们没有一个形而上的先验维度,与欧美主流文明“两个世界”的世界观不同。美国社会约有80%以上的家庭每个星期天都上教堂。他们是所谓的“践行基督徒”。美国是政教分离的国家,实际上渗透在日常生活的机制、行为、心智中的宗教性和其对美国社会的根本与全面影响,我们至今的理解与把握可能是不很充分的。
人类的精神生活、精神历程、精神现象,当然不只是西方独有,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并不能涵盖万物生灵。中华文明传统的基本性质不是制度性一神教宗教文明,包容着多重宗教性传统,有着多种多面精神生活的维度和情怀及其不同传承,这其中就包括浪漫主义传统,现代的浪漫主义传承,徐志摩是现代浪漫主义的一位代表人物。
在中国极为多重多面的现代文化史中,如何把握各有差异的文化传承和运用其中无法简单分类的价值资源,可能还有比较长的路要走。比如,人们往往把浪漫诗学及其人生实践轻易浅薄化,跟深刻复杂的中国革命简单对立起来。那天去看“徐志摩”这出剧,我有一点感慨,想到了丁玲。在1931年初胡也频等左联五人被逮捕杀害之后,她面临严酷人生考验。那时丁玲年轻,刚当母亲,很多人不敢去看她,但奇怪的是一天有人敲门,竟然是徐志摩来访。丁玲感到十分意外,新月《诗刊》的世界与《北斗》的世界,两者似乎很遥远。徐志摩并不很会说话,他说:“本刊素仰先生文章,特来向您约稿;这是我们预支的稿费。”他就把一笔钱给了丁玲,把钱留下他就走了。同年年底,徐志摩飞因机失事去世。半个多世纪后,上世纪八十年代,丁玲再次回到北京,和人谈起这件事。这件事,她记了一辈子;这句话,她也记了一辈子。
生死之间,他们有一个相通的地方,就是有对现实格局的超越。这种超越有时候是要付出代价的。也许代价在形式上很不一样,徐志摩拥有财富、美貌等大堆符号,丁玲则更被赋予诸多符号,但在这种时刻,他们互相是懂得对方的。我不太同意有一段时期我们在回顾历史的时候把某些人生中的精华给扔出去了,比如说有一些对丁玲的评价,我觉得是不够公平的,她具有的珍贵品格,不是符号所能命名或阻挡的,其中的内涵我们很可能还需要重新思考。
同样,现在来谈徐志摩,我觉得是好事。李欧梵有一本书,叫《浪漫的一代》,写的就是他们这一群,包括“五四”及后来的一些浪漫主义作家。我觉得他写得不错,把这个命题提出来了,同时觉得他写得似乎还不够。在现代中国这样一个环境中,当欧美的浪漫主义被翻译到、被转译到直至被实践到中国的环境里、而不是风花雪月的表面文章时,它有一种深刻的革命性。我们可以重访、凝注的这种精神,是-超越精神的。这种精神是深刻的,它带着人生中最深刻的代价。
从这儿想开去,有多少人多少事可以重访。观众不是文学史、艺术史家,不一定也不需要有专门知识。这些重访带给人们的是一种直感,好像碰到了一个朋友,碰到了生活中一种人性的支援。人性是需要支援的。在一个巨变的环境中,可能常会遭遇对人性也许微小、具体但又是终极性的挑战,没有援军,是会塌方的。变动越延伸,需求越深入。中国今后十年、二十年的时空,可能尤其如此。所以我觉得能够上演关于徐志摩的戏,就值得庆贺。批评是容易的,不妨可以讨论,形成一些争论。
问:从刚才讲的来看。您是否觉得,不管是赵耀民的剧本,还是舞台呈现,是否还有很多东西未能挖出来?
答:是的,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很多东西。比如说林徽因。林徽因常被写成那种小姐才女,常被风花雪月的基调纠缠。前些时北大出版社翻译出版了我的一本书(指《中国现代女作家与中国革命》),英文版封面用的是林徽因的一张照片。那是1937年林徽因、梁思成和助手们沿着铁路线去做田野调查,勘找中国古建筑、古庙宇。她坐在一个烧砖的地方记笔记,一束光线从窑口照进来。我和我的编辑一起选定,封面设计师在构图上作了处理。我觉得那张图特别能传递一种精神气质,既是瞬间也是久远的一种精神存在。林徽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在美国学习并获得艺术建筑学学位的女性。在当时中国的环境,对女性的尊重是珍贵的,也就是说是稀少的。现代以来,对女性的尊重要真正从骨子里形成,还有待多少努力,这是一个大话题。中国传统文人中根深蒂固的封建性,是另一个大话题。
对于林徽因,把她捧得如花似玉本身就是对她的一种看低。她有两件事值得注意:一是在李庄的时候,抗战处于惨烈之时,林徽因也成了难民中的一员,她病得非常严重,骨瘦如柴。大家比较多提到的,是费正清去看望他们,非常吃惊。他说,时局都这样了,身体都这样了,这两位仍然在做他们的建筑研究。大家不大注意的是,她的孩子后来回忆的一个细节:那个时候陷在李庄太孤单,她没有谁可以聊天,就和自己的两个小孩子聊莎士比亚、歌德,“我们两个听不懂,就像两头小牛,她天天和我们对牛弹琴。终于有一天,我忍不住问:‘妈妈,日本人要是打到李庄来怎么办?妈妈看了看我说:‘你看那外面有一条河,妈妈就跳到那河里去了。我就问:‘那我们怎么办?妈妈拍了拍我们的脑袋:‘那时候妈妈就顾不了你们啰。”这话似乎是在和孩子说话,但认真想,她真会那样做的。孩子跟母亲的关系是天底下最割舍不掉的亲情,但林徽因这样说了,她也会做的。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性格呢?我是在有了一定的生活阅历以后,开始懂得重新认识自己的母亲时,读到这一细节,感到震动的。她是这样的一种女性。怎么能想象,她时常被弄成一个特权花瓶?
二是建国之后,她总算有了一个机会,那就是设计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长期以来,林徽因是作为梁思成心爱之人和学术副手被提及,或是作为文人墨客的“沙龙太太”被雅遇。新中国成立后的清华大学,立即给了她一级教授的职位,这是在梅贻琦当校长的时候没有过的,哪怕她是从宾州大学、耶鲁大学这样的常青藤盟校学习毕业。她正式参加了国徽设计,事实上是设计组的灵魂。在我看来,这是她真正拥有的一次历史性的机会,她紧紧地抓住了,他们的设计方案被选中。接着是人民英雄纪念碑,林徽因主要承担的是须弥座装饰浮雕的设计。完成之后,她很快就去世了。现代史上还有另外一位相似的设计师,即南京中山陵的设计者,是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学的建筑设计,叫吕彦直,也是设计完了就去世了。这告诉我们,这样的工作的强度和要求。林徽因设计纪念碑底座,“由此上溯至1840年”,她是用全身心去表达,她就是这么认为的。这些人离开过故国热土远道求学,以“睁眼看世界。”她们经历过流离失所和酷烈的八年抗战。她是这样对自己的孩子说实话,她是这样用自己最后的生命设计了历史的和人生的纪念碑。一个人一生中有了那么一次历史机会,你看她使用到什么程度,她交付出了生命。林徽因去世后,她设计的饰雕刻样被移在她的墓碑上,碑的上方刻着:建筑师林徽因之墓。碑上没有铭文,只有一只浮雕花环,橄榄枝环抱着牡丹、荷花、雏菊。
我们如何去凝神注视这样一位女建筑艺术家呢?我们可以试想一下,林徽因的故事怎么讲?
我看过《人间四月天》,对林徽因《你是人间四月天》这首诗写给谁有不同臆测。共识较多的一说,倾向认为是写给她刚出生的孩子,我觉得基本是准确的。诗中寓意,大家谈得较多的是年轻母亲对亲子的浓郁情感。同时,“四月天”是非常英国的,即在英国的文化中,有十分特殊的意味。所谓“英伦四月”不仅仅是自然美,“人间四月”在英伦的文化中,就好像我们的“春华秋实”一样,有一系列的文明记忆,有经典人文意象的群聚星座,比如在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之一华兹华斯眼中,“四月的金色水仙花”,“在树荫下,在湖水边,连绵不绝;如繁星灿烂,在银河里闪闪发光;沿着湖湾的边缘,延伸成无穷无尽的一行行;一瞥中呈现的,万朵金色”。大自然经由人文艺术的照亮,成为本体性的人世呈现。所以林徽因这首诗的内蕴,一如她跨越建筑、绘画、工艺、音乐、文学、戏剧诸多领域的诗学,是跨文化的。其中的艺术精神,汲取了多种文明的养成,而达成的是在形式和内容两个层面上相当完整的—种现代中国诗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才华和能力呢?还有凌淑华、还有张幼仪。这里面提到的人,提到人群之外的更多的人,一圈一圈,是中国人文的、艺术的共同体吧,像一个层层漾出的波澜,一直可以环跨太平洋,可以环跨大西洋,实际上是有世界性的。
你觉得是不是可以继续做下去?我的感觉,现在的观众,包括80后、90后会喜欢。话剧观众在中国诞生以来,即以受过较好教育的青年至中年为主。他们有大把的生命,有充沛的愿望。这些愿望如何通过艺术感受获得沟通、通过沟通活跃起来?话剧以它的现场性和社会性,成为承载和活跃这种愿望最有效的—种形式和方式。
赵耀民这个戏是个好尝试,不仅因为它比较好看。中国人的物质生活里,精神世界里,现在才开始有一些条件,不再把诗情当作奢侈品。这就是机会。我们能否用林徽因式的力量去把握呢?问:剧中陆小曼似乎也写得过于颓废了一些。我们看到的陆小曼的这个面相和她的实际情况相去甚远。不过戏里我还是看到一点闪光的东西:她是非常有个性的,敢担当的。尽管戏里她离不开烟枪,自己也难以自主。但从她对胡适表现出的那种叛逆也好,个性也好,这恰是她性格里非常闪亮的—点。
答:一般叙述中的陆小曼是挥霍型的,对感情也是挥霍的。但陆小曼学习法文出身,也懂一些英文;徐志摩去世之后,她完完全全过另一种生活了。建国之后,她鸦片戒除,人生转轨。有一定阅历的人知道这个转变是何等艰难。陆小曼经历了两次转轨剧变,第一次是在沉重保守的社会压力下,第二次是在人生最为惨痛的教训中。能做到这种剧变转轨的是具有什么样性格和能力的人?理解这样的女性,中国文化界需要什么样的能力?
近代以来中国男性世界的危机裂变和困境突围,或成或败,也同样挑战我们的认知。当时的中国社会居然能够出现对浪漫主义的一种真诚的向往(不说它是信仰),徐志摩确实是一位真诚的践行者,这跟在英国的环境里出现浪漫主义根本不具有一个范畴的可比性,代价根本不一样。现代英国、当代美国,他们对自己的多重文化现象和记忆,是惜之如金、渲染铺陈。在一个大变化的境遇中,如何把握、表达、处理大变化中的才华人生?我们如果在这方面更为成熟了,我们的文化能力就不同了。这里面有文化自爱的问题,也有文化能力的问题。对于我们的现代历程,我们需要的,可能还有更多一点的自觉。
问:如何从世界范围内、跨文化的角度看《志摩归去》的意义呢?
答:现代中国文化遗产的世界性是内在的,是现代中国的历史道路使然。比如在语言表达的层面上,剧中主要历史人物都有双语能力,这种双语能力并不是现在凭空而降的现象。目前我在上海交大教授的一门跨媒介艺术史论博士生研讨课,专业定位在跨媒介艺术文化,听课的有中国语言文学专业也有英国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我知道中文出身和英文出身的同学感受是不同的。好比听管弦乐,一方只听到弦乐的声音,另一方只听到管乐的声音,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是管弦乐交响乐。现代以来的中国艺术与文化,当是交响乐的世界;如何去重访和认知其内涵外延的方法,需要在对多重文明经验开放中扩展和更新。我们的文化使命,是要打开更多的思路,一方面连着中国的历史,一方面连着世界的意义,来活跃我们的资源。这出话剧中,徐志摩、林徽因、胡适,属于现代以来中国跨文化积累中的一个部分:还有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白薇、田汉、安娥;还有陈衡哲、冰心、袁昌英、林风眠、钱钟书、杨绛;还有一代代的科学家、工程师们,包括“两弹一星”元勋中的烈士、曾在康奈尔大学任教的郭永怀等等。他们在知识、心智养成中,对于另外一种文明中的精华部分,通过对于自身根本性的扩展而获得的汲取和包容。如果说人的心智有结构的话,那不是不言自明的固化中国,其中有复调,有重奏,有交响。李洁非在他的《典型文坛》里重访了丁玲。他说丁玲从本质上说不像一个中国人。因为丁玲的行为不符合中国传统的一些东西。同时,他们当然是中国人,现代中国人,对此作从形式到内涵的研究,会很有意思的;而要作艺术性的重访,就更有意思了。语言不仅是一种信息表达的技术系统,更是一种精神现象,是一种文明的精神现象。如何获得对不同文明的主动把握和包容而不是被动追随和模仿,在提升深化与不同文明逻辑的谈判能力中,造就中华文化的世界性,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心命题之一。
现在我们全社会的双语使用,与世界近代史上的双语现象,如在印度、南非等国出现的状态,有着根本的不同。中国的双语使用,是以中文这一世界史上唯一没有间断、从古文明持续到现当代的语言为本,是更为主动的决定,是为了扩展人的语言能力及其使用。其中正在形成的能量,蕴含着世界史意义上的文化契机。
问:请您谈谈《志摩归去》的其他方面的意义。
答:我们通常说话剧是综合艺术,包括了文学、绘画、建筑、舞蹈、音乐、工艺设计等等。在一个媒介技术大革命的时代中,跨媒介的视觉文本强大发展,成为文化生产界定性的特征之一。《志摩归去》对视觉的使用、比如对中国书法的舞台使用,在审美上十分有效;原剧本有歌队,作者的审美创意比现在舞台化的演出更多维的追求。也许我们不同专业的同行们可以相聚观剧,跨领域谈想法。语言文字文本与视觉意象文本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非常重要。因为语言文字文本的时间记忆性质,关系到民族文化变革传承的问题;视觉意象文本的空间直观性质,关系到各民族文化提升自身世界性的问题。在当下经济全球化的湍流中,这是每一个国家都会遇到的大问题。话剧以语言文字为本,又内在地拥有综合使用各种表达意义的样式——包括视觉意象的结构性能力;因此相对其他艺术形式,在中华文化赢得世界性意义的努力中,有着更为具体深刻的民族性和前沿性。
这个戏真正的缺陷是什么呢?我觉得是一种——暂且这么叫——“不存在主义”的基调。剧作家不仅是说现代中国的浪漫主义是失败的,而且是不真实不存在的;不仅是退出了历史舞台,而是从未有过真实的历史生命。我对此的认知有所不同。这里的要意不在于现实中是否存在真实、如何真实。因为就认知本身来说,“真实的现实”是一个所有人都可以有看法、但可能谁也不能做绝对结论的命题,因为真实的现实太多面了。可见的不一定就是真实,真实的不一定都获得表达,但确是存在的。有所不同的重点亦非关于现代中国浪漫主义在历史上的内涵外延、流产命运或夭折属性。因为历史剧不是历史学,我是指我们的剧作家对徐志摩式艺术践行的关注,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不仅是“志摩早死”,而是此类人活不成。当然,徐志摩活过、并且活成了,因为现在还有人在写出并演出他的话剧。这样的人活不成、存在不了是当下某种感知的暗示或预设。
重访现代中国及其艺术精神,可能需要少一些积淀的心智结构或预设的审美透视。同样,作为一种艺术文化精神活动,这种重访本身,来源于更新历史想象与人生可能的潜在要求和能量。凝历史中国艺术精神,塑当下社会心智形态,对人生有所期待的人,珍惜所有,开阔当下,“有力地、坚韧地,横过历史”(林徽因《彼此》,19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