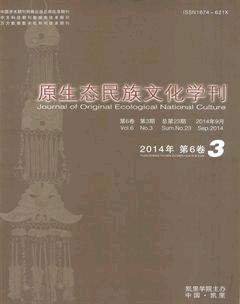论民族文化与环境的适应、冲突及其对生态恢复的影响
李红香
摘要:统万城地处毛乌素沙地的南沿,该区域的原生生态系统属于半干旱疏树草地。历史上,类似生态系统中的草本植物大多植根于厚厚的风化壳中,风化壳层下方则是厚厚的沙土层。这是沙漠风携带的沙土积淀而成的松散土层。其风化壳层甚为脆弱,一旦开发不当,在干旱多风的条件下往往会导致其破损,使沙土暴露在强风侵蚀之下而脱水,诱发为“就地起沙”,最终形成连片的沙地,并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这就是所谓的土地沙化生态灾变。因此,要维护当地生态环境的稳定,首先得维护沙土表层的风化壳和植物残株的稳定存在。充分发掘历史上生息在该区域各民族的本土知识,对土地沙化生态灾变的救治才有望收到成效。
关键词:灾变救治;民族文化;生态恢复;土地沙化
中图分类号:S28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4)03-0010-09
2011年3月25日至28日,作为统万城绿化工程志愿者之一,我参与了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科研考察,对“统万城绿色都市恢复基地”的建设作了跟踪观察和资料收集。在此过程中,特别关注历史时期统万城及其周边地带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变迁之间的关联性,因此在下到统万城绿化基地之前,查阅了当前有关该地区生态研究的相关成果,并搜索了有关历史文献。在考察点,也特别关注该地区的植被层次、土壤构成以及地表覆盖物,认真听取带队老师李令福教授的详细讲解。最终发现。统万城及其周边生态环境变迁,除了本身生态系统的属性外,还与历史上民族文化指导下的人类开发直接关联,因此,考察统万城及其周边地带的生态环境变迁之因,总结生息其间不同民族的开发模式与自然环境的兼容和冲突,就显得尤为重要。
目前涉及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从统万城的兴废看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的影响》、《大夏国铁弗匈奴社会经济状况探析》、《统万城废弃的原因分析》、《毛乌素沙地历史时期环境变化研究》等等。以上研究为深入探讨不同历史时期统万城及其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变迁,揭示生息在该区域各民族生计模式与环境的兼容奠定了基础。为了深入探讨这一课题,本文拟从目前该地域生态系统的属性出发,结合统万城的历史变迁,从生态人类学的视野去探析沙化灾变治理的诸方面。
一、统万城及其周边地区生态系统的现状
历史上的统万城位于今陕西省靖边县城北58公里处,地处红柳河北岸的黄土高原台地上(见图1),因统万城遗址残留的城墙呈现为白色,故本地人将该遗址称为“白城子”。这座古代名城为东晋时代南匈奴贵族赫连勃勃所建,当时为大夏国都城。这座古城距今已有近1600年的历史了。据研究,历史上该处及其周边地带水草丰美、牛羊成群,属典型的疏树草原地带,草原植被下蕴藏有丰富的沙源。在生态环境良好的情况下,覆盖其上的地表风化壳处于稳定状态下方的沙源,暂时处于休眠状态。这样的生态结构,表层风化壳甚为脆弱,不适宜在此地进行大规模的固定农垦,否则,将会导致整个生态系统的灾变,退变为当前所见的沙地生态系统。其后,统万城由于长时段遭逢了人类的无序滥垦,导致地表风化壳及其植物残株受损,才出现了持续的就地起沙现象。目前,该城已处在毛乌素沙地包围之中,干燥度在1.5-2.O之间。加之当地受半干旱区气候环境诸多因素的侵蚀,致使所在地区草原面积严重萎缩,草场退化,湖泊沼泽大面积干枯,植物种类趋于单调,形成了流沙遍地的荒漠景观。这样的沙地荒漠生态系统生物的生长力甚为低下,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一)强风肆虐、气候干燥。统万城及其周边地带位处毛乌素沙地的南沿,年均降水量为300—400 mm,降雨时间主要集中在七、八、九月三个月,年降雨极不均匀。这样的气候条件,在植被稀疏的背景下会造成土壤的粘黏性下降;再加上地表沙土层本身结构疏松,保水能力差,在强风作用下必然会表现为大气与表土的双重脱水。这些气候特点,在植被受损的背景下还会导致湿地退缩,地下水位下降,使整个地表被流沙或沙丘所覆盖。成为学术界所称的沙地。
(二)地表布满了沙丘和流沙,植被极为稀疏,生物年生长量低下。统万城及其周边地带土层中有丰富的沙源,其物质结构疏松,易受风蚀而移位。原有植被遭人类的干扰后,风化壳和地表植物残株受损,失去了庇护的沙源,在强烈的风蚀作用下,就会形成可移动的沙丘,使植被的自然恢复受阻,表现为不可逆的生态受损。统万城废弃后的300多年间,当地各族居民仍然沿袭着古老的游牧生计和资源利用方式,这对维护疏树草地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十分有利,但其后随着北周、隋、唐三个王朝的更迭,为了强化对边墙的防卫,驻军日渐增多,大规模的垦殖随之而至。在这样的生态系统中,从事固定农耕必然要翻动不该翻动的地表风化壳,并清除所有植物的残株,从而使风化壳下方的沙源暴露在强烈的风蚀作用之下,最终酿成流沙遍地的荒漠景观。据气象资料表明,当地风速达到每秒5米以上的强风,平均每年要出现220次以上。这对就地起沙、沙丘南移以及流沙地貌的形成起着关键作用。如果地表有完好的风化壳,而且布满了植物残株,即是风速再大,贴近地表的风速也表现为相对平静,不会引发就地起沙。但试行固定农耕后,风化壳和地表植物残株一旦受损,就地起沙就在所难免了。因而,是否会形成流沙,关键在人而不在当地的特殊地理环境。可见,今天要治理流沙,关键的措施还得回到如何维护地表风化壳与植物残株的存在这一根本性问题上来。
(三)植物物种单调并严重特化。统万城及其周边地带的植被在历史时期经历了群落种类组成渐趋简单、旱生沙生植物增加,荒漠植被明显上升等变化过程。当前该地的乔木主要为人工栽植的榆树、杨树、樟子松等,并生长有沙柳、柠条、沙地柏、优若藜等灌木,平沙地上还有旱柳生长。草本植物主要以早生蒿类植物和丛生小禾草植物为主。蒿类主要是沙蒿、籽蒿、旱蒿、蓖齿蒿等,均属于耐旱的菊科植物。丛生的小禾草主要有沙生针茅、克氏针茅等,它们都属极度耐旱的禾本科植物。此外还有一定数量的百合科植物,如多根葱、蒙古沙葱等等,这些百合科植物生长季短,可以利用头一年储集下来的水资源,完成其年生长过程,能够规避夏秋之间的极度干旱环境。总之,当前该地的植物物种结构,比之于原生的疏树草地生态系统,物种多样化水平趋于低下,而且均属于极度耐旱的草本植物,牧草生长量低下,载畜量大大不如此前的疏树草地生态系统。而人工种植的乔木,与草本植物不相匹配,自身会浪费当地可贵的水资源,对地表风速的降低,也不能发挥积极作用。最终使得现有植被,不可能导致流沙的移动,更不可能引导生态演替逆转,不会自然恢复为此前存在的疏树草地生态系统。因而,即是实施了人工种树、种草,生态灾变救治的成效依然不明显。
有幸之处在于,除了上述能适应流沙环境,但不具备抗风蚀能力的特化植物外,还残留有少数早年疏树草地生态系统的残留植物物种,如白刺灌丛、沙地柏、沙蒿等。这些植物具有较强的抗风蚀能力,可以成为在当地实施生态恢复的先锋物种。其中,生长在这一地区的沙地柏经长期自然演变,目前仍有连片生长的灌木群落。沙地柏根深,能吸取下层地下水为生,叶成针状,具有抗旱、保水、固土等特性,其枝条匍匐生长,植株呈团状存在,郁闭度达0.8-0.9 m,能与沙蒿伴生,形成能够遮蔽地表的灌草群落。一旦其规模扩大,可以有效的减低地表风速,降低地表气温,提升地表大气湿度,有助于让其他不耐早的植物,也能伺机成活繁殖,柏刺灌丛也有同等功效。用好此类植物,人工扩大其覆盖生长范围,可望成为灾变救治的先行手段。
(四)地表风化壳不仅太薄,而且不连片,无法发挥抗风固沙的作用。地表风化壳是由丰茂的林木落叶和草本植物在每年枯死后,经长年累月的积淀最终形成的腐殖质和沙土的混合物,其结构连片而疏松,可以透气透水,又能给地表降温保湿,还能抵御风蚀。风化壳本身肥沃,又具有储水保墒的功能,因而它是沙地生态恢复的关键。目前对沙地救治的要害,就是要恢复风化壳,尽可能多的保留灌丛和牧草残株的稳定存在。但要恢复风化壳和地表植物残株,单纯的植树种草还不能解决全部问题,原因在于在当前的沙地环境下,地表温度和湿度的变幅很大,植物落叶和残株降解速度极为缓慢,腐殖质难以熟化,并由此而降低了风化壳的形成速度,解决的办法是需要在植树种草的同时,进行适度放牧,使每年新长出的植物,能较快的通过牲畜转发为粪便,粪便的降解速度就会明显提高。从而,加快风化壳的积累速度,同时又可以巩固牧草残株的稳定存在。如此,才有利于生态演替向良性方向发展。
目前当地呈现的沙地生态系统,在历史上由于受到汉文化本位偏见的干扰,早年的汉文典籍往往将这样的生态系统称为“不毛之地”。然而,这样的“不毛之地”,并非不可逆转,只要认真发掘当地各游牧民族的本土知识,就能找到引导生态演递向良性方向转化的对策来。其要点体现为,需要适度放牧,包括浅牧、快速移动放牧,目的是要让牲畜均衡地将当年长出的牧草消费掉,转化为牲畜粪便均匀地铺洒在地表,使之尽快就地形成腐殖质,发挥粘连沙土的关键作用,成为风化壳加厚的骨架。这样的对策看似简单,但却完全符合生态系统中生产者、消费者、降解者并存互动的生命格局。在这样的多物种复合作用下,风化壳才能呈现为滚动加厚的态势,牲畜消费后留下的灌丛和牧草残株在浅牧的背景下也能逐年加密,从而发挥降低地表风速的关键性作用。沙地灾变才能逐步得到抑制,并推动生态系统向良性转化。由此可见,谢绝一切形式的放牧,显然违背了生态演替的一般性规律,而简单的植树种草,又不能推动风化壳的形成与加厚,这显然对生态恢复发挥的作用难以显化。为此,如果人为破坏这样的风化壳,疏树草地生态系统的稳定延续就会受到威胁。但如果反过来,大力推动植物的消费,推动风化壳的再形成,那么看似难以治理的流沙也就找到了治理的良方。
由此看来,历史上统万城及其周边地带的生态系统,正好是与当地无机环境相适应的产物。这样的生态系统,在游牧民族看来既正常又富饶,可以养育他们赖以为生的牛、羊,而不会退变为荒漠。从文献记载来看,当地的各少数民族在不同的季节进行南北转场循环放牧,以恢复地力。但对于农耕民族而言必然萌生将草原改为农田的想法。然而一旦改建成固定农田,大规模种植农作物后,就会导致这一地区植被覆盖度降低,诱发沙化面积的扩大。今天统万城及其周边地带的荒漠化景观,无疑是长期以来由于使用了与当地不相兼容的民族文化,而引发就地起沙的恶果。为了充分说明这一变化过程,就得对统万城及其周边生态环境变迁,做一番清晰地剖析。
二、统万城及其周边地带生态变迁的脉络
对于统万城及其周边地带的生态环境变迁,前人已经做了很多研究,但由于学科背景及研究主题的差异,坚持自然成说者有之,倡人为原因者有之,兼收自然原因与人为原因共同作用者亦有之,而且各自都提出了有力的证据,但却难以达成共识。侯仁之先生认为,统万城及其周边沙地,“除去它(本身)的现状外,还必须了解它的过去,特别是要了解由于人类活动所导致的沙漠本身的变化”。因此要了解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就得分析不同民族文化规约下的人类群体,他们的开发模式与环境的关系对生态结构的影响及其后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其生态环境的变迁,从民族文化的视角把握其成因,进而提出有效的救治措施来。
历史上这一地区“水草丰美”“树木茂盛”,畜牧业发达,零星的种植业在社会经济结构中虽有一定地位,但只起辅助作用,疏树草地地表的风化壳并未大规模受损,这才使得生态环境直至唐代以前均未严重受损。据研究,在西汉时代的史料中,从未提及过有关土地“沙化”的记载。南北朝时,才偶然提及流沙影响到军事行动。但影响范围,仅限于个别区段。风沙肆虐,并直接威胁到夏州城(唐代统万城名)的灾变事故,是唐代中后期才见诸史料记载。因而,这里生态的变迁脉络,可以总括为直到隋唐之际才明显退变。
据考古研究,在郝连勃勃建统万城时,这里植物甚为繁茂,以蒿属为主,伴生有黎科、寥科、毛茛科、十字花科、菊科等多种牧草,其间还间生麻黄一类的特种草本植物,还有部分树林稳定存在。《晋书》卷一百三十《赫连勃勃传》载,匈奴赫连勃勃于公元413年营建大夏国都统万城,都城落成后,刻碑城南。碑文云:“近详山川,究形胜之地……石郭天池,周绵千里”,城里有“华林灵沼……土苞(原意为蓆草,此处泛指水草丰美)上壤。”《元和郡县志》卷四《夏州朔方县》载,公元413年匈奴族首领赫连勃勃巡游到统万城,这里的生态环境就非常好,当时他看到这里的自然环境曾感叹地说:“美哉,临广泽而带清流,吾行地多矣,自马岭以北,大河以南,未之有也。”《太平御览》亦载,赫连勃勃赞美统万城周边环境而发出的感慨:“美哉,斯阜!临广泽而带清流。吾行地多矣,未有若斯之美!”以上资料可以反映在南北朝时期,统万城及其周边地带是“林草盖地”“水碧山青”,自然环境良好。
至唐朝时,统万城更名为夏州城。此时由于唐朝政府在此实施军垦和民垦,鼓励垦荒,实施大面积的草地芟除,使得植被及覆盖沙源地表风化壳大面积破坏,该地才会出现沙丘和流沙,并在文献当中得到记载,这充分表明唐代时当地土壤沙化已经十分明显。《新唐书》卷三十九《五行志》载,长庆二年十月(822年)“夏州大风,飞沙为堆,高及城堞”。李益诗说,统万城一带“无定河边数株柳,风沙满眼堪断魂”。咸通年间(860-872年),许棠作《夏州道中》诗亦云:“茫茫沙漠广,渐远赫连城。”这里的沙地生态景观,到此时已经呈现为大规模扩展态势。
到了宋代,为防西夏入侵,宋廷在夏州筑城屯垦,随着地表风化壳的铲除,导致了当地土壤沙化更趋严重。宋人说:“从银(今榆林南部地区)、夏(州)至青、白两池(今定边地区),地惟沙碛。”“碛”,即沙石积成的浅滩。宋人的记载进而明确说道,统万城深在沙漠之中。雍熙元年四月(984年),宋供奉官王延德在回到京城后,叙述其出使高昌,途经统万城及其周边地带的所见景观时,说:“初自夏州历玉亭镇,次历黄羊平,其地平而产黄羊。渡沙碛,无水,行人皆载水(方可行)。”又云:“次历茅女王子开道,族行人六窠沙。沙深三尺,马不能行,行者皆乘橐驼(即骆驼)。不育五谷,沙中生草名登相,收之以食。”凭借这一记载可知。当时这一地区的土地沙化现象,已经极为严重。以至于离开了骆驼就无法穿行。更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记载中明确提到了“登相”这一特化植物。登相,即碱蓬,这是一种菊科植物,不仅耐旱而且能够在极度强盐碱化的土壤中生长。其枝叶苦涩,无法入口。但种子富含油脂,是一种美味的食品。这种食物的普遍存在,而且还能充作粮食实施,足证其生长规模甚广。当地突然已经呈现为强碱性。要发展到这一步,往往是地表风化壳和植物残株,被大规模清除后,在经历两三百年的日光暴晒,地表水被蒸发才可能出现的土壤酸碱度变迁。这一演化需要的时间恰好与文献记载相互应征,即从唐穆宗到宋真宗时,前后经历的时段,恰好与土地呈现为强碱性所需要经历的时段,大体相近。
明代时,明廷沿长城实施屯垦守边政策,调动汉族军户在长城内屯垦自给,农垦规模更趋扩大。使得具有防沙护泥功能的地表风化壳和植物残株挖掘殆尽,沙化规模更趋严峻,对此清代成书的《靖边县志稿》卷四《艺文志》载:“陕北蒙地,远逊晋边,周围千里,大约明沙、扒拉、咸滩、柳勃居十之七八。有草之地仅十之一二。明沙者细沙飞流,往往横亘数千里。扒拉者,沙滩陡起,忽高忽陷,累万累千。”这一记载说明流动和半流动沙丘已随处可见。与之近邻的神木地方文献亦载:“边外有沙漠田者,能生黄蒿,俗名沙蒿。生既密,频年叶落于地,借以肥田。如是或六七年,或七八年,蒿老而地可耕矣。然仅种黍两年,两年后复令生蒿,互相辗转,至成黄沙而止。”沙蒿系多年生草本植物(见图2),为骆驼、牛、羊喜爱的牧草,该植物多为成片生长,茎为丛生,其落叶长期掉落地上后,经长年积累会形成厚厚的腐殖质层,此层土壤十分肥沃,能够支撑其他植物的生长,也能最大限度的防止水分的无效蒸发。凭借这一记载可知,当地各族居民,已经认识到了这种特有植物的生态价值,并作了充分的利用,借以实现农牧交替运作,并收到确保生态脆弱稳定延续的成效。这对今天的沙地治理,无疑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随着农地垦殖规模的扩大和耕种频率的提高,导致来之不易的腐殖质层不断遭到破坏,最终引发了当地土壤的严重沙化,尤以清末实行的借地养民政策为最。而且,其恶果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时期。
民国时期,屯垦的规模更大,特别是受到军阀混战的影响,控制这一地区的军阀,无论是冯玉祥还是傅作义都致力于扩大垦殖以充军饷,影响所及至今还难以挽回。加之民间的乱垦滥伐有增无减,统万城及其周边地带草原面积急剧缩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该地已经村落较多,耕地成片。土地大面积沙化,统万城及周边地区,至此完全被扩大的毛乌素沙地所吞没,统万城遗址也就成了沙漠腹地的历史陈迹。早年统万城周边的湿地与河流,包括连片的柳林,目前已经彻底被沙丘所覆盖。几乎找不到早年的生态痕迹了,仅仅留下了红柳河这个地名,还可让今天的人依稀可以想见当年水草丰美的景象。
从上可见,统万城及其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变迁主要是采用了与之不相兼容的开发模式,所诱发的生态灾变,因此要维护统万城周边地带生态环境的稳定,就得维护地表风化壳及其着生其上的植物残株的稳定存在,故探讨历史进程中生息在该区域的民族文化与环境的兼容就显得必不可少。
三、生态人类学视野下的沙地治理
生态人类学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是由美国学人维达和拉帕波德(An-drew P.Vayda&R0vA Rappaport)等提出的,该门学科主要是致力于研究人类与环境之间复杂关系的一门新兴学科,探讨内容涉及“人类对环境的生理与形态的适应,人口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营养结构与人类体质状况,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充分利用,以及从不同人类群体的谋生手段出发,探讨自然资源开发与生态系统循环的关系,生态和文化的相互渗透和影响,揭示生态系统的运行规律和寻求保护生态平衡的正确方法”。因此借鉴生态人类学(或称生态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揭示统万城及其周边地带各族居民维护牧场稳定的本土知识,以服务于我们今天的生态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
历史上,统万城及其周边地带长期为各游牧民族的生息地,水草丰美,草场优良;其后,由于开发模式不当,才使得原有的草地变为今日黄沙漫漫的沙地。显然,这与人类经营模式直接关联。如上文所言,统万城本来就是建立在疏树草地生态系统之上,该生态系统中的枯枝落叶,经过长年的历史积淀,才形成厚厚的风化壳,这样的风化壳和着其上的植物残株具有维护地表稳定和储养水源等诸多生态功能,对维护当地的生态稳定一直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历史上,生息其间的各游牧民族居民在此实施放牧的生计模式,这样的生计模式由于看重的是牲畜产出的稳定,因此十分注意地表植被充分利用和风化壳的维护,并积累了丰富的本土知识,因此总结其成功经验,对于当前该地的生态恢复大有裨益。
(一)充分利用植被层次结构,匹配家畜比例有序。据研究,统万城及其周边地带,在筑城以前或筑城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该地区水源充足。水丰草美,沟谷、河岸边生长有椴、桤木、榆、胡桃、杨、柳及沙地柏等喜温湿的乔木,林下是中生和湿生草本群落,河流、湖泊,沼泽中水生植物繁盛。而在河湖干涸的丘间低洼处或盐碱性的土壤上分布着黎科、菊科、寥科等早地植物,还分布有耐早性能稍次的禾本科、十字花科、蔷薇科、豆科、缴形花科、龙胆科、胡颓子科等草本或灌木。高原台面上或山丘上还分布有松柏林。这样的层次结构,可以尽量的荫庇地表,保持土壤的湿度,可以为各类家畜提供丰富多样的食物来源。剩下的植物残株还能抵御风蚀,对稳定地表风化壳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对于这样的疏树草地生态系统,当时的各游牧民族绝不会大规模翻耕土地,而是合理的配置多畜种的比例,实施合群放养,尽可能地维护地表牧草的均衡利用。因此畜群规模虽然很大,但畜群消费的仅是植物的枝叶而已,并不会翻动地表的风化壳,更不会扰动土层结构。对此,仅略陈3例汇为表1,以见一斑。
从表1可见,从赫连勃勃建国到唐朝中期,统万城及其周边地带畜群的规模之大,特别是北魏接管这一地区后,畜牧业更为发达,如果用“羊单位”折算当时的载畜量,一个“羊单位”仅占用不到二亩的牧地。其载畜量之高,即使是今天畜牧业最发达的国家如荷兰也难以企及,故上述记载也引起了学界的质疑。有学者认为在当时情况下。区区统万城地区根本不可能产出如此规模的家畜。然根据统万城考古时期的植物构成,再结合近年来学界对有关家畜食草及活动状况的调查和研究,完全可以证明:家畜食草特点与环境的关联性,具体情况请参见表2。
从表2可见:绵羊仅吃含水量降低的“干草”或灌丛的嫩叶。山羊则是觅食灌丛的枝叶。牛、马则采食禾本科、菊科等优质牧草。骆驼食灌木或乔木的树叶及嫩枝。以上诸类家畜的食性特点各不相同,从中揭示了各游牧民族对家畜与食草环境的深刻认识,进而为维护当地生态环境的稳定发挥了关键作用。对此,台湾学人席慕容在《新民晚报》刊发的《发菜与开什米》中亦言:“蒙古人的五畜,顺序不变,永远是马、牛、骆驼、绵羊、山羊这样的排列。在吃草的习惯上,马爱吃草的尖端和籽粒,所以要寻找草较高的牧场。牛是用舌卷草吃的,矮草即可。羊(绵羊)的牙齿锐利,每每啃到草根,所以放过羊(绵羊)的牧场,一年只使用一次,除非新草再生,不然无法放牧。而山羊更是毁草毁得利害,牧民原来养山羊的头数是很少。”上述论证基本符合实情,但仍有误解之处。其实,山羊很少取食草本植物,除非是质地特别坚硬的牧草才偶尔取食。因而蒙古族饲养山羊,关键是要在疏树草地生态系统中放牧,绝不会在典型草原和荒漠草原中放牧。典型草原和荒漠草原主要是用来放牧绵羊的。因为绵羊主要是采食牧草。但绵羊绝不会刨根取食。在极度饥饿时,绵羊会取食马粪,但也不会刨根。骆驼主要是在疏树草地放牧,或者在典型沙漠中的琐琐林放牧。蒙古族放牧牛要选择相对湿润的草句草原,或者相对湿润的“柴达木”(蒙古语指低洼的盆地)。总之,“五畜合群放牧”是随生态环境而变的。一旦饲草不足,蒙古族牧民要么出卖牲畜,要么就屠宰牲畜,绝不会让牲畜掉膘,眼睁睁看着受损失。将畜牧业理解为牲畜多了过牧,随时处于牲畜过牧状态,显然是从农耕文化的视角,而做出的误判。
另外,除了历史时期统万城及其周边地带庞大的载畜量食草特点外,还需要注意草原产草量在年度内和年际间极不均衡这一现象,草原上家畜的放牧半径大得惊人,如马的放牧半径为80公里,牛为50公里等,羊的放牧半径要超过20公里,这样放牧才能将零星的饲草资源利用起来,并将牲畜粪便均衡的撒遍地表,支持风化壳的加厚,确保免遭风蚀干扰。使以后的产草量逐年稳定上升。这些立足于当地本土生态知识的做法,如果改用专业术语来说,可以归结为快速移动式浅牧,或多畜种的匹配放牧,其执行结果都不会导致牲畜过载,更不会出现明显的草原退化而不能自我更新。因而,将牲畜过载归结为草原退化的主因,显然站不住脚。如果不改变类似偏见。文献所载的巨额载畜量,就无法得到合理而科学的解读。
(二)培育匍匐类、丛生类植物,让牲畜对乔木进行计划性修剪。统万城部分地段种植有沙地松,这样的沙地松呈蔓生状爬地而生,其匍匐茎长到那儿,与之伴生的丛生状草本植物也就随之长到那儿,进而在爬地松下方形成一片隐蔽带,在隐蔽带内气温相对降低,湿度相应提升。据李令福教授介绍,这种木本植物是匍匐长在沙地上,对沙地有很好的遮蔽作用,掉落的叶子经常年积累后,最终形成厚厚的风化壳,能够最大限度的遮盖地表,防止强烈的太阳光直射地表,防止地表增温,抑制水分蒸发的速度。因而,风化壳有储水之功能,让其他植物的种子在此发芽、着根生长。在这样的风化壳上生长的植物大部分都是丛生和蔓生的植物,因而能最大限度地保持地表覆盖物的稳定。
如前文所言,统万城及其周边地带是干旱疏树草地生态系统,虽生长有一定量数量的大型乔木,此类乔木的存在,也具有抵抗风沙,加厚风化壳的积极作用。但统万城及其周边地带,雨量甚少,风大,高大乔木的生长耗水量极大,因此水资源的持续稳定成为了当地生态结构稳定的关键要素,特别是降水奇缺的季节和年份,不实施修剪,大树就会枯死,进而还会导致牧草短缺。为了应对这样的自然变数,历史上该地区各民族都习惯于实施规模化的骆驼饲养,并让其有计划的取食高大乔木的枝叶,帮助乔木实施强制修剪,使这些乔木都能顺利熬过干旱的侵扰。这不但维护了地表植被的稳定,进而还能扩大牲畜的承载量。
(三)乔、灌、草混栽,以利于植被的全面恢复。据研究纯林构成的生态系统隐患无穷,其危害性体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1.生物多样性水平低,生命物质年增长量低下;
2.地表覆盖率低下,水土保持能力差;
3.生态系统脆弱,极容易感染病、虫害。
此外,单一的物种稳定性能极差,抗干扰能力弱,一旦受到外来因素的无序影响,很有可能使原有的生态系统崩溃。因此,统万城及其周边沙地的治理必须强调在作物栽种时的植物比例的搭配,最好是乔木与草本植物混栽,灌木与乔本植物并存。毛乌素沙地的专业治沙人阿尤木斯那介绍,治沙应注意乔、灌、草相结合,治沙时宜先“从沙丘的底部开始,先栽一行沙蒿,然后再栽一行榆树,乔灌草结合,高低结合,在治沙过程中相机造林,在造林中优化治沙成效”。这一做法,从其选定的地点看,是沙丘的底部,沙丘底部相对顶部而言,湿度较高,有利于植物的生长。又据笔者在统万城植树时发现,当地人在植树时,不会全面清理沙地上的各类植物,而是直接将樟子松与杂草混栽,同时还会混栽下一定量的柠条、沙地松等。据带队老师李令福教授介绍,2003年在统万城南侧,采取乔、灌配合种植的8000余株樟子松,成活率极高,目前已蔚然成林,郁郁葱葱。
从上文看,我们只要弄清楚了历史时期统万城及其周边地带的植被构成,层次结构,揭示生息在该区域各民族的本土知识和技术技能,就能为当前的生态灾变的救治提供经验。
四、结论与讨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历史上北方地区,特别是干旱、半干旱地区,农业垦殖的最终经济效果并不理想,原因是这样的干旱区和半干旱区干燥少雨,地下又蕴藏有丰富的沙源,要维护这一区域的生态稳定,就得维护地表风化壳和着生其上植物残株的稳定存在。一旦采用与之不相兼容的开发模式,就会导致土壤层下面的沙源大面积外露,在强烈风蚀的作用下必然酿成就地起沙的恶果,引发当地生态系统的灾变,影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今天,统万城及其周边地带的荒漠景观就是一例。对于这一景观,20世纪30年代,美国学者G·B葛德石认为:“在生态环境脆弱的半干旱草原地区,一旦地表的植被由于过度耕垦而被破坏,表层土壤被裸露出来,在风力作用之下,沙粒上的细物质被吹走后,便只剩下沙子和石块了。”
历史时期统万城及其周边地带土壤沙化成因,给我们很大启示,如果要加快当地的生态恢复,我们就需按照历史上统万城植被构成,采取乔、灌、草混合种植模式,在不同的区域逐步推行,使之尽可能的覆盖地表,形成厚厚的风化壳。同时还得改革我国北方草原政策,让各游牧民族居民可以实施合理放牧,以便加快风化壳的积累。这样才有可能真正恢复以前的疏树草地生态系统。据日本学者言,当前这里的荒漠生态景观。只要我们维护得当,此类沙地依然可以得到生态全面恢复。那就是当这样的沙地上有足够厚的风化壳覆盖后,土壤达到足够的湿度时,只要持续十多年就可以全面恢复当地的疏树草原生态系统,真正实现历史上“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壮观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