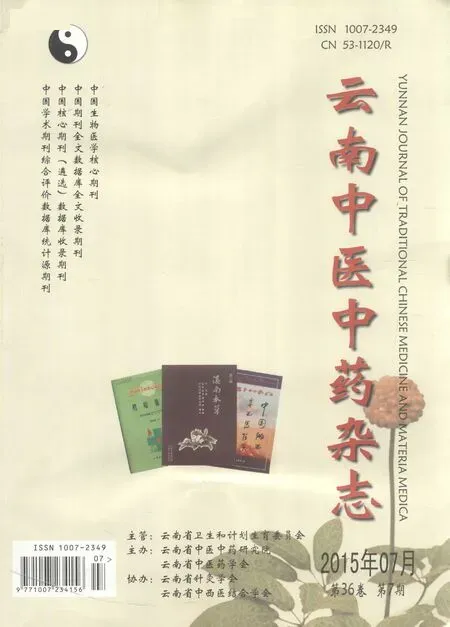毕摩在彝族传统医药知识传承中的地位和作用*
罗艳秋,徐士奎,郑 进△
(1.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 100029;2.云南中医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3.云南省食品药品检验所,云南 昆明 650011)
毕摩在彝族传统医药知识传承中的地位和作用*
罗艳秋1,2,徐士奎3△,郑 进1,2△
(1.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 100029;2.云南中医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3.云南省食品药品检验所,云南 昆明 650011)
本文通过对毕摩社会功能和历史地位的叙述,辨清毕摩等同于巫师的错误认识。毕摩不仅负责彝文古籍的传抄工作,还肩负着彝族文化传承的重任,在彝族医药文化传承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毕摩经书对彝族医药的继承与发展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毕摩所使用的医祭混合的医疗方式属于彝族医药发展的早期形态,也是医学发展必须经历的阶段;毕摩经籍是见证毕摩认识、从事医疗实践活动最确切的历史档案,通过寻医找药的记载,详述彝族医药的发展脉络和演变规律;通过作祭献药的记载,反映彝族对生命规律认知的思维体系。
毕摩;彝族;传统医药知识;传承
历史上人们一直认为在没有形成彝族医药专书之前,彝族无医无药,主要依靠毕摩使用医祭混合的方式治疗疾病。如元代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罗罗》说:“有疾不识医药,惟用男巫……”,其后明、清直至民国,一些志书有类似的记载[1]。如果把毕摩等同于巫师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毕摩作为彝族氏族部落首领即执政者,不但在彝族共祖阿普笃慕(约为春秋时期的彝族历史人物)时代即是如此,而且延续到了有汉文献可资考察的唐宋时期[2]。由毕摩随之产生的毕摩文化必然是彝族社会的“官方文化”,所掌握的彝文经籍是彝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毕摩是彝族社会中从事于原始宗教活动的祭师,是彝族文化的传承者,是彝族古代的语言、文字、哲学、历史、谱牒、地理、天文、历法、民俗、伦理、文学、艺术、医学、农学、技艺等丰富知识的集大成者,不仅是宗教仪式的主持者,也是主要的疾病诊疗实施者[3]。彝文古籍说:“毕摩诵经文,毕职行斋祭,经史得流传”[4]。大部分毕摩通晓彝文,负责彝文古籍的传抄工作,毕摩的职能决定其与彝文古籍必然产生不可分割的联系,肩负着彝族文化传承的重任。毕摩在彝族医药文化传承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毕摩经书对彝族医药的继承与发展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毕摩经书包括了大量医经合一的彝文典籍,记载着重要的医药内容,如《尼苏夺节》、《供牲献药经》等文献。
毕摩对经书的传抄不仅推动了彝族传统医药的继承和传播,而且其严格的师承授受关系维护了彝医药的保真性和系统性。在彝族早期发展历史中,有毕摩谱系的人才有资格当毕摩,随着彝族氏族部落社会结构“君、臣、毕、民”的分化,毕摩的传承逐渐从祖传制向师传制延伸,形成了具有特殊社会功能的群体,才有更多的人群通过师传的方式从事毕摩的职业。
1 医祭混合的医疗方式推动了医学的发展
学术界对毕摩经书的研究侧重于研究其文字、历史、文学、谱牒、民俗、宗教等方面内容,忽略了医药内容的研究。人类早期的文明与巫事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如《金枝》中说:“他们不仅是内外科医生的前辈,也是自然科学各分支的科学家和发明家的前辈。”在我国古代巫与医二者为一体,即一身兼二职。《山海经》中记载的巫彭等10位传说中的巫师,都是医术高超的医师。《论语》中说:“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史记·曰者列传》引当时博士贾谊所言:“吾闻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卜医之列”。从孔子说的“巫医”与贾谊提的“卜医”可以看出古人是将巫术与医术都视为治病手段的,彝族也是如此。巫术作为一种“信仰疗法”,至今仍然深深扎根于彝族民众思想之中。
对于这些“信仰疗法”,学界一般是将其归入民俗信仰或宗教仪式范畴。其实,在古代中医也是存在“信仰疗法”的,并将其与其他类别医书并列。最早的目录学书籍《七略》在“方剂略”下将医书分为4类,即医经、经方、房中、神仙4类,可见早期的中医也是将巫术视为诊疗手段之一。巫医结合是彝族传统医药发展过程中的特定阶段,表现为彝族先民对天地与人体的认识以某种混合的统一性来领悟世界万物,学者将此现象称为“互渗律”。从这个角度说毕摩不仅是祭司,更是彝族的“兼职医生”。通过这样的现象就可以解释产生于古代的传统彝医学理论体系中的某些概念与道家的概念在以某种混合的统一性领悟世界万物时有相通之处。
为了解毕摩的医疗职业特征及其文化特点,笔者3年来走访了滇川黔等地三十多位毕摩,发现一些彝族患病后首先是请毕摩进行占卜,然后施行各种治病仪式,在仪式过程中,毕摩经常会给患者喝一碗草药。此可以将治病仪式看作形式,将草药作为治疗疾病的内容。彝族宗教与彝族医药是相互依存的,这种形式和内容的关系使得人们无法辨清毕摩宗教与彝族医药的关系,究竟是仪式起作用,还是那碗药汤在发挥治疗作用?毕摩在以宗教的方式治疗疾病的同时,也应用一些医药知识,笔者发现在许多毕摩经书上记载有医药知识,包括药物和药方。
这种医祭混合的医疗方式属于彝族医药发展的早期形态,也是医学发展必须经历的阶段。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李世康对滇川黔四十多位彝族毕摩开展调查,据统计三分之一的毕摩是草医,且存在另外2种情况:一种是祖上为毕摩,后来绝传了,但毕摩神一直供奉着,后嗣当了医生,彝民认为有毕摩神保护的医生能治好病;另一种是毕摩家族中,有的做毕摩,有的当医生。这样的例子很多,如四川省凉山州越西县申果庄区沙玛比古是毕摩,其长子是医生;楚雄州南华县五街乡咪黑村公所五力么村周正元是毕摩兼道士,其弟是医生;武定县猫街镇石板河村李应高家族中,有的做毕摩,有的当医生[5]。并且可以证实的是,彝族的毕摩神谱中有一位药王神,各地毕摩都奉药王神,说明在彝族毕摩中是比较重视医药的,医术是其掌握的重要技能之一,毕摩在传抄经书时涉猎医学内容也就无可厚非了。
但令人遗憾的是,1949年以后由于毕摩等宗教职业者队伍不断萎缩,毕摩经书也逐渐失传,加上中医学和西医学传入彝族地区,彝族医药的发展随着宗教形式的弱化也逐渐退居二线。可以预料,随着毕摩的逝世,毕摩文化后继无人,这些经书内容将永远无法解读,这是彝族医药发展和传承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难题之一。
2 毕摩经书对医疗活动观察和实践的重视
彝族是一个善于观察思考的民族,“心里想知识,手里写知识,口里讲知识”已经成为彝民族的优秀传统。如果仔细查阅各类彝文典籍,就会发现彝族先贤对医药知识孜孜不倦的探索和追求。各类毕摩经籍常会穿插记载人类“寻医找药”的故事,寻医找药的道路艰难,充满荆棘,但通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在牧羊女等劳动者那里获得辨药识药、诊病治病的方法。通过对毕摩的访谈和观察,毕摩在进行作祭时,必有一场“献药”的祭仪,前来吊丧的亲友均要喝此药汁。可见,彝族对生命、疾病与医药的认识和实践始终渗透于彝民族生活劳动的各个方面,彝族传统医药理论正是彝族先贤通过长期的医疗实践的观察和验证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2.1 通过寻医找药的记载,详述彝族医药的发展脉络和演变规律 不同地区挖掘的彝文医药典籍都不同程度记载了彝族寻医找药的故事,通过找药的历史记载,反映彝族对疾病和药物认识的发展和经验的积累。在早期彝文医药典籍中,从事彝族医药活动主要有3类人:一类是彝族的祖先,通过类似神农尝百草的方式积累了大量药物知识,如彝族祖先英臣什诺;一类是代代传承医术的世家,如古代略氏家,略比尔玉嫫既能打卦占卜又能医治疾病;一类是在不断劳动实践中积累医药经验的劳动人民,此类在彝文古籍中最为多见,记载较多的为牧人,其中以女性居多。
懂得医药知识的多数为女性是彝族医药古籍记载早期寻医找药历史的特点。如古代彝族炼丹术创始人徐玉波及其女儿徐玉阿梅(《挖药炼丹》),还有《尼苏夺节》中记载的“贤学小姑娘”,《祭祀经·找药》中记载的“谢比偻姑娘”。《彝族创世志·艺文志·采药之歌》记载恒颖氏族女性阿默妮最早学会使用药物和辨识药性,为“播良药之人,识药物之人”[6]。《物史纪略·女权的根源、医药的根源》中也谈到“女的治好病,女的医好病;女的有知识,百病她来治[7]。”此外,彝文古籍中大多记载的是母亲生病为其寻医找药,《祭祀经·找药》:“纳比偻他妈,他被病魔缠。”许多典籍都反映出彝族医药起源于母权制时代。
彝族的祖先英臣什诺采百草,尝百药,不断积累医药知识,是彝族医药的早期发展阶段,为彝族医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流传于云南新平地区的彝文典籍《哦姆支杰察》记载:“在荒古年代,世上的人们,有病不会医,病了吟哼哼。我们的祖先,有英臣什诺,上山采百草,尝遍苦酸辛。百草有百样,一样采一百,百样治百病,有病不再哼。后人学什诺,如火星火种,什诺的医药,一代传一代”。
四川发掘的《寻药找药经》和云南发掘的《挖药炼丹》、《祭祀经·找药》等典籍所记载的“寻找不死不病药”的故事十分类似,记载为了解除疾病的痛苦,迫使人们不畏艰险寻找药物,对药物的认识是从识药辨毒开始的。向世人表达了药物的寻找只有劳动者才能找到,通过劳动实践获取药物治疗作用和有毒无毒辨别的方法。药物是十分珍贵的,不付出艰辛和汗水是不可能寻找到药物的。同时也向世人说明人世间是不存在不死药和不病药的,说到:“世间不死药,给了太阳神,世间不病药,送了月亮神[8]。”“有病可医治,月有缺圆时,命有终尽时。长生不老药,实在真荒唐。药只能医病,人不免一死,万物皆如此[8]。”本书记载的故事说明了生病和死亡是人类无法避免的,必须正视疾病和死亡。
《寻药找药经》记载了天君(指首领)、天臣(指头目)、天师(指祭师、毕摩)一起出发寻找药物,但是始终找不到“不病不死药”,当统治者束手无策时,只好向劳动者请教。向牧羊的天仙女求助,书中写道:“他们三位(天君、天臣、天师)很是不甘心,寻找天仙女,一心访良药。这位天仙女,放牧羊去了。”书中描述刻画了药物的珍贵,人们不惜以“九黑牛为礼”、“六羊六黑牛为礼”、“三羊三黑牛为礼”去找药寻药。在发现药草的过程中这样写道:“到了宏兽山,因为羊儿病。心中暗焦急,急忙找药草。掰一枝黄药,绕向羊儿身,不见羊儿起,这不是良药。觅到青叶药,急忙采一枝,绕向羊儿身,羊儿站起来。羊儿喃蹦跳,这正是良药”。对动物细心观察发现药草,说明彝族药物的发现和应用是以生活实践为基础的,彝族人民在劳动实践过程中积累了大量药草知识。
还有许多彝族医药古籍文献描述了彝族发现药物的经过和故事,表达了彝医是起源于生活实践,而不是源于巫术的思想。其中,始终贯穿全文内容的还是如何运用药物治疗疾病这一主导思想。《挖药炼丹》通过略比尔访医寻药讲述了疳痨的治疗方法,痨疫表现为面黄肌瘦、眼眶凹陷、四肢枯槁、眼皮沉重,“面饥黄,双眼似研臼,两手象钉耙,眼皮重千斤,拉成一条线[9]。”使用草乌、墨蛇胆、獐子肝和细猴药煎服。
远古传下来的彝族阿哲药书《挖药炼丹》讲述了古代略氏家,代代传医术,略比尔玉嫫既能卜卦又能医治疾病,但是后来病重由其子略比尔访医寻药的故事。知母而不知父的略比尔,找到了古代彝族创始炼丹术徐玉波的女儿徐玉阿梅讨要治疗母亲疾病的药物。《挖药炼丹》、《尼苏夺节》这些古籍均记述了治病首先要学习如何辨认药物和毒药,通过对药物形态,花和根茎的颜色和形态以辨别药物是否有毒。“毒树与药材,原在一处长,药叶绿油油,毒叶毛刺刺,药叶亮光光,毒叶色黯淡[10]。”如今在彝族地区,对于识药、采药、用药、种药几乎已成为民俗习惯,很多人都能认识掌握几种甚至几十种彝药及其治病方法,有些地方几乎家家户户的门庭院落、房前屋后皆种植一些常用药草,形成人们应用彝药或草药及单方土法治病极为普遍的特点,有的彝家村寨素有“百草皆药,人人会医”之美誉[11]。
2.2 通过作祭献药的记载,反映彝族对生命规律认知的思维体系 在彝族医药古籍的调查和研究过程中,收集到有关丧葬的毕摩经书,书名多以“献药”进行命名;与疾病相关的占卜和历算的彝文古籍,书名多以“测病”进行命名,疾病占卜和丧葬这两类彝文古籍运用彝族十月太阳历、八方位年对疾病进行占卜病因,并为亡灵作祭献药。很早以前,彝族得了疾病活着时只能延巫祓除,死亡后子女则痛其先人带病辞世,到阴间必然受到疾病折磨,所以彝族不论贫富贵贱,人死后,亲人必为他作祭,这是倮人追悼亡人最大的典礼,作祭时必举行药祭仪式,为死者医病。焚灵草之后,送亡人之事基本结束,然而死者生前往往患有某种疾病,子孙不能为之医好,恐死后继续受疾病之苦或另患其他病,故又献药以医治,使亡人在阴间健康安乐[12]。《作祭献药供牲经》中说:“我等且配植物果木药,调到禽兽药,配合禽兽药。调到蛙蛇药,配合蛙蛇药。家畜五谷药,配合畜谷药。奉饮植物药,植物不死药。为服草木药,草木不死药。奉饮禽兽药,禽兽不死药。消除疾病药,世间我配祖来饮,我等奉承祖辈听;阴间请祖去配饮,服药到病愈,服药到症清[13]。”
曾广泛流传于云、贵、川三省的《供牲献药经》说道:“作祭来到灵堂内,灵堂里面把灵祭。恭请家神转来,恭请财运转来,恭请福禄转来。……死者骑着阴间马,死者赶着阴间牛,死者牵着阴间猪,死者抱着阴间鸡,死者踏上阴间路。……世间健步走一日,阴间骏马越七处。骑上阴马乐悠悠,死者马上不畏途。……如果灵魂不升天,下到阴间位卑微。如果灵魂不升天,去到阴间恐染疾,去到阴间会受难。灵魂升天肉体干,清清净净尘不染[14]。”肉体虽死,灵魂犹在。灵与肉的相剥离而存在,并与太自然永恒共存这是彝族先民对生命形式的朴素认识,这种良好的愿望表现了彝族先民原始的生命观[15]。
《造药治病书》一书记载了内、外、妇、眼、杂病以及兽病的142种疾病的治疗方法,为凉山彝族当时的常见病和多发病。本书虽然记载巫术的内容,但总体来说仍是重于医而轻于巫。书首的一段话开门见山地说:“这是造药治病书”,开篇就强调此书的宗旨是治疗疾病,是在巫术统治下产生的一部书,但是却又竭力冲破“巫”的束缚,是彝族人民聪明才智的结晶[16]。《造药治病书》反映出彝族从“生时求鬼神,死后方得服药”进化到现今的“生时服百药,死后求鬼神庇佑”的漫长岁月正是彝文化向文明发展,彝医药向科学发展的艰难历程。
我们应当辩证地看待彝医药与巫术的问题。毕摩在彝族社会处于知识分子的地位,彝文大多为毕摩所掌握。毕摩在进行作祭时,必有一场“献药”的祭仪,届时,将香附根、艾蒿、生姜、草果、胡椒、鸭蛋壳等多种药物放入土锅中煎煮,并加入动物的胆汁,前来吊丧的亲友均要喝此药汁。另外,由于毕摩能识会写彝文,在一定程度上记录和保存了彝族医药知识,促进了彝族医药的发展。因此,在许多毕摩经书中,诸如《献药供牲经》、《寻药找药经》、《献药经》等经书记录了医药的内容。此部分内容也是彝族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用辩证客观的态度去对待这些毕摩经书。随后,毕摩文化典籍中产生了以医药内容为主的专门著作,标志着彝族原始文化的分化和发展,是一种发展趋势和必经过程。
另一方面,在疾病的预防和治疗过程中,彝医强调要积极治疗疾病,反对盲目求助于巫师鬼神。《劝善经》中说:“有了病就积极治疗,不要相信鬼神,就会人丁兴旺,而那种有病不去医治而去送鬼的“龙烘人”,最后连人种都灭绝。”还说:“汉人不献鬼,汉人种不绝。而彝人呢?白彝不献鬼,白彝种不绝。龙烘兴献鬼,死的死,绝的绝。”告诫人们“不要相信巫师编造的凶兆,献鬼浪费财产,使生活困难。”
3 小结
可见,彝族医药是我国西南地区独具一格的医药文化体系,具有适合其自身发展需求的规律性与规定性,需要独立发展的空间和思路,对彝族医药古籍文献深入挖掘、系统梳理研究可以为彝族医药发展注入新鲜血液,逐步完善彝族医药理论体系,为彝族医药学科构建奠定理论基础。
[1]朱琚元.彝族文化研究荟萃[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144.
[2]朱琚元.彝族文化研究荟萃[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127.
[3]沙学忠.彝族毕摩仪式治病的医学理论初探[J].中国民族医药杂志,2012,(10):8-9.
[4]张纯德,龙倮贵,朱琚元.彝族原始宗教研究[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8:2.
[5]李世康.毕摩药神与《献药经》[J].彝族文化,2001,(3):51-52.
[6]陈世鹏.黔彝古籍举要[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4:118.
[7]陈世鹏.贵州民族学院学术文库.黔彝古籍举要[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4:118.
[8]尼苏夺节,李涛,普学旺.红河彝族文化遗产古籍典藏[M].第2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258.
[9]裴妥梅妮——苏嫫(祖神源流),师有福.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译注第30辑[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1:85-86.
[10]尼苏夺节,李涛,普学旺.红河彝族文化遗产古籍典藏[M].第2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256.
[11]王敏.彝族医药古籍文献综述.//彝族古文献与传统医药开发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编委会编.彝族古文献与传统医药开发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G].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134.
[12]马学良.彝族原始宗教调查报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90.
[13]佟德富,巴莫阿依,苏鲁格.中国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经籍汇编·毕摩经卷[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383.
[14]张仲仁、普卫华译.供牲献药经[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13.
[15]陈春燕,王敏.略论彝族医药古籍中的传统文化意蕴[J].楚雄师专学报,2000,15(1):96-97.
[16]王敏.彝族医药古籍文献综述.//彝族古文献与传统医药开发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编委会编.彝族古文献与传统医药开发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G].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7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彝族医药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研究”(NO:12XMZ077)阶段成果。
罗艳秋(1982-),女,馆员,民族医学博士,研究方向:彝族传统医药知识体系、中(彝)医临床、中(彝)医学教育。
△通信作者:郑进(1958-),男,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医药教育和科研管理、中医理论教学与研究、民族医药理论研究等。E-mail:zhenjinkm@163.com;徐士奎(1980~),男,主管药师,药学博士,研究方向:彝族传统医药知识体系、彝药标准、彝药资源学。E-mail:1946509651@qq.com.
R29
B
1007-2349(2015)07-0101-04
2015-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