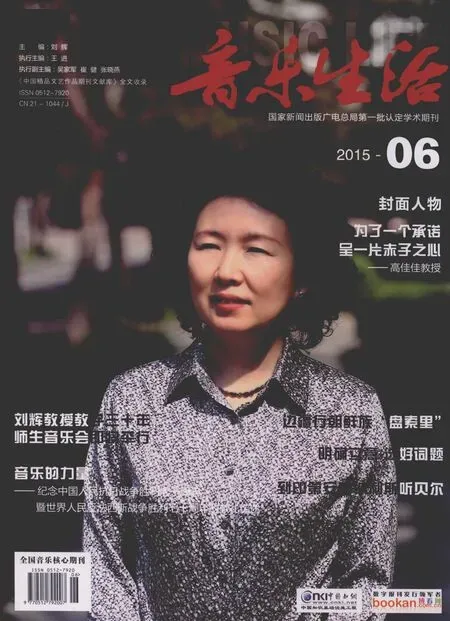他山之石能攻玉否
——对艺术人类学介入中国音乐研究之宏观层面的思考
文/陈金玲
他山之石能攻玉否
——对艺术人类学介入中国音乐研究之宏观层面的思考
文/陈金玲
近些年来中国的艺术人类学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语境下处于醒目的位置。通过理清西方艺术人类学理论这块“他山之石”的概念以及发展脉络,可见其能够琢磨中国音乐研究这块璞玉。艺术人类学理论能够协助中国音乐研究打破其自身的壁垒,走出以建立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和对中国传统音乐遗产进行收集整理为旨趣的“前学科”阶段,进入“音乐”与“文化”接通,以对象和问题意识为导向的“跨学科”研究时期。中国音乐研究也正需如此。
艺术人类学 中国音乐研究 跨学科
艺术人类学作为一种合时入世的研究视野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大潮的汇入共同激发了艺术各学科与人类学的合作与交流。回顾2006年12月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在北京成立,其宗旨即是在承认人类学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廓清艺术与文化、社会的关联。正如王建民教授所言,艺术人类学已经卷入到了中国学界热热闹闹的集体文化运动中,对这种文化现象人类学界以及艺术学界将如何思考与反思?中国音乐研究在论及音乐与文化相互打通时,艺术人类学能给予我们什么启示?
考察“艺术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art)概念的中西差异,涉及西方“art”的概念演进、中西文化翻译和人类学对艺术研究的局限几个方面。西方“art”涵义和中国的“艺术”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1992年版的《朗文英汉双解字典》中“art”词条这样解释道:“art”指技艺,与“skill”相通,另一个意思是美术,尤其是绘画(painting)类的艺术品。再看1980年版的《辞海》对中文“艺术”的释义:艺术即“通过塑造形象具体的反映社会生活,表现作者感情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艺术通常分为表演艺术(音乐、舞蹈),造型艺术(绘画、雕塑),语言艺术(文学)和综合艺术(戏剧、电影)”。因此,此“艺术”非彼“art”,把“anthropology of art”翻译成“艺术人类学”,使中国学者理所当然地认为艺术人类学涵盖音乐、舞蹈、绘画等领域。西方“art”曾是一个变化的概念。符・塔达基维奇在《西方美学概念史》中对西方“艺术”概念的演进有着清晰的表述:“在近代的运用中,对‘艺术’的含义时常是有限制的,这一情形表现在两个方面,亦即,或是将这一名称只保留在视觉艺术中,或者是将其保留在最高水平的、最优秀的艺术创造中。……在我们这一规定的意义上,艺术的全部领域被划分为两个部分,其中只有一部分(即视觉艺术)才是被称作‘艺术’的。” 英国的雷蒙・威廉斯称:“自从17世纪末,art专门意指之前不被认为是艺术领域的绘画、素描、雕刻与雕塑的用法越来越常见,但一直到19世纪,这种用法才被确立,且一直持续至今。” 《当代西方社会学、人类学新词典》中“艺术人类学”词条也明确指出:“人类学对艺术的研究相对注重造型艺术与绘画艺术,而较少注意表演艺术。”因此,我们理解的艺术人类学要远远大于西方“ anthropology of art ”的外延。
广义的艺术人类学在西方的发展有两条脉络可循。首先是发生在人类学内部的视觉文化人类学,以狭义的“艺术人类学”称谓。从人类学古典进化学派称那些视觉资料为“原始文化”,虽然此时的人类学家对无文字社会和群体的艺术感兴趣,并把它们纳入了自己的研究视野,但并没有另起炉灶把“艺术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或是研究方法提出来;第二条脉络是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审美人类学和舞蹈人类学。民族音乐学在西方的形成与发展来自人类学的影响。虽然比较音乐学的文化类型的概念已经有了人类学文化传播论的影子,但真正地从价值观到方法论的确立是发生在它过渡到民族音乐学之后。如果说比较音乐学仍是文化进化论的学说,那民族音乐学广泛认可音乐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而区别于比较音乐学。民族音乐学的领军人物梅里亚姆是美国人类学历史学派赫斯科维茨的学生,他从老师那儿借鉴了实证主义方法和文化相对主义的价值观用于音乐研究。他还受益于人类学功能学派马林洛夫斯基,注重田野工作的经验材料,并运用于自己的研究实践。梅里亚姆在《The Anthropology of Music》这本著作中总结出音乐的十大功能,也是受马林洛夫斯基的功能理论启发的产物。阐释人类学所提倡的 “文化分析不是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门阐释意义的科学”,随后应用到原住民音乐和仪式音乐研究中。但民族音乐家们并不仅仅对人类学理论随意剪切、拼贴,也不满足于直接借来为我所用,而是根据音乐对象本身的特点逐渐孕育出自己的孩子。从它诞生起不断有理论推进,由此获得独立的学科品质。其中包括梅氏的概念、乐音、行为的三重模式的理论基石,在赖斯三重模式的基础上增加了历史的分析模式,因此音乐分析拓展成为历史构成、社会维持、个人运用、象征体系的四级目标模式等等。理论的推进使得民族音乐学蓬勃发展并且研究成果丰硕。研究领域从非西方音乐到西方音乐,21世纪民族音乐学拓展到城市移民音乐、女性主义音乐等等。
音乐学研究者并不满足于人类学把音乐当做文化的载体看待,也不满意社会学仅仅把音乐作为社会事实的说法,他们认为在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学科内来看音乐现象,都把音乐当做社会生活的附庸,涉及音乐的人类学和音乐社会学只是“围绕音乐”、而非“穿越”,仍有一定的认识缺陷。音乐研究者研究音乐现象的内在规律,既可通过音乐自身、也一再借助“文化”、“社会”的外力来看音乐事实。从学科发展史来看,两门学科发展不均衡:人类学在经历了古典人类学理论探索人类学普通规律的科学到“实验”的文化批评阶段。而中国音乐学的发展仍处在“前学科”时期,有着自身的学科关怀。中国音乐学研究者一方面致力于建立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以应对世界音乐的现代性危机,另一方面对中国传统音乐遗产进行收集整理。人类学为艺术各门类横向拓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把它置于社会文化的语境中观照,跨学科的学科边界问题以及如何在相互借鉴中达成以“研究对象”为导向的跨学科深度问题在一定时期内长期存在。虽然人文学科之间的流动性日益增强,为概念和方法在多个领域的运用成为可能,但学院体制的“专业化”是共同的。如此,在学院知识生产上,各学科背后有自己的目标和追求,甚至学位论文的标准亦影响研究维度和结果,包括知识生产的权利关系和文化表征的反思,即布迪厄所谓的“作者是在何种权力场以及该权力场的何种位置上进行写作。” 现代学科体制把世界知识碎片化,肢解了作为“整体知识”相互间的联系。米尔斯以及克利福德・吉尔兹所认为的各学科之间观念与方法的流动性正日益成为当代学术发展的趋势,是对现代学科分化的回应。西方知识界所谓“知识碎片化”的反思则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的“advance seminar”科学革命运动 。这一思潮使得有关“跨学科”的讨论成为知识界的焦点。“世界需要完整地被表述”(马尔库斯)不仅是对人类学面对现代意识批评的反映,以回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相对主义的理想,也是对世界知识“现代性疏离”的呼吁。跨学科的要义则是反思现代学科的分化。作为“人”的科学应是整体、犬牙交错的复杂系统。沃尔夫在《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也曾反思这种疏离:政治和经济学从社会关系中抽离的做法的结果造成“专业化社会科学摒弃了整体视角,他们也变得像古希腊神话中的达娜厄姐妹那样,被判罚将水注入各自的无底容器中去。”
目前,“跨学科”已成为人文学科显著特点。以对象和问题意识为导向的研究有可能调和音乐本体研究取向和侧重文化、音乐互动关系的民族音乐学之间的矛盾,那就是“问题意识导向”的研究是以上两种旨趣作为视角审视研究对象而各有侧重。如是,应更进一步考虑“音乐”和“文化”如何接通。“音乐”作为文化的一部分是不争的事实,模糊其中任何一项、忽视它们之间真正的内在联系都难以接近研究对象的本质。就个案研究看,民族音乐学的视野已从非西方重回西方、从异族到本族,精英音乐研究也渐获合法地位。无论是西方和非西方的精英音乐,音乐家都是职业性的,社会、文化、仪式、语言层面也是研究者用“内部持有者”、“文化系统内部经验”的眼光来体察的,他(她)的研究可取音乐或文化当中的任何角度。如果从音乐层面来操作,即通过研究音乐本身即可澄清一些概念和事实,这取决于研究者自身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旨趣。而作为时空上、精神上的“他者”身份进入对象的“异族音乐研究”,或“非精英音乐类型”研究,我们无法从文化内部理解,那么在音乐之外的文化、社会中寻求解释无不是最佳手段。从民族音乐学建立之初梅里亚姆就如此批评柏林学院派的、实验室的比较音乐研究:“我们对于音乐自身的声音给予了很大的重视与强调……我们把音乐声音作为结构系统来看待,是一个静止的状态……”到今天对中国民族音乐“去音乐化”的非议,无非是“音乐”与“文化”之间的制衡过程。中国民族音乐应走出“前学科”阶段,在扎实的个案研究中开出理论之花。民族音乐学将听到盼望已久的、来自中国自己的声音。到那时,艺术各学科在人文学科中的意义将凸显为:艺术可作为一枚棱镜以透视出人类生活的其他方面。那更需要的是一种打破学科壁垒的、学科间良性互动交流的“去学科化”的广阔视野和学术胸怀。
[1]《朗文英汉双解词典》[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2.65.
[2]《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550.
[3]符・塔达基维奇. 西方美学概念史[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0.51-52.
[4]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 [M]. 北京:三联书店,2005.17.
[5]黄平、罗红光、许宝强.《当代社会学人类学学新词典》[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192.
[6]詹姆斯・克利福德等编著. 写文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305.
[7]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7.
[8]Merriam,A.P.The Anthropology of Music [M]. 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Pree,1964.36.
(责任编辑 霍 闽)
陈金玲(1982—)女,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讲师。